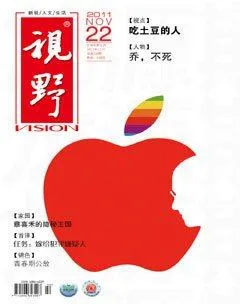扶与不扶,这是个问题?

两千多年前,一位叫孟轲的中国人曾经这样说,“今人诈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两千多年后,面对跌倒的老者,扶与不扶,在礼仪之邦成了一个问题。
两千多年的忙活啊,我们是“进步了”还是“退化了”呢?
拜文明所赐,我们有了“科学”。煌煌大国的卫生部发布了科学的扶助跌倒老人指南。拜法治所赐,我们又有了“权利”。在“科学”的统计之后,人们发现,那些反诬“好心人”为“肇事者”的被扶跌倒老人,以老年女性为主,于是专家出来建言:要保留事后追索其诽谤的权利。
这一套一套的道理,还可以列举很多。比如我们可以反驳孟先生,你说无恻隐之心就不是人,未免高估了“人”,人同时是天使和魔鬼,性既善又恶,否则又何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说?我们也可以说,善恶不在人性,而端看他/她生活在一种怎样的社会制度中。如果这个制度能惩恶扬善,人心自然会自觉地抑恶向善,所以,问题不在个人,而在制度。
我承认这些说法种种都有道理,而且每一种都难以辩驳,可我隐隐觉得,人不能只靠讲道理而活着。尤其是现今,道理愈发会层出不穷,“公婆各自说理”也充分展示了一种多元而非独断的美好一面,但是,有理由担心的是,人们会在各种道理面前耗尽心智,却未必能求得一个“正解”;更可怕的,是道理会耗尽行动的冲动,结果,我们很可能会心怀悲悯,却在围观中坐等“制度”的改变,或者坐等佛陀或耶稣的出现,好在制度未变的时候,扶跌倒的老人一把。
我们等待他们,是因为他们与我们不同,他们不靠道理活着,而是听从内心的召唤。信仰的力量,正是从环境的险恶下得以浮现。或许,在他们眼中,所有的道理,善恶相间、制度未变,不过是我们内心胆怯的借口?
从西洋以至东洋,两千多年的忙活,现代人早已不再崇拜英雄、追求“美德”,人们喧嚣着顶礼明星、退守不违法的“道德底线”,可我们真地更加幸福了吗?如果是,那么,扶与不扶,就不会再是一个问题。
顺便想到,这阵子大家都在热说“辛亥”。百年前的制度革命,让我们从皇权走向了共和。可我突然有了一个小小的疑问:在宏大叙事的浮云背后,我们的社会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制度革命”之前,路遇老人跌倒,人们扶还是不扶呢?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孟子一门的老师曾经说过:“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在他看来,“我欲仁,斯仁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