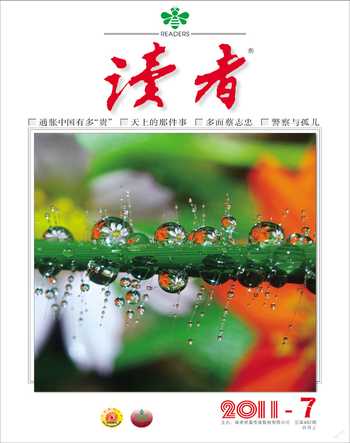想起了费孝通
许知远

他的身上,凝结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精英的智慧与道德勇气,但他的文化遗产似渐失去传人。
29岁时,费孝通出版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江村经济》。这部作品不仅帮助一名刚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青年在学术界赢得国际声誉,还在42年后让已经白发苍苍的老人获取了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
像那一代的很多杰出人物一样,生于1910年的费孝通不仅身经20世纪中国的种种磨难与挫折,更表现出那一代中国知识精英面对挑战时的生命力、智慧与道德勇气。在《江村经济》出版的1939年,中国的抗日战争正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在书中,他饱含深情地写道:“不管过去的错误和当前的不幸,人民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将再次以一个伟大的国家屹立在世界上。”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陷入有史以来最大的国家危机,知识青年开始努力地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
比起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那一代知识分子,成长于三四十年代的新一代开始更多地借助西方世界更系统的学科、方法来观察中国。借助于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人类社会学,费孝通试图通过对中国一个小小村落的研究,揭示中国广阔的、沉默的农村世界的秘密。
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所表现出的风貌,似乎已成为旷世绝响。1938年回国后,费孝通先后在云南大学与西南联大工作。在炮火声中,几千名年轻人与他们的老师唱着歌,忍着饥饿,徒步从北京穿越大半个中国,来到昆明这个大后方。在空袭警报中,他们创造了学术史上最繁荣的时刻。半个世纪后,费孝通回忆那段时光时说:“这一段时间的生活,是我一生里最值得留恋的。时隔越久,越觉得可贵的是当时和几个年轻朋友一起工作时不计困苦、追求理想的那一片真情。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对自己的事业有抱负。那种一往情深,何等可爱。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鲜红的,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
社会学试图解释个体与复杂的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剧烈的社会变迁,是所有社会学家梦寐以求的题目。全球市场与工业社会的兴起,造就了马克思、韦伯等。而作为20世纪人类最壮观的实验场,中国是所有思想与学科最理想的研究课题。在被禁止这种探索整整30年之后,已错过创造力最旺盛时期的费孝通开始帮助中国开创自己的社会学传统。他先后担任不同的学术领导职务,还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但这一切没有什么比教书、写作、实地研究更让他兴奋的了。
中国社会正从一个封闭的、乡土的、传统的社会,转变成一个开放的、现代化的,甚至是后现代的社会。正像费孝通所说:“重大的社会改革理应在思想领域引起相应的激情,孕育一代文章。我们不应辜负这个伟大时代。”一直到90岁时,费孝通仍在继续写作。
我总是忘不了那一幕场景:27岁的费孝通在伦敦经济学院外闹哄哄的街头闲逛;躲在马林诺夫斯基的讨论会的角落里。他的苏州口音的英语暂时还插不上话,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们的各种口音的英语发言,他也经常听不懂,他只好一个劲儿抽烟。在长期的烟雾缭绕之后,他似乎抓住了些什么。
我常对费孝通那一代人的亲身经历与智力冒险深感崇敬。他所留下的三项主要遗产,似乎已经失去了传人。
首先,他坚持一点,在理解一般问题时,最好的方法是研究具体事例,但是在进入具体环节时,他又未忘记其与更广阔的整体环境间的联系。其次,知识精英如何与大众社会产生联系。他既未躲藏在自己的世界里,也未丢弃自己的原则。他深知,知识的功能既是用来改进现实社会,也是为了完善自我。最后一点是,他们那一代人的道德勇气。我从不相信,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若只沉迷于眼前利益,缺乏更具有超越性的目标,缺乏在面对压力时对道德与智力原则的坚持,这个国家能够取得什么伟大的成就。
(凌峰摘自《作文素材》2011年1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