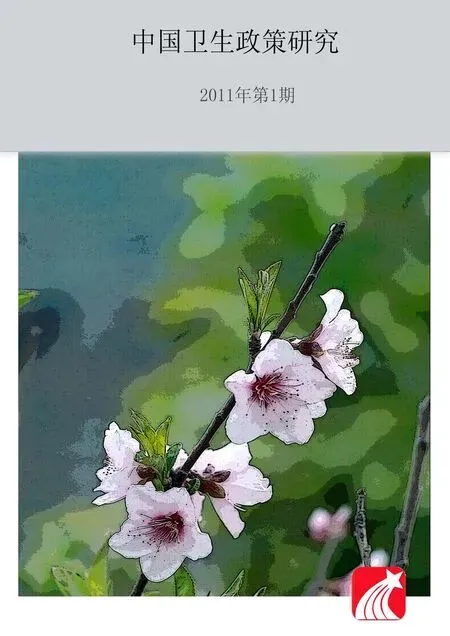日本艾滋病疫情处于低流行状态的原因分析和思考
徐 鹏 刘康迈 吴尊友 韩孟杰 曾 刚 吕 繁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北京 100050
在艾滋病防治中,日本似乎是个充满“矛盾”的国家:日本出现过因血液制品导致艾滋病流行的“污血事件”[1],但近年经血液传播艾滋病几近绝迹;毒品使用泛滥[2],但经吸毒传播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的人数极少;性风俗业盛行[3],但日本籍女性感染HIV的人数并不多。其疫情形势、流行特点及防治经验值得同处于东亚的中国关注和研究。本文通过文献综述和专家访谈,对日本艾滋病疫情、应对策略和措施进行了整理,对疫情较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1 日本艾滋病疫情
1.1 艾滋病疫情报告
日本1985年报告首例艾滋病病例,截至2008年底,累计报告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15 451例,其中艾滋病病人4 899例(表1)[4-5];日本总人口为1.27亿人(男性6 200万人,女性6 500万人);全人群报告艾滋病感染率为0.012%。
根据WHO和UNAIDS的资料[6],估计日本1990年存活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约3 500例(3 300~3 700例),1998年约6 900人(6 500~7 300例),2005年约9 200人(8 100~9 800例);估计1997—2001年日本每年因艾滋病死亡人数少于100人,2002—2005年少于200人。

表1 日本1985—2008年报告的HIV感染者和病人(例)
1.2 日本艾滋病疫情特征
1.2.1 传播途径
在日本,性传播是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截至2007年底,累计报告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13 894例,其中,异性性接触为5 071例(占36.5%),男男性接触为5 761例(占41.5%),注射吸毒为78例(占0.6%),母婴传播为49例(占0.4%),其他及不明途径者2 935例(占21.1%)。
从单年度看,2008年日本报告1 126例HIV感染者,999例(占88.7%)是经性途径而感染(其中,779例是男男性接触传播,占感染者总数的69.2%,220例是异性性传播,占19.5%);同年报告的431例艾滋病病人中,336例(占78.0%)是通过性接触途径而感染的(189例是男男性接触传播,占总数的43.9%,147例是异性性传播,占34.1%)。
哨点监测数据显示[7-8]:男男性接触人群的HIV抗体阳性检出率较高:1996年达到19.4%,1999年和2000年分别为3.1%和2.9%;女性性工作者、孕产妇(代表一般人群)中未检出HIV抗体阳性者。[9]
1.2.2 人群分布
国籍分布。截至2008年底,累计报告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15 451例,其中,日本国民为12 138例(占78.6%)。在2008年报告的1 126例HIV感染者中,日本国民1 033例(占91.7%),外籍93例;431例艾滋病病人中,日本国民378例(占87.7%),外籍53例。
年龄分布。截至2007年底,累计报告的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以20~40岁为主。20岁以下为244例,20~30岁为3 994例,30~40岁为4 709例,40~50岁为2 603例,50岁以上为2 331例。
性别分布。累计报告的HIV感染者中,男性高于女性,但日本籍女性低于外国女性。截至2007年底,男性感染者为11 447例(日本籍9 864例,外籍1 583例),女性为2 447例(日本籍863例,外籍1 584例)。
1.2.3 地区分布
日本东京和关东地区(神奈川、崎玉、千叶、茨城、群马等县)是报告感染者数量最多的地区。这些地区报告的HIV感染者占全国报告数的比例较大,2006年报告HIV感染者528例(占全国报告数的55.2%),艾滋病病人211例(占52.0%);2008年报告HIV感染者606例(占53.8%),病人203例(占47.1%)。
1.3 日本艾滋病流行的总体状况
根据以上资料可判断,日本艾滋病疫情处于低流行状态。近年,因血液和血制品造成的艾滋病传播基本被杜绝;因注射吸毒而感染HIV的人数极少;在异性性传播方面,日本籍女性感染艾滋病的比例较低,母婴传播HIV极少。但是,男男性接触传播是重要危险因素。
2 日本艾滋病疫情处于低流行状态的原因分析
首先,吸取经血液制品传播HIV的教训,日本政府加强血液管理,采用先进检测技术,降低了经血液传播艾滋病的风险。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因血液制品第Ⅷ因子造成1 000多名血友病病人感染HIV的事件后,日本政府出台法规,加强了血液管理。在血液检测方面,采用了核酸检测技术,进行严格的血液检测,日本红十字会应用病原体核酸检测技术(Nucleic Acid Testing,NAT),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三个NAT中心,1999年采用500人份混样,2004年采用20人份,成为世界上最早在全国范围内采用NAT对血液进行HBV、HCV、HIV 筛检的国家,使感染者在感染后数天即能检出病毒,将HBV、HCV和HIV感染的平均“窗口期”分别缩短9天、59天和11天[10],使输血传播HIV的危险性降到最低。
其次,由于传统文化影响和法规严苛,静脉注射吸毒人数少,经吸毒途径感染HIV的人数少。从文化背景上看,日本国民对吸食鸦片者非常排斥。在宣传教育方面,政府大力宣传毒品的危害,缩小毒品影响的人群范围。在法律方面,对毒品交易严厉打击,先后制定了《大麻取缔法》、《冰毒取缔法》、《鸦片法》和《麻醉药品管理法》等,不仅打击毒品的供给方,而且处罚需求方,如贩运、持有或者使用毒品都是犯罪行为,都会受到惩罚(有期徒刑和追加高额罚款等)。在使用毒品的种类上,以新型毒品(如冰毒和摇头丸等)为主,例如,2005年日本处罚的毒品犯罪人员约4万人,其中冰毒犯罪者约为3万人,而鸦片犯罪人员不到500人。[11]这些因素都降低了艾滋病在吸毒人群中传播的危害,截至2007年底,在累计报告的13 894例HIV感染者中,因静脉注射吸毒感染HIV的仅为78例。
第三,日本的性教育较早而且较普及,国民的安全套使用意识高,降低了经性传播HIV的风险。日本国民对性比较宽容,在小学阶段就已经开始性教育,中学生们已经可以从学校里学到避孕知识。学校的生活老师会指导青少年学会使用安全套,以保护自己。日本性风俗业被称为“性风俗特殊营业”,2000年该产业产值达到4兆日元以上,创造了巨大财富。[12]日本性风俗业具有历史渊源,1946年,根据美占领军的《废除公娼备忘录》,日本废除了公娼制度,但由于大量妓女失业带来的社会压力,政府设立了“特殊饮食店区”,将娼馆聚集于该区,实行登记营业。1984年实施《风俗营业的规制与业务适正化等相关法》,规定了营业的地域、时间等,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部分性产业的合法地位。此外,日本是世界上使用安全套比例较高的国家,日本已婚妇女性生活中持续使用安全套的比例是43.1%,而同处东亚的中国和韩国分别是4.3%和15.1%。[13]严格的管理、较早的性教育和国民使用安全套的习惯,促成了风俗营业场所较高的安全套使用率。这些因素减少了异性性传播艾滋病的数量,截至2007年底,累计报告的13 894例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中,日本籍女性仅为863人。
第四,具有较强的危机意识,抓住了预防传播的最佳时机。在艾滋病低流行时,政府和相关机构就意识到了艾滋病流行的严重危害,及时采取措施,包括:(1)制定法规和技术指南。1999年4月,日本实施《感染症法》,促进了性病和艾滋病的综合防治;2006年3月,日本根据形势修订了《艾滋病预防指南》;(2)建立多部门合作机制,加强协调和督导。2006年6月,日本政府建立了部门联络委员会,包括司法、教育、文化、体育、科技、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确立了艾滋病防控国家目标,建立了重点地区艾滋病预防联络委员会;成立了由学者、HIV感染者、非政府组织、政府部门组成的艾滋病评估与审查委员会,以监督艾滋病防控措施的执行;(3)完善自愿咨询检测系统。政府要求保健所开展HIV免费咨询检测,每个保健所都有独立的艾滋病咨询室,开展标准化的自愿咨询和匿名检测工作;2004年,增加艾滋病检测渠道,委托医疗机构进行免费的匿名检测,检测费用由红十字会支付;2006年,将每年6月1—7日定为HIV检测宣传周,促进各地开展HIV检测服务,提高公众检测意识;(4)加强医疗服务系统建设。到2006年建立了1个国家艾滋病治疗中心,14个核心医院和369个网点医院。
第五,发挥保健所在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宣传、咨询和检测的作用。在地域和职责都体现出广覆盖特点的保健所,对日本预防传染病起到了重要作用;1947年,日本实施《保健所法》;1960年,根据人口密度,保健所的数量不断增加;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完善,1994年《保健所法》更名为《地区保健法》;2000年,保健所公共卫生职能进一步扩大,分布广泛的保健所对公共卫生有全面的职责:健康教育、医疗、传染病预防、人口统计、食品卫生、环境卫生、妇幼保健等。2003年日本几乎没有发现SARS病例,起主导作用的就是分布于全国各地的保健所。[14]在艾滋病防治中,保健所主要起着实行自愿咨询和检测的作用,发现了大量的HIV感染者,如2006年,到保健所自愿咨询并检测的接近13万人,发现了感染者近900人。
第六,开展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教育活动,加强青少年安全性行为教育。每年“艾滋病日”前后,日本政府组织开展健康教育活动,包括明星参与和倡导、街头宣传和发放材料等。在其它时间,由非政府组织针对目标群体(例如青少年、男男性接触群体)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如针对中学生的“青少年社会幸福感工程”,针对男男性接触人群开展安全套使用宣传教育。日本大力加强青少年安全性行为的宣传教育,倡导普及使用安全套;建议家庭加强和保健所、学校的联合,多与年轻人交流;编制艾滋病预防手册,广为散发,以提高青少年的艾滋病防范意识;开展针对年轻人的免费HIV检测,发起“男孩保护女孩”的活动等。
第七,日本的HIV感染人数少,并且主要集中于一些地区。从1985年发现第一例HIV感染者后,截至2008年底,日本累计报告了HIV感染者和病人约15 451例,主要集中于一些大城市,如日本东京和关东地区报告的HIV感染者占全国报告数的比例较大,2006年报告HIV感染者和病人占全国报告数的50%以上。HIV感染者集中在某些地区的特征降低了艾滋病的传播范围和速率。
第八,日本政府注重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开展预防艾滋病的工作中,日本政府积极动员和发动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士组建非政府组织,利用其灵活性,开展艾滋病及其它疾病的健康教育活动,活动经费主要由政府资助,还为这些组织的活动提供条件,如租赁场地等;如东京AKTA中心(日本最大的男男性接触人群干预组织,主要针对MSM人群开展艾滋病预防工作),其经费是向厚生劳动省申请的,日常工作是将目标人群与社区、检测机构、医院等部门联系起来;非政府组织在艾滋病防治体系中,起到了沟通政府和高危人群的作用,对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流行起到了积极作用。
3 日本艾滋病疫情上升的因素
在分析日本艾滋病疫情低流行状态的同时,要看到日本艾滋病疫情也存在着上升的危险因素。首先,日本艾滋病的主要途径是性途径传播,这就具有向一般人群传播的危险,而且,随着年轻人性行为的活跃化、网络化等,艾滋病有在中学生中蔓延的可能。其次,男男性接触人群中艾滋病传播较严重,该人群将是未来日本艾滋病疫情上升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1998年之后,男男性接触感染HIV的比例上升迅速,高于异性性接触的感染比例,2008年报告的1 557例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中,968例是男男性接触传播,占62.2%。再次,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刚在日本出现时被渲染成了“外国病”,现在一些日本人仍然持有这样的态度,表明日本公众对艾滋病的防范意识需要进一步提高。第四,因为偷渡、人口走私而被迫卖淫的外籍女性,其安全套使用意识远低于日本女性,将成为日本艾滋病传播的一个重要风险。
4 思考
艾滋病病毒只能通过血液途径、性途径和母婴途径传播,因此,预防艾滋病也主要从这几个途径入手;本文通过分析日本艾滋病疫情特征,结合我国艾滋病防治情况,有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在控制经血液传播艾滋病方面。日本有过因血液制品造成艾滋病传播的沉痛教训,但采取的措施非常有效,基本杜绝了因血液传播艾滋病。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一些地区出现了艾滋病在有偿采供血人群中流行的情况,通过出台法规,严厉打击非法活动,我国控制了经血液传播艾滋病。由于艾滋病“窗口期”的存在,目前血站采用的检测技术难以完全筛检出含HIV的血液,会造成经输血感染HIV,影响了临床用血的安全。日本在全国范围内采用核酸技术对血液进行HIV 筛检,将“窗口期”缩短到11天左右。因此,有观点认为我国也应该在全国范围内采取核酸技术;但也有观点认为,这项技术要求的人力、设备和设施等成本太高,而效益并不明显,不适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艾滋病流行状况,因此,核酸技术采用与否,需要在成本、效益、艾滋病疫情、医学伦理等方面权衡。
第二,在吸毒感染艾滋病方面,只有静脉注射吸毒并且与他人共用针具才有可能造成艾滋病传播,因此,预防经吸毒传播艾滋病的方法就是不吸毒或者不采用静脉注射吸毒或者不与他人共用针具。[15]根据日本的情况,吸毒者多使用非静脉注射的新型毒品,经吸毒感染艾滋病的人数极少。在我国,估计现存活的74万HIV感染者和病人中,经静脉注射吸毒传播的占32.2%,那么,在吸毒较多并且艾滋病高流行的地区,就应当采取措施,有效落实提供清洁针具这一不得已的方法,以减少共用针具从而降低艾滋病传播风险。
第三,使用安全套对阻断异性性传播艾滋病具有重要作用。日本的性教育开展较早而且较普及,国民的安全套使用比例很高,已婚妇女性生活中持续使用安全套的比例是43.1%,这就形成了一道屏障,截至2007年底,日本籍女性感染者只有863例。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国策,主要是通过安放节育器和结扎手术等来避孕,已婚妇女持续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低,仅有4.3%,因此,在一般人群中宣传使用安全套避孕是非常必要的,但由于传统做法的影响太深,还需要有关部门营造支持性的环境。
第四,日本男男性接触人群中传播艾滋病严重,是日本艾滋病上升最重要的因素。我国估计2009年当年新发感染者中,男男性接触传播占32.5%。[16]预防和控制男男性接触人群的艾滋病流行是各国的难题,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无疑是主要的方法之一,调动、引导和规范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是防控艾滋病的重要方面。
第五,在母婴传播艾滋病方面,截至2007年底,日本累计报告母婴传播HIV仅有49例(占0.4%);而我国估计现存活的74万HIV感染者和病人中,经母婴传播的占1.0%,绝对数比较大。鉴于母婴阻断成功率较高,对控制艾滋病传播效果明显[17],我国在母婴阻断方面应逐渐加大力度。
当前,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正处于攻坚阶段[18],需要进一步完善符合中国疫情特点的防治体系和探索更加有效的防治措施,在加强与欧美国家的交流与合作的同时,还应借鉴同处亚洲、在文化上有着某种相近之处的日本的一些策略和方法。
致谢
感谢北京协和医学院张孔来教授、中国疾控中心性艾中心蔡国喜博士、中日技术合作艾滋病项目刘新凤主任医师提供的材料和相关建议。
[1] T.Tomono和日本红十字会NAT筛查研究组. 日本进行HCV、HBV和HIV病毒核酸筛查的现状[J]. 国外医学:输血及血液学分册, 2003, 26(20): 111-113.
[2] 张斌, 邓立军. 日本的毒品问题及其诱惑侦查的理论与实务[J]. 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 2003, 3(4): 42-45.
[3] 肖军. 禁止下的规制:性产业在日本的法律境遇[J]. 时代法学, 2007, 5(6): 92-98.
[4] UNAIDS. Report to UNAIDS-HIV/AIDS Trends in Japan[R]. 2009.
[5] UNGASS COUNTRY PROGRESS REPORT JAPAN[R]. 2007.
[6] UNAIDS, WHO. 2008 Report on the global AIDS epidemic[R]. 2008.
[7] WHO, UNAIDS, UNCIEF. Japan Epidemiological Fact Sheet on HIV and AIDS(2004 Update)[R]. 2004.
[8] WHO, UNAIDS, UNCIEF. Japan Epidemiological Fact Sheet on HIV and AIDS(2006 Update)[R].2006.
[9] WHO, UNAIDS, UNCIEF.Japan Epidemiological Fact Sheet on HIV and AIDS(2008 Update)[R].2008.
[10] 王迅. 核酸检测技术(NAT)及其在血液筛检中的应用[J]. 中国输血杂志, 2004, 17(6): 465-468.
[11] 张海东.日本对毒品犯罪的侦查方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日本问题研究, 2006(4): 61-64.
[12] 贾秀芬. 日本性风俗业与东南亚妇女的法律境遇[J]. 东南亚研究, 2009(6): 73-78.
[13]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Family Planning Worldwide 2008 Data Sheet [R]. 2008.
[14] 淳于淼泠. 日本保健所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的作用[J]. 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2007, 23(2): 143-144.
[15] 吴尊友. 大力开展我国艾滋病行为干预研究[J]. 疾病控制杂志, 2000, 4(1): 4-8.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2009年中国艾滋病疫情估计工作报告[R]. 2010.
[17] 王临虹, 方利文, 王前, 等. 我国不同的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措施的效果研究[J].中国艾滋病性病, 2009,15(4): 352-355.
[18] 郑灵巧.抗艾进入攻坚阶段[N/OL]. (2009-11-30) [2010-10-06]. http://211.154.163.181/jkb/html/2009-11/30/content_6103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