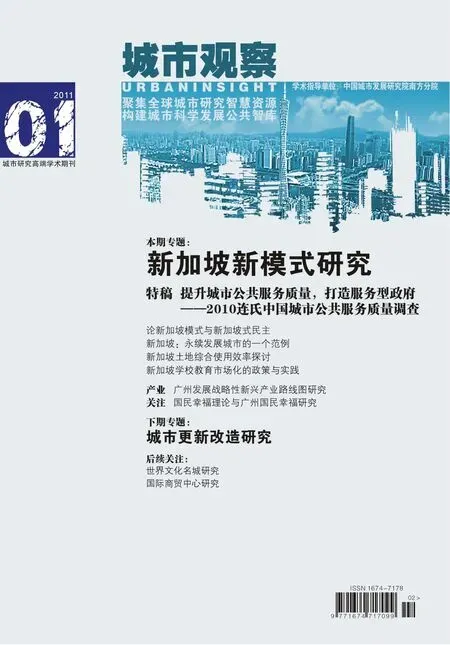国民幸福理论与广州国民幸福研究
◎ 林 洪 曲 博 温 拓
国民幸福理论与广州国民幸福研究
◎ 林 洪 曲 博 温 拓
本文分析了国民幸福理论的起源,梳理了有关幸福研究在国内外的发展情况,比较了国民幸福指数与其他相近或相似指标的关联,在调研数据的基础上对广州幸福指数进行了计算和分析。
国民幸福 广州 幸福指数
霍尔巴赫(1977)在其《自然的体系》中说:“我们的一切教育、思考和知识,都不过以怎样能获得我们本性所不断努力追求的幸福为对象。”人类向往幸福,相关的思考和实践由来已久。
一、国民幸福理论的起源
24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曾尝试对统治者的幸福程度进行度量;18世纪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鼻祖边沁,是试图将幸福度量纳入近代科学轨道的第一人。然而,学者们对幸福能否被度量一直持怀疑态度。
真正把幸福的测度付诸实践、将个人微观感受与社会宏观发展结合起来的,是不丹国王旺楚克。他通过创建举世瞩目的“不丹模式”,彻底推翻了学者们的疑惑,也使得国民幸福成为了世界各国关注的话题。上世纪70年代,不丹国民生活贫困,文盲率居高不下,几乎没有像样的现代化基础设施。旺楚克于1972年推行“全民幸福计划”和“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概念,创建了“不丹模式”。在GNH国策下,经过30年的治理,不丹不仅在人均GDP方面领先南亚,而且国民的幸福感更令其他国家望其项背。2005年10月,联合国环境署将当年的“地球卫士”奖颁给了不丹国王和人民,不丹以人均GDP 700美元的低收入水平名列全球幸福指数排行榜前茅,成为国民幸福成就举世瞩目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不丹整体人文发展景况与GDP增长并非呈现显著的正态势关系,人文发展显著快于GDP的增长,虽然经济不发达,但不丹人民很幸福。
二、国民幸福理论在国内外的发展
国民幸福是人们对客观现实生活“满意程度”的主观心理体验,其既与客观生活条件密切相关,又集中体现个人需求和价值取向,涉及心理学、伦理学、经济学和发展观诸多内容。国际上和我国都创设机构积极致力于国民幸福的研究。国际上,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哈特负责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是国际上最具权威的“幸福指数”研究机构;美国联邦政府和英国内阁都拨巨资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聘请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等专家致力于“国民幸福总值”的研究;我国学者也积极参与幸福指数及其指标体系的构建和实践。
目前,从经济角度进行分析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⒈宏观国民幸福研究领域。
以不丹模式的GNH指标为理论与实践的典型代表,它由持续公平的社会经济发展(Sustainable and equit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环境保护(Conservation of environment)、文化传承(Preservation and promotion of culture)、政府善治(Promotion of good governance)四大支柱组成;罗伯特·巴罗(1996)提出了幸福函数(Felicity Function),以效用反映幸福,将人均效用流量与人均消费数量相联系,作为拉齐姆模型的增长因素之一;200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卡尼曼(2004)以及奚恺元(2005)等行为经济学家对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和货币增长与幸福快乐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丹尼尔·卡尼曼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的测度方法——日重现法(DRM)。英国在创设“国民发展指数”(MDP)时,将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也纳入其考量的范围;日本则强调了文化方面的“国民幸福总值”; 2004年,美国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利用其设计的幸福指标体系对82个国家的幸福指数进行了测算和排名。
在我国,钟永豪和林洪(2001,2002)首先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标体系设计和综合度量设想;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则提交了题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建议从国家层面上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要素组成的我国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
⒉城市幸福研究领域。
美国《福布斯》杂志发表2005年度“税负痛苦指数(Tax Misery Index)”调查报告,该指数根据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雇主社保金、雇员社保金、消费税以及财富税加总得出。
在我国,奚恺元(2004)与《瞭望东方周刊》合作,对中国六大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指数测试;零点调查公司于2004年10月对全国7个大中城市、7个小城镇及8个行政村进行了类似的调查。2005年4月,深圳市在全国率先完成“城市文明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编制,文明指数由7个一级指标组成,包括:关爱指数、人文指数、诚信指数、廉洁指数、安全指数、环境指数和幸福指数;2006年初,由客观统计指标和主观评价问卷组成的“和谐深圳评价体系”在深圳社会科学院完成设计。
⒊微观幸福研究领域。
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和经济学教授艾伦·克鲁格从微观个体的幸福体验来描述国民幸福,他们让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对不同活动所得到的愉悦感进行排序。生活质量是“幸福指数”的内核,人的生活质量应包括三个方面: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时间和可支配的个性发展,即三个disposable;幸福的人生包括三个方面:美满的家庭生活、惬意的工作环境和愉悦的社交娱乐。
在中国,邢占军(2006)认为,幸福感是反映人们主观生活质量的一种重要指标,他从个体满意感、总体满意感、心理健康、体验幸福感等不同的角度研究幸福指数。另据网上调查,对城镇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的指标按照影响力排序依次为:物价变动承受能力、个人职业满意度、个人经济状况满意度、国家总体发展方向正确性评价和个人业余生活满意度。
近年来,中西方学者对幸福的研究都积累了不少成果,但从对幸福感的理解和追求途径来看,中西方在幸福观上存在差异,对幸福感的诠释不同,主要反映在“集体主义”及“个人主义”思维的差别上。黄馨萍(2002)认为西方文化强调以个体的主观情绪感受与生活满意度的认知评估来界定幸福感,而东方文化中则倾向寻求社会关系中的良好互动而获得幸福感。
中国人的幸福不是来自于外表,而是来自于自身内在的修养,还强调带动他人,达到“和谐”幸福的状态。因此,中国人的幸福是以整体而言的,并认为没有群体的幸福就没有个体的幸福可言。这种整体不单单体现在人际关系上,也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的幸福更重要的来自自身理想和目标的实现,其目的是使得个人幸福最大化。
三、国民幸福测度探究
幸福的结构即心理体验是幸福的主观形式,人生的需要、欲望、目的之实现是幸福的客观标准。一个人只要自己觉得幸福,他确实就是幸福的;但是,他所享有的幸福究竟是何种幸福,却是客观的而不依他主观感觉而转移。所以研究国民幸福理论,就必须把个人主观的需要、欲望、目的的实现程度和客观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有机结合起来,才能进行有效的评价。
(一)采用国民幸福指数测度的优越性
1.国民幸福指数与和谐发展指数之比较
和谐是人类的主题,自从中央明确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任务,如何评价和谐社会发展进程就成了重要的研究课题。
2007年11月9日,由华东理工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教授组成的课题组首次公布了中国30个省区市、41个城市和谐发展指数,它从理论上界定了和谐发展的本质,并从中国城市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设计和架构了中国地区和谐发展指标体系。
国民幸福指数与和谐发展指数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民幸福指数与和谐发展指数作为和谐社会的评价指标都是以度量和评价和谐社会发展进程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及数学建模进行量化。两者均可从整体及部分两个层面对和谐社会发展进行度量与评价,但在理论上的描述不一致。国民幸福指数认为和谐发展的本质在于以人为本,某个地区或国家是否和谐或和谐程度有多高,需要以这个地区乃至国家的国民整体幸福感作为评价标准。而和谐发展指数认为和谐发展的本质是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人文素质、社会进步和生态文明水平。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上,两者所构建的指标不同,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不同。国民幸福指数采用日重现法,以问卷的形式收集数据,通过理论指导及数据分析,以家庭和个人因素、性格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环境因素及其他因素六大影响因素建立国民幸福指数测度系统,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最后得到某个地区的国民幸福指数。和谐发展指数则是从“经济增长指数”、“人文发展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生态文明指数”四大维度评价省区或城市的和谐发展水平。
2.国民幸福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之比较
人类发展指数(HDI, Human Development Index)也称人文发展指数,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0年人文发展报告》中提出的用以衡量联合国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是为了弥补GDP作为衡量发展指标所存在的缺陷而提出的。其主要由人类生活的三个基本要素(指标)组成:预期寿命、知识和生活水平。
国民幸福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都认为人的发展是发展的本质和最终目标,两者指标的设立都是围绕这个主题来构建。然而,在具体的指标选取、构建及计算方法上,两类指数大不相同。国民幸福指数以人的主观幸福感为出发点,通过对影响人的幸福感的因素分析构建国民幸福测度系统,以问卷形式收集原始数据,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最终得到某个城市或地区的国民幸福指数得分。人类发展指数则从预期寿命,知识及生活水平三个维度共4个指标分别构成单项指数,再通过算术平均得到人均发展指数。人类发展指数所采用的维度及指标过于简单,且选取的均是客观指标,无法全面准确地衡量人文发展状况。人类发展指数利用简单的转换及加权得出各个国家的得分,通过得分排序得到各个国家的人文发展指数排名,这样的计算方法及权重安排较为随意且无明确的理论依据,且历年计算结果的口径不一致,不利于纵向比较。而国民幸福指数通过建立结构方程计算最终的国民幸福指数得分,该得分具有明确的理论依据及推演过程,可信度高。
3.国民幸福指数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较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的总和。GDP作为宏观经济理论的中心指标,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统一标准。但是其仅仅指的是在一定时期生产的货物和服务的流量,不能反映可持续发展,更不能反映人民生活的幸福程度,它的缺陷主要集中在环境和福利两方面。一味地追求高GDP,往往会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作为代价。因此,GDP的价值只能说明社会财富的增加值,其仅仅是能够带来幸福的因素之一。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很多非物质的因素对幸福的影响却越来越大。这是因为人们的幸福感往往取决于两类比较:一种是时间性的比较,一种是社会性的比较。一个国家乃至一个社会的最大目标不是最大化财富,而是最大化人们的幸福。国民幸福指数以人的幸福为根本目标,把经济因素纳入衡量幸福感的五大因素之一,测度和分析更全面。
4.国民幸福指数与绿色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较
绿色GDP是指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考虑了自然资源(主要包括土地、森林、矿产、水和海洋)与环境因素(包括生态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影响之后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即将经济活动中所付出的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从GDP中予以扣除,它是对GDP指标的一种调整,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反之亦然。绿色GDP核算能更好地体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好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
由于绿色GDP核算的数据不完整性,技术方法的局限性,环境问题的滞后和积累性等问题,导致它实践起来比较困难。另外,绿色GDP只反映了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影响,而我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是指经济、环境和社会三个系统的协调发展,绿色GDP并没有反映出经济与社会、环境与社会间的相互影响,不能同时关注就业、收入分配等问题。国民幸福指数综合了环境因素,它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考察,包括居住环境、工作环境、生态环境、治安状况等。很显然,绿色GDP和国民幸福指数有一定的相关性,都不把经济增长作为最终目的。国民幸福指数以最大化人们的幸福感为目的,它不仅考虑了经济对人们幸福的影响,也考虑了环境等各因素对人们幸福的影响。国民幸福指数重视主观感受,因此得出的幸福值也会因人而异,即使是同一地区的居民,其幸福值也可能相差甚远。而绿色GDP不会因人而异,它测量的是某个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所以,绿色GDP只能反映宏观层面,不能反映微观个体。而国民幸福指数既可用于反映整体的幸福感,也能反映个体的幸福感。
5.国民幸福指数与社会进步指数之比较
社会进步指数(Index of Social Progress),缩写为ISP,是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理查德·J·埃斯蒂斯(R. J. Estes)教授在国际社会福利理事会的要求和支持下于1984年提出的,它涉及10个有关的社会经济领域,选择了相应的36项指标。1988年埃斯蒂斯在《世界社会发展的趋势》一书中又提出了加权社会进步指数(Weighted Index of Social Progress), 缩写为WISP。该指数将众多的社会经济指标浓缩成一个综合指数,以此作为评价社会发展的尺度。社会进步指数是评价社会发展状况的一个有效工具,它不仅可以用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间社会发展状况的比较,也可用于一国内部不同地区间社会发展水平的横向比较,还可用于一国不同时期发展水平的动态比较。
社会进步指数和国民幸福指数考察了除经济增长以外的其他指标,都不单纯以社会财富的增加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它们在编制指数的时候都考虑了诸如人口、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能较全面反应社会进步和国民幸福。但社会进步指数编制存在指向不明的缺陷,社会进步究竟指的是什么,是生产力的进步还是人的自由发展,而衡量一国社会进步的程度也因人、因不同地区而异。
综上所述,国民幸福指数的应用有明显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国民幸福指数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根本目的。国民幸福指数从人的主观感受出发,以最大化人们的幸福感为最终目的,能更好地体现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及地位,更符合我国现阶段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主题。
第二,国民幸福指数方法更加科学可信。可以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找出国民幸福指数计算中的潜变量及潜变量与各子指标之间的相关程度,计算最终的国民幸福指数得分,其具有明确的理论依据及推演过程,可信度高、说服力强。
第三,国民幸福指数更贴切生活,更能反映人的主观心理感受。由于其测量的不仅仅是经济因素,因此更能解释在物质文化高速发展的现代,为什么人们的幸福不随经济增长而增长的问题。
第四,国民幸福指数既可反映宏观层面,也可反映微观个体。它突破了一些指标适用的局限性,可以研究个体幸福感,也可以上升到国家层面,分析整个国家的国民幸福。
(二)国民幸福指数在我国的实践
幸福问题在中国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国内对幸福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是多维的,有的从心理学角度,有的研制幸福感测量量表,有的则通过建立国民幸福指标体系来描述国民幸福。
1.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
各类群体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包括了以年龄为特征的研究、以城乡为分类标准的研究、不同社会群落和学生群落的研究等等。
以年龄阶段为特征的研究,通常是针对青少年及老年人建立主观幸福感测度。
丁新华等人在《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研究述评》中在对主观幸福感的概念、构成、测评工具予以介绍的基础上,回顾了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基本状况,并对影响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生活事件、家庭因素、神经质和外向性、自尊、控制感)的研究进行了介绍。①
杨彦春(1988)较早采用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对我国老年人幸福度进行了调查研究。②这一量表在最近几年国内的老年群体幸福感研究中得到较多的运用。刘仁刚与龚耀先(2000)以346位城市老年人为研究对象研究其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涵盖一般情况、个性、婚姻家庭、工作、退休、住房、健康、收入、兴趣与活动9个方面。研究表明,个性是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不同个性维度对幸福感的不同方面有不同的影响力,多种因素通过个性影响幸福感。③张红静、马颖竹(2002)以107名老年大学学员为研究对象,用人脸测验和阶梯测验、特质应对问卷、家庭功能问卷和一般社会指标调查表为研究工具了解老年人的一般心理状况,探讨各项社会因素、家庭功能、应对万式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及影响。结果表明,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主观幸福感较高,其幸福感受社会、家庭及自身多重因素的影响。④
以城乡为分类标准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则以邢占军(2005)为代表。他在研究中主要运用量表来测量主观幸福感。认为“幸福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主观反映,它既同人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密切相关,又体现了人们的需求和价值。主观幸福感正是由这些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⑤。他制定的一套针对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量表,由54个项目组成。研究表明,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在年龄、教育、婚姻、职业、收入、地区以及城市规模等方面存在着组群差异,认为目前这些因素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一定的影响。研究还表明,从总体上看我国城市居民中无婚姻生活者主观幸福感高于有婚姻生活者,性别是影响城市居民婚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重要因素。
谢彦明(2008)等人采用指标体系对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展开研究。以云南省325 户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为例,以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为视角,首先从农户特征、经济状况和生活环境三个纬度构建了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模型,其次建立了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指标体系,采用二元Logistic 和AHP 相结合的方法,确定了指标的权重,最后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指标体系进行了综合评价,提出了研究存在的不足以及研究的趋向。⑥
对不同社会群落和学生群落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多且深入。张雯与郑日昌(2004)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中用幸福感指数量表、社会支持量表及归因量表等对1~4年级的400名大学生小团体施测。结果是大学生幸福感城市生高于农村生,且存在显著性差异,而性别差异未达显著水平;大学生幸福感与自尊显著相关,其中“总体情感指数”与自尊的相关最高,等等。显然个体的自尊、社会支持与归因等因素都对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且各有不同的特点。
段建华(1996)采用修改后的总体幸福感量表对大学生群体施测,发现总体幸福感存在一个正态分布的趋势,男女生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别。在各分量表中,正性情绪状况及健康状况上也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但负性情绪状态则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的负性情绪显著少于女性。
还有学者特别针对贫困大学生或某个地区的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比如华南师范大学郑雪(2001)等人运用《国际大学调查》(ICS)问卷,对广州市200名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考察了广州市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的基本状况,并对主观幸福感与各维度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分析。分析表明,男女幸福感没有差异,主观幸福感主要是由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决定,外在准则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间接的;个体的自我体验和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外界准则等相关,但与外界准则的相关最大。⑦
2.幸福指数测算实践
2004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与《瞭望东方周刊》合作,对中国六大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指数的测试,测试的结果是:杭州、成都、北京位居三位,西安、上海、武汉居4到6位。
然而,真正掀起幸福指数研究的热潮,是始于国家统计局2006年提出的发布国民幸福指数的构想。在国家将构建和谐社会作为科学发展战略目标之后,人均GDP等“硬指标”已无法对此量化。国家统计局提出了发布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的设想。当时国家统计局负责人称此举将“适应各方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民生、人文各方面的需求”。
2006年,北京先行试算国民幸福指数,北京市统计局采用了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方式。有效样本量7000余份,覆盖了18个县区,群体特征涉及年龄、职业经历、教育背景等多个方面。2006年7月,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开展了一次题为“北京市国民幸福感”的调查。调查问卷包括:收入水平及其满意度;健康状况及其满意度;社会秩序、社会公平;对家庭的认同、和睦程度以及人际关系及其满意度;工作状况及职业满意度;期望和信心;归属感和幸福的综合评价。
深圳市也展开了有关的测量研究,基于“幸福=美满生活+愉悦身心+和谐关系”的认识,主要从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背景、个人社会阶层、个人生存状况和改善预期及其实现度来确定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和设计《个人幸福测量表》。
(三)国民幸福指标体系的设计与测度
借鉴国内已有的较成熟的理论,国内很多学者对幸福测量形成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对不同的职业、行业、城市都进行过有价值的实践。然而,现有的研究都是针对某个特定行业或某个特定群体,所得到的结果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且站在宏观角度对整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幸福的研究则更少。本文认为,“幸福”就是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作为“社会的人”生活的舒适和快乐的状态、体验,可以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对国民的幸福构成要素进行分解和归集,设计出相应的指标体系。
1.国民幸福构成要素的分类和归集
(1)国民幸福的物质生活指标
包括:A.人均可支配收入。物质生活水平取决于收入水平,只有较多的收入才可能支付较多的物质消费。可支配收入应包括居民的劳动报酬收入、各种投资收入、亲友赠送等转移收入,还包括居民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物品的作价收入;B.人均年末住房面积。考察国民幸福时,不仅要看居住面积,还要看其住房质量。因此,住房面积还应按房屋结构或房屋造价分类分级考察;C.人均主要耐用消费品年占有量。它包括家用电器(如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空调机等)和家用交通工具(如:小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等)以及家用健身器材(如:运动机、按摩椅等);D.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是指居民家庭全部生活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所占的比重。在总支出中食品支出比重越低,生活水平越高,家庭越富足,幸福感受越好;E.人均主要农畜产品年消耗量。这个指标也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反映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变化。在物质生活水平较低时,消耗量大的是粮食、蔬菜,而随着肉、蛋、奶类等消耗量增大,居民物质生活水平也得到提高,这也是国民幸福的一种重要和实际的体现;F.每万人的卫生健康状况。它具体是每万人拥有的医疗卫生机构数、病床数、医生数等。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的自然和生理状况延续及幸福感受的物质保障,故其也是关于幸福的物质生活指标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指标;G.个人及家庭的社会保障状况。这主要用以反映城镇职工下岗增减变动、城镇和农村贫困户及贫困人口增减变动等。这些方面的状况及问题都对“国民幸福”有直接和导向性的影响,应该在物质生活指标中反映出来。以上反映国民幸福的物质生活的七个指标可进一步细分,然后按照马斯洛对“幸福”的层次划分归集到各个层次中去。
(2)国民幸福的精神指标
包括:A.个人教育和就业状况。受教育是人从“自然人”成为“社会人”的必然环节,是人类精神生活的载体,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就必定没有良好的精神生活;就业是人们物质生活之源,更是基本的人权和精神幸福。正因为此,所以反映“国民幸福”首先就要考察这两个方面;B.个人婚姻家庭状况。婚姻和家庭是个人幸福的追求,它具有社会性和精神性的特质。初婚年龄、结婚率与离婚率、再婚人口数、亲和家庭比例、婚姻状况满意率等,都是这两种特质的体现,它是与个人关联的国民幸福的重要的支撑点,要在有关的精神生活指标中反映出来;C.个人人际关系状况。人本主义不排斥反而十分重视个人的人际关系状况,人与人之间的纠纷、矛盾、敌对、家庭暴力等等,都会从根本上毁灭国民幸福,毁掉美好的精神生活。因此,作为一个反映国民精神生活的指标进行统计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D.个人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人作为生命体十分在意自身生理、心理的内在感受,社会人的平均期望寿命、精神疾病发病率、家庭心理负荷等。将人所具有的生理、心理精神内质外化成有形的精神感受,是对国民幸福从精神生活方面的选择性描述,既有意义也有总体价值;E.个人精神享受状况。愉悦来自精神享受,幸福产生于愉悦之中。艺术的陶冶多寡、快乐时光维系的长短、休闲设施的完备状况等等,都对个人的精神享受、国民的幸福状况有较大的影响,可以作为精神生活的一个侧面来进行体现;F.个人对环境的满意程度。人们总在执著地追求“同在蓝天下”的意境,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精神世界。因为幸福的精神感受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环境、社会风气、工作氛围、个性发展、社区服务以及对政府公共政策的期望和社会安全度等。对这些极大制约个人精神生活和状态的环境因素如果不去表现和反映,国民幸福的内涵就有重大的缺失。这也是设计这个指标的出发点;G.个人的人权保护状况与实现状况。生存权、名誉权、人身安全权、宗教和言论自由权、受教育权、就业权、发展权等等,无一不体现出人对“幸福”的精神境界的亘古追求。同样,这七个指标也可进一步细分后按马斯洛对“幸福”的层次划分归集到各个层次中去。
2.“国民幸福”指标的综合与指数计算
为了取得对“国民幸福”现实状况的综合评价,并且便于动态分类对比,首先需对上述指标进行无量纲处理。取得观测结果后,在每一个指标中选择一个指标值,如在“人均主要耐用消费品年占有量”中选择广州市在这个指标上的观测结果为标准值,然后将各个城市该指标的观测结果与之对比,以消除观测结果的计量单位,其式为:

然后,对观测结果的综合与赋权。在这里,要将经无量纲处理后的观测结果进行综合,以形成对“国民幸福”状况的总的认识,综合的结果就是国民幸福指数。为方便和直观计,可以采用下式计算:
我们以式3计算的结果来描述一定时期和范围内“国民幸福”的状况。连续进行这样的统计计算,就可以反映国民幸福程度的变动状况了。
如果将各个指标对“国民幸福”的影响程度的差异大小也考虑进去的话,则需要对各个指标赋予一定的权数,进而演化为:

这里的权数 ,可以通过德尔菲方法取得。具体的操作和计算,还需根据指数系统中分项资料的细化和取得情况作进一步的确定。
该方法提出了较为新颖的从国民幸福指标体系测度国民幸福指数的途径。其权数的计算方法德尔菲法是依据系统的程序,采用匿名发表意见的方式,即专家之间不得互相讨论,不发生横向联系,只能与调查人员发生关系,通过多轮次调查专家对问卷所提问题的看法,反复征询、归纳、修改,最后汇总成专家基本一致的看法,作为预测的结果。这种方法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较为可靠,但该方法也存在自身的不足:由于其结果为各专家独立调查归纳最后汇总而得,必然受到各专家工作生活经历和自身感受的影响,从而影响其结果的客观性。另外,该国民幸福指标测度方法本身也存在缺陷。如精神指标中各个细分指标大多是人们的主观感受,无法通过观测直接获得指标值。所以,这里更多的是反映作者对国民幸福测度的一种测算思路。
四、广州国民幸福指数测度与分析
(一)广州国民幸福指数测度与分析
在实证部分,本研究将幸福感分为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和政治和谐感三个水平。其中,工作满意度包含工资水平、工作职位、工作环境三个观测指标;生活满意度包括生活信心和居住条件两个指标;而政治和谐感包括政策制定和行政效率两个观测指标,共七个观测指标,这是该部分国民幸福指数测算考量的重点指标。对于问卷中涉及的其他十三个观测指标,属于影响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和政治和谐感三个方面的因素,并不直接影响幸福感。
对于国民幸福单项指数计算是由某项指标值(取值为从1至5,即按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一定、同意及非常同意得顺序赋值)除以最高标度5后再取均值,用百分制表示时再乘以100,其中各单项指数等权看待。2009年广州国民幸福指数的测算结果如表1:
从总体上看,广州地区生活满意度指数2009年(69.01)最高,工作满意度(57.46)次之,政治和谐感(54.88)排名靠后。
从工作满意度来看,工作职位指标2009年(62.86)最高,工作环境(58.89)次之,工资水平(50.63)排名靠后。
从生活满意度来看,居住条件指标2009年(77.70)最高, 生活信心指标(60.32)次之。
从政治和谐感来看,政策制定指标2009年(58.49)最高,行政效率指标(51.27)次之。
根据我们对调研资料的深度数据挖掘,可以发现:
1.2009年工作职位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0.79)最大,其次为工作环境(0.75)和工资水平(0.65)。可见,人们对工作满意度的认可,首先考虑的是工作职位本身是否有长远的发展空间。工作职位的好坏,是人们考虑工作环境和工资水平的重要前提条件。
2.生活满意度考虑更多的是生活信心和居住条件。2009年生活信心(0.68)与居住条件(0.41)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差别较大。可见,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主要来源于两大感受:一是物质层面的,比如住房等居住条件;二是精神层面的,比如未来生活的预期,即生活信心,这两大感受有明显的轻重之分。居住条件的改善,或者生活信心的增强,都会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
3.政策制定(0.82)与行政效率(0.76)对人们的政治和谐感影响较大,且政策制定的影响略高于行政效率。广州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政府部门在政策制定方面有着浓厚的改革色彩。因此,对人们政治和谐感的影响也最直接和深入,此其一。其二,广州政府部门务实的行政效率,又进一步加深了人们政治和谐感的认同。
4.在性格因素方面,乐观、开朗、快乐、勇敢这四个内生指标较好地反映了性格因素。其中,乐观(0.82)和勇敢(0.76)对性格因素的影响最大,快乐(0.68)和开朗(0.35)次之。选取这四个内生指标的主要目的在于,验证性格因素这个内生潜变量。两年数据的统计判断,也证明了这一点。
5.本研究事先选取物价水平、医疗保障、福利保障和交通因素四个内生指标来验证经济感知内生潜变量,得到结果:2009年各指标对经济感知的影响分别为0.52、0.46、0.58、0.54。对比结果发现,2007年四个指标的影响水平差别很小,几乎处在同一水平。

表1 2009年广州国民幸福指数测算结果(满分100)
本文认为,其他感知内生潜变量存在的原因在于,前人以及本次研究中还存在着其他未被考虑到的因素。因此,调查时着重挑选了以下五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内生指标,分别是生态环境(0.65)、治安状况(0.59)、外界看法(0.30)、闲暇程度(0.06)和健康状况(0.34)。结果表明,生态环境的影响增大了,治安状况、闲暇程度和健康状况的影响基本保持不变,外界看法的影响变小了。除了闲暇程度的影响程度较小外,其他四个内生指标都较好地反映出了验证其他感知的存在。
(二)对策建议
通过对广州城镇居民调查数据和具体情况的分析,核心研究结果如下:
1.主观幸福感可以细分为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和政治和谐感三个水平。三个水平以生活满意度为中心,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相对较大,其他水平间影响很小或者无影响。因此,对于广州城镇居民整体主观幸福感的提高,首先可以考虑提高人们的工作满意度。即:要重点改善居民的工作环境;提高人们的职业规划意识,从而增强人们对工作岗位的认同感;工资水平要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即使受经济环境变化因素的影响,也不应波动太大。
2.生活满意度是人们主观幸福感的核心,受到经济感知、性格因素、其他因素和工作满意度的显著影响。因此,为了提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度,首先应该引导人们的心态向乐观积极的方面发展,可以建立一些心理咨询和辅导机构,让人们在快节奏的工作环境中,也能调整和化解工作压力,保持身心健康。其次,政府应该加强人们医疗和福利保障政策的执行和落实力度,从根本上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此外,城市建设水平的提高、治安状况的改善都有利生活满意度的提高。
3.政治和谐感与其他主观幸福感水平的相互影响比较小。原因在于政策制定、行政效率的和谐度与其他因素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判断过程,人们对政治和谐的认同和评价趋于客观,但并不意味着政治和谐感对主观幸福总体水平没有影响。通过经济感知和其他感知的变化,可以明显地影响人们的政治和谐感,从而影响到总体主观幸福感。
4.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可以概括为性格因素、经济感知和其他感知三个方面。比较而言,性格因素对生活满意度影响最大,经济感知对工作满意度和政治和谐感影响最大,其他感知的影响正面显著,但效果小于前面两者。因此,政府部门在制定和调整政策时,可以有针对性的调整对相应的影响因素观测指标的影响程度,从而提高对主观幸福感某个水平的影响程度。
5.从时间跨度来看,短期的时间效应不会对人们主观幸福感的具体水平和影响因素产生显著变化,即使在2008年出现了世界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也不会大规模地显著影响它们的排名状况。因此,本文认为时间不是改变主观幸福感的主因,通过时间的推移,改变影响因素对主观幸福感水平的影响程度,才是影响机制发生和传导的主要路径。
注释:
①丁新华,王极盛.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04,(1).
②杨彦春.老人幸福度与社会心理因素的调查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88,(1).
③刘仁刚,龚耀先.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0,(2).
④张红静,马颖竹.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因素分析[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2,(11).
⑤邢占军.测量幸福[M].人民出版社,2005,5:39.
⑥谢彦明,李灿,冯洁.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其综合评价[J].农村农业农民,2008,(6):46.
⑦郑雪,严标宾,邱林.广州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研究[J].心理学探新,2001,(4).
[1]Alan Carr著,郑雪译.积极心理学:关于人类幸福和力量的科学[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8:1-36.
[2][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商务印书馆,1986:163-173,213.
[3][德]包尔生著,何怀宏,廖申白译.伦理学体系[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7:347.
[4]辞海[M].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607.
[5]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商务印书馆,1976:236-237.
[6]林洪.国民幸福指标体系及综合度量探析[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99-102.
[7]傅红春,文燕平等译.满足与幸福的经济学[M].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8:287.
[8]林洪,李玉萍.国民幸福总值(GNH)的启示与国民幸福研究[J].当代财经,2007,(5):14-17.
[9]候杰泰,温忠麟,成子娟.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7:170-197.
Research on National Happiness Theory and the Happiness Index of People in Guangzhou
Lin Hong, Qv Bo, Wen Tuo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origin of National Happiness Theory, reviews relevant literature abroad, compares it with other similar indexes, and analyzes the happiness index of people in Guangzhou based on data from surveys.
national happiness; Guangzhou
F120.3
林洪,广东商学院国民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曲博,广东商学院国民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国民经济核算与分析;温拓,广发证券股份有限高级理财顾问,研究方向:金融与证券投资分析。
(责任编辑:卢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