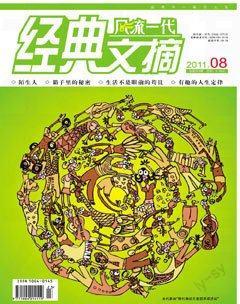从蚁到神
高纬
女作家尚德兰曾经给诗人顾城当过法文翻译。她曾回忆当年的顾城:那是1993年的一天,顾城给她写了两幅字,一幅是“鱼在盘子里想家”;另一幅是“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尚德兰回忆说,那天下午,诗人顾城先是在厨房里磨了很长时间刀,那专心致志的样子令人发怵。他给尚德兰写这两幅字时,情绪激动;写完了,如释重负……一年之后,诗人顾城自杀了。
看过一个外国电影:一个干坏事进了监狱的男人,在监狱里,他和狱长一起看电视。电视上正播放着悬赏百万寻找救人英雄的一个新闻节目,男人对狱长说,那个人就是我啊。狱长给了他一耳光,说,若你是英雄,那么这里的每个人都是总统——事实上,电视上寻找的那个英雄真的是这个犯人,他救了好多人,但是却盗用了其中三个被救之人的信用卡去买了东西,他因此而进了监狱。影评家王书亚曾说,“一个人的美德并非是他英雄行为的动机,一个人的卑微也不是他错误的必然根源。”
从蚁到神,这其中需要多大的想象力?
我时常把自己的灵魂撤离出来,看着具象的我。我自己就是一个排。她们列队站着:女人;母亲;妻子;写诗的我;社会的我;人群中的我;会场我;私下我;好我;坏我;小我;大我;统一我;分裂我;外在我;内在我……是的,我自己就是一个排,从蚁到神。我纷纷出场,在不同的场合,出现在不同的岗位。更多的时候我必须戴对面具,不然我就会把生活之戏演砸了。我不知道命运将在哪个拐角处使用哪一个我?我也不知道这些我将把我人生的大杂烩乱炖成什么模样外加什么滋味。
我将死于蚁,还是将死于神?
从蚁到神,我将被各种自己分裂成什么样子?
哲学家说:没有最低点,就没有最高点。这是不是说,没有我们的蚁性,就没有我们的神性?没有蚁性,我们是神而不是人。我们有着各种人性的弱点,说明我们活得像人。可是,如果我们让自己的生命神性缺失,一个活成蚁虫的人终究又有多大意思?所谓行尸走肉,是不是就意味着,一种神性的彻底丧失?
每一个人,从蚁到神地活着。一些人更接近蚁性一些;一些人更接近神性一些。每一个从蚁到神的人,都需要我们多么庞大的想象力;数以亿计的从蚁到神的人,需要我们数以亿计的多么庞大的想象力。红尘的好玩与红尘的不可忽视,生活的无趣与生活的敬畏,皆因如此。
(摘自《青岛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