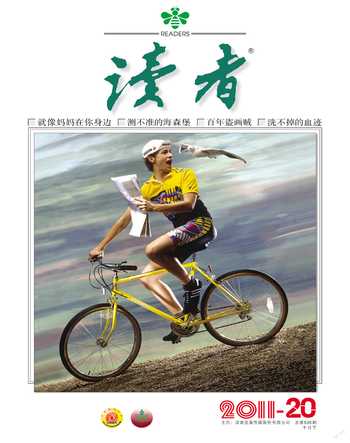心灵之镜
罗伯特·弗格汉姆
在希腊克里特岛一个岩石密布的海湾,有一个叫哥尼亚的村庄,村子附近有一座希腊东正教修道院。在修道院旁边,由修道院捐赠的土地上建有一所研究院,其宗旨是传播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和平,尤其是恢复德国人和克里特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可是战争的创伤使这个任务几乎不可能完成。
这所研究院的位置很重要,站在这里向远处望去,能够看到马里门机场上的小型跑道,纳粹空降部队就是从这里入侵克里特岛的。也正是在这里,纳粹部队遇到了挥舞着菜刀和长柄镰刀的当地村民的顽强抵抗。克里特居民也为此遭到德军的野蛮报复。全村的居民都被抓起来后列队枪杀,只因他们袭击了希特勒最精良的空降部队。研究院的上方是一处公墓,那里只有一个十字架,标志着这里是克里特游击队烈士的公墓。在海湾对面的另一座山上也有一处墓地,里面埋葬的是纳粹伞兵。烈士公墓里的墓碑摆放独特,任何人看一眼便永生难忘。对于克里特人来说,仇恨是他们最后拥有的唯一武器,也是许多人发誓永远不会放下的武器,永远不会。
正因为有这样沉重的历史背景,仇恨的巨石压在当地人的心中,根深蒂固。而就在这样一个地方居然有这么一所致力于治疗战争创伤的研究院,的确让人感觉自相矛盾。这样一所研究院怎么会建在这里呢?是因为一位名叫亚历山大·帕帕德罗斯的男士。
他是一位哲学博士、教师、政治家,住在雅典,但出生在克里特。战争结束时,帕帕德罗斯逐渐意识到,德国人和克里特人其实可以从对方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们可以给世人树立一个榜样,因为如果他们都能够互相谅解、摒弃仇恨,建立一种有创造性的关系,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人不能这么做呢?
长话短说,帕帕德罗斯成功了。他终于在这个曾经腥风血雨的地方建立了这样一个集会研讨的场所。事实上正是在这个地方,两国的学者互通有无,颇有收获。仅一个暑期班的时间,他们就完成了关于靠人们之间的相互给予而实现伟大梦想的多部书籍。亚历山大·帕帕德罗斯成了一个活着的传奇。
在一个为期两周的希腊文化研讨会最后一天的上午,帕帕德罗斯从希腊各地聘请的各领域的专家和学者进行最后一次讨论。这时坐在房间最后面的帕帕德罗斯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到前面一扇打开的窗户前。希腊明亮的阳光照在他的身上。他站在那儿,向窗外望去。我们顺着他的视线,目光越过研究院前方的海湾,落在了德国墓地那个铁十字架上。
他转过身来,问道:“还有问题吗?”
房间里一片寂静。在这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大家的脑海里已经产生了许多疑问,足够用一生的时间去思考,但这一刻大家都选择了沉默。“没有问题?”帕帕德罗斯的目光在房间里扫视了一遍。于是我问道:
“帕帕德罗斯博士,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照例这个问题引来了一阵笑声,人们骚动起来,开始准备离开。帕帕德罗斯抬起一只手,示意人们安静,接着久久地注视着我,用眼神询问我是不是认真的,并从我的眼神中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他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掏出钱包,从里面摸出一个非常小的圆镜,大概只有25美分硬币那么大。接着他说:“克里特岛之战时我还是个小孩,家里很穷,我和家人住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一天,在公路上,我发现了一些镜子的碎片。这是一辆德国摩托车在那个地方被毁后留下的。
“我试图找到所有的碎片把它们拼起来,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只把最大的一块留了下来。就是这块。我在一块石头上把它磨圆,把它当成一个玩具摆弄。我发现用这个玩具我能把光线反射到那些太阳永远照不到的黑暗角落——深洞、裂缝,还有漆黑的壁橱,这个发现令我十分着迷。于是,把光线反射到我能找到的最不可能到达的地方成了我玩的一个游戏。
“我一直保存着这面小镜子,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不管我走到哪,我都会在闲暇时拿出这面镜子,继续玩这个游戏。长大成人后我渐渐懂得,这不仅仅是小孩子玩的一个游戏,它更是一种隐喻,告诉我在这一生中可以做些什么。我渐渐明白,我既不是光,也不是光源,可光(真理、理解和知识)就在那儿,只有通过我的反射,它才能照亮许多黑暗的角落。
“这只是一面镜子的一块碎片,我不知道整面镜子的形状,但是,我可以将光线反射到世界黑暗的角落,反射到每个人心灵深处那些阴暗的角落,帮助一些人,改变一些事。也许其他人会看到并效仿。这就是我的作用,这就是我人生的意义。”
说完,他举起那面小镜子,小心地调整角度,捕捉从窗户射进来的缕缕耀眼阳光,然后将它们反射到我的脸上,又反射到放在桌子上的双手上。
那年夏天,我了解了很多关于希腊文化和历史的信息,它们大部分都已从我的记忆中慢慢淡去,但直到今天,在我心灵的钱包中却始终装着一面小小的圆镜子。
(苏林摘自《新东方英语》2011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