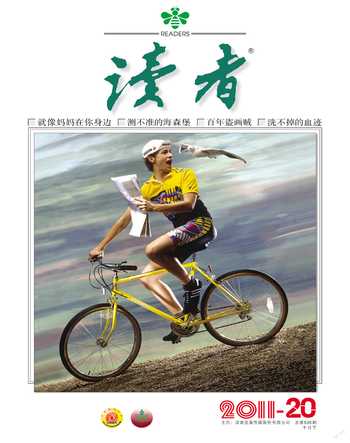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
卿卿
我们家五个孩子就像长长短短的五根手指,大姐比二姐大两岁,二姐比哥哥大两岁,轮到我时哥哥一下就大我四岁多,妹妹又只小我一岁。后来我才知道,爸爸妈妈当初并没打算生我和妹妹,是哥哥一不小心掉进水塘后爸爸突然做出的决定。爸爸想再生一个儿子,这样,家里就像点燃了两盏灯,哪怕灭了一盏另一盏也会亮着,怎么都不至于闹个黑灯瞎火。谁知天公不作美,我出生后竟是个女孩,他们一鼓作气,第二年妹妹又出生了。爸爸妈妈不敢再生,他们的收入养不活更多的孩子,两人索性把哥哥当宝贝来养。厂里有很多华侨,他们能买到国外的东西,于是妈妈就从牙缝中挤钱出来请他们买高级营养品给哥哥吃。听说,哥哥小学期间一直用美国黄油拌饭吃,还吃过巧克力。
这天,早早地我们就起床了,很快吃完早点背上书包,准备去上课。就在这时,妈妈突然反手关上了门,把我们三个拢在一起,嗓门压得低低的,问:“如果有人问起家里是什么成分,你们怎么回答?”
我还以为妈妈要说什么呢!这事有什么可神秘的?推开妈妈的手,我满不在乎地说:“不就是旧军人嘛。”
话音没落,妈妈便扇了我一耳光,她恶狠狠地看着我,依旧压低嗓门说:“现在村里已经有人说我们是解放军用枪押送回乡的了,你还嫌不够,还想方设法地抓些帽子往头上戴,是不是想叫大队开会的时候把我也拉到台上去站着?”
在昆明,老师说过成分的事,老师说家里的成分主要以爸爸为准。爸爸生在旧社会,又当过兵,不是旧军人是什么呢?
妈妈转身去问哥哥。哥哥说:“佃中农。”
妈妈又问妹妹,妹妹睁着天真的大眼睛对妈妈说:“如果有人问起,我让他到家里来问你行吗?”
妈妈打开门放走了哥哥、妹妹,转过身来继续问我:“你再说说看,家里是什么成分。”
就像被鬼缠住了,我脱口说出的又是旧军人。妈妈脸都气白了,她狠狠地扇了我俩耳光,说我是故意的!
我伤心地哭着,觉得十分冤枉,我怎么会故意呢!我记性不好,十分不好,那大脑中就像少了根弦似的。次次被老师留在教室背书,我很难过,回去后我忍不住问妈妈,我的脑袋为什么记不住东西?妈妈说,我出生时错打了她的止血针,昏死过去三天,大脑因此受损,和正常人相比就有些不同。妈妈的意思是说我有点傻,可外面的人个个都说我聪明,就连老师都这么说。还没上学,我就能心算加减乘除法,爸爸厂里的大人经常把我抱到桌子上站着,出题给我做,我只眨巴几下眼睛就能算出来。我想,大脑受损是假,可能是太聪明了,记性没地方长了,所以什么都记不住。这么一想很难过,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傻一点,但长个记性,这样至少不用三天两头被老师留在教室背书。
妈妈大吼一声,叫我不要再哭了,然后又问家里是什么成分。这一次我不敢信口开河了,认认真真地想,一字一句地做了回答。
妈妈看了我一阵,仍然十分不放心地说:“你好好地再记一下,到真不会说错才能去学校上课,否则你出去胡说八道会给家里惹麻烦的。”
妈妈出去了,我生怕待会儿紧张再说错,更怕妈妈哪天突然袭击时我说成别的,便一遍又一遍地背“佃中农”这三个字,可背了半天都没办法熟记于心。真奇怪,栗山岭怎么会有“佃中农”这种成分呢?在昆明只听说过地主、富农,突然听说个“佃中农”,我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把它和成分联系在一起。思来想去,我决定找个字音和它相同的东西帮助记忆。可找什么呢?突然,我想起电灯。对,电灯!“佃中农”三个字中,我最记不住的就是那个讨厌的“佃”字了,如果用电灯做引子,那记忆起来不就容易了吗?
妈妈进来了,问我:“记住了吗?”
我肯定地说:“记住了!”妈妈看着我,慢腾腾地说:“那么,我再问你一遍,家里是什么成分。”
妈妈的脸离我那么近,连一根根睫毛我都看得清清楚楚。说不出害怕什么,我的心怦怦地狂跳起来,就像有个小人儿在我肚子里打鼓似的。
妈妈的脸凑得更近了,问:“是不是又记不住了?”
我往后退了一步,急促地答道:“电灯!”
这一次妈妈没有扇我耳光,她从床底下抽出一根棍子,把我抱到床上拉开裤子就打屁股。妈妈边打边说我顽固,说我故意气她,说就是去问个白痴也不会说自己家的成分是电灯。我呼天抢地地讨饶,说再也不敢了。这样一来妈妈更加肯定我是故意的,下手比先前又重了许多。等妈妈准我去学校上课的时候,我的两只眼睛都肿得睁不开了。
(巴山摘自云南人民出版社《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