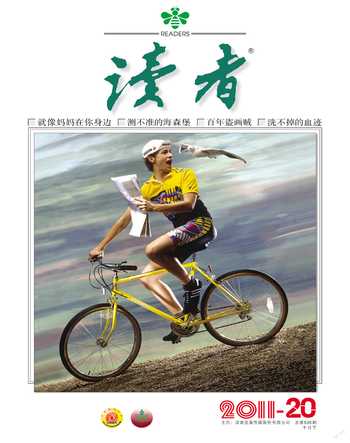聆听父亲
张大春
我不认识你,不知道你的面容、体态、脾气、个性,甚至你的性别,尤其是你的命运,它最为神秘,也最常引起我的想象。当我也还只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不时会幻想:我有一个和我差不多、也许一模一样的孩子,就站在我的旁边、对面或者某个我伸手可及的角落。当某一种光轻轻穿越时间与空间,揭去披覆在你周围的那一层幽暗,我仿佛看见了另一个我——去想象你,变成了理解我自己,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去发现我自己,结果却勾勒出一个你,一个不存在的你。在你真正拥有属于你自己的性别、面容、体态、脾气、个性乃至命运之前,我迫不及待地要把我对你的一切想象——或者说对我自己的一切发现,写下来,读给那个不存在的你听。
这个写作的念头突然跑出来撞了我一下的那一刻,我站在我父亲的病床旁边。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夜光均匀地洒泻在他的脸上,是月光。只有月光才能用如此轻柔而不稍停伫的速度在一个悲哀的躯体上游走,滤除情感和时间,有如抚熨一块石头。老头儿果然睡得像石头,连鼻息也深不可测。要不是每隔几秒钟会有一条腿猛地痉挛那么一下子,他可以说就是个死人了。那是脊椎神经受伤的病人经常显现的症状:一条腿忽然活跃起来,带着连主人也控制不了的力气,朝什么方向踢上一踢,有股桀骜不驯的劲儿,仿佛是在亢声质问着:“谁说我有病?”每隔几秒钟,它就“谁说我有病”一下子。掩映而过的月光完全没有理会这条腿顽强得近乎可笑的意志,便移往更神秘的角落里去了。而我在月光走过的幽暗边缘被一条兀自抽搐的腿逗得居然笑出了一点眼泪。
我想先从洗澡说起。
应该不独中国人是这样的,每个降生到世上来的孩子所接受的第一个仪式就是洗澡。一盆温热的水,浸湿一方洁净的布,将婴儿头上、脸上、躯干和四肢上属于母亲的血水和体液清除尽去,出落一个全新的人。这全新的人睡眼惺忪,还察觉不到已然碾压迫至的命运。中国人在这桩事体上特别用心思,新生儿落地的第三天还要择一吉时,将洗澡之礼再操演一遍,谓之“洗三儿”。讲究的人家自然隆而重之,他们会请教精通医道的人士,调理出一种能强健体质的草药香油,涂抹在新生儿的身上。“洗三儿”是非常务实的,如果有任何一丁点儿深层的隐喻在里面,不过就是希望这孩子常葆焕然一新的气质。中国人也从不认为洗的仪式有什么清涤罪恶、浸润圣灵的作用。
我在一个天主教会办的小学念一年级的时候,一度对那个宗教所有的仪式非常着迷,因为圣诗唱起来庄严优美,而每个星期五的下午,被称为“教友”的同学还可以少上一堂课,他们都到教室后方庭园深处的教堂里去望弥撒领圣体——一块薄薄的、据说没什么滋味的小面饼。我非常希望能尝尝那种小面饼。
“好吃吗?”我问我的教友同学。
“像纸一样。”教友同学说。
后来我吃了几张剪成小圆片的纸。然而那样并不能满足我成为一个教友、张嘴接住神甫指尖夹过来的圣体以及逃掉一堂课的渴望。想当教友很简单,教友同学们都这么说:去受洗就可以了。据说受洗一点儿也不疼,神甫会在你的额头上抹些油,教你祷告祷告,大概就是这样。我跟我父亲说我要受洗。他想都不想就说:“你在家好好洗洗就可以了。”
偶尔,父亲愿意从病床上下来,勉强拄着助行器到浴室里洗个澡。“连洗个澡也要求人。”他低声叹着气,任我用莲蓬头冲洗他那发出阵阵酸气的身体,然后总是这样说:“老天爷罚我。”
“老天爷干吗罚你?”有一次我故意这么问。
“它就是罚我。”
在那一刻,一个句子朝我冲撞过来:“这老人垮了。”
我继续拿莲蓬头冲洗他身体的各个部位。几近全秃的顶门、多皱褶且布满寿斑的脖颈和脸颊、长了颗腺瘤的肩膀、松皮垂软的胸部和腹部、残留着枣红色神经性疱疹斑痕的背脊。
这老人还没垮的时候(要讲得准确些应该是,他摔那一跤之前的几十年里)几乎没在家洗过澡。他的澡都是在球场里洗的。差不多也就是从我出生那一年起,他开始打网球。我第一次看见他的身体就是在球场的浴室里。那是一具你知道再怎么样你也比不上的身体,大,什么都大的一个身体。吧嗒吧嗒打肥皂、哗啦哗啦冲水、呼啊呼啊吆喝着的身体。
对我来说,洗澡必然和这最初的视像融接合一。其意义似乎就是:你得眼睁睁地凝视一种比你巨大的东西,那是非常原始的恐惧。日后我在希区柯克和狄帕玛的惊悚电影中体会到:人在洗澡的时候,在赤裸着接受水的冲洗浇注的时候,其实无比渺小脆弱。持刀步步逼近的凶狂歹徒只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人类无所遁逃,它碾压迫至,必然得逞。
你尚未赤裸裸地到来,而我已着实惊着了。因为在身体的最核心,我有重大的欠缺,那是从我父亲、甚至我父亲的父亲……就已然承袭的一种欠缺。简单地说:我们这个家族的男子的恐惧都太浅薄,我们最多只能在命运面前颤抖、惶惑、丧失意志;再深入进去,则空无一物。我们都不知道,也没有能力探究命运的背后还有些什么。于是,一具健康伟岸了76年的躯体在摔了一跤、损伤了一束比牙签还细的神经之后,就和整个世界断离。
作为一个人,父亲只愿意做三件事:睡眠、饮食和排泄。这将是他对生命这个课题的总结论。如果你再追问下去:“为什么?”他会说:“老天爷罚我。”如果我央求他试着起床站一站、动一动、走一走,他会说:“你不要跟着老天爷一起罚我。”我若不做声,静静坐在他眄视不着的床尾,就会发现他缓缓合上眼皮,微张着嘴,在每一次呼吸吐气的时候轻诵道:“罚我哦——罚我哦——”
(燕青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聆听父亲》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