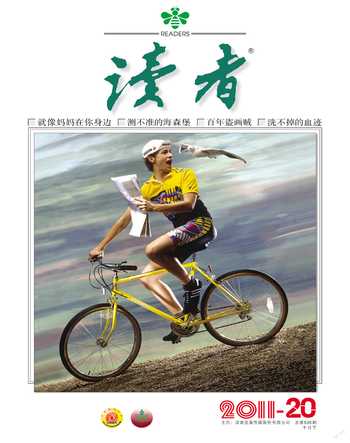穷孩子有没有春天
潘晓凌等
拿到班级花名册时,陆铭注意到,全班60多个同学,农村籍学生只有5个。
作为北京大学某文科院系2009级1班的班长,陆铭此前一直以为,通过高考选拔获得中国这所顶尖大学通行证的同龄人,多数该有着和他类似的成长经历:出身农村,家境贫寒,独立自强,品学兼优。
这是这名来自四川的22岁寒门学子从小被灌输并认定的世界观:知识改变命运,逆境辈出英杰。
现在,手上的花名册颠覆了他的信念。而这正是眼下中国名校生源变迁的缩影。
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约占三成,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系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那年的高考考场里,62%是农村考生。
不仅仅是北大、清华,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结论是,国家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开始不断滑落。
哪些障碍垫高了陆铭这样的孩子考入名校的门槛,封锁了他们努力向上攀爬的通道?知识改变了陆铭的命运,可绝大多数寒门子弟还有机会改变自己命运吗?
寒门少年都去了哪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系讲师晋军指导他的学生完成了对清华生源状况的调研。调查做了两年,指向高度集中。“一名清华本科生的典型形象是这样的,”晋军说,“出身城市,父母是公务员或教师,每年与父母起码外出旅行一次,甚至高中就有出国游学的经历。”
在复旦大学招生办一位老师的印象中,这几年被招进复旦的寒门子弟的人数不断减少,大多数学生的父母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与体面的社会地位。“无论是招进来的,还是从来没机会进入我们视野的年轻人,他们都在复制父辈的经历。”他说。
学习刻苦,成绩不错的寒门少年都去了哪?
教育学者杨东平的研究显示,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以湖北省为例,2002~2007年,考取专科的农村生源比例从39%提高到62%,以军事、师范等方向为主的提前批次录取的比例亦从33%升至57%。而在重点高校,中产家庭、官员、公务员子女则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
向上流动倍感艰难的不仅仅是农村少年。2004年,厦门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对全国34所高校的生源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普通工人子女考入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人数分别下降了7.9%与5.6%。
学者廉思说:“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
连专科都考不上或不愿读的大有人在。廉思曾选取河北一个普通村庄作为研究样本,那儿浓缩了中国基层的模样——马路上平常看不到什么人,一旦闹出点什么动静,一大帮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立即呼啦啦地从网吧、桌球室里跑了出来。
看着他们在转型期中国一小片弥漫着尘土与工厂粉尘的土地上挥舞着年轻的肢体,廉思觉得,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个体命运的转型却陷入停顿。
那扇门在高考前就被关上了
仝十一妹一直庆幸,自己在上帝关上门的前几秒及时跳了出来。这位来自河北沧州农村的24岁女孩,现在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研一学生。
儿时,这个在家族中排行第11的女孩就被告知,自己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改变命运,要么念书,要么参军。
仝十一妹的小学、初中分别在乡村与县城度过。中考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为成绩一路优异的她报考了衡水中学。在这所将应试教育发挥到极致的军营式河北省超级中学,仝十一妹与来自全省最优秀的同龄人度过了紧张且竞争激烈的3年,2006年,她以年级第15的排名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那一年,衡水中学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共42名,占据两所高校分配给河北省名额的33.87%。
“如果我当时留在县城念高中,我肯定考不上北大。”仝十一妹说,那一年,县城中学年级排名第一的学生也只考上了南方一所二线名校。
这是优质教育资源高度集中的体现。超级中学是各省重点中学的升级版,它们拥有丰厚的教育经费与政策支持,像抽水机般吸纳当地及周边县城最优秀的学生与最优秀的老师,每年几乎垄断了其所在省份北大、清华的招生名额。
这是超级中学与省重点中学选拔机制的结果,根据单独招考成绩,排在最前的直接入学,后面的根据相差的分数缴纳赞助费,此外还普遍存在“拼爹妈”的条子生、择校生。农村孩子,尤其是远离省会城市的农村孩子,即便再努力,表现再好,考入超级中学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
不平等的起跑线
得益于近年系列高考新政,保送、加分、自主招生的机会,大多被各省最富竞争力的高中包揽。例如,全国13所外国语学校,每年最优秀的学生都可直接保送进入北大、清华。2010年,北大、清华在陕西自主招生名额的98.9%、保送名额的97.3%被西安的五大名校垄断。
裸分考上北大、清华的几率越来越小。据来自北大招生办的信息,2010年北大在某省招收的70名文理科学生中,只有10人没有任何加分,其余60人则通过自主招生加分、政策性加分、保送的途径进入北大。他们绝大多数来自超级中学。
教育学者杨东平说:“这一被大大拉长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把低收入家庭排斥在外了。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又叠加了优越家庭的优势,寒门子弟拿什么和他们竞争?靠什么改变命运?”
越来越窄的向上通道
在北大,陆铭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特殊:出身寒门,毕业于一所县城中学,高考没有加分。
对于陆铭来说,最有可能的加分是获得省三好或省优干,但这些有限的名额往往更容易被超级中学及省级重点中学获得。最顶尖的考生之间分数往往只有一两分之差,而省三好的加分是20分,省优干的加分是10分。
在甘肃会宁这个以寒窗苦读闻名的状元县做实证研究时,清华大学新闻学院2009级本科生张晔遇上了一名垂头丧气的农村少年,刚从自主招生考试的考场上下来,“很多题目,他连看都看不懂。”张晔说。
自主招生的考题涉及面广,往往是城市孩子才可能接触到的事物,比如五线谱,比如歼-10……
艺术加分与寒门子弟更是绝缘。来自北京大学招生办的资料显示,最近5年北大招收的体育特长生绝大部分来自东部地区,七成来自大中城市,来自农村的只有6%;而艺术特长生,迄今没有一位来自农村。
“高考扩招后,寒门子弟考大学不难,难就难在4年后,拿什么改变命运?”毕业之后,宋永亮旋即陷入就业痛苦。
其他同学的经历类似,有人至今还无力还清助学贷款。他们也大都出生于农村及乡镇,毕业于当地的县城中学,家中日渐老去的父母还盼着他们从此改变一家的生活际遇。
北京大学副教授刘云杉将农村城市化的速度与农村生源考入重点大学几率下降的速度对比分析得出,前者的速度远低于后者。换言之,农村人口的减少,并非名校农家子弟比例下滑的主要原因。
“这意味着,中国高校扩招后,并没有增加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杨东平说,“相反,普通高校文凭的市场竞争力在扩招后越来越弱,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难度越来越大。”
如同超级中学一样,城市像抽水机般将最优质的资源、机会、人才与财富从四面八方抽离、集中。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这个国家过去20载社会变迁的切面——税制改革与国企改革使资源向城市集中,财政收入向上级集中,基层政府越来越弱,农村走向凋敝。
陆铭也回不去了。寒假回家,他与小学、初中同学的联系越来越少,围坐在这位北京大学高材生旁边,那些在县城工作或从外地打工返乡过年的同学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唯一共同的话题是:他们都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仍然保有向上的理想。
(高飞摘自《南方周末》2011年8月4日,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