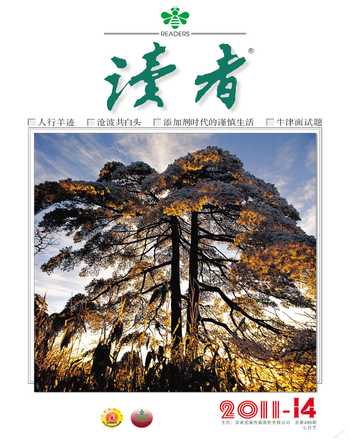母亲的神灵
摩罗
一
我母亲是乡村最普通、最善良的一位老人,一生拜菩萨。我刚刚记事时正赶上“文革”,那时候乡村的菩萨和庙宇早就遭到“扫荡”,没有人敢在自己的村子里、在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长的眼皮底下拜菩萨,我母亲和她的同修们多次到十几里之外一个小山谷的一棵树下拜菩萨,那棵树长在山谷的池塘边。母亲说那个地方叫蛇王庙。
又有山谷、又有水、又有树,必定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我们村里的香客都认为那里特别灵验。
那时候人们心里特别紧张,若有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对这些香客追问一句无关紧要的话,这些香客就会惊恐万状,拔腿猛跑,一口气跑出那个并不险峻的山谷。有的人就因为这一拜、一跑,几个月的病也就不翼而飞。于是香客们益发传说那个菩萨灵验。我十来岁的时候,也曾跟着母亲一干人马去那里求过仙丹。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那不过是树底下随意码放的几块砖头,根本没有所谓菩萨塑像之类。香客们将当地的神灵,请入这堆寒碜的石头里,接受自己的祭拜和索求。
母亲9岁那年,家里房子被日本飞机投弹炸掉了,从此无家可归。外公远走他乡,外婆靠打短工养大我母亲和舅舅,常常连盐也吃不上。一听说来了部队,外婆一手提着包袱,一手牵着我舅舅的小手,我舅舅再抓着我妈妈的小手,跟着村里人往大鸣山深处猛跑。小时候经常听母亲谈到“躲兵”时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故事。谁都不知道,日本人的炸弹什么时候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谁能保佑这些绝望的人?只有菩萨。我母亲从那时候起,就跟着长辈拜佛吃斋。那时她拜的是观音菩萨,每次吃斋期为3天。
进入20世纪90年代,鄱阳湖北岸的乡村地区,修建寺庙的风气渐盛。后来我在家乡进行宗教考察,发现某个行政村竟然修造了8座具有一定规模的寺庙。我们村很穷,建不起大庙,我母亲起心动念,想在村西建一座小庙。风水先生说,我们村下关太低太敞开,聚不起钱财,养不出人才。如果能在村西建座庙,就能充实下关,聚敛财气人气,造福村民。这种说法村里人都认为在理。
族叔爱来先生说,建庙是全村受益的事,何必要你一家花钱,可以让全村人自愿捐钱。爱来叔一生当干部,具有组织能力。由爱来叔和我父亲牵头,向村里人募捐了一点钱,在村西头建起了那座一人多高的老嘎嘎庙。从此以后,我母亲每月初一、十五都去小庙上香磕头。母亲拜菩萨的时候,家里老老小小每个人的名字都要念到,生怕落下一个。我的名字自然也常常出现在母亲许愿的声音中。
几年之后,母亲的信仰由于一个特殊的灾难而出现了危机。修庙期间,有一天二哥从小镇回到村里,看见村里捐款榜上母亲捐款最多,100元。二哥就跟母亲说,那个捐款他出一半,并随手递上50元钱。二哥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向他募捐也许有所不便,他主动捐款让我母亲好一阵欢喜。然而正是二哥的支持,让母亲产生信仰危机。小庙建起来不几年,二哥因为意外事故不幸去世,年仅39岁。
我的母亲虽然一辈子吃苦,但是儿女很旺。她生了6个孩子,个个长大成人,这在贫困乡村甚是难得。中年时期的母亲,总是被村里人和亲戚家请去参与打理婚嫁喜事,比如给新娘扯面、给新人铺床之类,就因为我母亲的儿女个个顺道,可以传播吉祥和喜气。每当这时,总是母亲最为光荣、最为幸福的时候。
可是,当母亲老了,她的正当盛年的儿子却遭遇不测。我深知母亲心头的至痛。
我离家以后,母亲天天在家哭喊:“菩萨呀菩萨,我二崽对你那么好,你怎么就不长眼哪!”
母亲睡觉前这样哭喊,一觉醒来又接着这样哭喊。
我母亲的信仰就这样一天天动摇。我在遥远的北国,默默地陪着母亲憔悴、衰老。对于自己的命运我们竟然如此无能为力啊。
二
好几年之后,我回家探亲,遇上母亲邀伴到村西小庙烧香。母亲在与寺庙和菩萨疏离几年之后,终于重新回到菩萨身边。看来母亲内心最为伤痛的一角,终于有了些微缓解,我因此感到高兴。
有一次,母亲和另两位老妇一起去上香。我跟去为她们拍照。她们的仪式完毕以后,我进庙拍摄神龛里的菩萨像。
出乎意料的是,那菩萨竟然是一段一尺来长、五官模糊的木偶。
我问母亲这是什么神,母亲说,这是老嘎嘎。老嘎嘎是我们那里对老爷爷的尊称,意思相当于可敬的老人。母亲只知道老嘎嘎是我们村里的一位祖先,这位祖先究竟什么身份,究竟是如何成神的,母亲没法说清楚。
母亲补充说,这尊菩萨不是老嘎嘎的肉身菩萨,而是从香火堂捡来的韦陀菩萨。我们村的香火堂,原先是祖堂兼神庙,除了供奉祖先牌位,还供奉三将军(张飞)和老嘎嘎。这尊韦陀菩萨,是三将军和老嘎嘎的护法使者。
“文革”时期,三将军和老嘎嘎的神位被砸烂,这位韦陀菩萨被丢在阴暗潮湿的角落,寂寞十几年。直到那年建庙,人们才找到这尊韦陀菩萨,当做老嘎嘎的肉身供奉在这里。面目模糊系木质腐烂所致。
那一天我意识到自己有两个发现。第一,我发现我母亲不是佛教徒,可是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母亲既然拜菩萨那就该是佛教徒。第二,我发现我对父亲母亲的精神世界原来一点也不了解,而且也从来不想了解。
不但不想了解,我在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按照书文上的说教在批判他们的信仰。我按照书文上的说法,一直把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的母亲的信仰,看做迷信。我从书本上学的东西越多,越认为自己很有学问,就越加坚决地否定父老乡亲们的信仰和习俗。我像所有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一样,骂他们愚昧无知,骂他们封建迷信。
所不同的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骂的是他们的下人,诸如阿Q、闰土、祥林嫂之类,每天给他们挑水、种地、舂米的劳动者;我骂的是我的父母,那每天挑水、种地、舂米将我养大成人的人。
很显然,我发现的这两个问题,乃是我一直犯的两个错误。
那一天我还不知道,老嘎嘎的故事,以及我的两个相关发现,将会改变我一生的文化立场。心灵的变化总是慢慢完成的,当它刚发生的那一刻,我们常常意识不到那种变化正在来临。
三
我按照制度的安排,中规中矩地求学几十年,按照我们村的说法,就是饱读了一肚子书。可是,我父母的信仰和神灵,却在我的知识之外,在我的视野之外。我的父亲母亲为了让我生活得更好,鼓励我学习其他知识,容忍了我对他们的知识体系的漠视。可是,我自己不能容忍。
我开始了对老嘎嘎的研究。我走访村中老人,我翻阅族谱,终于弄清了老嘎嘎就是本村发祖南乙公的孙子。
从老嘎嘎开始,我着手对家乡的宗教信仰和神祇体系进行调查研究。
从老嘎嘎开始,我着手对千百年来底层社会的所谓民间宗教进行研究。
我发现底层人的信仰是如此坚不可摧。精英阶层的信仰像走马灯一样变来变去,乡村社会的信仰却十分稳固。他们还在按照千百年前万物有灵的信念,随社立神。所谓随社立神,就是他们在哪里建立了村社,就将那里的神灵立为自己的保护神。每个地方的老百姓,都有自己独特的神灵。乡村社会底层人群精神世界的底色,依然是他们自己的神灵。
千百年的社会动荡中,乡间草民像麦子一样一茬一茬生生灭灭,可是他们的信仰体系、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如此坚不可摧。心底里,他们依然在用几千年前的宗教原则支撑自己的生活。
乡村社会,才是真正坚不可摧的世界。我母亲并不是标准的佛教徒,她甚至不知道还有顶礼。她的所谓信仰,只是以她内心的至诚至善,跟人间和冥冥世界进行能量交换。她没有学习过任何一种宗教的教理教义,她信的是内在的虔敬和善良。这正是信仰的真髓。无论多么伟大的神灵,体现的也都是宇宙大生命的虔敬和善良。
我母亲是最伟大的信徒。
(青豆摘自东方出版社《我的村,我的山》一书,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