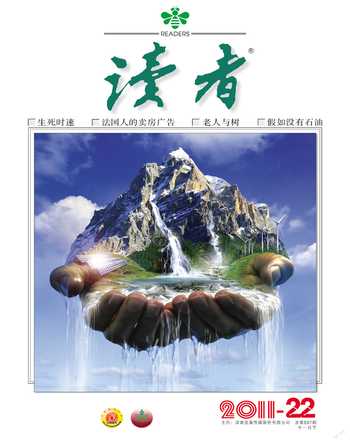最踌躇的门
林特特
如果一个人对你而言意义非凡,想到他,你便感到软弱。
临见的一刹那,面前如横着一道门,心酸、兴奋、怯懦,及至推开,又不知说什么。啊,那真是世上最踌躇的门。
这种情形我在三毛的《蓦然回首》中读到过。
三毛写道,她和恩师顾福生约好见面,她早到了两分钟,却不敢进门,只静静地站在夕阳下等。
等时间到了,有人领她进了院子,通往客厅“短短的路”,却让她感到“一切寂静,好似永远没有尽头”。
就在见面前的几秒,她还希望有人通知她,“顾福生出去了,忘了这一次的会晤”。但门终于开了,顾福生就在她的面前,于是“20年的光阴飞逝,心中如电如幻如梦”,她变回少女时的样子——“情怯依旧”。
三毛说,顾福生当年改变了她的命运。
时间推至20年前,她因跟着顾福生学画,走出自闭,恢复生机。
时间再推至10年前,她有个机会去见顾福生,但她在芝加哥的密歇根大道上,“来来回回地走,眼看约定的时间一分一秒在自己冻僵的步子下被踩掉”,最终还是没有去。只因他太重要,重要得她不知见面该说什么,重要得怕自己不够好——“没有成绩可以交代,两手空空”。
蒋韵在《心爱的树》中,写过类似的感受。
大先生的前妻梅巧和他的学生私奔后,过得并不好。最艰难时,大先生通过女儿接济梅巧——他始终爱她。
得知自己时日无多,大先生收拾书房,发现过去写的一封没发出的信:“梅:你这可恨的女人,你还好吧……”他握着它,手抖,泪流,站不住。犹豫再三,他通过女儿约梅巧见面。在此之前,梅巧也曾问过女儿关于大先生的情况。“她哽了一下,眼圈红了”,用伤感、温存的语调说:“你爸爸,他还好吧?”同样的五味杂陈和踌躇。
再相逢,一个对着恩人,一个对着爱人,却“愣愣地,你望我,我望你”。大先生打了几次火,终于给彼此都点上了烟,“跨过34年的岁月,来到一个车站,好像就是为了在一起抽一支烟”。
始于踌躇,终于无言的相见,恐怕都源于深刻、深沉的情感体验。
我想起我的偶像——一位女作家。我曾模仿她的笔调写作文,因她确定了高考志愿,多年后结婚,穿什么都照搬她描摹过的新娘。当我终于和她面对面聊天时,一瞬间,我忘了曾热烈地找过她,曾千方百计索取她的联系方式,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想哭。“只由衷地感激你美好如初。”后来,我写给她。
我想起我的一个女友,她认识了一位画家,并爱慕他。但画家给她信息、邮件,她从来不回。“其实也回过,只是删删写写,写写删删,永远没发出去。”
一次,画家邀她看画展,她没说去却去了。远远地,她看到画家,逃也似的飞快走到一边——如电视剧《李春天的春天》中,李春天每每撞到梁冰的情景。“见了他,我说什么?”从画展归来,女友惆怅地两手一摊。
我推开一扇踌躇的门,发现那人美好如昔;女友靠近却溜走,没推开那扇门,也没给自己失望的机会——我们都算幸运。
要知道,不幸的推门者比比皆是啊。
黄佟佟在《最爱的男子》中写到齐秦。一度,齐秦在台上唱《不必勉强》,问:“听到这首歌,你们是不是想起了初恋情人?”她哑着嗓子,几乎要冲口而出:“那不就是你吗!”但两见齐秦,接触到真实的偶像,让她幻灭。日后,在电视里看到有齐秦,她都会马上换台。
老舍在《微神》中写到初恋。他对初恋的回忆凝固在旧时门边的一双绿拖鞋上。他后来去找初恋,初恋已变成暗娼。他鼓足勇气,再去找初恋,初恋已睡在一口薄薄的棺材里——彻底幻灭。
我总想,最幸运的推门者是谁?
是那些挨着透明的门,无限接近,试图推开,却始终推不开的人吧。
如罗曼·罗兰。
“我来到波昂,贝多芬的故里。”
“我重新找到了贝多芬的影子和贝多芬的老朋友们……”
“在多雾的莱茵河畔,在那潮湿而灰色的四月天……我跪着,由贝多芬用强有力的手搀扶起来。”
他在《贝多芬传》的序言中如是说。
他没有见过贝多芬,却终生从贝多芬身上汲取力量。
(百合花摘自《中国青年报》2011年9月13日,图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寂寞又美好》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