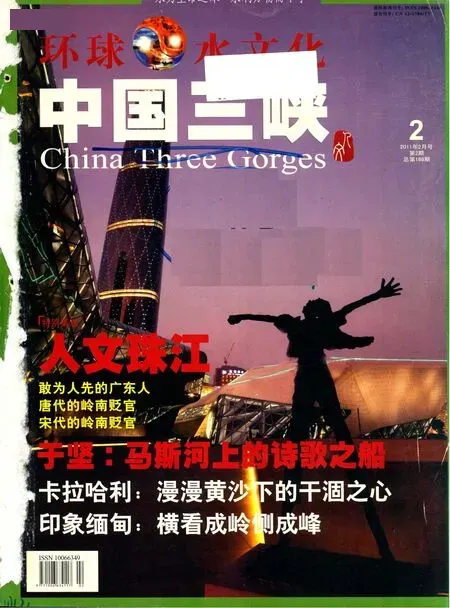印象缅甸:横看成岭侧成峰
文/于翔汉 编辑/任 红
同样的一件事物,如用外族的发音译成中文,便平添了一份浪漫与神秘。比如,香格里拉、马铃薯。
“我住江之头,你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彼此是亲戚,语言多同轨,团结而互助,和平力量伟。”这是1957年底,陈毅副总理所写《赠缅甸友人》的诗句。中国和缅甸是“胞波”之邦,两国人民有着传统友谊。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4年,周恩来总理就对缅甸进行了访问。他一生先后九次访问缅甸。
正是因为这种先入为主的好感,当我知道能随集团商务团队前往缅甸采访,心中便由衷地向往。朋友打趣说:“你去的可是政局有些不稳的第三世界国家,小心走失,被捉去砍甘蔗。”
萨尔温江,在想象中流淌
知道萨尔温江,是中学读书的事。这条在中国叫怒江、在缅甸叫萨尔温江的河流,曾经在我的想象中流淌。
缅甸河流密布,主要的河流有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钦敦江和湄公河,支流遍布全国。其中,伊洛瓦底江(独龙江)、萨尔温江(怒江)和湄公河(澜沧江)均发源于中国。
缅甸可利用水力发电潜力很大,据2006年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勘测,缅甸蕴藏水力的装机容量为1800万千瓦,而实际装机容量仅为120万千瓦。缅甸已将水电发展列为国家优先考虑投资的领域。
这也是我们此行的目的。集团将在缅甸萨尔温江投资修建水电站,此行便是与缅甸政府签订开发萨尔温江孟东水电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
从昆明乘机去缅甸仰光,大约需要4个多小时。当空姐告知我们飞机已在缅甸的上空,我透过舷窗俯视大地,一样的山川,一样的河流,但因为居住着不一样的族群,便诞生了不同的风土人情。从这种意义上讲,人类所居住地球,除地理差异外,更多的是人文所带来的差异。
现代工业文明,让我们在几个小时之内便可以抵达另一个国度曾经的首都。这种便捷,来自于人类的智慧,更来自于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的“恩赐”。不知道这样的“恩赐”是否会无限期地不需要“回报”,如果需要“回报”,那么,这种“回报”将会以何种方式达成。
心惊肉跳中的时光错乱
我们下榻在仰光SEDONA酒店,这是一家五星级的商务酒店,距机场仅3公里,距繁华的市中心,也只有2公里。
在通往酒店的路上,沿途随处可见佛塔,令人对这片有着“佛教之国”称谓的神圣土地肃然起敬。但最为令人惊异的,是来往于狭窄街道的各色公交车。

下:身着袈裟的僧侣,在缅甸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摄影/于翔汉

上:缅甸已将首都从仰光迁往内比都,新都未动,大金塔先行。图为缅甸在首都内比都建设的大金塔,除在形制上与仰光大金塔略有区别外,其他别无二致。摄影/于翔汉
条件最好的公交车,是那种在日本已经淘汰了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电影中经常可以看到的公交车。
而那种产于缅甸、车厢为绿色、车头保持货车形态的公交车较为普遍。这种车型流行于二战时期的欧洲。这种车的车厢很高,车门踏步仅有一级,足足有半米高,没有灵便的腿脚还真不方便。那位售票员大叔是吊在车尾踏板上的,真是难为了他。
奔跑在街道上更多的,是那种由破旧的中型货车或小型皮卡直接加个斗篷和车尾踏板的公交车。接我们的女孩告诉我,缅甸人称这种公交车为“傣纳”。小型的“傣纳”一般可以坐10人,大型的“傣纳”一般可以坐16人左右。但这显然满足不了乘客的需求,除去车里站着的人,挤不下的就吊在车厢外,更为夸张的是一辆从我们身边驶过的“傣纳”车顶上,居然坐了好几个人。
这样的场面,令人心惊肉跳,我特别为那些坐在上面的孩子们担心。不过,他们倒是谈笑风生,神态自若。
或许是对公交车过于关注了吧,直看得我眼花缭乱有头晕的感觉。好在这段路只有三公里。不过,就是这短短的三公里,也足以让人有一种时光错乱之感,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不,三十年代。那些街头驶过的各种车辆,实在像是从博物馆或者废旧车场里开出来的。
令人遗憾的是,我被告知不能拍照,因为正值大选的敏感时期,怕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入住的仰光SEDONA酒店——2010年6月温家宝总理访问缅甸仰光,就曾在此下榻。说是五星级,然而里面的设施实在陈旧,时下国内稍好些的县城宾馆也要比它讲究得多。酒店周围的一派热带风光,那种叫不出名字树冠却很大的树,将这座热带城市装扮得富有热带风情。
此刻,已开始日落。落日的余辉撒在宾馆边的湖泊上,让人一下子安静下来。
我们到缅甸之时,正赶上缅甸大选。在过去的20年里,这个偏隅一方的东南亚国家,因由军人政府统治无法实现民主选举而广受国际社会关注。更因为软禁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在西方社会声名狼藉。说来也巧,据说昂山素季软禁之所,就位于我们下榻宾馆边上的一池湖水中的一个小岛上。前些日子,一位美国大兵试图游过去与昂山素季会面而被拘禁。
在去缅甸的前一夜,凤凰卫视新闻报道说,缅泰交界发生冲突。画面上看,场面几近失控。然而,在仰光,在缅甸新的首都内比都,所到之处却一派祥和。

2010年12月6日,仰光,一对情侣坐在码头边看日落。 摄影/DrnGetty Images/CFP
漫步在仰光街市,触目所及的,是特色鲜明的缅文,再就是英文招牌。城区随处可见约有百年历史的英式建筑。它们仿佛在提醒人们,这个国家与英国的殖民关系。或许是这样的建筑太多的缘故,大都陈旧斑驳,布满历史的沧桑。而偶尔出现的新式建筑,反倒让人觉得有凤毛麟角之感。
或许与长期被英国殖民统治有关,街头小贩大多能用还算流畅的英语进行沟通。而街市上过往的人们悠闲而安详。从他们悠然的表情上,根本看不出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着一场世界为之侧目的变革。倒是街市上时不时看到有荷枪实弹的军人,在提醒着人们,这仍旧是个用枪杆子说话的国家。
在我们离开缅甸的第二天,昂山素季获得自由。当我在电视画面上看到昂山素季的支持者们在欢呼,心中五味杂陈。17年前,昂山素季失去自由之时,正值风华正茂,而今,曾经的秀发已见灰白,曾经年轻的脸已添沧桑。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相信缅甸军人政府会在选举后尝试改革,从而让政权逐渐走向民主化的道路。
当国内仍在为怒江上还是不上而纠缠不休时,其下流萨尔温江已开始了大规模的水电开发
转天下午,集团将在缅甸新的首都内比都,与缅甸政府签订开发萨尔温江孟东水电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中缅泰三国,将在萨尔温江投资修建东南亚最大水电站。
当国内某些环保人士纠结于开发怒江水电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是否会对生态造成破坏、是否会破坏“三江并流”自然景观等,其下游缅甸的萨尔温江,已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水电开发步伐。澜沧江下游湄公河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公交车在市区运行 摄影/Edu Bayer/CFP
怒江是全国最贫困,也是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里有世界级的水电资源,其可开发装机容量达4200万千瓦,为全国六大水电基地之一。自2003年起,围绕怒江水电开发的争论,至今不绝于耳,并成为环保与发展争议的标志。水电是清洁能源,这已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常识。有人说真理越辩越明,然而,八年的争论,却仿佛让人感觉真理距离我们越来越远:有人甚至质疑水电是否是清洁能源。争论声,八年便过去了。八年的时间,怒江的水依然奔腾,怒江的人民依旧贫穷。谁又会为这八年无休无止的争论所消耗的成本埋单呢?
缅甸政府对与中国、泰国联合开发萨尔温江水电项目高度重视。在正值大选这一敏感而关键时期,缅甸电力一部部长、电力二部部长、国家最高检察长、财税部部长、国民计划与经济发展部部长,悉数出席签字仪式。
缅甸第一电力部部长吴佐明在接受采访时说,缅甸立足于国内丰富的水力资源,正在进行多个水电项目的开发与建设。目前,与国外公司合作的水电开发总装机容量已达到3747万千瓦。
代表中方联合体签字的三峡集团副总经理毕亚雄介绍,孟东水电站库容约等于三峡电站库容,其优良的发电品质可以推动区域电网建设,是东南亚已有、在建和规划水电站中装机规模最大的水电站。毕亚雄说,将来孟东水电站所发电量,除满足缅甸本国需要外,剩余电量拟输往泰国等邻国。

身着民族服装的缅甸少女 摄影/于翔汉
对签字仪式,缅甸国家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给予高度重视。对此,用三峡集团董事长曹广晶的话说:“相对于海外对发展水电的态度和效果,国内对水电的认识需要重新定位。水电属可再生清洁能源,这是常识。”
缅甸孟东水电站开发项目将以BOT模式,由以三峡集团控股的泰、缅三国联合开发,规划装机约700万千瓦,预计投资额约100亿美元,建设工期为15年。
BOT是英文Build、Operate、Transfer的缩写,通常直译为“建设、经营、转让”。这种译法直截了当,但不能反映BOT的实质。所谓BOT,是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经营的一种方式,以政府和私人机构之间达成协议为前提,由政府向私人机构颁布特许,允许其在一定时期内筹集资金建设某一基础设施并管理和经营该设施及其相应的产品与服务。
作为一种投资与建设方式,近年来BOT广为发展中国家采用并取得一定的成功。追溯BOT,自出现至今已有至少300年的历史。有人说,BOT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引入了强有力的国家干预。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一方面,BOT项目的大部分经济行为都在市场上进行,政府以招标方式确定项目公司的做法本身也包含了竞争机制,这便能够保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另一方面,BOT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尽管BOT协议的执行全部由项目公司负责,但政府自始至终都拥有对该项目的控制权。
在飞机上鸟瞰缅甸这个国度,会让国内的房地产开发商看红眼:大片大片的稻田,大片大片的森林,而湖泊,则像串成串连成片的葫芦。这令人想起我们过去的江汉平原。说是过去,是说虽说仍有成片的稻田,却没了这许奇观般的广袤。而森林、湖泊,早已难觅踪影。那网状的河流,让事先“备过课”的我分不清,哪一条是萨尔温江,哪一条是伊洛瓦底江。只能空发感叹:曾经,我们也有“千湖之省”啊。
晚霞中的瑞德宫大金塔美轮美奂
早上,完成了对曹广晶董事长的专访,此次缅甸之行的工作,基本上可以告一段落。还余下近一天的时间,可以体会一下向往已久的缅甸大金塔和翡翠。
一个时期以来,翡翠在国内已被炒成了“天价”。即便是大部分在统计数据中“被中产”的“精英后备”们,对此也只能望尘莫及。实在愤不过,可以在心里暗自“呸”一声:不就是块石头吗?
在缅甸的街市,到处都是翡翠店。在此逛,不必为语言问题担心。因为店主、店员基本上都是华人。据说,在缅甸花上几万买一块货真价实的翡翠,带回国后,到玉器店可以看到,同样的货,会买上几十万。不过,这里有个语言陷阱,你总不会为了一块几万元钱的翡翠开个店,或到拍买行拍买。因此,不懂这里面的事情,还是姑且听之吧。

孔雀是缅甸歌舞中的永恒主题,与中国孔雀舞不同的是,雄孔雀在缅甸歌舞中也是主要角色。 摄影/于翔汉
店里的翡翠琳琅满目晶莹剔透。从几百元到上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人有个贱毛病,一旦有好的,就看不上相对不好的。可那好的又消费不起,那就闪人吧,不就是块石头吗?
玩不起物质,那就追求精神吧。缅甸是个佛教国家,有“千塔之国”的美誉。或大或小的佛塔,形制不一,颜色却是统一的,一律的明黄色。在缅甸,看佛塔,因为缅甸人信佛;在西方,看教堂,因为西方人信基督;在中国,看庙,因为中国人信祖宗。一千个中国人,是不是有一千个祖宗呢?
在缅甸,有超过80%的人信佛,身穿黄、橙红色袈裟的和尚和尼姑随处可见。在缅甸观光,佛塔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而其中最著名的佛塔,便是仰光瑞德宫大金塔。大金塔是缅甸的国家象征,也是仰光的城市标志。
瑞德宫大金塔,耸立于仰光市中心丁固德拉山岗上。瑞德宫大金塔始建于公元前588年,至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在缅甸百姓心中,大金塔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每逢月圆日或佛教节日,大金塔都有盛大的佛事活动。
香客信徒云集的瑞德宫大金塔,占地14英亩,由4座中塔和64座小塔组成,它们呈众星捧月状环绕在主塔周围。每座小塔的壁龛内,均供奉着大小不一的佛像。主塔和小塔上贴满金箔,仅主塔贴金就重达7吨多。大金塔主塔高110多米,从塔底至塔顶按坛台、云锣座、缘钵钟座、飞檐座、莲座、蕉包的次序层层砌高。塔顶由宝伞、风标和钻球组成,并镶嵌着无数的宝石翡翠,最顶端镶有一颗重达76克拉的钻石。
游览大金塔,需赤足游览以示对佛的虔诚。塔的壮观与诵经声,令人感受到宗教艺术的完美和宗教力量的神奇。
瑞德宫大金塔上下四周悬挂着一万多枚金银风铃,风吹铃动,十分悦耳。大金塔东、南、西、北四方建有四道正门,每门入口处均有造型独特的缅式狮身人面兽守护。
清晨,仰光的太阳从佛塔间升起,大金塔建筑群和着阳光,散发着金子般的光芒。在这样的早晨,虔诚的缅甸人开始了他们一天的生活。
傍晚,大金塔在布满晚霞的天际中凿出优美的轮廓。常常,在她的身后,是一轮火红的落日,她注视着大金塔,就这样静静地沉下去,这便是著名的“落日熔金”。不久,“落日熔金”又转成了鲜红的晚霞,天地间被晚霞的红色笼罩着。偶尔,会有鸟儿从塔间飞过。此刻,时光仿佛在这里停下匆忙的脚步,而人的心灵也变得愈加平静。
缅甸是一个电力不足的国家。每到夜晚,除了大金塔那样享有崇高地位的建筑可以安装上彩灯继续发光外,居民区的用电都为限时供应。缅甸人依旧习惯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对于他们来说,日落便意味着一天的终局。
佛教在缅甸流传一千多年的历史,曾被尊崇为国教。对佛的信仰和“佛化”的生活观念,渗入到每一位缅甸人的血液中。缅甸人的平和、淡然和单纯,常常让人有种感动,他们生活得简单而平和,不急不躁、积德行善、以求来世。
十八世纪中叶,仰光是仰光河畔的一个渔村,古称“大光”。1755年改名为“仰光”,意为“战争终止”。这是个饱经战争创伤的国度。
尽管缅甸仿佛离开世界经济发展轨道很多年,尽管政局仍在军人控制下的缅甸给人以时局不稳的印象,但在这个信佛的国度里拥有着国民包容、友善、乐观的天性,以及得天独厚的丰富资源,一旦寻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机制,缅甸一定会快速融入世界经济潮流。
——仰光:走向新街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