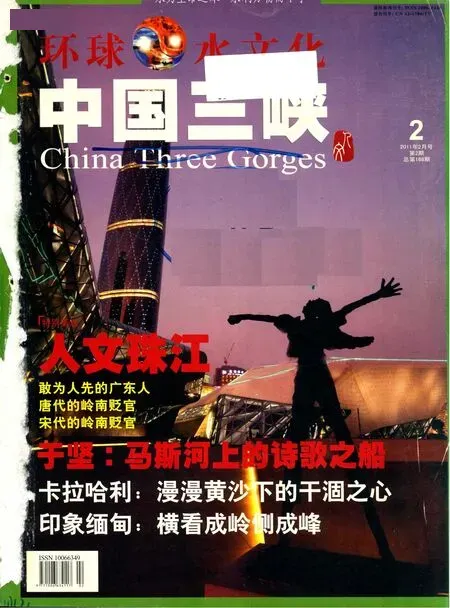于 坚 :马斯河上的诗歌之船
文/于 坚 编辑/任 红

1996年建成的伊拉斯谟斯大桥位于鹿特丹市中心,横跨马斯河,高139米,长800米,是鹿特丹新的标志性建筑。摄影/胡炜/CFP

于 坚:
1954年生于昆明。1984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1985年与韩东等人合办诗刊《他们》。1986年发表成名作《尚义街六号》。1994年长诗《O档案》被誉为当代汉语诗歌的一座里程碑。于坚是第三代诗歌的代表性诗人,曾获《人民文学》诗歌奖、《联合报》十四届诗歌奖、首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著有《棕皮手记》、《人间笔记》、《丽江后面》、《云南这边》、《老昆明》等。海外著作有《0档案》(法文版),《飞行》(西班牙语版),《作为事件的诗歌》(荷兰语版),《诗72首》(英文版),《元创造》(比利时版)。另有纪录片《碧色车站》(2004年参展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
摄影/都市时报/CFP
马斯河在流,旧时代的流速,前方是大海,船上坐着各国的四代诗人,年龄最大的是墨西哥的Sabines,生于1926。相貌威严的老人。最小的是新西兰的Ranger,13岁的美丽女孩。法国的大诗人Robaud坐在我后面,眺望河岸上的欧洲塔,就是他为我们念了印第安人的《云》,一首这次诗歌节每个人都记住了的诗。原籍南斯拉夫移居美国的诗人Simic,高贵而亲切,充满智慧而谦和,他处于船桅的阴影中,他的诗歌已经穿越两个大陆的语言。诗歌之船。没有斗争,没有先锋派和保守派,没有过招式的强词夺理的饶舌。这条船满载的是各种美丽生动的富于神韵的语言,它们是河流,滔滔不绝。世界小了,最后的辽阔在各种母语和它的诗人中间,在诗人们的舌头后面。
我仅仅是诗人,一个对母语的魅力的无可救药的迷狂者
世界的飞机场都是一样的,灰色的水泥建筑,尾蛇在城市的郊区,密封的玻璃墙,护照、海关、免税店……从一个机舱进入另一个机舱,从B747到A300;世界的机舱是一样的,安全带、空姐式的笑,犹如罐头中的罐头,吃着统一配制的食物,在预定的时间中,从出租车的铁门出来,进入机场的玻璃门,进入飞机的铝门,在曼谷机场的玻璃密封大厅中待六个小时,然后通过一个管道从另一个铝门进去,再从另一个铝门出来,钻进另一辆丰田汽车,停止的时候,你已经离开象形文字的故乡,站在嵌满字母的欧洲。
世界已经如此之小,如此缺乏细节,等我缓过神来,翻翻地图,才发现在十多个小时中,我已经飞越云南高原,越过澜沧江、湄公河平原,已经越过印度次大陆和中东、越过了地中海……越过了社会主义、联邦制、资本、议会、原教旨主义……如此辽阔的历史和空间,我看见了什么?金属的管道、电视屏幕上的好莱坞电影、小窗口外面没有温度的天空,像一位印第安的诗人写的那样“云,变了”。
世界已经变得如此之小,鹿特丹犹如欣欣向荣、高楼成群的昆明,公司、购物中心、水泥街道、汽车、茶色的玻璃摩天大楼,映出另一座写字楼。鹿特丹被称为荷兰的小曼哈顿。鹿特丹人并不喜欢这样,他们解释说,没有办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人的飞机炸毁了一切。
他们重建了鹿特丹。但昆明,经历了什么大战?令一个千年之城成为废墟。瞧啊,一座新城,水泥,玻璃,瓷砖,自动电梯,我几乎以为我是回到了昆明。世界确实小了,参加诗歌节的三十五位诗人,来自遥远的墨西哥、新西兰、来自非洲、伊拉克,来自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来自波黑,不同的语言,完全不同的对诗歌的理解,但几乎人人都会讲英语,英语已经成了通行世界的“普通话”,一个法国诗人,要进入世界,他得通过英语,一个拉丁诗人,他要进入世界,要通过英语。

停泊的海港,船只与桅杆。 摄影/CFP/CFP
于是生来讲英语的美国诗人在晚餐的时候,一边切面包,一边用母语问候所有的诗人,讲美国式的笑话。我们开始通过翻译交谈,关于美国你知道什么?我说惠特曼、弗罗斯特、基斯哈林、蓝调、阿什伯里、瓦尔登湖……关于中国你知道些什么?李白、杜甫、毛、北京。老天,要么是古代的中国,要么是革命的中国,他是否具备了解一个国家的常识?在革命之外,在古代之外,具有普遍性的是什么?他是否知道中国世界的啤酒瓶盖、锅烧肉、茶、生儿子以及体会日子中的诗意。随后他自然而然地,就像问今天为什么下雨那样通过翻译问我——一个只讲汉语,终身用汉语写作,并且是云南方言的中国诗人:你为什么不学英语?他并没有居高临下的口吻,他只是问问,问得那么自然,那么亲切。他的晚餐位于荷兰,他在另一类诗人的母语中,但他没有一秒种想过要学荷兰语。
我说:你为什么不学汉语。美国人耸耸肩,大概以为我太不国际化,太民族主义。不对,我只是诗人,我只是用汉语写作,我太专注它,太热爱它了,我没有工夫再去注意另一种语言,这令我落后于时代吗?这令我不能与世界接轨吗?如果是这样,我宁可在沉默中而落后。我仅仅是诗人,一个对母语的魅力的无可救药的迷狂者,如果不是由于这一点,我们干吗和他们坐在一起?这个世界上会讲英语的人多的是,用卡车装。我立即失去了与这位美国诗人谈话的兴趣。想起只说法语的萨特,如果来访者不会讲法语,他就放弃交谈,他不需要什么与世界的沟通,于是世界只得垂下来,聆听这个家伙说了些什么。

海鸥与少年 摄影/CFP/CFP
我对墨西哥的那位老诗人有好感,他一言不发,他的每一句话,都要经过翻译,即使他说的是仅仅是“No”,他保持着神秘的原声。我不太喜欢那位黑皮肤的诗人,他喋喋不休,“讲一种愚蠢的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的混合物”,讲纯正美式英语的诗人鄙夷地告诉我的说荷兰语的翻译。我奇怪,他以什么语作为诗人?

鹿特丹城市上空亮起数百道光束,美化了夜晚的马斯河。 摄影/UPPA/CFP
诗人是一条河流,一群诗人却是一群美丽的麋鹿
世界性的诗歌节,颇有些像中国文人的笔会,大家住在一个旅馆里,在旅馆的大堂聊天,握手。修长的诗人与笨拙的诗人、害羞的诗人与人见人爱的诗人,冷傲的诗人与喜欢合影的诗人。不谈诗,更不恭维别人的诗。这一点和中国一样。谈论尼德兰变化无常的天气。去同一饭店吃饭,喝红葡萄酒、咖啡和茶。在午后两点集合于码头,乘船游览马斯河。
马斯河从鹿特丹市中间穿过,两岸,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集装箱,红红绿绿。看不出河岸一词原在的含义。我们是另一种集装箱中的诗人,船上流通的自然是英语。但不久,富于外交效应的英语就被忘记了,诗人们回到各自的母语中,神秘而辽阔的沉默。
学生从入学学习中医伊始,就每日清晨利用30分钟时间诵读,感受经典的古韵,提升中医人的行为素养。期间的中医基础理论及中医诊断学学习中也会涉及《内经》原文的出处,由于每日诵读,自然会加深印象;当时学生不一定能够理解其义,只觉朗朗上口,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业的深入,自然会深入理解,铭记于心。这期间教师要注重在阅读方法上给予指导,培养学生阅读的兴趣,学期末可以以诵读比赛的形式激励学生,既可以作为形成性评价的一部分又丰富诵读的内涵。
法国诗人Tarkos坐在我旁边,我们通过翻译进行交谈。因为诗歌节的主题之一是法国诗歌的四代人。我不免问起他四代诗人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们之间相处得很好。他指的不是故意要相处得很好,而是为什么要有不好的关系。我们没有听到预料中的那种轻视、讥讽,或者压制与仇恨。算起来,中国也该有四代诗人的,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革命与批判。彼可取而代之。造反。唯我独尊。超越。“他过时了。”难道不是吗?是什么令中国的诗人们在十多年间就跑到了后现代,就打倒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和六十年代,新诗永远从新一代开始吗?
马斯河在流,旧时代的流速,前方是大海,船上坐着各国的四代诗人,年龄最大的是墨西哥的Sabines,生于1926。相貌威严的老人。最小的是新西兰的Ranger,13岁的美丽女孩。法国的大诗人Robaud坐在我后面,眺望河岸上的欧洲塔,就是他为我们念了印第安人的《云》,一首这次诗歌节每个人都记住了的诗。原籍南斯拉夫移居美国的诗人Simic,高贵而亲切,充满智慧而谦和,他处于船桅的阴影中,他的诗歌已经穿越两个大陆的语言。诗歌之船。没有斗争,没有先锋派和保守派,没有过招式的强词夺理的饶舌。什么是知识分子写作?让鱼去讨论这种令它们鳞壳掉光的问题吧。
这条船满载的是各种美丽生动的富于神韵的语言,它们是河流,滔滔不绝。世界小了,最后的辽阔在各种母语和它的诗人中间,在诗人们的舌头后面。每个诗人是一条河流,一群诗人却是一群美丽的麋鹿,高贵、雅致、灵敏,垂听一切的耳朵,洞察秋毫的视力。当此船经过时,钢铁和狮子,护照和制度,都变成了波浪的手。海鸥、忽明忽暗的太阳,照耀着黄色的诗人、黑色的诗人,白色的诗人。云,变了。
一位诗人像祭司那样,很轻地把这行被覆盖着的诗揭开
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创立于1970年。是荷兰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活动之一。诗歌节主要在诗人们中间具有影响,今年是第28届。它的经费三分之二来自荷兰政府,三分之一来自赞助。

变幻莫测的海天 摄影/Imago/CFP
国际诗歌节的常设工作人员只有四人。新任的主席泰加娜女士是通过报纸上招聘诗歌节主席的广告应聘的。她并非诗人,她以前是阿姆斯特丹一个文学组织的工作人员,她有丰富的文学活动组织经验。一个诗人可以在诗歌上德高望重,但并不保证他同时就有操作文学活动的能力,这一点,在我国往往搞错。
泰加娜31岁,她热爱诗歌和诗人,她愿意为诗歌的传播工作,她是一个风一般行走,清楚工作的所有细节,并决定一切的主席。诗歌节的会场在鹿特丹城市剧院,二楼的一个休息大厅是工作室,犹如一个指挥台,电脑、传真机、文件、连成一长排的写字台。诗歌节聘请了二十多人为它工作,这些人很多是志愿的,没有报酬,或只有很少的报酬。他们从四月份就开始工作,为了六月十四日至二十日的六天完美地进入诗歌。
泰加娜有许多研究各国诗歌的顾问,他们很多人都是翻译者。他们向她推荐诗人,然后她亲自阅读这些诗人的作品,并决定邀请谁,在邀请上,它的宗旨主要是邀请那些在荷兰尚不为人知的外国诗人。其实我可以把这一段略过不提,我可以省略所有细节,只说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诗歌节,让其中的暗示令某些整天在大使馆附近汲取“世界性灵感”以接轨的诗人们听了心痛,让读者模糊地以为参加这个诗歌节就是“接上了轨”,或者具有了国际影响。但事实仅仅是,有一到五个关心中国诗歌,并懂汉语的荷兰人喜欢我的诗歌,他们相信,可能还会有两百到五百个住在鹿特丹附近的荷兰人喜欢我的诗歌(一本诗集在荷兰最多可以印五百本左右),于是我接到了邀请。
诗歌节的会场经过精心的制作,富于诗意的暗示。诗歌节的标志是一根红色的羽毛。从门厅到舞台放置了很多废纸处理厂制造的巨大的废纸砖,在这些废纸做成的砖块中间,挂着所有诗人的照片。诗歌朗诵的舞台上也有一座废纸搭成的墙,后面则是幻灯片打出的一片荒原。放置麦克风的台子是一个角焊接的铁架,其中放着中国灯笼、牛仔裤、旧电话、玻璃瓶等什物。诗歌节的活动主要是诗歌朗诵,也有关于诗歌起源的讨论,关于某国诗歌的专题讨论以及诗歌谱成的歌曲的演唱,也出售各式各样诗集和印有诗句的圆领衫。

荷兰鹿特丹港口 摄影/ChinaFotoPress/CFP
活动有两个剧场,一个可容纳七百人,另一个可容纳一百五十人。主要的活动在大的剧场进行。活动每天下午都有,免费。主要的活动是在晚上,参加晚上的活动要买票,每张票是17.5盾,小孩或老人减价5个盾。休息大厅里放着一部电脑,里面储存着诗歌节的各种档案,包括诗人的档案,观众可以自由调阅。

海鸥在优雅的环境里繁衍生存,看上去很美。摄影/滨海之光/CFP
诗人受到公爵般的尊重和礼遇。每天晚上,城市剧院都挤满了人,珠光宝气、衣冠楚楚、鸡尾酒、葡萄酒、咖啡、老太太、青年、美妇人、男子、知识分子、教授、作家、中产阶级……在雷诺阿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那种文化沙龙似的场景。
诗人不是大众的讥讽对象,也不是大众的卡拉OK,更不是胁肩谄笑于御前的侍者,而是倍受尊崇的古老而新鲜的智慧。不是附庸风雅,不是施舍,不是好奇,不是对事件的渴望,也不是光临指导,纯粹的欣赏。尊重诗歌和诗人是一种常识,也是普遍的教养,已成传统的一部分。诗歌在这里从未有过类似我国的经验,一下是全民打油,一下又成了少数人自我神化、自我戏剧化的工具。
我习惯于在诗人和他们的批评家眼中被视为“非诗”,在正统眼中被视为“异端”,在人群中被视为穷人、自作多情者甚或精神病人,我亲耳听到过这样的话,“你们看,那边那个就是诗人,像不像神经病”,或者,在酒足饭饱之后,“我们这里有个诗人,站起来朗诵一首,啊!”在这种场合,所有的人彬彬有礼为诗人让路,要求你与他合影,拿着你的荷兰语版的诗集请求签名,那么崇敬地看着你,犹如看着误入人群的神使。我确实很陌生,有些受宠若惊。
我习惯了由于写诗而被人们嘲笑和轻视,我从不指望什么“挺住就意味着一切”,我指望的是别来烦我,让我自言自语吧。我从未想到,还有人会把把诗看成一种圣体,“所有的事物中都有一双眨着的眼睛”,诗歌节的一个活动,是在鹿特丹城市剧院的外面,在一群表情庄严的读者簇拥下,由一位诗人像祭司那样,很轻地把这行被覆盖着的诗揭开。
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它与人生、大地是一种亲和的关系
参加诗歌节的诗人都有半个小时的念诗的节目,诗歌节为此付给诗人报酬。我聆听了法国诗人Tarkos念他的诗,法语非常好听,戏剧化的音乐感。这不是由于他戏剧化的朗诵的结果,他仅仅是念了这首诗而已。是词的力量使他的念出现了戏剧性的起伏。朗诵总是虚假的,如果词本身没有说话。翻译告诉我,他念的诗叫做《牛奶》,其中说道,这个词,这个词撒谎,这个假词。我非常喜欢这首诗的言说方式。如果说真有什么可以接轨,我以为这就是接轨。这个世界已经被普遍地升华了,诗歌是一种穿越谎言回到常识的运动。
我的节目是在闭幕这一天。主要大厅坐着大约五百左右的听众。我站在台上,后面高悬一面屏幕,当我念时,我的诗的荷兰语译文会同步出现在屏幕上。下面鸦雀无声。他们指望我念些什么,朦胧而神秘的东方,孤芳自赏的佳人,一片净土,或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我知道中国当代的那些出口的诗歌已经给他们留下了这种印象。又来了一个愤世嫉俗的,绷着脸随时准备就义的。
我开始念,《啤酒瓶盖》。我坚信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它与人生、大地是一种亲和的关系,它不是为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也不是为了从世俗人生中向偶像升华被创造出来的。它的自然、朴素、亲切、温和、优雅、幽默感和人间化是普遍性的,可以被任何一种听觉感知。下面开始微笑,开始大笑,开始笑得前仰后合。我有重听的耳朵都听见了他们在笑。我知道我的诗歌已经生效,我为他们展示了一种仅仅需要常识就可以理解的生活,一种来自日常世界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幽默,这种幽默遍布世界,只要人们打开一瓶啤酒。我不敢说我的诗有多么好,但我敢说,我没有装神弄鬼,没有夸大其辞。看啊,在那里。如此而已。翻译告诉我,他听见有听众说,没想到中国人还有幽默感。是了,瞧瞧这个世纪,我们写下了多少苦大仇深的文字。
说话间,黑暗中伸过来一只出版商的有毛的手。“我们很欣赏您的诗,想出版您的诗集,如果同意的话,请与我们联系。这是名片。”我早已习惯出版社是不出版诗集的或者诗人必须自己掏钱求他们出版诗集的惯例,所以他说了两遍我才明白了他的意思。犹如忽然听见一位素昧平生的美女对我说她爱我,我一时语塞。
荷兰的白天无比漫长,晚上十点半了,天空还在亮着。城市剧院的外面是一个木板铺成的广场,对面是杜布伦音乐厅、剧院和电影院。周围有许多的咖啡店,来自世界各地的乐队在里面演奏。人们或听音乐,或看话剧,或在酒吧间里谈话,到处可以看到诗歌节的招贴,诗歌之风轻轻地从他们之间穿过,人们并不都去读诗,但他们感受到生活的诗意,他们也许不热爱,但他们尊重诗歌。
黑夜终于降临,云,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