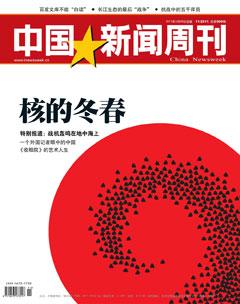随笔
不那么倾城之恋
每次灾难当前,我总是控制不住地会去回忆那些与此相关的小情小爱,虽然有点羞愧,但我总是安慰自己:因为有情有爱我们才能活下去的呀,无处可逃的灾难只会更加确认这一点吧。
知道日本地震的时候正好在看西尔维·库尔廷·德纳米的《黑暗时期三女哲》,序言里说:“要了解这个怒气冲冲的人世间,要和这个世间和解,无论如何都要爱这个世间,爱命运,爱世界。”
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坐在北京的办公室里,四五个小时里联系不上在四川的家人,明明窗户大开,我却总有某种致死的窒息感,一直在想我要变成孤儿了我要变成孤儿了我要变成孤儿了我不想活了⋯⋯在几乎喘不上一口气的时候,电话终于响了,而且真的是来自家乡的电话。那是一个很多很多年前喜欢过我的男同学,他急匆匆地在一片嘈杂中跟我报了平安,电话就断了。他后来告诉我,地震的时候他冲到大街上,然后开始不停拨电话。他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第一个电话会拨给我。这样荡气回肠的故事却并没有一个荡气回肠的结局,他四处相亲、谈恋爱,终于有一天,又是在一片嘈杂中,我再次接到电话,明显喝高了的他说:“我结婚啦!”
同样是在汶川地震中,因为太担心某个走入了映秀就音讯全无的人,我在深夜中假冒他的家人打电话去他的单位询问。没过几分钟有人回电过来,我支支吾吾地没法把谎话说圆,最后一头大汗仓皇失措地挂了电话,但是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听到了他平安的消息。过了两天,我自己也飞去了四川采访。坐在直升机上看着已成废墟的北川,漫天灰尘组成的白雾从城中升腾而起,我终于忍不住悄悄落下了眼泪。然后我在灾区就再也没有哭过,因为再没有什么比一座坍塌的城市,更能让人想象那其中上演的所有故事。
张爱玲坚持说,香港的陷落,不过是要成全她的白流苏和范柳原,因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然而大部分的我们,所拥有的故事都太平淡了,只是不那么倾城之恋。日本地震后的这几天,微博上总是有人说,和自己的那个人已经约好了,如果遇上灾难,就在哪里哪里等。有人约在共同工作的报社楼下,有人约在新光天地前那家星巴克,还有人说,我就在未名湖那条翻尾鱼的旁边等你,不见不散。但是我要跟我身边的人说,我不打算在任何地方等你,因为我们不要分散。
文/阿花
种菜记
老公的一个同事为人极讲究,不吃任何来路不明的东西,包括食堂的饭菜。因此雇了一户农民帮她种地养猪,所吃的蔬菜全部产自自家地里,猪也是吃自家粮食长大的,肉质可靠。
这件事情让我很感慨。一方面我觉得此人矫情,另一方面又有点羡慕人家有条件矫情——农夫,山泉,有点田,好奢侈啊。
去年春天,一直阴冷不见阳光,让人心情抑郁。我同事看了不少灾难片,预言北京将变成《后天》里的冰天雪地,或者沙漠气候。于是我和老公决定在自家的窗台和阳台上,培育些蔬菜,以防天灾人祸菜价暴涨。
我从早市买了小西红柿和黄瓜的种子,又从丝瓜瓤里抠出没掏完的丝瓜籽儿,开始了育苗工作。脸盆里种的是西红柿,一把种子撒下去,蒙上保鲜膜,等小苗出来,再把保鲜膜揭开。间苗间掉一些,寒风冻死过一些瘦弱的,剩下4棵还算有点模样的,就分别移到花盆里,放在南边窗台尽量向阳的地方。
丝瓜和黄瓜种子在湿棉布里捂一宿,待幼芽儿撑破外皮,就可以种到土里了。老公说丝瓜需要的肥料多,在花盆里种,楼层低光照也不足,秋天能吃到丝瓜的希望不大;黄瓜可能还靠谱点,但不管怎样,种花也是种,种菜也是种,看看叶子也好啊。
经过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等到初夏时,剩下两棵像样的黄瓜和一棵丝瓜,并且开始卷须了。老公便四处寻找长树枝之类,为它们搭架。黄瓜移到朝南的窗台上,纠缠着窗外的爬山虎一起生长,开过三四朵花,都是公花,好容易有两个结黄瓜纽儿的,却生长缓慢,过一个星期看看,还和以前一样大。东边窗台的丝瓜除了蓬蓬勃勃长叶子充当窗帘之外,连开花的意思都没有,却要每天浇水。
一个炎热的夏日,老公出差回来,说起在某地的饭馆吃过一份凉拌丝瓜秧,口味很不错——若是咱种的丝瓜不肯结果,就把它凉拌了吃掉吧。说着,他打开窗户一看,见证了奇迹发生的时刻:丝瓜干死了,叶片干到一碰就酥掉,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我无辜地说,可是我早上浇水的时候还好好的呀⋯⋯或许它知道了你这个念头,就马上决定不活了吧。
南窗外的黄瓜依旧在不紧不慢地生长,直到一个周日的下午,我突然听到轰的一声,仿佛有人从窗台上跳了下去。向外一看,窗外堆放的木板木棍等都不见了,黄瓜藤蔓断掉,花盆摔得稀烂,还殃及了旁边的西红柿。
等到秋天来临的时候,所有的蔬菜都死了,没有留下任何存在过的痕迹,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冬去春来,老公说,今年种点啥?我说,什么都不种了。遥望对岸的日本,管它什么菜,有命吃就好。
文/闫晗
女鬼的发型
我从小就爱看鬼片。我觉得鬼片是所有电影里最有想象力、最刺激的一种类型。不喜欢看的人当然也有理由反驳:音效大同小异,桥段千篇一律。他们说,鬼片连价值观都单一,拍来拍去就两种:怨鬼寻仇和人鬼情未了。我有位朋友就不爱看鬼片,他说他一想起电影里面的鬼都穿着清朝服装双手平举两腿挺直一蹦一蹦地走路,就觉得那简直不是鬼片而是搞笑片。对鬼片留有这种印象的人,恐怕已经有20多年没有看过鬼片了吧?
上世纪90年代录像带流行的时候,的确风行过一阵子清装鬼片。里面的鬼都留着长辫子,脸涂得白白的。那时的鬼片很正统,鬼就是鬼,道就是道,居其位,行其职。不像现在,后现代主义,也太解构了。大家段子化生存,无段子不欢。鬼不单只有厉鬼,也有欢喜鬼;捉鬼的道士也不光计算阴阳术数,还研究鬼之心理学。前阵子办公室里流行一个段子:老道士教导徒弟说,周日晚上12点过后,是鬼魂最活跃的时候,最为凶险不过。徒弟奇怪道,这可是阴阳上的讲究?老道士摇摇头,非也非也,实在是到周一,鬼才想上班。
其实鬼片是很需要文化共识的电影类型,不是凭空想象出来就能被人认可的。一说起韩国鬼,你的眼前就会浮现出穿着校服的高中女鬼;泰国的佛学基础好,所以他们的鬼片部部深奥有典故,只只鬼都有使命感;而越南因为有法国殖民的背景,他们的鬼喝咖啡画油画,品位不是一般的高。最厉害的当然是日本的鬼片,风格迥异,类型多元。不过他们的女鬼有一个共同特点,白色长袍黑色长发,看起来很文艺女青年的样子。经典的人物形象是《午夜凶铃》里的贞子。当年我被这部电影吓得不敢看电视不敢接电话,有人献计说,把电视放得高一点,让贞子一爬出来就摔死;或者,把电视面对墙放,让贞子一出来就撞墙。
不过,女鬼披长发似乎确实是鬼故事的标志性造型。长发的女鬼有多吓人?说是学校厕所有个老太太一天到晚在那拖地,镜头拉近拖把,原来是一个长发女人的头。又有一个故事说,一个男孩看见一个扎马尾的女孩向墙蹲着在哭,男孩问她怎么了,女孩回头,男孩看到的还是一根马尾辫。
有没有发现亚洲人特别相信鬼?美国人就无法领略个中奥妙。有个段子说中国人和美国人一起看电视,电视忽然自动关闭,中国人环顾屋子看看有没有什么灵异之象,美国人则直接去检查插头和电源。所以美国人拍电影水准一流,就是鬼片始终拍不好。他们拍过一个《惊声尖笑》的系列鬼片,里面的鬼块头大胆子小。好在美国人还算是知道,女鬼必须是长头发的。只是,作为一个资深的鬼片影迷,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一只波霸女鬼披着金色长波浪在喷水池边跑啊跑啊,水洒过来,音乐响起,慢动作,生生将一部鬼片拍成了洗发水广告。
文/上上签
宋徽宗的御梳
女人的头发最易引起男人的幻想。所以,如果她当着某男的面,解散、拨弄或梳理头发,就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生理上的挑逗。不论人或动物,在生理上都乐于接受抚摸。因而赠梳传情,也就有了一种性暗示:在某种程度上,它代替了手⋯⋯
古时“梳”和“篦”统称为“栉”,齿密为篦,齿疏为梳。篦子的用途,《清异录》解释为:“篦诚琐缕物也,然丈夫整鬓,妇人作眉,舍此无以代之,余名之曰鬓师眉匠。”也就是说,篦子是用来梳理胡子和眉毛的。真搞不清古人的长相和现代人有何差异,也许当时的美女眉毛更浓,需要用篦子梳理。那是不是男人都长着关羽、张飞一样的长胡与钢须?不可考。
梳篦是古代男人的随身之物。那时的男子可能普遍很“娘”,比起今天喜欢臭美的帅哥有过之而无不及。《挥麈后录》记载:宋徽宗某天忘记篦子,在站班时向王晋卿借篦子梳理胡须,因为王的篦子精致非常。后来王派高俅送徽宗一把相同的篦子,篦子送到时,徽宗正在踢球。结果高俅凭着踢球的雕虫小技,竟然平步登天,混成了一个堂堂的正部级领导。
篦子的另一用途是用来捉虱子。古时卫生条件一般,也没有各种品牌的洗发水。因此古籍里关于虱子的记载很多。《晋书》里说王猛见桓温,一边畅谈时政大事,一边伸手捉虱子,完全不顾在场者的心理感受。《墨客挥麈》说,王安石被神宗皇帝召见时,有只虱子从他的衣领悄悄爬出,一路蜿蜒,攀上胡须,王安石浑不知觉,“上顾而笑”。下朝后,王安石问同僚王禹玉,皇上笑啥,得知缘由后,忙命人搜寻该虱,准备一举歼灭。乖巧的王禹玉建议说:“此虱屡游相须,曾经御览,未可杀也,或曰放焉。”一代名相尚且如此,平常人等自不必说。难怪民间有言:老皇帝身上,也有三个御虱。宋代以后,典籍上关于虱子的记载,与上层人士有关的就很少了,大家认识到虱子是一种比较脏的寄生虫,不能再和风雅扯在一起。
《清异录》中描写洛阳少年崔瑜卿,多资,喜游冶,曾为娼妓玉润子造绿象牙五色梳,费钱近20万。出手如此阔绰,如同现在的有钱人为年轻情人二奶买钻石项链,买房买车。我知道买不起房的“80后”为此很郁闷,但想想世风自古如此,或可聊以自遣。
文/黄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