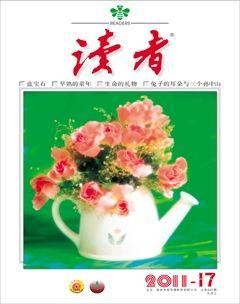树枝的疏忽
顾城
我喜古诗,不因文学史,不因人们的仰望,而在它的美丽,文字清简明润,如玉如天;在于它显示出的中国哲思,那一无言就在眼前,若张九龄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诗如禅,如顿悟——骤然风动云散,黑暗退隐,你看见万物万象,明媚自如。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气象柔和空阔,红豆生于南国,红豆生出南国,色空互化,得真意而得光明。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人相合于无形的造物本身,望树望山望月望水,凝望中自身也在幻化。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意味尽在神会,恰如释迦拿起一枝花而微笑。
“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诗人在一片化境中,有时更愿意回味为人的经验——“今夜谁家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这种解脱没有一丝对人世的轻蔑,反而更亲近了生活本身,似乎也传达出了释迦何以与人说法的秘密。
当然唐宋诗词并非一片静水,其中也有直流千尺,烽火三月,胡天飞雪的动荡;也有举杯邀月,分麾下炙,西窗剪烛的风情;也有凄凄惨惨戚戚的悲哀,或衢州人食人的大呼。但在这一切之中,你都可以感到那个明丽生动的主线,那个依据,就像播下万壑水声的无声冰雪。多姿多态的希腊神像也曾透出同一寂静。
生逢末世的李煜,似同中古诗人相悖,虽也知佛,更多时候却生活在女子中间,只是受了惊吓,才退进自己明艳的梦里。这种方式多少有点天真烂漫,他不做如是达观,涂抹近在眼前的生死,反而移情于梦,做了一个“流水落花”之后的“天上人间”。
这种任性,李煜死后,便失了踪影。至近代,诗的无言索性成了多言怪异的趣话,长篇小品,瀚瀚可观,实际上却是回到无可奈何的感喟中去了。这种情境一直延续到《红楼梦》的出现。
中国有两次人间天国,陶渊明做了个人物模糊的桃花源,曹雪芹做了个《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大观园洞开一扇,就补足了近代诗中的无灵缺欠,人们才知道,那无处不在的春江明月,已化做清洁的女儿世界了。
我看见月亮又落进盆里了,就小心地端进屋子,结果月亮没有了,换成了灯。我试了很多很多次,终于感到了厌倦,不是对失去,而是对获得。这时心里倒常常出现了月亮。
从来就不乏奔月、盗火的人,说明有一个一直的黑暗——恰如“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恰如飞蛾扑火,它们的感人不是因为它们的成功,而是因为它们绝望努力的本身成为一个瞬间的永恒光明。
希腊有一个寓言,说一个男孩爱上了自己的影子,最后变成了水仙花。面对中国悠远的诗境,我看不见时间、评注、那么多黯淡繁琐的生活,只看见那片光自在圆满。
我唯一的所得是静静地看着,而不去捕捞它们。
树枝因疏忽
使我得见月
而月不见我
亦不见树枝
(罗倩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树枝的疏忽》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