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阔的视野与向经典的回归
□刘 波
前几年,不止一次遇到有人如此规劝我:你应该多向你身边的人学习。我指的是诗歌,尤其是网络诗歌,以及其它与诗歌相关的网络言论。最初,我也很认真地听取了这些好心人的建议,将目光从那些老诗人的作品上收回来,大量阅读网络诗人的作品,以虚心的态度向他们学习。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自己的诗歌视野并没有因此变得开阔,相反越来越狭窄,相应地,我对诗歌的审美也开始变得缺乏标准。这是我向网络诗歌与言论学习的结果,以至于我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写作与展开批评。在遍地开花的网络上,一个人很容易失去诗歌写作与鉴赏的方向感。在此,我并非排斥网络这个重要的载体,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清楚:这个载体在为新世纪诗歌带来繁荣的同时,也为诗歌的普遍粗鄙化带来了它适宜的环境。读多了网络诗歌,对我们的审美也会产生冲击,也即鉴赏的标准也可能会因此趋于混乱。
我也读过很多“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鲁迅先生说,当年一些年轻人看多了“广告式批评的符咒”所哄抬出来的小说后,“胸口痒痒的,好像要呕吐。”(1)我曾与当时的年轻人一样,从网上读到了太多的分行文字后,不但没有感受到诗歌美的因子在心灵深处的颤动,相反,脑海里却增加了一种诗歌更加荒芜的印象。阅读了一些作品,没有一种美感的促动,甚至连诗歌中常有的“丑”与“恶”的促动都没有。一切显得平淡无奇,毫无力量。我想,诗歌在网络里失去了经典性,连一些传统诗人们都在朝着平庸的诗歌“嘉年华”狂欢场景投去他们艳羡的目光。
经典的力量在我们的诗歌视野里已经变得遥不可及了,但当我们重新回过头来准备将经典纳入到自己的诗歌视野中时,一切是否为时已晚?!经典诗歌之所以能打动人心,就在于它们所透露出来的一种开阔的气息,一种永恒的美学,一种普适的价值,这种气息、美学和价值接近于人类的终极理想。
当下,不是新诗“颂歌大合唱”的时代,也不是诗歌混乱得毫无理性的时代,新诗也已经不是简单的“时代传声筒”的方式。但就在这样的中庸形式下,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新诗逐渐丧失了它的经典性。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狂热地背诵《相信未来》、《致橡树》、《神女峰》、《回答》、《一代人》、《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口耳相传的作品了。除了海子这个特殊的诗歌烈士之外,而稍后于坚的《尚义街六号》、《0档案》、韩东的《有关大雁塔》、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翟永明的《女人组诗》、西川的《死豹》、杨黎的《冷风景》、李亚伟的《中文系》和伊沙的《结结巴巴》、《饿死诗人》等,只是在诗歌圈子里有一定影响,而越过这个圈子,它们的辐射区域也只是占了文学界很少的部分。到了后来,在极端个人化风格的诗歌写作上,先锋派人士层出不穷,年轻人完全可以拿诗歌当游戏,进行语言的冒险与感官的刺激。而到了新世纪,网络诗人们似乎又重新找回了自我,并进行大面积的实验写作,口语与玄学并驾齐驱,让诗歌又开始朝繁荣的道路上豪迈地挺进。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想想,诗歌果真又像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样繁荣如初了吗?“新世代”、“中间代”、“第三条道路”等命名标示着诗歌又有流派和团体了,连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都成了现代房地产商们推销楼盘的广告词。面对此情此景,有人不免要问:诗歌都进入寻常百姓家了,难道还不算是繁荣吗?我不得不说:这并非诗歌真正的繁荣,很可能是它式微的回光返照,表象的繁荣掩饰不了内里的虚假。当下,诗歌成了一次性消费的文字游戏,再也不像那些经典一样被人们传诵。诗人们不再敢以文化精英自居了,以前的那种话语权也旁落非诗歌人士之手,风光不再的朦胧诗人与“第三代”诗人们聚集在一起,总会有一些文化风水轮流转的惺惺相惜之感,而又无尽地叹息后来者们将诗歌与语言糟蹋得只剩下了一具空空的躯壳,精神、内涵与力量等价值性元素都部分或全面被丢失了。如今看来,重建诗歌精神的重担,似乎仍然落在了这些对诗歌仍存希望的经典诗人们身上。经历过诗歌狂热时期的诗人们,为什么要不懈地去寻求诗歌精神,去挽回诗歌式微的局面,因为他们知道:在语言和价值被糟践的时代,需要用诗歌去拯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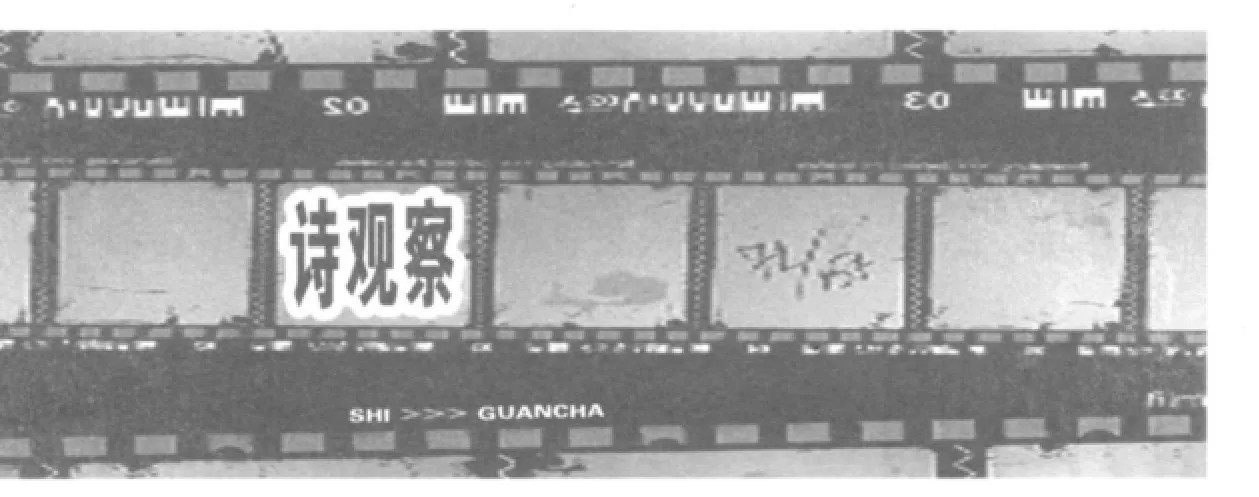
在网络上,对于很多读者来说,诗歌成了一次性消费品,而对于诗人写作来说,诗歌同样也成了流水线上的快速产品。网络在线写诗,短时间完成,瞬间被阅读,也瞬间遭到遗忘,连诗人自己可能都记不清了。诗歌源于人心,也能滥于人心。要想挽救语言之精华的诗歌不再堕落成为一次性消费的专栏文字,我们只有重新回到经典,重新将诗歌纳入到人性内部最为隐秘的部分。诗歌首先必须关乎语言,但又不仅仅只关乎语言,它还必须有一种情感和思想的本真渗透其中。所以我们不但要在诗歌中注入人性化的成分,而且还得向经典学习,只有如此,诗人们的视野才会开阔。否则,诗歌在网络上的最终结局,就是走向更为狭隘的道路,最后直至走进死胡同。
诗歌走向大众,进入日常与当下,这是一个方向,但这并不代表诗歌必须书写柴米油盐与琐碎的人情世故,它应该描绘人类隐秘的孤独,被失败感所包围的情绪,以及被隔绝的灵魂状态,还有情感与心灵之外人类精神生活中那些暧昧的部分。古今中外诗歌史上的优秀之作无不如此,它们都书写了人类情感状态下的普遍共鸣。它们是批判的,也是包容的,它们是纯粹的,也是澄明的。所以,我一直对杨炼在其组诗《诺日朗》前面关于“诗的威力和内容”的阐释情有独钟,他真实地表达了诗歌永恒存在的立场:“诗的威力和内在生命来自对人类复杂经验的聚合。把握真实和变革语言、批判精神和自我更新,体现诗人的才能。传统不是一条河,它活在我们对自己的铸造中。加入传统要付出艰巨的劳动,但谁放弃这个努力就等于放弃了自身存在的前提。”(2)对于诗歌,我们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还要主动地创新,这是一个有着内在生命质量的诗人所应具有的情怀和责任。
在网络与纸媒发达的时代,一些人越来越倾向于用诗歌的多元化倾向,去理解与宽容作践诗歌的行为。宽容并非无奈之举,它也不是诗歌被迫生存下去的前提。很多时候,恰恰无条件的宽容,会导致诗歌创造倒退得更加迅疾,因为它离我们理想中的诗歌之美相差远了,甚至离我们曾经的经典诗歌有了一段遥不可及的距离。这一责任,也不应该仅仅归咎于诗歌大环境的不景气,而网络和一些诗歌杂志也应负有责任,它们将诗歌的门槛降低到了谁都可以进出的程度。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诗人内心残存的那份对诗歌的虔诚已经极端功利化了,一颗功利化的诗歌之心随着滚滚而来的文化游戏狂潮被卷进了泛滥的商业化物质深渊,再想脱身做一个深刻的诗人,已基本没有可能;浮躁的心态已经包围了诗人从外至内的每一层肉身,包括灵魂。
经典的诗歌外表干净而纯粹,这是进入人们阅读视野的首要前提,但是在这种干净而纯粹的表象之下,诗歌的内在肌质应透出一种对人性的指涉,也昭示出一种强大的语言与精神力量,这两者的结合使得优秀诗歌成为人们阅读共鸣的基础。任何一首经典之作,都不会拒绝让人进入,如果说里尔克的《杜依诺哀歌》拒绝让中国读者进入的话,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里尔克所在国家的文化背景与中国人的文化习俗或阅读习惯不同所造成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来自翻译语言的晦涩,这就涉及到翻译者的水准了,此点困惑见仁见智。但是,我们不能就由此否认《杜依诺哀歌》的优秀,诗里所传达出的悲悯与开阔的气息深具经典的力量。尤其是那种强烈的历史厚重感与深远的忧患性都铭刻在每一句诗歌中,它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诗歌难度的范本。而在我们当下的诗歌创作中,几乎很少看到这种关于人类灵魂深处的孤独、忧伤以及历史边缘性的抒写,即使有一些具有悲悯感的诗人正在作这方面的努力,他们也只是在“现实主义的叙事”基础上加进些虚幻的经验情感,这种依仿经典营造出来的悲剧色彩,因为没有诗人生命质量的体验,也显得做作与虚假。它们或许会引得其他诗人读者一时的共鸣,但是由于缺乏原创性,瞬间的共鸣之后就是无情的抛弃。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全民写诗是不正常的,而一个国家没有诗人与读诗者,也是不正常的。诗歌必须在它应该获得的空间里生存,它的自由性就在于诗人对其的把握程度。向经典诗人的学习与诗歌视野的开阔,并非要将诗歌的形式单一化与模式化了,而恰恰是需要以开放的姿态来抒写人类的情感现实。一旦撇开了诗歌精神,在面对“所指”时绕道而行,或者对词语所呈现出来的意义视而不见,甚至故意抛弃,由此造成所谓的理性的、零度的描述场景,这种冷漠的书写已经脱离了人性的渗透,甚至脱离了人本身,朝着极端物化的方向靠近,诗歌的生命意志也就在此停滞了。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能正是对一种关于人的真正的诗歌精神的背叛。
关于“人”的书写一旦呈现出了时间的意义,要求趋于永恒,它就要“穿过并把握时代——是穿过,而不是跳过”。(3)经典诗歌的特质是需要穿越时代,并将这种书写方式(语言)与精神留存于这个时代,以便延传下去,直至永恒。经典诗人都有这样为永恒而书写的理想,并在朝这个理想努力,因此,诗人全部的精神内核,都体现于书写的过程以及最后所到达的美感和力量中了。当然,诗人在具备了开放的姿态与开阔的视野的同时,还必须学习经典诗人如何“穿过时代的意识”。阅读经典诗歌,受经典诗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与自我心灵和时代精神的对话一旦成为可能,一个诗人至少不会在繁复驳杂的诗歌丛林里迷失方向。因为有着经典诗人诗作的影响和指引,他们不再漠视或脱离人性与时代,而是紧紧地贴着人、语言和这个世界最基本的关系,以此呈现一种厚重感和力量感。这是向经典诗人与诗歌学习最好的路径,如果只是一味地模仿,而没有发展与创新,这一切都可能成为无聊的语言游戏,终将被淘汰。
以当前网络上的态势来看,诗歌的深度书写正遭遇困境,一些口水的分行文字同样被纳入到了诗歌的范畴,但它们缺少或没有诗味。网络分行文字,并不是简洁美学所要求和提倡的诗歌形式体现,而是这样的文字剔除了人的想像与复杂的情感因素,希望在形式主义上一步到位,中间省略了真正的情感与思想创造过程。经典诗人奥登在《论写作》中对这种偷工减料的写作做过如此评价:“如果诗歌可以在迷离恍惚之际一挥而就,其中根本没有诗人自觉的劳动,那么,写诗将是一件枯燥乏味甚至令人不快的活动,只有金钱与社会地位这样的物质报酬才能诱使一个人来写诗了。”(4)而很多人可能正是冲着这种功利目的在电脑上随意涂鸦。而还有一些人则纯粹出于发泄的诉求,不假思考地在网上粘贴他或口水或散文化的分行文字,毫无节制,一味地追求见面率。出于这两种目的,一些网络诗人似乎都意识不到诗歌写作应该是一件有难度的事情,相反,他们还在随心所欲的路上乐此不疲,然而,最终的结果是:他们中坚持到最后的人不多。很多曾经在网络上活跃的诗人,现在都沉寂了,有的不写诗而转向其它文体了,还有的则如昙花一现般消失于网络,从此不再现身。
虚拟的网络世界让诗歌也变得虚幻,同时还丧失了诗歌写作的力度和美感,粗鄙化成为我们阅读网络诗歌以及一些从网络上被选入纸刊的诗歌最深的印象,但对此作自觉反省的人并不多。这一切的后果,并非全都要归罪于网络,而应该由具有判断力的诗人们自己来承担。他们完全还有重新拯救诗歌的能力,重新让那些经典之作回归我们的视野,重新恢复诗歌写作的难度,重新建立真正具有时代感的诗歌精神,让网络这些外在因素对诗歌的影响变得更小,从而还原诗歌写作真实的、人性化的状态。
注释:
(1)鲁迅《我们要批评家》,《鲁迅全集》第4卷,第2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舒婷等《致橡树》,第178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3)[德]保罗·策兰《保罗·策兰诗文选》,第177页,王家新、芮虎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4)奥登《论写作》,载《准则与尺度》,第296页,潞潞主编,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
- 诗选刊的其它文章
- HUAYU话语·批评精神,是诗的必要条件
- 生活的别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