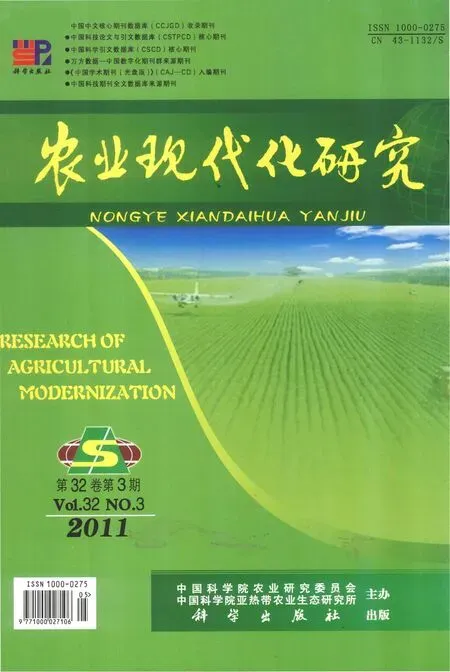新形势下新疆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类型与扶贫对策
朱金鹤,崔登峰,2
(1.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石河子832003;2.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3)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5年5月指出:扶贫开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历史任务,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201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新形势下新疆工作的目标任务是到2015年新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和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达到西部平均水平,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由于自然、历史、地理和政策等方面原因,新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新疆要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重点在农村贫困地区,难点在国家级贫困县。新疆国家级贫困县是新疆贫困人口最多、最集中的区域,居民收入水平更低、城乡收入差距更大,仍有较多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此外,这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县级财政收支差距大,居民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较低,是实现以上目标任务最为艰巨的地区。因此,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的新疆,在跨越式发展、西部大开发新阶段、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新时期,扎实、稳健地推进国家级贫困县的扶贫开发,不仅关系到“稳疆兴疆、富民固边”的大局,对于新疆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和谐社会都显得非常迫切和必要。
1 国家级贫困县的确定与新疆国家级贫困县的分布
1.1 国家级贫困县的确定
1986年中央政府第一次确定了国家级贫困县标准:以县为单位,1985年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50元的县和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00元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对民主革命时期作出过重大贡献、在海内外有较大影响的老区县,给予重点照顾,放宽到年人均纯收入300元。1994年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时,中央政府重新调整了国家级贫困县的标准。具体标准是,以县为单位,凡是1992年年人均纯收入低于400元的县全部纳入国家级贫困县扶持范围,凡是1992年年人均纯收入高于700元的原国家级贫困县,一律退出国家扶持范围。重点县主要在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范围内确定,确定重点县的主要依据是:贫困人口数量、农民收入水平、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以及扶贫开发工作情况,适当兼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财政收人等综合指标[1]。根据这个标准,列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扶贫开发任务重、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国家级贫困县共有592个,分布在21个省区市,涵盖了全国72%以上的农村贫困人口。国家级贫困县数量较多的省区是:云南(73个)、陕西(50个)、贵州(48个)、四川(43个)、甘肃(41个),新疆被列入的国家级贫困县的数量为27个;数量较少的省区是:广东(3个)、浙江(3个)、吉林(5个)、海南(5个)、西藏(5个)。从集中连片的角度看,这些贫困县主要分布在18个贫困地区,显示出国家级贫困县的确定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1.2 新疆国家级贫困县的分布
目前,新疆有30个贫困县,其中自治区扶贫开发重点县3个,国家级贫困县27个,重点乡(镇)276个、重点村3607个;新疆国家级贫困县的数量占新疆县(市)总数(91个)的29.67%,其中有17个是边境贫困县,所占比例为62.96%(表1)。新疆国家级贫困县分布范围较广,涉及地域较大,情况既不均匀,也不平衡,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克孜勒苏州的国家级贫困县个数明显较多,占新疆国家级贫困县总数的70%以上;同时也说明新疆国家级贫困县绝大多数都分布在南疆三地州。

表1 新疆国家级贫困县分布情况
2 新疆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现状
2.1 贫困率与恩格尔系数指标分析
贫困率指标反映一个区域中贫困户所占的比重。贫困率指标的计算公式为:贫困率(%)=总贫困户数/总户数[2]。截至2OO8年年末,新疆农村总户数约230万户,27个国家级贫困县总贫困户数约100万户,贫困率约43.50%,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左右,说明新疆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率较高。
恩格尔系数也是常用的衡量贫困程度的指标。通常恩格尔系数与农民生活水平有以下关系,恩格尔系数>59%为绝对贫困,恩格尔系数处于50%-59%之间为勉强度日,数值介于40%-50%为小康水平,数值在20%-40%之间为富裕阶段,当恩格尔系数<20%时为最富裕。2OO8年,27个国家级贫困县中恩格尔系数大于59%的县(市)有7个,恩格尔系数在50%-59%之间的有6个,在40%-50%之间的有11个,只有3个县在20%-40%。2009年,新疆国家级贫困县的恩格尔系数为52.52%,可见有约一半的贫困县的人口处于勉强度日或绝对贫困状态,生活资料匮乏,基本生活缺少保障,生存受到一定威胁。
2.2 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新疆国家级贫困县经济总量较小,经济实力较弱。2009年,新疆国家级贫困县总人口577.69万人,占全疆总人口的比重为26.76%,但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为全疆国民生产总值的8.96%。27个新疆国家级贫困县的GDP总量均低于乌鲁木齐市、伊犁州、巴州、克拉玛依市和昌吉州;新疆国家级贫困县第一、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7.78%、21.32%和40.90%,与新疆的总体情况以及乌鲁木齐、伊犁州、巴州、克拉玛依市和昌吉州等地区相比,产业结构明显很不合理,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偏高,分别比新疆、乌鲁木齐市和巴州高19.98、36.25、21.78个百分点;二产所占比重分别比新疆、乌鲁木齐市和伊犁州、昌吉州低23.78、21.61、13.94、18.08个百分点(表2),如果与巴州和克拉玛依市相比差距就更为悬殊。通过对比可知,新疆国家级贫困县在主要国民经济总量指标方面较为落后,产业结构存在明显不合理现象,从而也使当地扶贫开发的难度增加。

表2 2009年新疆国家级贫困县经济指标比较(单位:亿元,%)
从人均指标落后程度来看,2009年,新疆国家级贫困县的人均农林牧渔业产值5018.95元,仅相当于新疆人均农林牧渔业产值的82.97%;2009年,新疆国家级贫困县的人均GDP远低于全国及全疆平均水平,为6634.49元,仅相当于全国人均GDP的26.34%和新疆人均GDP的33.27%;其中墨玉县人均GDP最低(3254元),只相当于新疆国家级贫困县人均GDP的49.05%。2009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新疆农民人均纯收入3883元,而新疆国家级贫困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810.07元,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和新疆平均水平的54.53%与72.37%;新疆国家级贫困县中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的三个县分别是阿合奇县、阿克陶县和乌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只有1482元、1615元和1630元。
2.3 财政收支指标分析
新疆国家级贫困县无一例外均出现高额赤字,财政不堪重负,收支矛盾极为突出;县级财政支出85%以上靠上级财政补助,对上级财政有着极强的依赖性。2009年,新疆27个国家级贫困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人15.41亿元,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达207.58亿元,相当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人的13.47倍,财政赤字192.18亿元,财政自给率平均只有7.42%,分别比2004年和2007年减少了2.96和6.45个百分点。财政自给率达到10%的只有6个县,尼勒克县财政自给率最高为20.13%;9个县的财政自给率低于5%,分别是柯坪、策勒、于田、墨玉、疏附、阿合奇、岳普湖、民丰、吉木乃,其中柯坪县的财政自给率最低,仅为1.78%(表3)。新疆国家级贫困县财政极为困难的状况具有普遍性、延续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县级财政资金极端匮乏,长期处于赤字状态,使得贫困县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公共基础设施、科教文卫、社会福利与优待抚恤事业严重滞后。

表3 2009年新疆国家级贫困县财政收支状况(单位:万元,%)
3 新疆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类型及原因
关于贫困产生的原因,经济学家纳克斯最早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的原因是“资本缺乏”,舒尔茨认为贫困的主要根源在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刘易斯则提出贫困是保守落后的亚文化在代际之间传递,而以研究饥荒和贫困问题著称的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的根源是基本能力的剥夺和机会的丧失,世界银行在《千年发展报告》中提出,贫困原因是某些个体或社会群体脆弱性高,在遭遇风险时极易导致财富损失或生活质量下降到某一社会认可的水平之下。新疆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是人力资本水平低下、社会文化落后和制度缺失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恶性循环,贫困原因既有外部客观性致贫因素,也有内部主观性致贫因素;既有历史、现实与人文因素,又有自然和生态等原发性因素;综合来看,本文将新疆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类型及原因划分为以下几种:
3.1 生态贫困
新疆国家级贫困县都位于生态环境极度脆弱和恶劣的地区,27个国家级贫困县有21个位于南疆塔里木盆地西南缘,呈现出集中连片的分布态势。例如表1中的和田、喀什和克孜勒苏州的南疆19个贫困县,有的紧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有的位于帕米尔高原,全都是新疆生态环境最为恶劣的地区;北疆和东疆有6个国家级贫困县呈点状分布在阿勒泰、塔城、伊犁和哈密地区,都处在天山、阿尔泰山脉的高寒山区,海拔高、冬季寒冷期长,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自然灾害频繁,春旱、夏洪、地震、风灾、雪灾、沙尘暴灾害交替发生,如疏勒县和伽师县耕地盐碱面积分别达89.50%和91.20%,并且盐碱化程度在加剧;英吉沙县土壤贫瘠,风沙、盐碱危害严重,春寒、干热风、霜冻、冰雹、沙尘暴等各种灾害连年发生。贫困与生态环境退化的恶性循环是造成贫困地区经济社会非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致使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矛盾更为尖锐。
3.2 地域贫困
新疆的国家级贫困县大多处于偏远地带,远离大中城市,如南疆地处888.50 km边境线的塔什库尔干自治县,距省会乌鲁木齐达1765 km[3];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复杂和封闭性的影响,造成交通不便、信息交流不畅、基础设施落后,不仅制约了人口的适度集中,使市场信息、资金、技术、人才等现代要素很难辐射到此,造成经济活动成本偏高,经济发展明显滞后,扶贫开发成本高、难度大。自然条件、地理区位和基础设施的恶劣状况,成为影响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直接因素,并最终制约了新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形成整体地域性贫困状态并加剧了这种贫困的自我维系。
3.3 民族贫困
新疆少数民族的分布与贫困人口的分布在地域特征上的吻合程度较高,国家级贫困县多为少数民族人口集中地区。2009年,新疆27个国家级贫困县中少数民族人口536.15万人,占新疆国家级贫困县总人口577.69万人的92.81%,特别是和田、皮山、洛浦、策勒、于田、疏附、英吉沙、伽师8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少数民族人口比重都超过了98%。
3.4 文化教育贫困
新疆国家级贫困县文盲率高于全疆平均水平,并且往往是科盲、文盲、法盲集中之地。2008年,新疆国家级贫困县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有7.29年,文盲半文盲所占比例为7.90%,小学占比43.90%,初中占比38.90%,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例只有9.30%;2009年,新疆国家级贫困县的劳动力仅有40.90%受过教育培训,用于学校及技术培训的费用在当年当年使用的5961.60万元扶贫资金总额中仅占2.56%。劳动力资源的教育贫困既成为影响他们掌握农业技术、应对市场风险、提高生产技术含量的主要制约因素,又成为影响其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的主要障碍,反而将形成“低水平教育-贫困-低水平教育”这一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同时,长期的物质贫困和文化教育落后容易导致精神贫困,主要表现为文化匮乏、因循守旧、安土重迁、懒散怠惰、自甘落后、乐于贫穷,不仅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和就业空间的选择,还阻碍了文明乡风的形成。
3.5 市场竞争引致性贫困
市场经济是讲求效率的“竞争经济”和“强者经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区域在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贫困地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竞争基础和起点的不平等会导致其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使得贫困人口的利益被忽视、被伤害。不仅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人力和技术,而贫困地区稀缺的矿产、资金、人才等资源向发达地区流动,这种由资源占有不平衡所带来的贫困状况日趋严重,可能加剧贫困人口的边缘化倾向。同时,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困人口生存环境也日趋恶化。新疆国家级贫困县经济最明显的特征是以农业为主的单一产业结构,在大农业中又偏重于种植业,种植业中又以某一种农产品为主;非农业产业发展很不充分,劳动力价格低廉且大量闲置,致使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农业技术的推广与应用面临较大阻力,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落后,造成市场竞争引致性贫困。
3.6 制度性贫困
城乡分置的二元体制造成农民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保障权利的缺失,很难公平地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大体一致的公共服务;农民在面临因自然灾害、疾病、市场风险等突发事件时,由于权利与机会匮乏,缺乏必要的经济和社会保障,经常陷入贫困之中,主要表现为因灾致贫、病残致贫和因学致贫[4]。2009年,新疆国家级贫困县24.30%的村遭遇严重自然灾害,农牧民因灾害致贫、返贫问题十分突出;2009年新疆国家级贫困县未能及时就医的人中91.80%是源于经济困难,南疆三地州19个国家级贫困县这一比例高达95.60%;国家级贫困县村有卫生室比重63.70%,村有合格乡村医生、卫生员比重65.70%,村有合格接生员比重64.70%。灾害致贫根源于农业保险制度的缺失与不完善,病残致贫体现出农村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与大病救助等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因学致贫与现行的财政体制、教育体制、转移支付等制度息息相关。
4 新形势下新疆国家级贫困县的扶贫对策
新疆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构成,使得新疆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变得尤为复杂,加上思想观念封闭保守,产业结构低度落后,弱势的地方工业缺乏反哺农业的实力,脆弱的绿洲生态环境和市场发育缓慢两大矛盾对贫困地区的小康建设的刚性制约将长期存在,境内外“三股势力”的破坏活动对南疆三地州扶贫开发构成现实威胁,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新疆国家级贫困县的扶贫开发工作在新形势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特殊性。
4.1 有效整合各种扶贫资源
各地实践证明,扶贫资源的有效整合有利于扶贫开发效率的提高。①整合扶贫政策。由于不同政策的思路、目标、方案存在差异,政策相互配合、衔接不一致、政策实施过程中发生偏离与“异化”现象等,都会影响扶贫政策的实效和贫困人口的脱贫进度[5]。因此,需要有效整合与扶贫相关的财政、税收、金融、区域、产业和投资等政策,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开发、移民搬迁和农用技术培训等扶贫项目也应符合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使之相辅相成合力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社会和谐“五位一体”的扶贫效果。②整合扶贫资金。有效整合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社会扶贫资金、地方配套资金、信贷扶贫资金等各类扶贫资金,发挥政府扶贫资金的“引爆”作用和“酵酶”作用,将有限的财政资金作为引导社会资金的“启动器”,努力形成多渠道、多元化的扶贫资金投入体系。③为非政府组织从事反贫困事业提供良好的法律与政策环境,引导社会力量广泛进入反贫困领域和拓展反贫困空间,继续开展“希望工程”、“幸福工程”、“光彩事业”、“春蕾计划”、“巾帼扶贫”等工程,使其与政府的扶贫资源形成有机互补,逐步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开放高效、运作透明、互为补充、互相监督、互相促进的创新型反贫困良性互动机制。
4.2 积极探索权益保障为主要内容的赋权式扶贫开发
赋权式扶贫开发:①在实施扶贫开发的过程中应赋予贫困农户应有的政策知情权、实施参与权、管理维护权和评估监督权等,强调贫困人口直接参与包括教育和卫生保健等方面社会服务计划的设计、实施、监测与评估的整个过程,立足于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从而扭转扶贫资源使用效率低下、扶贫代价高昂、扶贫开发的可持续性较差等局面。②应大力推广小额信贷扶贫,60%扶贫资金通过小额信贷方式投向特色种养业、家庭加工业,建立农户间的互助、良好关系,促进贫困人口对反贫困战略的参与及自我选择、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增强其参与扶贫开发和脱贫致富的积极性[6]。③将外部组织干预转变为引导贫困人口建立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的“乡土合作组织系统”,培养贫困人口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创新的能力,充分发挥其管理渠道明晰、运行高效迅捷、弥补政府资源不足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激发贫困人口的主体意识,以实现扶贫效益的可持续性。
4.3 加强以结构调整与龙头企业为动力的产业扶贫
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是实施西部大开发、增强边疆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根本性措施。①依托资源优势,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农村区域化布局、产业化经营,围绕粮、棉、畜、林果四大基地建设,扶持和发展林果业、设施农业、畜牧养殖业等特色优势产业,走产业化扶贫开发道路。②大力扶持民族特色家庭手工业的发展。着力打造乐器村、小刀村、花帽村、地毯村、丝绸村等专业村,重点发展和田地毯、艾得莱丝绸、维吾尔小刀等特色产品,拓展贫困农民的就业渠道及增收空间。③大力推行“公司+农户+基地”的发展模式,鼓励龙头企业发展的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延伸产业链,努力使龙头企业肩负起标准化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任。④设立“边疆民族贫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对成长性好、有发展潜力的特色产业项目给予必要的资金引导和政策扶持,并在土地、供电、铁路运输、人才培训等方面给予相应支持,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4.4 促进以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为核心的科技扶贫
以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为核心的科技扶贫:①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推广网络。鼓励科技人员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技承包和技术服务,建立科技人员直接到户、良种直接到田、技术要领直接到人的农技推广新机制;围绕产业基地建设重点推广优良品种、高效栽培、畜禽饲养和加工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节水灌溉、农产品保鲜加工储运等先进实用科技成果,提高贫困县农业科技覆盖率。②加强科教扶贫,努力提高贫困农户的科技文化素质与生产技能。实行农科教相结合,通过加强对农牧民和各类职业技术教育和专项技术培训,提高贫困县各族群众的科技文化素质和掌握先进实用技术的能力,力争使每个贫困户至少掌握一、两门脱贫致富技能,增强自我发展和脱贫致富的能力。③结合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调配、充实、培训国家级贫困县的基层干部队伍,通过完善干部轮换、下派挂职锻炼制度和应届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锻炼制度,形成既流动又相对稳定、向贫困县、乡、村输送智力资源的规范机制,努力在新疆国家级贫困县实现每个村有一名以上中专程度的农牧业先进技术的传授者和示范者,每个乡级班子中有一名以上大专以上程度的、懂技术、懂经营、会管理的领导骨干,每个县党政职能部门中有一名以上大学程度的、专业业务熟练、有较强组织协调能力的领导骨干。
4.5 全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短缺是新阶段致贫和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反贫困中的重大作用在于有助于减少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为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的保障,形成有效的社会安全网。①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实现“五通”(通水、通电、通路、通电话、通广播电视)、“五有”(有学上、有医疗保障、有科技文化室、有集体经济收入、有强有力的村级领导班子)和“五能”(能用上安全饮用水、能用上电、能有一项以上有稳定收入来源的生产项目、能有经济适用房住、能及时得到培训和获得信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是解决制约新疆国家级贫困县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发展的林网建设工程、农田水利工程、病险水库加固工程、防沙治沙工程、“一池三改”工程(建沼气池、改厕、改灶、改圈)、抗震安居工程、饮水安全工程、村村通公路工程、广播电视电话村村通工程。②健全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建设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农民促进教育与医疗卫生服务公平,解决农民学有所教和病有所医的问题。③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特殊的保障对象与薄弱的经济基础是新疆农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严峻现实。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贫困人口的大病救助制度等,将其作为新时期农村扶贫创新的重要着力方向,构建农村反贫困安全网,提高弱势群体的社会风险承受能力,遏制因灾致贫、病残致贫等返贫现象的产生和蔓延,缓减城乡间与区域间的收入差异和社会矛盾。
4.6 根据贫困类型和群体特征相机选择扶贫措施
选择扶贫措施:①应考虑资源禀赋状况,对于具有自然资源开发优势的地区,适宜采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优势的扶贫策略;对于具有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地区应采用鼓励劳务输出的扶贫措施;对于缺乏自然资源优势和生产生活条件恶劣的北疆高寒牧区、戈壁荒漠和边境地区,就地脱贫建设成本高、生态环境代价大、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应实行生态移民,采用异地搬迁或者异地开发式扶贫政策[7]。②应考虑不同类型的贫困人口,对丧失劳动能力、负担过重的贫困家庭,应建立社会互助与救济制度,以保障其基本生活;对因灾致贫人口,应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和重大自然灾害紧急救助制度,提高其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对于南疆三地州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扶贫开发需要将资源环境保护、生态建设与计划生育相结合,改善贫困地区的生态、经济、社会环境,着力培育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将扶贫与扶志相结合、输血与造血相结合、治穷与治愚相结合、自力更生与社会扶持相结合,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地进行的综合开发式扶贫。
[1] 孟 戈.新阶段新疆农村扶贫开发的实践与思考[J].新疆社科论坛,2009:(5):62-66.
[2] 陈见影,王 哲.新疆扶贫重点县贫困线确定[J].新疆农垦经济,2008(2):63-66.
[3] 刘 娟.我国农村贫困的新特征与扶贫机制创新[J].乡镇经济,2008(2):31-34.
[4] 朱金鹤.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与效率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250-269.
[5] 赵 曦,罗洪群,成 卓.机制设计理论与中国农村扶贫机制改革的路径安排[J].软科学,2009(10):69-73.
[6] 徐志明.我国贫困农户产生的原因与产业化扶贫机制的建立[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8,29(6):711-714.
[7] 洪名勇.我国贫困地区的开发扶贫机制探讨[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9,30(3):329-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