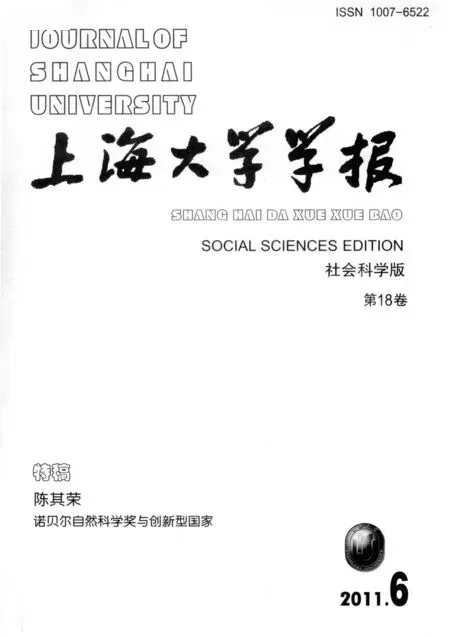“空间”与“越界”——论全球化时代好莱坞电影的类型特征与叙事转向
李显杰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9)
本文着眼于类型电影的叙事空间问题,从“越界”追求的层面,重点讨论“全球化时代”好莱坞类型电影在叙事空间上呈现出的变化与革新,试图概括出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类型电影的叙事变革所表征的文化趋势和美学意味。
一、“越界”概念与类型电影
“越界”指的是对原有的界限、成规、惯例的打破与重构。越界概念自身包含着强烈的空间意味。所谓打破成规与惯例,首先就意味着对原有的既定疆域(界限)和相应时空的破除和越过。
与郑树森在其《电影类型与类型电影》一书中提出的“越界”概念——从类型电影的“国别”角度谈论的“模仿”和“移植”现象(所说“越界”似主要意指“越出国界”)[1]不同,笔者所说的“越界”概念和“越界”现象,更多地立足于考察类型电影自身系统的内部和外部叙事空间的跨越现象。
从电影叙事空间角度讲,所谓类型电影或叫做类型化电影叙事,指的是从电影诞生初期散乱无序、纷繁杂多的叙事天地中,划分出不同的故事版图和各自的叙事空间。而故事版图的划分和相应的空间疆域的构筑,意味着不同故事题材、不同讲述方式和不同叙事话语规则的确立。其内在需求来源于对故事讲述的趣味性和有效性的实现上。
从最初类型电影的划分特征看,“长故事片”之所以成为类型电影特征的要素之一,是因为它的叙事空间比此前的1-3本的短片(包括短情节片)包含有更为复杂曲折的故事情景,更能够“引君入瓮”,进而打动人心。电影明星之所以成为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基本要素、票房保证(所谓“稳定生产的最重要的手段”),对应着“电影眼睛”能够细致入微地展现出演员的明眸皓齿、姿态神情和内心情怀,①“长故事片”、“明星”成为“稳定生产的最重要手段”,是美国电影学者刘易斯·雅各布斯(Lewis Jacobs)对最初美国类型电影形成特征的概括。除此之外,还包括“使生产标准化”,“‘公式化’影片”成规模出现,用“大规模宣传战”,“把大众消费固定下来”以及“影院放映网”的形成等多项指标。参看刘易斯·雅各布斯:《美国电影的兴起》,刘宗锟等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使表演的“视觉空间”与观众的“心理欲望”空间——“美好向往”空间契合起来,进而成为大众生活空间的一种提升和补充。
在确立了长故事片(时间向度)的大前提下,具体类型电影的叙事特征其实主要是依据其空间关系来划分的。比如西部片与犯罪片、歌舞片与间谍片显然具有各自的空间布局,因而也呈现出不同的叙事偏重。用爱·布斯康布的话说,“不管怎么样,类型的主要规定性特征仍然是视觉元素:强盗片里是枪支、汽车、衣着;歌舞片里是衣着和舞蹈(当然除了音乐!);恐怖片里是城堡、棺材和牙齿”。[2]可以说正是由于视觉元素——空间造型的各有侧重,不同的类型叙事空间形成了自己的表述方法和套路,进而使电影的故事题材、叙事话语、人物形象刻画乃至主题取向呈现出各具特色、各异其趣的叙事格局。
从影片实际看,好莱坞电影中的西部片,其叙事空间主要寄寓在天远地偏、相对散落的边陲小镇和广漠的西部荒野中(由是才会有法治的鞭长莫及和歹徒的肆无忌惮)。也正是由于这种叙事空间的疆域划分,奠定了西部片的主要叙事元素:土地、骏马、枪支;框定了故事内的人物形象:狂妄的匪徒、行侠仗义的独行客、怯懦胆小的小镇平民、昏庸的或倔强的警长等——这些人物形象多是扁平化的类型角色。尽管好莱坞西部片并非是对美国西部历史的径直照搬,毋宁说是高度类型化的神话表述,但其叙事模式的基本风貌却与美国西部文化的生活风貌和精神内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描画的是有关美国西部地区的牛仔、匪徒与英雄乃至白人移民与印第安人冲突的故事,彰显的是美国西部拓荒时期的人性情怀和生活风貌。
犯罪片则大多以城市生活作为故事背景和叙事空间,其故事版图或叙事空间相对具体和狭窄,常常限定在某一个城市或某一个地区之内,并且与特定社会时期的法律法规密切关联。例如,早期强盗片的经典代表作《小凯撒》(1931)、《公敌》(1931)和《疤脸大盗》(1932),与当时美国社会颁布禁酒的法律分不开,而且三部影片都是根据现实社会中的真实黑帮人物和事件改编而来,这使犯罪片比其他类型电影带有更为鲜明的社会现实印记。但这并不妨碍早期强盗片把强盗形象加以类型化的浪漫处理,甚至涂抹上一层“义胆豪情”的江湖色彩。这也间接表明当时的禁酒令其实并没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当然,越到后来,强盗们的活动空间越大,像乔治·克鲁尼、布拉德·皮特、马特·达蒙、阿尔·帕西诺等好莱坞大牌男星主演的《十二罗汉》之类的强盗片已经是以世界各地作为犯罪场所了。总起来看,犯罪片中不论是强盗片还是侦探片,由于主要围绕着罪行展开,是对社会法制的挑战,它们的叙事基调是阴暗的。人物总是在隐蔽黑暗的环境里行动,并且伴随着血腥和残忍。因此犯罪片让我们更多地感受到的是城市中特有的那种压抑、阴暗的视觉符号,空气中似乎弥漫着让人毛骨悚然的气息和神秘感,一个烟雾缭绕的昏暗酒吧或一所在夜色中孤独耸立的小旅馆(《精神病患者》)中所隐含的阴谋与谋杀随时可能出现。后者(神秘的谋杀与死亡)在希区柯克的悬疑式犯罪片中得到了经典的诠释。现代犯罪片则在现代大都市的豪华景观、现代银行的高科技装置和现代交通工具所构建的全球化网络空间中彰显出城市空间的暗疮与危机。
从上述不难看出,西部片与犯罪片的类型空间,具有十分明显的不同特征:前者立足于西部荒野,场面宽阔、格调明朗,即使是生死决斗也是站在街上,面对面地拔枪互射,空间相对开阔而贴近大地;后者藏匿于都市一角,场景逼仄、格调阴暗,常常用机枪扫射来表现强盗或黑帮的残暴与残忍;或者用现代高科技手段与精密算计的智慧来展现当代世界大盗的贪婪,空间相对封闭,被分割成不同的区域(哪怕是置放于全球空间的景观中也具有明确的空间区块标识)。
因此从类型空间划分这一角度讲,类型化的电影叙事,实际上意味着电影故事的不同题材选择、影片叙事基调与话语的细分与差别化,尤其体现在文本结构层面上的视觉呈现空间(造型元素的不同侧重)和故事的内在心理—文化空间(人物关系上的不同剖面)的不同选择与风格差异上。托马斯·沙兹用“确定空间”与“不确定的空间”来界定好莱坞电影中的八大类型片和它们的叙事活力。并以“确定空间”中的“个体主人公”与“集体人物”之间的象征性舞台关系来阐述类型电影的叙事成规与其中的文化冲突关系。“空间确定性对于叙事结构、题材兴趣和类型形式的仪式功能是极其重要的……不论类型的环境是确定的抑或是不确定的空间,我们所涉及的类型都是通过成规化的叙事结构来解决文化冲突和矛盾,从而达到褒扬社团理想的目的。”[3]可以说类型片的空间关系,直接决定了影片的人物形象定位和主题内涵的取向。西部片中的人物不可能是都市里的白领或黑帮,相应地也不会产生都市中的烦恼或罪行。间谍电影中的主要人物一定不会是平民百姓,要解决的矛盾冲突往往也与日常生活中的伦理关系无关。
同时,类型电影作为对人类生活故事、生存经验的人性情怀、道德观念和娱乐需求的程式化表现与神话式述说,既是艺术创作经验的累积与提炼,亦是对接受者(读者与观众)的艺术欣赏趣味的培养与建构。电影叙事由于其流逝性的影像呈现方式和相对固定的有限时间流程,要求其故事的讲述必须简单明了、善恶分明、情节曲折、结局完整;因而类型片叙事空间的划分和叙事成规(套路)的构建,成为电影叙事赢得广大接受群体的最为有效的手段和方式,进而成为以美国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电影工业最成功的运作模式也就顺理成章。
然而类型化叙事并不意味着千篇一律、一成不变地讲述单调老套的故事,它们是在相似的叙事空间和模式化的故事结构中追求着不同特色的讲述。特别是那些广受观众喜爱和好评的优秀类型电影,一定会在叙事的套路中展露出个性化的风采。在既定的模式中作出富有创意的视觉元素组合,在熟悉的故事情节进程中结构出新的叙事空间关系,从而使影片具有新的故事意味、形象风貌和人性情怀是它们的内在追求。克里斯蒂娜·格莱德希尔在讨论“肥皂剧”时谈到:“文类生产不仅仅是关于标准化的——关于固定规范和观众的。如果所有肥皂剧都是相互之间极相似的,它们很快就会失去观众,因为它们会变得太可预见、太重复。所以文类生产同样也事关差异化——运用产品的差异化来将不同的观众最大化,吸引他们,并密切关注不断变动的观众情况。”[4]这里的所谓“文类”就是我们所说的“类型”。也就是说,类型电影的生产和运作在标准化的基础上和前提下,要努力做到差异化的表现才是其获得成功的根本之道。
如此看来,类型模式在创立之初就已经开始尝试“越界”了,虽然早期的“越界”还主要表现为模式框架内各种叙事元素的花样翻新。对此,詹姆斯·纳雷摩尔曾这样描述:“事实上,每部电影都是跨类型或多元的。不管是电影工业还是观众都不会遵循结构主义的规则,而各种电影成规(conventions)早已混血到一起。基于同样的理由,每一个重要的类型都被一种在历史和社会中形成的拉科夫所说的‘链接(chaining)’手法所塑造。链条上的特定结点会以不同的方式连接在一起,并将完全不同于链条上的其他结点(《琼宵禁梦》[Clash by Night]和《劳拉》[Laura]并无多少相似之处,尽管都被归类为黑色电影)。因此,不管我们对类型做出怎样的调整,我们都无法得到清晰的边界和统一的特征。我们也无法得到一个‘正确’的定义——只有一系列有趣的用法。”[5]
对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好莱坞类型电影而言,纳雷摩尔的说法可能有点超前,所谓跨类型的追求,当作为对新好莱坞类型电影的概括更为贴切。但纳雷摩尔的论断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类型电影的生命力恰恰不在于它的墨守成规,而是立足于成规基础上和前提下的“越界”与创新。在于“有趣的用法”和“成规”的“混血”。
在这个意义上,“越界”叙事其实是类型电影追求艺术创意、文本个性的固有属性。这从类型电影定义之纷乱与杂多上,也可以得到证明。类型电影与次类型电影或曰亚类型电影的纠缠不清,具体文本中呈现出的类型元素混合都印证着类型电影空间的不断“越界”和渐趋杂糅的空间特征。
从最初的主要以类型元素的组合杂糅式“越界”,到后来的新好莱坞电影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以不同类型模式(包括某种程度上与“作者电影”的融合)的“越界”蔚为大观。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20世纪90年代以降)到来之后,类型电影的“越界”现象越来越成为常态。譬如“公路片《邦妮和克莱德》(阿瑟·佩恩,1967)、《塞尔玛和露易丝》(雷德利·斯科特,1991)和《天生杀人狂》来自于犯罪片类型……《火星人玩转地球》(蒂姆·波顿,1996)、《黑衣人》(一译:黑超特警,巴里·索南菲尔德,1997)和《X-战警》(布莱恩·辛格,2000)混合了漫画书与球星卡和动作—科幻电影的类型”。[6]这或许正是类型片作为一种相对固化,持续多年的电影叙事模式却能够经久不衰、不断翻新的内在原因。换言之,类型电影的空间元素和结构框架是相对稳定、固化的,但具体到每一文本的叙事方式、对元素的处理和配置乃至对类型模式的结构性空间,都可以做出多元的变化和多样的越界处理,所谓“花样翻新”、“热点轮换”正体现出类型电影发展的一般规律。
这些无不告诉我们类型电影的空间关系与“越界”叙事密切关联。换言之,类型片在确立了空间版图和模式规则之后,必须追求一种差异化的表现,这是由其作为娱乐—艺术—文化产品的基本属性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类型电影作为消费产品必须能够吸引观众、满足观众的心理期待和消费欲望才能够产生效益。因为作为虚构叙事的类型电影“既不相当于一件人工制造的物品(a manufactured good,在人造制品的实用意义上——笔者注),也不是一项传统(意义上)的服务(a traditional service,如传统的公共服务性行业:旅馆、酒店等提供的服务——笔者注)”,所以“经济学家无法忍受电影业,因为它的产品(生命——编者加)看上去如此短暂”。[7]所以在短短的90分钟到150分钟的时间之内,能够让观众获得乐趣、受到感动乃至接受某种教益,是需要非常高超的叙事技巧和结构能力的。“熟悉的陌生人”,旧瓶装新酒,于套路中翻出新意等一系列看似带有悖论色彩的类型电影理论描述,恰恰表明了类型电影自身所蕴含的内在创作机制和生命活力。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则使类型电影的“越界”叙事追求更加自觉、更趋深化。
二、“越界”叙事与全球化时代
所谓全球化时代,它既是一个标志时间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标识整个世界经济、文化开始走向一体化的变革概念。变革意味着打破原有格局,同时又意味着产生某种动荡和不稳定,是一个包含着复杂而丰富内涵的概念。从现实实践看,全球化时代尚处于初步形成期,因此也存在着某些尚待厘清的不确定性。
何谓全球化及什么时间开始进入全球化时代是人们众说纷纭,热烈讨论然而并无定论的问题。譬如有学者从经济一体化角度作出界定,认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和策划的”;也有学者从文化角度阐述:“美国文化的‘全球化’被形象地概括为‘三片’,即代表美国饮食文化的麦当劳的‘薯片’、代表美国电影文化的好莱坞‘大片’、代表美国信息文明的硅谷‘芯片’。西方主流国家的强势文化对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英国学者汤林森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殖民文化,是文化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扩张。”①以上引述转引自薛晓源:《全球化与文化战略研究》,见王治河主编《全球化与后现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150页。这种看法主要是从两极分化的立场看待全球化的到来。因此全球化成为‘西方强势文化霸权”入侵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文化的霸权表现。但按照鲍曼的看法,“全球化概念所传达的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世界事务的不确定、难驾驭和自力推动性;中心的‘缺失’、控制台的缺失、董事会的缺失和管理机关的缺失。全球化其实是乔伊特的‘新的世界无序’的别称”。[8]鲍曼的看法带有更多的悲观主义色彩,他从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角度把“全球化”看成是“自由贸易规则”的泛滥所造成的国家主权的削弱和世界政治秩序的失控,既不是西方霸权的表现,更不是西方的胜利,而是全人类共同的灾难。但也有学者比较乐观地看待全球化现象,认为全球化并不会带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独霸世界的同质化现象。如马克·柯里(Mark Currie)所谈到的:“海德格尔以来的大多数文化理论家都认同,如果把全球化作为一个压制和统一的进程来构想,那么同时它也是一个多元化的过程,一个增加多样性意识或在全球(化)时期增强文化个性化的过程……差异的增生与世界的标准化看上去要手拉着手,所以全球化既是集中也是播撒。”[9]相比较而言,柯里的看法更为客观,也更切合实际。
在我看来,全球化代表了人类经济、文化(包括政治)走向一体化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同质化是其最终目标。虽然全球化的启动似乎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发起的,但发展中国家并不一定会被压制而边缘化。西方的强势文化看起来的确是来势汹汹,市场经济、全球制裁大有一统天下之势。但这只是一种表象,并非全球化的实质。如同上面所提到的,全球化的过程应该是世界各国,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走向相互关联、相互融入的过程,而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对立与争论或霸权主义意义上的市场占领、文化入侵甚至战争摧毁的过程(虽然不排除西方发达国家中一些策动者最初可能抱有这样的动机)。它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实现双赢(尤其是后者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地位会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提升,但不等于一定要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文化模式的标准来衡量和选择),进而使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差距拉近,最终实现世界走向大同的人类理想。
之所以可以这样说,是因为笔者所说的全球化是建立在数字化技术所带来的电子媒介和信息革命的基础之上,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人类文化交流方式和进程(在排除外来因素操纵的前提下)是以消解霸权、摧毁专横、双向互动、不分贫富与贵贱为本质属性的,所以互联网就其自身而言体现的是全球共享、自由选择、一视同仁、双向或多向互动的特性,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跨界”属性。因而它是多媒体的(媒介层面)、跨国的(文化层面)和个体性的(民主层面)(尽管这种普遍化的自由选择由于其广大和隐秘会产生出另外的不利于人类文化发展的一面)。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发达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强势不可能再维系单向输出和同化的过程,而会成为一种自我解构的矛盾存在。举一个可能并不十分恰当的例子来讲,Inter+微软+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个人电脑和网络铺设销往全世界的比例越大,铺设的网络越广,它给世界人民提供的获取知识的能力就越强;这种获取知识的能力越强,越会使人们做出更多样、更主动乃至更为个性化的选择,而不会只停留在被输入、被灌输强势文化的被动接受状态上。所以柯里提出的“全球化既是集中又是播撒”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而2009年11月5日新华社以《“.中国”标志西方互联网霸权重要支柱开始崩解》为题的报道,也表明发展中国家正逐步在国际网络空间中获得更多的发言权。
从时间上讲,全球化进程是何时开始的呢?薛晓源在《全球化与后现代性》的总序中提出:“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通信技术和因特网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全球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联系和交往在日甚一日地加强。全球化现象于是凸现,全球化成为最时髦的词语,在全世界主流媒体和大多数人的嘴边流动。”[10]理查德·J·佩恩(Richard J.Payne)与贾迈勒·R·纳萨尔(Jamal R.Nassar)在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与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一书中谈到:“21世纪伊始,全球化在政府、商业界甚至在学术界开始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概念。政府常会把它们的经济失败归咎于全球化。……但全球化并不完全是一个新现象。它已经以一些形式和其他的层面围绕着我们很长时间了。全球化的进程就是总体上相互依赖的进程。至于全球化有什么新的东西,那就是它在过去十年来不受挑战的传播。”[11]两者的论述基本上一致,都把全球化的大规模传播和兴起置放于20世纪90年代初。虽然佩恩等认为全球化现象实际上早已在经济之外的其他方面出现。比如说,好莱坞电影其实早在二战前就成为世界电影生产制作的霸主了,在二次大战后更是传播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城市,成为世界电影市场的主要支配者。但就严格意义上的建基于高科技数字化基础上的“全球化时代”概念而言,说其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更合适。因为世界范围内个人家用电脑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才开始普及,中国的个人家用电脑90年代初才开始进入家庭。西方的因特网于1969年诞生,①参看《“.中国”标志西方互联网霸权重要支柱开始崩解》,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11/05/content_12393354.htm中国因特网的正式建立是在1994年。②参看《南方周末:互联网经济10年凉热(1994—2004》,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4月22日。正是在家用电脑的普及和国际互联网的建设基础上才可能出现当今整体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
必须看到,整体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虽然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就某些文化层面或文化症候来讲,其“跨国”式的运作和空间布局的“越界”早已开始,一如佩恩所描述的“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新现象”。
从“越界”叙事的角度考察,新好莱坞电影时期的类型片创作,实际上就是把经典的类型模式空间与“作者电影”的个性化叙事追求加以混搭和融合,可以说在类型叠加的意义上做出了“跨类型”的“越界”叙事。比如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1979),说它属于战争类型片当然可以,但它仅仅是战争类型片吗?影片对人性与兽性、个人与环境之矛盾冲突的思考足够深刻,带有强烈的问询色彩,可以说打开了影片思想力量的空间,那么说它是哲理电影也未尝不可。倘若就其采用第一人称的画内“我”充当叙述人,并主要围绕威拉德上尉的行动和心理的二元空间来刻画人物讲,说它是揭示人物的心理压力与人格变异关系的心理片同样有一定道理。再比如斯科西斯的《出租汽车司机》(1976),从空间看,说它是城市电影没有问题,但是特拉维斯身上又带有西部片(西部片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乡镇电影)中孤独英雄的色彩,一腔愤世嫉俗的热血只不过更加迷茫。其实特拉维斯只是一个怯懦、寡言、文化程度不高且性格内向的普通越战退伍军人,他是一不小心“被成为”英雄的,其中的反讽意味耐人咀嚼。影片的风格同样呈现出强烈的问询色彩和个人心理探索的痕迹;而影片松散却不无趣味性的情节元素(雏妓、约会、买枪、暗杀等),突兀且不无血腥的结局又使该片打上了恐怖片的印记和黑色电影的讽喻色彩。可见“跨类型”的“越界”叙事,在新好莱坞电影那里得到了相当程度上的发扬光大,进而使新好莱坞电影从经典的好莱坞类型电影中脱颖而出;不但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类型电影的叙事模式和方法,而且赋予了它们以更为开阔的艺术想像空间,呈现出取代好莱坞经典类型电影模式的倾向和浓郁的个人化言说的“作者电影”风格。因此,上述两部作品都获得了当年的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
但不能不看到,这种“跨类型”的“越界”追求是有一定限度的。尤其是对好莱坞电影的生产和发行机制而言,当电影艺术创新超过了以市场导向为准则的大方向的时候,就不能够得到好莱坞电影体制的认同和支持,其背后的主要动因仍然是票房—观众的认同度问题。这从《现代启示录》的票房惨败,以至于直接影响到科波拉此后艺术创作之路的实例中可以得到证明。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好莱坞电影产业的残酷,任何不能与市场需求融合的艺术追求都将被无情抛弃。也就是说,当《现代启示录》以一种作者电影的姿态,企图在一部战争题材类型片中更多地揭示战争与人性的关系问题时,它忽略了类型模式本身的元素制约,比如敌我双方的冲突、对峙与部署,战争的国家与民族利益的基本立场等,这些在《现代启示录》中都被淡化了。而是把它拍成了反思战争与人性问题的探索片。影片中威拉德提出了许多问题和疑惑,这些问题和疑惑可能也使本土的观众陷入了焦虑与迷惘,这显然与观众对影片的期待产生了较大的距离和隔膜。因而影片的本土票房惨淡,最终使科波拉的创作一蹶不振。相比之下,科波拉此前的“跨类型”创新之作——《教父》(三部集,融合了黑帮电影、社会问题片、家庭伦理片等类型元素)就在“越界”的限度上把握得比较好,做到了叫好又叫座。因此,辩证地看待好莱坞的类型与“跨类型”的“越界”追求,是正确理解好莱坞电影的产业化与艺术性的关键。
全球化时代到来之后,这种“跨类型”的“越界”叙事,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尝试和运用。不但继续在各种类型模式基础上作出创新的“跨越”,而且将各种外来文化元素与类型片混搭,显示出了新的文化趋势和叙事转向。同时新好莱坞电影后的类型电影也在某种程度上汲取了科波拉们的教训,在“类型化”的模式与“越界”叙事的追求上,注重把握度的得体与渐进。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以“反类型”的“越界”手法,强化对某一类型模式的叙事创新。如伊斯特伍德的《不可饶恕》(1992),就是以“反类型”的手法使西部片这一已经失去了昔日雄风的类型模式再一次焕发出光彩。《不可饶恕》之所以被称为“反西部类型的西部片”,原因就在于它对西部片的固有元素做了颠覆性的艺术处理,影片整体的空间格局体现出打破成规,反向“越界”的叙事追求。而《怪物史莱克》(2001)更是以颠覆传统爱情片类型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深情的真爱故事。可以说是相当精巧地反用了“公主与骑士”、“英雄救美”的传统套路。前者使西部片的英雄形象与老迈和落魄联系在一起,虽然使西部神话的敞亮风格有所减弱,却使该片的叙事空间向更为人性化的方向拓展。影片的结局段落,芒尼的最终爆发不是来自获取金钱的欲望而是来自对友情的珍视,这当然是对西部片中舍身取义情怀的致敬。后者的颠覆性“越界”叙事则使爱情片打破了郎才女貌的模式,将丑陋的外表与淳朴的心灵(史莱克)、为了爱情宁可选择丑陋的外表和美丽心灵(美丽的公主菲奥娜获救之后不是恢复原貌而是让自己变成史莱克怪物一族)并置对比,从而使影片的叙事空间具有了更多的思辨色彩和想象天地;同时又不脱离爱情片“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基本类型框架。
二是将类型模式做多元化的混搭运用,这也是近年来好莱坞类型电影行之有效的修辞策略。
譬如将本土文化与外来因素混搭,可称之为跨文化混搭。好莱坞类型电影中近年来频频出现的中国元素就是证明:中国导演、中国演员、中国的功夫、中国暴力美学意义上的枪战镜头等,都成为好莱坞类型电影混搭式“越界”的运用元素。应当说这些外来文化和电影元素的混搭式运用,使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叙事空间及其艺术表现力不再固守在西方文化空间系统而融入了些许东方文化的因子,使影片的表述更加具有国际化色彩。其实好莱坞类型电影中的混搭现象,特别是东方文化因子——中国元素的融入,在李小龙的功夫电影中已见端倪。李小龙的功夫电影当是最早的中美电影文化的交流或者说混搭的产物,只不过不是好莱坞类型电影的主动选择和有意识的搭配而已。
其他像风格化混搭,像昆汀·塔伦蒂诺的《杀死比尔I》中,将美国凶杀片的血腥色彩与中国功夫片的动作风貌和日本武士片的格斗姿态在全片的各个段落交叉呈现,既是杂糅又形成对比,呈现出强烈的风格化混搭意味。再比如互文性混搭,将其他文本的人物或桥段挪用在当下的文本之中。较为成功的文本如布拉德·塞伯宁(Brad Silberling)的《天使之城》(City of Angels,1998),整体上化用了维姆·文德斯的《欲望之翼》,虽然弱化了原文本的思想性与哲理思考,却在情感的浓烈和爱情的真挚上更为感人肺腑,因而也使该片拥有了更为广大的观众层面。还有文体性混搭、戏仿性混搭等等,都是这种混搭式越界的体现。
可以说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好莱坞类型电影更加关注全球的电影市场,追求“越界”叙事成为其赢得全球电影市场的重要叙事和修辞策略。如果说早期的经典之作的“越界”追求尚处于类型片自身系统的调节运作、花样翻新;那么全球化时代的“越界”叙事则成为其因应全球化时代变革作出的“跨类型”追求。前者的创新是对所属类型模式的维系与强化,后者的追求则意在突破类型化的模式规范,进而拓展出新的叙事空间与美学意味。这可视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类型电影的当代发展所产生的共振现象。
三、“越界意识”与全球视野
全球化时代好莱坞类型电影的“越界”追求,不仅体现在具体文本的“反类型”或混搭类型的叙事操作上,更体现在其艺术思维方式、文化视野的整体观念的变革上。特别是近年来的好莱坞类型电影已不再固守在类型模式的“越界”上,而提升为一种站在全球视野上的整体性战略诉求。我把它叫做“越界意识”。
所谓“越界意识”,指的是一种既依附类型又超越类型的创新意识。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好莱坞电影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类型电影,也不同于新好莱坞电影,或许可称之为后好莱坞电影或后类型电影。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追求和趋势上。
(一)全球化时代促使人类文化走向整合,使类型电影的题材空间从民族化走向国际化
此前由于文化上的隔膜,人们相互不了解,在对电影的认识和文化表现上,往往囿于自身的文化传统而相对武断地看待“他者”文化。这尤其表现在以好莱坞类型电影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强势文化在世界电影市场的占有率上。
从这一角度讲,早期的好莱坞类型电影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更多地属于强制性的单向输入,一定程度上还带有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殖民性质。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到来后,在国际文化走向一体化、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对“他者”文化的认知已然有了更多地客观、宽容和相对公正的眼光。也就是说,银幕上的英雄不必都是美国人或西方人,也可以是少数民族和非西方族裔人。世界也不必以美国文化或西方哲学为主导,或许将东方哲学、东方文化与其汇流才是拯救世界的更有效、更合理的路径。
或许正是由于这样一种世界文化汇流趋势的影响,好莱坞电影的生产和营销战略,开始以一种新型的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国际化制片路线,大力拓展类型电影的题材范围和叙事空间。无论是灾难片、科幻片、间谍片,还是神话片、灵异片、动画片都已经不再固守在以本土文化为准则的传统题材及其空间关系上,呈现出题材选择上的开放性。
于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邦德电影中的邦德女郎出现了更多的有色人种:中国姑娘、黑人女性,这使影片的国际化色彩更为明显。更值得关注的是新邦德女郎在影片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她们不再作为“花瓶”和陪衬、作为供邦德放松和消遣的对象出现,而是故事空间中的主要人物,并且是起到关键性作用的角色。如杨紫琼在《明日帝国》(1997)中饰演的中国女特工林慧,哈利·贝瑞在《择日而亡》(2002)中饰演的美国特工金克斯,在影片中都是身手不凡、英姿飒爽,其表现出的胆识、智慧与能力丝毫不亚于邦德。因而她们不再是传统邦德片中的“邦德女郎”而是“女郎邦德”。于是在《黑客帝国》、《尖峰时刻》、《木乃伊 3》、《2012》、《阿凡达》等影片中,用包括中国功夫、中国自然景观、中国制造、中国文化在内的多国文化元素共同构筑影片的文化空间,成为好莱坞类型电影的不二选择。这些无不表明好莱坞类型电影正在进一步走向国际化的尝试和努力。
后类型电影题材的跨文化、跨民族、跨国家性,使原本主要以地域题材、本土文化为主导的类型电影的叙事空间和文化边界不再局限于本土和本国,这无疑是全球化时代电影创作的最明智的选择。这种对类型模式的整体化“越界”追求,既包括笔者上文提到的在好莱坞本土类型电影中融入外来文化因素,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体系的电影人请进来,以加强和丰富类型电影的文化包容性;还表现在直接以外国文化中的故事题材制作影片,例如动画片《花木兰》、《功夫熊猫》,包括近期上映的《功夫熊猫2》等,这些影片在中国内地电影市场获得的高票房收入充分证明了跨文化叙事的有效性。说这是好莱坞电影的题材枯竭也好,是讨好中国电影市场和观众也好,总之都彰显出好莱坞敏感的电影市场触角和适时应变的叙事策略。一如《阿凡达》的制片人乔恩·兰道所说的:“这不但是中国电影的幸运,也是全球电影的幸运——其实最主要还是好莱坞的。全球市场正在一体化,中国市场将会全球共享,成为新的增长点。”[12]这里尽管不乏好莱坞电影市场营销策略的考虑,但从根本上讲,还在于其“越界意识”的自觉,是好莱坞类型电影适应全球化时代,走向国际化舞台的内在需求和布局世界电影市场意义上的文化扩张。
不同文化元素的融合,跨国导演、演员的兼容并包以及中国元素的广泛运用,对外来文化、不同民族的故事题材秉持开放性的拿来主义,揭示出后好莱坞电影在全球化时代正以国际化的战略眼光建构电影叙事的全球空间,表明了后类型电影新的市场策略和发展动向。
(二)数字化技术在类型电影叙事中的普遍运用,使类型电影的叙事空间从故事性走向修辞化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建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全球运用和网络文化的普及所带来的信息交流和文化构成与消费方式上的革命。这种立足于信息革命的变革具体到电影叙事领域,首先体现在电影叙事空间的变革上,包括银幕呈现空间的扩展、影院放映空间的改造乃至观众接受心理空间的嬗变。
譬如,当今的影院从过去的大影院(可容纳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变成了多个只容纳一两百人甚至几十人的小放映厅,即所谓“多厅影院”。这种改变使影院在同一个时间段内,可以安排放映多部不同影片。从院到厅的变化实际上意味着观众到一个影院或影城时,可以做出观看不同影片的多样选择。与此同时,银幕却从过去的一般银幕、宽银幕变成了覆盖观众面对的整个幕墙的超大银幕,再加上带后环绕音响装置、先进的多分频杜比DTS立体音响设备,宽大舒适的座椅,使电影放映厅不再拘囿于观看一个电影故事,而成为观众体验电影文化,享受休闲生活的愉悦活动。可以说这种物理环境空间和呈现与放映条件的硬件变革,使银幕呈现空间与观众的接受空间形成了新的视听互动关系,极大地改变了电影叙事与观赏的传统方式,进而带来“软件设计”的变革。换言之,这种新型的空间关系打破了传统类型电影注重故事讲述的线性结构,即相对更强调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时间轴线上的变化、转折乃至结局的因果式故事结构;而开始以叙事空间的扩展为叙事突破的方向。于是营造出更为壮观、绚丽的银幕影像,追求IMAX、3D电影的视听美学效果,成为全球化时代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发展趋势。
像近年在中国大陆引进上映的被人们称为“好莱坞大片”(“大片”是个约定俗成却相对模糊的概念,笔者另文申说,只在“大制作”这一基本含义上运用)的类型电影,就相当充分地显示了这种场面壮观、景观神奇、华彩炫目、气势磅礴的“大制作”的视听魅力。像《黑客帝国》中尼欧与一百个史密斯在广场决斗的场面,宏大壮观,动静有致,展现出的是姿态和动作之美;像《魔戒2》中,当越来越多愤怒的树人活动起来,迈开迟缓而坚定的大步,摧枯拉朽般地展开对半兽人的进攻场面,那种奇特景观、磅礴气势,是唯有大自然本身——中土世界最古老的生物树人树精们才可能呈现出的力量和风貌。
《阿凡达》中那些美丽晶莹、像水母般透明的神奇花朵,不光是展现在银幕上让观众看(多少有些被动),更是让它们从观众的眼前和身边向银幕上漂移,这种3D电影的拟真效果,有力地强化了观众与影像的空间关联,改变了观众与电影原本的观看关系——从被动观看到拟真感知。类似的感受我们从《怪物史莱克4》中那些驮着驴子、公主和史莱克在空中自由飞翔的小飞龙的影像呈现中也能够获得。
这种空间感知形式的革命性变化及其未来发展,蕴含着极为广阔的发展潜力,或许最终会从根本上颠覆电影艺术呈现与观看的审美方式和审美性质,从而把观看变成为人们实践性参与的影像互动活动。因此这一层面上的“越界”追求所具有的深远文化意义和美学意味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
基于上述,笔者认为电影叙事化已使得电影的叙事方式从注重故事性讲述转换为强化修辞性言说。所谓修辞化言说,即指电影以营造强化的主观影像世界和宏大奇特的空间景观为主导,使观众沉浸在视听影像的流动韵律之中,进而达到实现娱乐性审美的交流效果。
当然说后类型电影的叙事空间转向修辞化,并不是说好莱坞大片不再注重讲故事,而是说它们不再注重讲述近距离观照生活的日常故事,更看重讲述那些具有超凡想像力和非同寻常色彩的未来景观故事,而在叙事的伦理情怀上追求普世化的价值情怀则成为这类大片叙事的内核支撑。
(三)立足于全球视野,建构太空视角,使类型电影的叙事视野具有开放性和前瞻性
所谓“太空视角”,指的是从宇宙空间的角度来反观地球风貌、呈现人类世界的叙事角度。科幻片开场常常出现的“太空景观镜头”不妨看成是这种叙事视角的镜像隐喻。从太空视角看,地球只不过是浩淼银河中的一个小小球体而已。站在本土文化、一国立场看是不得了的大事,站在全球角度看可能不算什么;站在地球视角面对的场景,移动至宇宙视角看则又是另外一番景观。这就是“太空视角”具有的空间视野和文化意味。
从后类型电影的叙事结构看,有了这样的叙事视角,会使故事的叙述、空间的架构不再是一种狭隘的一地之事、一国之见,使叙事具有更为充沛的想像力,更具有人类意义上的普世价值与世界情怀。自然也会使故事的呈现拥有更广大世界范围的电影观众群体。就此而言,后类型电影叙事的“越界意识”和全球视野,是全球化时代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趋势的体现。近年来大行其道的科幻电影可谓是这种意识和视野的文本实践。
对比来看,如果说早期的好莱坞灾难片多从灾难发生的某一地点来结构空间,更多地是对人类历史上各种具体灾难加以艺术写照,今天的灾难片则更多地与科幻汇流,不去呈现具体的灾难(无论是来自自然,还是源于人类自身),而是从全球视野来幻想和预言灾难。如近年来的科幻灾难片《后天》、《2012》;其他类型的科幻片同样具有这种面向未来的预言性质,例如科幻英雄片《第五元素》、《黑客帝国》等,有时候这种追求会以一种发掘远古文明的反向方式呈现,例如科幻神话片《魔戒》、《阿凡达》等。
《2012》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地球的全面崩溃),来揭示人类面临的困境,呼吁全人类不分国家民族共同承担救赎的责任。《阿凡达》则在科幻的类型模式中融入了更多的神话元素,将古老文明与当下物化世界的冲突作为基调,进而从整体上否定了发达国家和霸权主义行为的合法性。《黑客帝国》在科幻类型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高度计算机化后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反思,揭示出高度科技化的社会并非是人类乐园。可以说这些好莱坞大片,无不是站在未来世界的角度来看待当前的人类文化现状。尤其《阿凡达》一片,讲述了地球人对纳威人生存环境和其古老文化根基(圣母树作为象征)的入侵和摧毁,和看似弱势的纳威人与潘多拉星球上全体生物的齐心协力、共同反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神话故事。这种叙事话语显然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政治与文化上的隐喻性。可以说是对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霸权主义行径的影像指涉,同时也是对所谓的西方强势文化的一种批判与讽刺。更深入地看,它是对当今世界物欲横流、缺乏人性情怀和关爱、无视自然规律、片面追求高速发展的一种反思与批判;与此对应的则是对美好、和平、智慧和平等的呼唤与赞美。
后好莱坞类型电影的这种立足于全人类文明结构叙事空间的“越界意识”,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对新好莱坞电影的批判精神和艺术特色的一种扬弃。所谓扬弃,指既有所继承,又有所改变。继承方面,表现在同样力求使影片的叙事主题、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人文内涵和问询色彩。改变的方面,则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些大片淡化了新好莱坞电影那种强烈的个人化印记以及政治性话语色彩(如反战、民主化、种族问题、冷战思维等)。而是从一个更高的也更为平和的视野来组织故事题材,结构叙事空间,在影片人文内涵的开掘上一般都具有比较明确的追求。如卡梅隆所说:“《阿凡达》是一部视觉性很强、很打动人的电影,它并没有和什么特殊的美国文化关联在一起。所以我想,这是一部为世界呈现的电影,它传递出的基本信息是——每个人都有爱,这也是这部电影强大情感纽带的所在。”[13]
由此可见,从超越地域空间和本土文化的太空视角来展开叙事,已是后好莱坞电影的自觉追求。站在太空视角审视人类命运和未来世界,必然需要呈现宏大、神秘、瑰丽的宇宙空间和对未来景观的猜想,科幻片的应运而生乃情理之中。因此,太空视角的建构实际上正是全球化时代类型电影叙事的“越界”意识之体现。科幻片中所呈现的景观环境、所刻画的人类命运、所揭示的灾难场面不是属于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民族的事件而是关乎到整个世界和人类全体。
建构太空视角,从全球视野的角度围绕正义与邪恶、善良与阴谋、真诚与欺骗、爱情与牺牲、保护与杀戮、无私与贪欲等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认同来做文章,显然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布局全球电影市场的战略选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网络文化普及之后,当代类型电影乃至电影叙事在审美向度和审美趣味上的某种转向。其内在的美学意味在于,今天的网络文化已经使个人化的言说:无论是满腹的牢骚、愤青的呐喊,还是对人生的体味言说或是对社会现状的点滴看法,抑或是对爱情的追求与表述、艺术的欣赏与评说(包括在网络上欣赏各类影视作品、发表观影心得),都有了相对自由的选择和较为宽松的释放途径。但这些并不能取代大银幕叙事、豪华影厅所带来的视听享受和心理震撼。好莱坞大片所呈现的那种幻想的、预言的、炫目的、神话的科幻影像天地,能够填补人们日常网络文化消费中所不具备的视听空缺,提供出更具有宏大空间意象的景观。或许可以说,营造一种令全人类同命运共呼吸式的集体愉悦或集体恐惧,或许正是全球化时代一种别样的回归家园的需求,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类型电影的当代发展所必然产生的共振现象。
对中国电影事业来讲,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电影叙事在产业化的道路上已有长足的进步,也出现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制作,但就全球视野和空间意识而言,中国电影尚缺乏明确的类型电影机制及其“越界意识”,更谈不上布局全球的战略眼光。因此辩证地分析、借鉴好莱坞类型电影尤其是后类型电影的生产、制作与发行经验,尤其是有针对性地汲取它在全球化时代所呈现出的“越界意识”和其文本实践的成功经验,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1]郑树森.电影类型与类型电影[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20-22.
[2]爱·布斯康布.美国电影中的类型观念[J].世界电影,1984,(6):37-52.
[3]托马斯·沙兹.旧好莱坞/新好莱坞:仪式、艺术与工业[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74.
[4]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64.
[5]詹姆斯·纳雷摩尔.黑色电影:历史、批评与风格[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2.
[6]Robert Kolker.Film,Form,and Culture(Second Edition)[M].New York:McGraw-Hill Ompanies,Inc.,2002:157.
[7] Douglas Gomery.The Hollywood Studio System[M].New York:St.Martin's Press,Inc,1986:1.
[8]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56-57.
[9]Mark Currie.Difference[M].London:Routledge,2004:112-113.
[10]王治河.全球化与后现代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
[11]Richard J Payne,Jamal R Nassar.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M].New York:Pearson Education,Inc,2003:116.
[12]高嘉阳,喻德术.中国喜好贯穿生产线 影片加中国元素套近乎[EB/OL](2010-03-31)[2011-03-20]http://yule.sohu.com/20100331/n271234480.shtml.
[13]詹姆斯·卡梅隆.我的电影仍能吸引孩子[N].周末画报,2010-01-30(A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