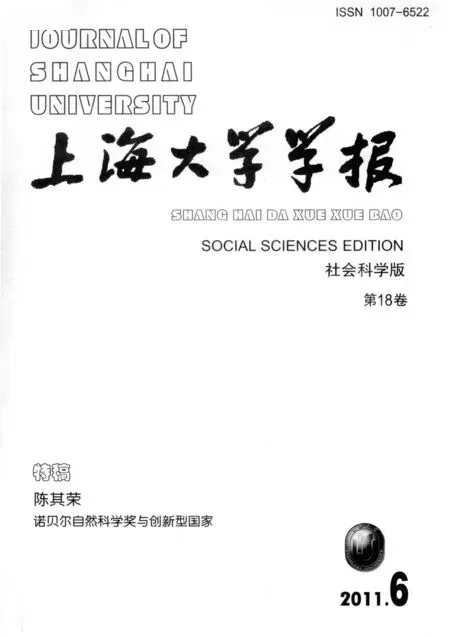沈曾植与佛教
张煜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同光体诗人中,对佛教浸润最深的,毫无疑问是沈曾植(1851—1922)。其佛学造诣之精深,诗作中佛典使用之繁多,均远超乎同侪。故欲研究沈曾植之诗歌艺术,不妨先从其与佛教之渊源来作一番探讨。
王蘧常《清末沈寐叟先生曾植年谱》曰:“初公论学尚实用。于人心世道之隆污,政治之利病,必穷其源委。王《序》”[1]33确实,光绪六年(1880),沈曾植三十一岁,中了贡士,同榜李慈铭也虚心推服,在日记中写道:“其经文四首,皆博而有要。第五策言西北徼外诸国,钩贯诸史,参证舆图,辨音定方,具有心得,视余作为精彩矣。”[1]15聚奎堂批《光绪六年庚辰科会试同年齿录》云:“观五策,于许书最熟,而于朔方事,历历如数掌纹,淹博无匹。合二三场观,知小学、地舆、经史无不淹贯,洵是通人。”[2]38则沈曾植之究研佛教,当在此之后。《沈寐叟年谱》光绪十五年(1889)云:“公早又沉潜有宋诸子之学,久之并旁通二氏。案公梵学最深,始业当在四十前后。……又考公所有梵经序跋皆在戊戌(1898)、丁未(1907)间。……录此以见公中年学佛之一斑。又案袁爽秋太常,亦湛深梵学,公必受其影响。庚寅(1890)有和公诗……”(第25页)考订颇为详尽。①钱仲联《海日楼札丛》及《海日楼题跋》之《前言》亦云:“沈氏治佛学,开始在四十岁前后。光绪末,游日本,得‘大藏经’全帙回国,致力益勤。”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作为一位学者、官员兼文人,沈曾植之于佛教,在义理、考据、辞章方面均有所发明建树。在义理方面,他其实有意通过佛教来融通东西文化冲突,解决各种现实与思想领域的矛盾,而这种佛学又是与儒学互为表里的。他曾这样感慨过:“噫,国其殆哉。夫道器文质,体用经权,理事神迹,非可二也,而今学士皆二之。道与德,政与教,知与行,定与慧,名与实,学与业,生与义,非可离也,而今学士皆歧视之。自他、心物、真妄、新故、今古、有无、是非、善恶,相待而著,非定有也,而今学士皆固执其成见焉。”[1]99康有为《赠乙庵尚书四章》其一云:“尽通文史儒玄学,证入慈悲喜舍禅。”[3]卷八此语庶几得之。
沈曾植主张儒、释、道相通,尤其是儒、释,不可偏废。毫无疑问,他是主张治学当以儒学为先的。《沈寐叟年谱》1918年条云:“公尝云欲复兴亚洲,须兴儒术。欲兴儒术,须设立经科大学。先当创设亚洲学术研究会。”但沈曾植同时又批评“儒门刻急”:“儒门澹薄,容不得豪杰。此宋时某师之言也。今日儒门一味刻急,吾恐天下豪杰,将有望望然去之患也。止为儒者不能摆脱世缘,故风俗愈恶薄,儒者亦愈刻急。(《潜究室劄记》)”[4]卷四又谓“禅令人薄”:“禅令人薄,学焉而知所不足可也。(《潜究室劄记》)”认为“近世禅学不振,由不读儒书之过”:“近三十年,缁徒随世转移,重科学,轻儒学。儒学疏,而佛学亦浸衰矣。有俗谛,而后有真谛。有世间法,而后有出世间法。所谓转依者,转世间心理为出世间心理。瞢不识世间心理,将何从转之。”[4]卷五辛亥革命后,沈曾植成为遗民,他取法黄宗羲:“案存南雷说,赞以知非章。”[4]卷八钱仲联先生注引彭绍升《居士传》云:“黄宗羲言明季士大夫学道者,多入宗门。如金先生及蔡懋德、马世奇、钱启忠皆是也。然皆以忠义名一世。宗门以无善无恶为宗,然诸公者,血心未化,乃儒家所谓诚不可掩者,在宗门不谓之知性也。”可见儒学、佛学是他的两大精神支柱。他欣赏白居易的“外袭儒风,内宗梵行”(《杂家言》)。[4]卷四又认为“佛理与庄子相通”[4]卷五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他在义理方面欲构建一圆融世界的努力。
在儒、释相通方面,沈曾植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即认为《易》通于密。他写有这样的诗句:“《易》教审显密,书禅会波戈。”①《海日楼诗注》卷三《石钦证刚诗咏斐亹读之有见猎之喜晨兴忍寒复得古体五首》其五。钱仲联先生引李翊灼《海日楼诗补编序》云:
庚戌(1910)访叟嘉兴,偕作西湖游,十日之中,晴晦、雨雪、风月,几无不备。寂然境中,妙现神变,枯木寒岩,顿有生意。予叹曰:“乾阳无死,《易》义故不虚耳。”叟曰:“余于是亦悟《易》义惟密,颇觉以密通《易》,应无不合,子能为我言作证乎?”予曰:“可。夫《易》之为义,即神变也。神变,即密之大用也。故《系辞》传谓“君子洗心,退藏于密”。盖不密宁复能《易》哉?且《乾》,金刚智界也;《坤》,胎藏界理也。《乾》、《坤》生六子,两界开四部也。《乾》、《坤》变化而有八卦,两界瑜伽而成曼陀罗也。演八卦而为明堂位,曼陀罗而现三昧耶也。如是义证,不胜枚举。《易》为儒密,又何疑哉?”叟笑曰:“诚哉是言!然而彼之轩轾儒佛者,匪唯不知佛,抑亦不知儒已。”
不仅仅儒、释、道圆融,沈曾植对佛门各宗派也一视同仁,没有偏颇之见。他认为“释迦乃否定外道者,非否定《吠陀》者”(《杂记》)。[4]卷五他融通小乘与大乘,认为“罗汉是出世法,菩萨是世间法”(《札记》)。对于中国佛教,他认为“禅宗、净土宗、戒律宗,为北方实际的佛教。三论、天台,为南方理论的佛教。北华严,为缘起论宗。南法华,为实相论宗。……佛学元与儒学不异”(《札记》)。其称引“龙树四教”:“龙树四教(出《华严经随疏演义抄》):‘龙树论师,乃西天第十三祖。尝立四教,判释经论。(1)有门,谓《阿含》小乘等经,说因果。(2)空门,谓《大品般若》诸经,说真空实相之理。(3)亦有亦空门,谓《深密》诸大乘经,说有说空,互相无碍。四、非有非空门,谓《中论》等说,即空之有,是非有;即有之空,是非空。互泯互融,是第一义。’按:此是三论宗所判教义。发端龙树,时代最先。”(《东轩手鉴》)颇为留意于龙树的判教思想。他的这种各宗派平等以及判教意识,对于此后太虚法师的佛教改革,可以说不无启迪意义。
他所作的《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序》,剖析中国佛教发展源流,亦甚为详备。其文云:洪惟我国佛教之隆,莫先于晋。士大夫好学深思,穷研心理,感彼西哲,联袂偕来。学泯町畦,情忘畛域。尔乃图澄密行,扬觉华于戈戟之林;道安清范,植慧根于饥歉之世。逮夫罗什诸德,振锡渭滨,开方等,出《楞严》,显菩提,宏《般若》,绎三论,颁五禅,敷《妙莲》,陈《梵网》,左挹《成实》,右领《婆沙》,耀文殊之珠,表普贤之相,彰慈氏之受诀,赞弥陀之度生。于时昙影疏其中观,道生申其顿悟,东林则专修安养,青眼则严护毗尼,华藏教诲,觉贤译其文,涅槃地持,昙摩发其秘。溯彼法流,汪洋泓演,历宋、齐、梁、陈、魏、周、齐、隋、唐,迄吴越、辽、宋、元、明,以至于清。若成实,若俱舍,若净土,若般若,若智论三论,若法华、涅槃,若地论,若摄论,若唯识,若华严,若真言,若律,若禅定,若牛头,若曹溪,若临济、沩仰、曹洞、云门、法眼诸宗,与夫高句丽之所传,日本之所述,南海西洋各邦之所授受,无不导源于是时者。……其谈心识也,则洞达性源;其示行相也,则备诠万德;其析物质也,则辨极邻虚;其衍法数也,则引而至于不可说,洵所谓大无外,小无内,穷三际,遍十方者矣。佛以一圆音演说妙法,历代宗师,绍承申绎,名理奥义,日新不穷。隋、唐而下,辟途尤众,所以广建法幢,启灵关而膺众生之咨求者,殆源源而无已。虽其间各树义宗,或正授,或别传,或显或密,有种种之殊态,迹其大权妙用,异派分流,要无非趣入一佛教诲,圣智出世,应众生根而为说法,亦各因其时耳。
其中对于中国佛教有相当高的评价,即使对于今日之学术界也甚有启迪。汉传佛教相较于印藏、日本乃至欧美佛教,不管是在教义还是研究方面,本来就应有其殊胜与无可取代之处,不可因为清末佛法、国运衰微,而妄自菲薄也。
沈曾植在佛教考订方面,也是多发前人所未发,最有成就。对于上座部佛教、禅宗、密宗的研究,都给今人以视野开阔、孤明先发的鲜明印象,远早于胡适后来对于禅宗史的考索与质疑。葛兆光先生《世间原未有斯人——沈曾植与学术史的遗忘》,①《读书》1995年第3期。高山杉先生的不同意见,亦可参《佛学艰深海日楼》一文,载《东方早报》2010年2月28日。对此类问题已有详尽论述。
沈曾植在晚清民国,虽然是第一流的大学者,但作为一个传统意义的知识分子,他恪守传统儒家的纲常信条,效忠于大清。他早年虽有维新思想,但到了清政府晚期,与当时不断前进的时代潮流,常常有扞格不入之处。1908年,“闻九年立宪之诏下,公叹曰:‘乾坤之毁,一成而不可变。’于是更号曰‘睡翁’,谓不忍见不能醒也。”[1]521909 年,“与某公书云:‘财政岌岌,官司解体,中外相疑。举海上妄人之说,一切悉纳诸宪政之中,作茧自缠,背水阵更无躲闪,波土覆辙,可为寒心。”[1]55入民国后,他成了一位遗老,楼居上海:“若与人世间隔,常以途人为鱼鸟,阛阓为峰崎,广衢为大川,而高囱为窣堵波。据《海日楼文集》卷下《余尧衢古希偕老图序》。”[1]58其后1917年张勋复辟,也积极北上参与,且抱定必死之志。《沈寐叟年谱》云:“案公此行亦自知其难为,特一心忠耿,生死利钝,乃所不顾,有可藉手,即投袂而起耳。……盖殉国之志,身后之谋,早决也。其后事未成而志未遂,天也,非人也。时代不同,见解亦因之而异。后之人,敬其志,哀其遇,可也。”[1]68-69了解了他在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困境与矛盾,我们就更能看清佛教对于他维持心理平衡所起到的特别作用,这些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尤为集中。
1900年在武昌,沈曾植即作有《病僧行》,自注云:“诗作于庚子(1900)竞起,卧病江潭,有感而作。”[3]卷二此诗因为多用佛典,邃于佛学,受到了陈衍的称赞。1910年,又作《自题僧服小影》,自注:“尔时著僧衣,同摄者:证刚、端士、石钦也。庚戌七月。”王遽常《沈寐叟年谱》:“宣统元年己酉(1909),公六十岁。时国事日非,公尝作僧服以欧法摄景寄朋侪题咏以寄意。明年自题云云。”其诗曰:“了此宰官身,即是菩萨道。无佛无众生,灵源同一照。”(卷三)1918年所作《病起自寿诗》其三云:“亦元亦史亦畸民,亦宰官身长者身。成住坏空看已尽,黄农虞夏没焉陈。平生师友多仙佛,至竟形神孰主宾。蓦地黑风吹海去,世间原未有斯人。”(卷九)著语沉痛,是他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至如《倚装答石遗杂言》其七:“思是无明思,怒亦无明怒。身到鹫峰头,那不解佛语?”(卷十)《和庸庵韵》其二之:“事去只如梦,心空无所为。”(卷十)《七月廿七日为檗宧百日礼忏于清凉下院病不能兴哭不成声诗不成句魂兮归来哀此病叟》其九之“万古原无续命汤,百年臧谷等亡羊。”(卷十二)《小除夕有感》之:“世间路已尽,天界路休迷。”晚年心境之凄凉,可见一斑。
沈曾植作诗的一大特点是喜欢用典,经史子集,经常是信手拈来,而且用典的密度大得让人透不过气来。这些典故中,当然也包含了大量的佛典。钱仲联先生《近百年诗坛点将录》称他“学人为诗,佛藏道笈,僻典奇字,层见叠出。盖硕儒大师,出其绪余,一弄狡狯,而见者则惊为西藏之曼荼罗画也。”[5]673其实沈曾植并不仅是在诗中有意炫博,他是有自己完整的诗学体系的。其一即是“雅人深致”说。他在《瞿文慎公止庵诗集序》中说:
昔者曾植与涛园论诗于公,植标举谢文靖之“訏谟定命,远犹辰告”,所谓“雅人深致”者,为诗家第一义谛;而车骑所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者,为胜义谛。非独以是正宋、明论诗者之祖师禅而已,有圣证焉。夫所谓雅人者,非即班孟坚鲁诗义“小雅之材七十二,大雅之材三十二”之雅材乎?夫所谓雅材者,非夫九能之士,三代之英,博文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之君子乎?夫其所谓深致者,非夫涵雅故,通古今,明得失之迹,达人伦政刑之事变,文道管而光一是者乎?五至之道,诗与礼乐俱,准迹熄王降之义,雅体尊,风体卑,正乐雅颂得所,不言风,有较四国之徽言,固未可与槃涧寤歌等类观之而次列之。自四家诗说略同。诗教衰而五言作,才性于汉魏之交,清言于晋,新变于梁陈,风降歌谣,镂画者殆不识雅为何字?至于唐之行卷,宋之江湖,声义胥湮,而陋者复淆以宗门幻语,诗终为小道而已。尝发此意于《渔洋生日诗》,公不余非也。[6]
一方面是以禅喻诗,其实很难说清楚第一义谛和胜义谛有什么区别,几乎就是一回事,说明沈曾植对于两谢之论诗,并无优劣之判,而是同等重视;一方面其实仍然是宋诗派以学问为诗诗论的延续,不过更加强调了诗歌的儒学内涵,增强了内容上的时代性。①详参李瑞明博士论文《雅人深致——沈曾植诗学略论稿》,2003年。但他《沈曾植的诗学观:“雅人深致”说》一文,将胜义谛理解为俗谛,则明显有误。文载《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6期。又他在文中认为沈曾植的《渔洋生日诗》批评严羽只知妙悟,及王士祯虽然晚年视野有所放宽,但仍有所缺憾,则言之成理。
沈曾植更完整的诗学理论的表述是在《与金甸丞太守论诗书》[7]中。金蓉镜学诗于沈曾植,也是同光体浙派的代表人物。此文为众多研究者所引用,因为内容重要,今不惮烦,复征引如下:
吾尝谓诗有元祐、元和、元嘉三关,公于前两关均已通过,但著意通第三关,自有解脱月在。元嘉关如何通法?但将右军兰亭诗与康乐山水诗,打并一气读。刘彦和言:“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意存轩轾,此二语便堕齐、梁人身份。须知以来书意、笔、色三语判之,山水即是色,庄老即是意;色即是境,意即是智;色即是事,意即是理;笔则空、假、中三谛之中,亦即遍计、依他、圆成三性之圆成实性也。康乐总山水庄老之大成,开其先支道林。此秘密平生未尝为人道,为公激发,不觉忍俊不禁,勿为外人道,又添多少公案也。尤须时时玩味《论语》皇疏,与紫阳注止是时代之异耳。……湘绮虽语妙天下,湘中《选》体,镂金错采,元理固无人能会得些子也。其实两晋元言,两宋理学,看得牛皮穿时,亦只是时节因缘之异,名文句身之异,世间法异,以出世法观之,良无一无异也。
就色而言,亦不能无抉择,李、何不用唐后书,何尝非一法门,观刘后村集,可反证。无如目前境事,无唐以前人智理名句运用之,打发不开。真与俗不融,理与事相隔,遂被人呼伪体。其实非伪,只是呆六朝,非活六朝耳。凡诸学古不成者,诸病皆可以呆字统之。在今日学人,当寻杜、韩树骨之本,当尽心于康乐、光禄二家。所谓字重光坚者。康乐善用《易》,光禄长于《诗》。兼经纬。……
……谢傅“远犹辰告”,固是廊庙徽言;车骑“杨柳依依”,何尝非师贞深语。鄙近尝引此旨序止庵诗,异时当录副奉教。
此文作于 1918 年。[2]469-470文中相对于陈衍的“三元”说而提出“三关”说,体现出了沈曾植除了唐宋诗歌外,对于六朝诗歌的同样重视。又其中对于刘勰“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批评,极其值得玩味。因为在沈曾植的诗学体系中,庄老(玄理)与山水(色、事)原本就应该打并作一气而不可割裂。并以佛教的三谛、三性理论来证成此说。法相宗以遍计所执性为妄情,故判为空;以依他所起性为众缘和合,故判为假有;以圆成实性为真实如常,故判为真空妙有,而与中道相契合。所以在沈曾植看来,一首好的诗歌,山水与庄老、色与意、境与智、事与理,应该是相统一的。所以“谢傅‘远犹辰告’,固是廊庙徽言;车骑‘杨柳依依’,何尝非师贞深语”,两者没有优劣之分,是同等地重要。只有两者相结合,既有文学形象,又有思想内涵,写出来的才是一首好诗。他觉得自己的诗之所以强于湖湘派的王闿运,正是因为自己的诗中有玄理,而不仅仅是“缘情绮靡”。
其实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在叹服沈曾植诗歌深博奥衍的同时,可能更加能够欣赏的,还是他的那些相对比较清通而又富于理趣的作品,其中不乏多用佛典者。正如陈衍在《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所言:“乙庵诗虽多诘屈聱牙,而俊爽迈往处,正复不少。”[8]其赠人之作如《寄苏庵》之:“一椎开法席,九变计民功。丈六身光在,超然镜影中。”(卷一)《答散原》其二之“君苦不能禅,我苦不能醉。醉乡无町畦,仙佛会一致。”(卷四)《闇伯有悼亡之感久无音问怀抱可知辄寄短章用广其意》之:“情澜一决爱河干,湖水鸳鸯咽不喧。香火缘深成眷属,冤亲尽处到泥洹。”《易实甫过谈》其一之:“虫沙变化朱颜在,服食从容素女俱。世界是空还是色,先生非有且非无。”《散原六十寿诗》其二之:“名山无量寿,沧海有情痴。”《云门偕子勤过谈归后贻诗次答》之:“诗怀淡欲味无味,物态静观生不生。”(卷五)《十月望日超社第十二集完巢招集樊园分韵得五物各赋七言古体》之:“报施直为通三有,生灭聊须观八不。”《和完巢自寿》之:“与君且作须臾计,露电光中寿者身。”《伯严诸君探梅邓尉归庸庵尚书觞诸花近楼唱诗竟日》之:“若阿字观真言宗,一相兼存空假中。”(卷八)《奉和西岩相国病起简同社韵》:“一念炽无明,千生堕无间。”《题苍虬愔仲落花诗后》:“花落春焉在,凭君善巧观。南山无相佛,篱下举头看。”(卷九)题画之作如《题沈云画渡海达摩像》:“眼光烁破四天下,不共诸师诤王舍。波涛浩涌龙宫迁,世界无尽慈无缘。不瓶不钵不袈裟,非报非应非昙摩。梁皇殿前一语多,少室十年禅则那。”(卷三)《为伦叔题文待诏画册》其五之:“佛如优钵昙,常在人世间。古寺晚钟声,分明识唵字。“(卷四)《题画》之“先生非有画是有,世界法华能转无。”(卷六)感怀之作如《听歌》其一:“子野闻歌复奈何,江城只是落花多。金刚香鬘人天眼,回向维摩一忏摩。”(卷二)《西园绝句》其三之:“但得心如境自如,方塘鉴影我知鱼。拈花一笑三禅喜,恰有回风与忏除。”《晓起》其一之“当时尽作缠绵意,直下难为露电身”,其二之“龙荒已无干净土,大旱冥随金石焦”(卷五)。《玄夜》:“玄夜万缘寂,真符豁开呈。一花一世界,一尘一香城。”(卷九)皆隽永有味,不同凡俗。《石遗室诗话》卷三十云:“昔沈子培论诗,以烂熳为最佳境。”[8]信然。沈曾植的很多诗歌,正是将学问、玄理与深挚的情感打并作一气,难怪钱仲联先生赞之为五彩斑斓的曼荼罗画。
其实在诗中用佛典,是历代文人惯技。沈曾植倡“三元”说,“三元”的大诗人如谢灵运、韩愈、白居易、苏轼、黄庭坚等的诗歌,均多有受到佛教影响之处。①详参拙著《北宋文人与佛教论稿》,即出。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则唐代诗人受影响多体现在诗歌意境方面,宋代诗人受禅宗影响,更多体现在“夺胎换骨”等作诗技法上。即使到了清代、近代,这些文学现象仍然大范围地存在着。辛亥后,当时与沈曾植唱和的超社、逸社诗人中,诗作中就多有用佛典的。如梁鼎芬《癸丑(1913)浴佛日伯严于樊园招饯林侍郎游泰山题诗何诗孙图上》:“死生聚散海一沤,不如登岱瞻鲁邹。”[3]卷五《逸社第一集止庵相国觞同社诸公于敝斋相国与庸庵尚书诗先成曾植继作》吴庆坻同作其三“闭门学枯禅,出门求友声。”(卷七)《玉胎羹以晚香玉花瀹竹孙汤清隽有味散原命此名》王乃徵同作:“惟诵西方教,须究六尘灭。贪着色香味,毋乃有习结。”瞿鸿禨《重九日同集乙庵海日楼完巢病起即次其近作五首韵》其五:“人生自古爱重九,佛法于今悲大千。”皆可视作同声相求,遗老们在易代之变后,通过佛教来获取心理平衡在诗歌中的一种表现。
浙派另一位重要诗人袁昶(1846—1900),也一样喜欢在诗中用佛典。如前所述,王蘧常《年谱》甚至认为沈曾植的耽于内学,是受到了袁的影响。不管怎么说,袁接触佛教,应该比沈要更早一些,这从各自的诗集中可以看得出来。不过两人的交往,其实远早于庚寅(1890)。《沈曾植年谱长编》光绪七年辛巳(1881),“十月二十三日(12月14日),袁昶来访。”并引是日《袁昶日记》:“暮访沈子培、子丰兄弟,此亦今之王逢原、深父也。”金天翮《再答苏堪先生书》,称袁诗“能从山谷溯太白,而得蒙庄之神。凡艺事有独至,必真率互见,乔松怪石,不掩其丑。渐西好用道藏佛典,乃为累耳。”[9]卷十其实袁昶的诗歌造诣很深,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三以为“樊榭、定庵两派,樊榭幽秀,本在太初之前;定庵瑰奇,不落子尹之后。然一则喜用冷僻故实,而出笔不广,近人惟写经斋、渐西村舍近焉;一则丽而不质,谐而不涩,才多意广者,人境庐、樊山、琴志诸君时乐为之。”袁昶的佛理诗,意境幽寒,清新脱俗,真实地体现出他在仕与隐之间徘徊的矛盾心态 。[10]而“法不孤起,仗境方生”,[11]自序可以说一直是他的诗学祈向,与沈曾植的意、笔、色之论,正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在用典方面,则又不如沈诗那么密集,而多了一份清静与流利。
其较偏于说理者,如《渐西村人初集》[12]卷四之《刘石庵相国有谈禅杂咏戏和其八题》之《观我诗》,论生、老、病、死:“生非汝有物常撄,脆似甘蕉只暂荣。知否诸天方便力,坚牢须向止观生。生”“雪里山看绀发皤,风来面皱亦观河。如何驻景丹丘诀,偏说收功一溉多。老”“道人示病即无衣,日减支离旧带围。到底蒙庄能作达,柳生肘喜客将归。病”“怪见壶邱似湿灰,月逢纳乙亦轮回。友人庄中白言:易气最重消息。《参同》云:节尽相禅与,继体复生龙。悄剥入川,息复出震。观此似大转四轮之说,良非无因。三番多事鸠摩咒,笑荷刘生一锸来。死”多有融通释道之语。又如《至人》:“世缘常有焚和厄,道术便于断际归。莫误千金礜作散,勿为五技鼠张机。何须辟谷追黄石,不待穿云入翠微。但守至人真诀在,非真非俗两无讥。”[12]卷七《戏题扑不倒翁》其一:“是翁造请应不妄,荣辱都将物论齐。谁谓眼前行路窄,充然试隐一丸泥。”[11]丁《夜读寒山大士集》:“得道者如麻竹苇,经声汹涌波涛中。亦有奔蜂化藿蠋,试拈弦索送归鸿。道人手未入麈尾,倦仆头已触屏风。块然槃特亡一句,灯花爆落荼毗融。”[11]巳
至于那些“写萧寥独往之趣,寄虚己游世之指”[13]自题词的诗作,更多是情、景、理交融之作。如《西湖杂诗时居孤山下诂经精舍》其十之:“日荡云成水,湖明艇接天。兴来成独往,佳处辄参禅。”[12]卷二《游烟雨楼三首》其二:“垒空出天籁,圆灵纳虚镜。动摇青颇黎,一水含一性。”[12]卷五《邻寺》:“梦回月淡树阴移,微钟忽度青松枝。苍茫危坐不肯曙,兔角焦芽何所思?”[12]卷十《夜起》:“欲知兀兀腾腾趣,只在萧萧黯黯间。寒角鸣陴鸡唱卯,梦回一枕富春山。”又如《独游华严寺》:“衰王不常嗤桔梗,世身皆脆悟芭蕉。独寻疏磬穿林至,小住芒鞋远市嚣。经叶蠹穿僧废律,花光凌乱客攀条。呼僮沽酒日西去,绿荔支携春一瓢。”[11]丙《爰居》:“爰居真讬避风乡,截鹤怜凫孰短长。用事军中非葛亮,为工柱下有东方。无端造化小儿困,何处波罗提木参。一刹那间心土净,侯封蚁穴两俱忘。”[11]庚《答和子培》:“入春禅病皆诗病,客慧顽空总未删。忽枉新篇动寥廓,入晞家行得原颜。眼花已废钞书课,足茧浑无作吏闲。只欲低头拜东野,逃虚伐翳藉追扳。”及《九月十二日又至皖口》:“枞阳江畔清可怜,何处射蛟台屹然。浮空楚岫不断碧,映水吴枫无数鲜。腐儒谁请尚方剑,学佛犹赊离欲天。自恨持戒律太浅,不办了界内因果,何敢更望出界外因果。风尘琭琭插手版,夜望北斗阑干悬。”[13]卷三玄理、佛理,忧世之心、出世之心,打并作一气也。
浙派另一位代表诗人金蓉镜(1856—1929),学诗于沈曾植,也邃于佛学。其《潜书·说佛》三篇,①此书刻于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八辑第十五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影印。期于打通儒佛,而达到世界大同。中且多有谈论佛教与科学的,可谓用现代思维来观照佛教之较早者:“其言天眼也,能辨水中微生物,即今之显微镜。佛以专精炼目,西人以专精炼镜,其理一也。其言处胎也,穷尽一千九节,八万户虫,今之图生殖器合。信氏以剖解得之,佛以炼性明之。其言四天下,即今之五大洲,详于邹衍之谈。其言百亿世界,即今之言行星天、恒星天,工于璇机之察。悬断于千载之上,而千载下应之,非圣能之乎?”(《说佛上》)沈曾植曾叮嘱金蓉镜除元祐、元和外,要努力打通元嘉一关,可见沈认为金除了学习宋诗派的学人之诗外,于晋宋之玄理、山水诗,还要更加著力。金蓉镜《论诗绝句寄李审言》其九云:“乙翁硬句接朱翁谓竹垞,不怕新来火雨攻。未到昆仑谁信及,中天原有化人宫。乙庵师论诗,不取一法,不坏一法,此为得髓。即竹垞诗不入名家意同一关捩。”[14]卷二又有《和乙庵师自寿诗》其三云:“推情合性是玄关,无得无名心地闲。佛法眼前观自在,先生胸次没遮拦。”[14]卷三评述乙庵诗法,称颂乃师,亦浙派之后劲也。
[1]王蘧常.清末沈寐叟先生曾植年谱[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
[2]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钱仲联.沈曾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1.
[4]钱仲联.海日楼札丛[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5]钱仲联.当代学者自选文库·钱仲联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6]钱仲联.沈曾植海日楼佚序:下[J].文献.1991,(1):175-185.
[7]钱仲联.沈曾植未刊遗文:续[J].学术集林,1995,(3):116-117.
[8]钱仲联.陈衍诗论合集[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9]金天翮.天放楼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0]孙之梅.袁昶的仕隐困境与“玄又玄”诗歌风貌[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134-138.
[11]袁昶.安般簃诗续钞[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2]袁昶.渐西村人初集[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3]袁昶.于湖小集[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4]金蓉镜.滮湖遗老集[M].民国 17年(1928)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