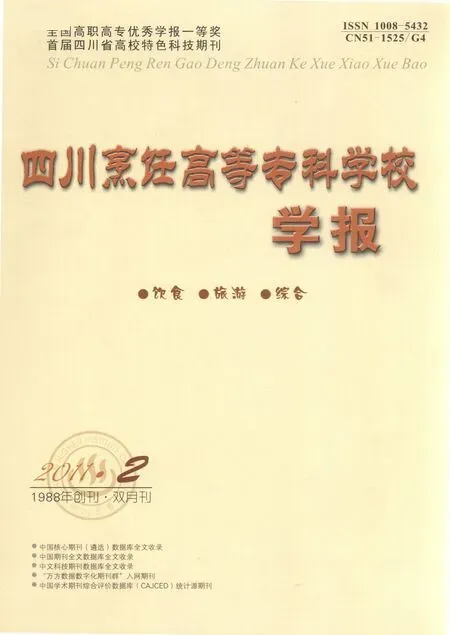四部分类法源于郑默《中经》说详证
夏红兵
(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四川 成都 610100)
中国传统文献自《隋书·经籍志》正式确定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名称和顺序以来,唐、宋、明、清诸史的艺文志或经籍志等史志书目,唐代元行冲、殷践犹、毋煚等编的《群书四部录》、北宋王尧臣、欧阳修等编的《崇文总目》等官修书目以及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等私家书目,分类多依四部,只因图书的增加,子目变动较大,清纪昀等所撰的《四库全书总目》钦定成书后,四部分类法成为中国目录学界整理文献的典范和标准。然四部分类法起于何时?源于何人?因文献记载语焉不详,学界理解差异,至今不能形成统一意见。笔者拟就此谈点个人看法,详细论证四部分类法源于郑默《中经》更为可信。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1 《中经》《中经新簿》编撰缘起
1.1 郑默《中经》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先有张角兄弟领导“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的黄巾起义,继之以军阀混战,尤其是董卓之乱,其后李傕、郭汜再乱,图书典籍遭受毁灭性灾难。隋代牛弘《请开献书之路表》曰:“及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汉末魏初,曹操一统北方,曹丕威逼汉帝禅让于魏,天下三分,曹魏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加之曹操父子喜好文学,致力文化典籍的收集,将文化整理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开始了继刘向父子校书之后对目录学乃至于文献学具有重大贡献的大规模图书整理工作。“魏国初建,(袁涣)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涣言于太祖曰:‘今天下大难已除,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以为可大收篇籍,明先圣之教,以易民视听,使海内斐然向风,则远人不服可以文德来之。’太祖善其言。”[1]曹操设秘书令,典尚书奏事,兼管秘记。曹丕即位后,以中书监、中书令代秘书令,在少府寺下专设秘书监,专掌艺文图籍,其正职为秘书监,副职称秘书丞,属官有秘书郎等。其中秘书丞协助秘书监统领官府藏书机构之各项事务;秘书郎中又称秘书郎,掌管图书的收藏及分判校勘、抄写事务。于是,“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2]。
1.2 荀勖《中经新簿》
景元四年 (公元 263年),魏伐蜀之役开始,郑默转为尚书考功郎,专典伐蜀事。秘书郎的职责是掌管皇家图书,故郑默所编《魏中经》应该在公元 263年前。公元 265年,晋王司马炎采取曹丕让汉帝禅位称帝的相同方式让魏元帝曹奂禅让帝位,西晋王朝建立,至公元 280年晋灭吴,三分天下的政治格局归于一统。终晋之世,以继魏为正统,晋武帝司马炎倡导各地呈献典籍,以充实政府藏书,凉州刺史张寔曾遣使护送图籍赴洛阳,各州郡亦纷纷响应,献书尤多。梁阮孝绪《七录序》记:“魏晋之世,文籍逾越,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文化建设的加强,为秘书监荀勖整理图书、编制书目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泰始十年,“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3]。于是有“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2]“魏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为朱紫有别。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馀卷,而总以四部别之”。[4]
2 四部分类法源于郑默之前贤论证
公元 290年,晋武帝司马炎卒,傻太子司马衷即位称晋惠帝。公元 291年,历时 16年的八王之乱爆发,五胡乱华、永嘉之乱旋踵,晋室无奈南渡,中国历史进入南北分裂、南北对峙、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文化典籍再次遭受毁灭性破坏。据隋代牛弘《请开献书之路表》记载:“属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永嘉之后,寇窃竞兴……宪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梁人阮孝绪,亦为《七录》。总其书数,三万余卷。及侯景渡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中经》《中经新簿》或因之散佚,四部分类法的起源亦成千古之谜,后人只能根据残存的文献资料的只言片语探究四部分类法的起源。总的来看,前贤讨论四部分类法起源问题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有四条:
其一,梁阮孝绪《七录序》:“魏晋之世,文籍逾广,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为朱紫有别。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
其二,《隋书·经籍志》:“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
其三,《初学记》卷一二引王隐《晋书》:“郑默,字思元,为秘书郎。删省旧文,除其浮秽,著《魏中经簿》。中书令虞松谓默曰:‘而今而后,朱紫别矣。’”
其四,《晋书》卷四十四《郑袤传》:“(袤子)默,字思元。起家秘书郎,考核旧文,删省浮秽。中书令虞松谓曰:‘而今而后,朱紫别矣。’”
基于这些史料,余嘉锡、王重民、王欣夫等先生认为,四部分类法源于荀勖《中经新簿》,理由如次:《七录》《隋志》均明确记载《新簿》分书为四部;郑默整理秘书,侧重于“考核旧文,删省浮秽”,虽著《中经》,但《七录》《隋志》均未说明其体例发生变化,则其仍然采用《七略》分类法;“因魏《中经》”只是“因”(承袭)郑默所著录的图书,而四部分类方法则为荀勖所独创。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基于相同史料,古有宋代杨亿、清代朱彝尊等大儒,今有汪国垣、来新夏、谢德雄、黄有铎等诸先生认为,四部分类法起源于郑默《中经》,强调荀勖是“因”郑默《中经》而编《新簿》,荀勖《新簿》以四部分类,郑默《中经》自然也是四部分类。简要介绍如下:
宋代杨亿《武夷新集》卷二十《与秘阁刘校理启》:“窃以中秘之府,实藏王者之书……薛夏建议,内外始分;郑默励精,朱紫斯别。既备三阁之制度,且列四部之籖题。”内外三阁始自薛夏,类分四部源流郑默之意必然也。清代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六十六:“刘歆之《七略》,郑默荀勖之《中经》《新簿》,其后四部七録,代有消长。”
汪国垣先生认为:“郑默《魏中经》之区类,尤难尽悉。但就阮孝绪《七录序》‘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一语推之,或四部分类之法,郑默已启其先。然则四部虽确定于李充,发韧于荀勖,而郑默《中经》之作,亦在筚路蓝缕之列矣。”[5]因此认定郑默《中经》已采用四部分类法。
来新夏先生认为:“据荀勖说,《中经新簿》主要是根据郑默的《中经》而纂。我们现在知道荀勖用的是四部分类。据此推断,《中经》很可能也是四部分类。”“所以说创四部之体始于郑默,立四部之名始于荀勘,定四部之序则起于李充”,[6]明确提出郑默《中经》,始创四部之体。
谢德雄先生认为:“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因者,因其成例也。魏称《中经》,晋称《中经新簿》,显系一脉相承。由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而推断郑默《中经》已用四部分类法,是比较合乎逻辑的。如果以《七录》《隋志》未言《中经》体例有所变更而断定《中经》仍沿用《七略》之法,似不足信。尤其是从‘荀勖《新簿》既行,默书遂废不用’来看,不但不能说明《中经》沿用《七略》分类法,相反,正好说明荀勖沿用了郑默的四部分类法,才使得《中经》没有必要再与《新簿》重复并存了”,谢氏更进一步指出:“魏时秘府藏书,多系卷轴,这种卷轴的书卷、书轶、书轴、书签、书带各以不同的颜色象征着书卷类别的不同。这是四部分类法出现以后书籍装治的重要特征。……汉时采用《七略》分类法时,因其书籍材料以竹、帛并用,无法以此方式统一装治书籍。因此,中书令虞松所说的‘而今而后,朱紫别矣’,正是指从此以后,四部分类法得以确定下来,足见郑默采用了四部分类法。”[7]
3 四部分类法源于郑默之新证
通过对史料的对比分析,结合图书版本源流情况,笔者认为四部分类郑默说更为可信。理由如次:
3.1 《中经》与《魏中经簿》《中经新簿》《晋中经簿》名称考
“中经”一词,始于三国魏郑默所撰《中经》,即郑默首先使用了“中经”一词,西晋荀勖《中经新簿》沿用“中经”一名。关于郑默编撰《中经》的具体史料,可追溯到隋秘书郎虞世南编《北堂书钞》卷五十七所引王隐《晋书》:“郑默,为秘书郎,删省旧文,除其浮秽,著《魏中经簿》。中书令虞松谓默曰:而今而后,朱紫别矣。”王隐,字处叔,陈郡陈人也,东晋史学家,《晋书》卷八十二记载:“太兴初,典章稍备,乃召隐及郭璞俱为著作郎,令撰晋史。”太兴初即公元 318年,其时距郑默编撰《中经》大约半个世纪,其描述“删省旧文,除其浮秽,著《魏中经簿》。中书令虞松谓默曰:而今而后,朱紫别矣”具有较高的可信性,故该史料后被唐代《初学记》卷十二《秘书郎第十一》、宋代《太平御览》卷二三三《秘书郎》、《玉海》卷五十二《魏中经》等广泛引用。然何以除《隋书·经籍志》外,历代典籍凡涉郑默所编书目,均称为《魏中经》或《魏中经簿》呢?
“中”是指“宫禁中”,“经”即经籍,本指儒家经典著作,泛指群书,“中经”本义为“宫禁中之经籍”,泛指宫禁中收藏的各类图书。秘书郎是三国魏始置官名,掌管图书经籍。魏初典籍凋零、图书散佚相当严重,从而出现了“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中外三阁”的情况,促成了秘书郎郑默奉命“删省繁文,除其浮秽”的文献整理编目工作,并最终形成国家藏书目录《中经》。《隋书·经籍志》作为隋朝史书中记载图书的专门目录,记载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情况,其将郑默、荀勖编撰的国家藏书目录的名称定为《中经》《新簿》应该是最正确的。至于《魏中经》《魏中经簿》、魏《中经》《晋中经》或《晋中经簿》等称呼,因荀勖编撰的《中经新簿》实为《中经》的新版本,魏晋之后的学界为相区别而名。这里,可由中国现代出版史得到佐证。
众所周知,《全国总书目》是国内唯一的年鉴性编年总目,由分类目录、专题目录和附录 3部分组成,1949年以来逐年编纂,收录全国当年出版的各类图书。其实,1935年生活书店出版过平心编的《全国总书目》,收录民国元年(1912)至 1935年全国各地书店、学术机关、学术团体、图书馆、研究会、政府机关等出版的图书约 2万种,然目前通过搜索中国国家图书馆书目数据库,却找不到这本书,只能找到平心编的《生活全国总书目》。[8]究其原因,是为了与建国后中国版本图书馆编辑的现行国家书目——《全国总书目》相区别,故对1935年平心编的图书冠名《生活全国总书目》。
3.2 《晋书·荀勖传》何以记载“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
西汉刘向、刘歆整理国家图书,图书数量多、种类全,“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内有延阁、秘书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汉之典文,于斯为盛……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2],故以集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类聚图书。东汉右文兴学,既广搜前朝典籍,又鼓励著述,“光武嗣兴,尤重经诰,未及下车,先求文雅。于是鸿生巨儒,继踵而集,怀经负帙,不远斯至。肃宗亲临讲肄,和帝数幸书林,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于前”。[2]东汉文献编校工作更是经常不断,东汉安帝永初四年 (公元 110年),“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后汉书 ·安帝纪》)。顺帝永和元年 (公元 136年),“诏侍中屯骑尉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后汉书·伏湛传》)。灵帝熹平四年(公元 175年)议郎蔡邕“与五官中郎将堂典……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后汉书 ·灵帝纪》)。“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2]班固、傅毅、崔骃等一大批学者文士先后受命典校秘书,“常以典籍为业,未遑仕进之事”(《后汉书·崔骃传》)。可见东汉一代典籍仍尊《七略》分类法为宗。
曹魏代汉,西晋代魏,均采用“禅让”方式,故曹魏直接承袭东汉、西晋直接承袭曹魏的官府藏书。然而汉末大乱,典籍散佚严重,西晋代魏前有灭蜀、后有灭吴,蜀吴典籍归于一统,加上魏晋文学繁荣,书籍急剧增长,故魏晋立朝后都将文献整理提上工作日程。魏秘书郎郑默《中经》因当时集部书急速增加,故将文人诗文集单独列为一类,并改刘向《七略》的六类为四类,“时之论者,谓为朱紫有别”[4]。晋秘书监荀勖受命整理典籍时,面临刘向、刘歆《别录》《七略》六分图书还是郑默《中经》所创的四部分类的选择,后荀勖“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3],反映了郑默《中经》所创的四部分类法实属删繁就简、甲乙编次的权宜之计,在晋朝初尚不为文献整理的主流文化所接受,因为四部分类法并非完全出于主观创新,而是郑默在整理曹魏官府藏书时,面对典籍散佚严重、编次无法完整的现状,在两汉以来的《七略》六分典籍的基础上,删繁就简、甲乙编次而成。
3.3 阮孝绪《七录序》中三“因”“更”释义
梁代阮孝绪《七录序》全文,共三处提到“因”字:“固乃因《七略》之辞,为《汉书·艺文志》……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删正,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自时厥後,世相祖述。”[4]对此,张固也先生认为:“序中三个‘因’字,用法实际上都不相同。班固《汉书·艺文志》不仅因袭刘歆《七略》的分类方法,而且删节‘辑略’附于各类之下为小序,撮取叙录的主要内容作为注释,这就是序中所说‘固乃因《七略》之辞’。李充则采用荀勖的四部分类法,又有所变通,这就是序中说‘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这两处都说得很清楚,一为因其辞,为因其分类。后者还明确地提到‘荀勖旧簿四部之法’,则荀勖为四部分类的创始人。”[9]唐明元先生认为:“西晋代魏,采取的是‘禅让’的办法,故西晋直接承袭了曹魏之官府藏书,《新簿》也必然而‘因’(承袭)《中经》所著录的图书。《新簿》之所能改者,惟《中经》之体例而已。”唐明元先生还就“更”指出:“就《七录序》‘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而言,似应理解为‘又’、‘再’之意,但就《隋志》‘又因《中经》,更著《新簿》’而言,则又不应释为‘又’、‘再’,盖前句之首用‘又’,后句之首也用‘又’义,似乎不符文法。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新簿》确实沿袭了《中经》之图书及分类法,依古人之行文简洁,《七录序》应为‘因魏《中经》而著《新簿》’,《隋志》则应为‘又因《中经》而著《新簿》’,二者皆无必要用一个‘更’字,分一句为二句。但二者皆将‘更著《新簿》’独立成句,说明此句意思非用‘更’字不能准确表达。笔者由此认为,此处之‘更’应理解为改、改变之义,‘更著《新簿》’则应为‘改著《新簿》’,方符作者之本意。”[10]其实不然,众所周知,一本图书,尤其是专业目录,不仅有内容,更能透过内容体现作者的指导思想,就郑默《中经》而言,不仅囊括了曹魏官府藏书,而且其藏书目录体系包含了郑默的典籍分类思想,故荀勖“因魏《中经》”指的是荀勖不仅“因”(承袭)《中经》所著录的图书,而且“因”(承袭)《中经》的四部分类体系。荀勖“因”(承袭)《中经》所著录的图书,也表明了西晋代魏,因采“禅让”方式而没有使曹魏官府藏书遭受损失,故荀勖只需对郑默《中经》编撰完成后西晋官府新增加的藏书作出整理即可,另一方面也解释了汲冢书何以作为整体分入丁部的缘故。至于“更”字,起于“因”字,荀勖不仅“因”(承袭)《中经》所著录的图书与《中经》秉承的四部分类体系,而且在此基础上收录了郑默《中经》编撰完成后西晋官府新增加的藏书,内容上相比《中经》更为丰富,“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中经》经过修订成为《新簿》,故曰“更著”,其实,荀勖《新簿》就是现代版本学上的《中经》修订版,故《隋书·经籍志》“始制《中经》……又因《中经》,更著《新簿》”总说《中经》的版本源流问题,而不存在唐明元先生所谓的“似乎不符文法”问题。所以,《隋书·经籍志》“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这段话明确了三个问题:首句点明曹魏代汉后的官方典籍收集工作;次句说明典籍收集后的藏书整理即《中经》版本源流及总括介绍;第三句详细说明整理藏书所依据的分类方法。
3.4 《晋太康起居注》等史料佐证
除前文所引史料外,四部分类法源于郑默《中经》说还能从《北堂书钞》卷五七、《初学记》卷一二、《太平御览》卷二三三所引《晋太康起居注》曰:“秘书丞桓石绥启校定四部之书,诏遣郎中四人各掌一部”、《通典》卷二六:“晋秘书郎掌中外三阁经书,校阅脱误。……武帝分秘书图籍为甲乙丙丁四部,使秘书郎中四人各掌其一”等重要记载中找到佐证。秘书丞是秘书监副手,主要协助秘书监统领官府藏书机构之各项事务,如果荀勖校勘记籍群书、编撰新簿、创始四部分类法已经完成,太康年间秘书丞桓石绥就不可能再建议校定四部书,只能说明荀勖“更著《新簿》”前四部分类法已经产生,需要把郑默《中经》后晋朝皇室新典藏的书籍按四部分类予以分判校勘,于是,“武帝分秘书图籍为甲乙丙丁四部,使秘书郎中四人各掌其一”进行各部图书的收藏及分判校勘、抄写。
总之,通过对史料的史源考察和词语语意环境的比较分析,四部分类法应起源于郑默《中经》,确定于荀勖,完成于李充。
[1]陈寿.三国志[M].长沙:岳麓书社,2004.
[2]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阮孝绪.七录序 [EB/OL].(2009-03-15)[2010-12-20].http://www.b log.sina.com.cn/s/b log_ 4e6 fd5c7010090qh.htm l.
[5]汪国垣.目录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6]来新夏.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概要[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7]谢德雄.魏晋南北朝目录学的新起点[J].学术月刊,1983(10):56-63.
[8]国家图书馆联机目录公共系统[EB/OL].(2010-09-02)[2010-12-20].http://opac.n lc.gov.cn/.
[9]张固也.四部分类法起源于荀勖说新证[J].图书情报知识,2008(5):69-73.
[10]唐明元.四部分类法之起源辨析[J].图书馆杂志,2005(9):7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