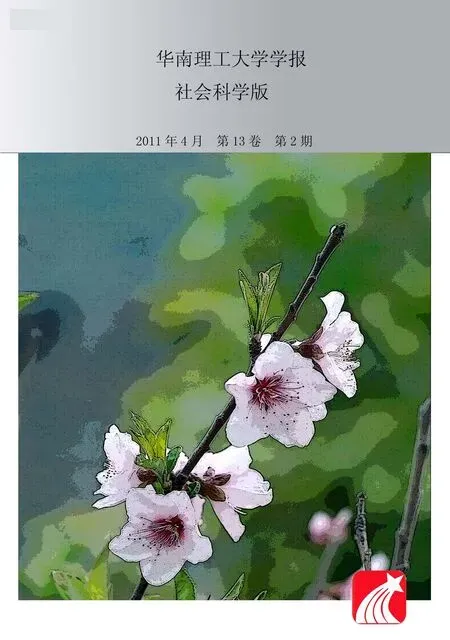论实质因素在法官程序思维中的选择功能及其约束*
冯健鹏
(华南理工大学 法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一、 问题的提出:“选择”作为沟通程序与实质的桥梁
法律思维可以描述为“依循法律逻辑, 以价值取向的思考、 合理的论证, 解释适用法律”[1]1的活动, 这是法律专业性的重要基础; “像法律人一样思维(think like a lawyer)”长期以来都是对法律初学者的谆谆告诫。[2]39虽然学界和实务界对于法律思维的内涵有不同观点, 但一个基本共识是: 围绕法律程序的思维活动在法律思维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法律程序思维的重要性是与程序在近现代法治中的重要地位密切相关的。“程序是法律的中心”,[3]73这已成为近现代法治的基本命题。追根溯源, 法律程序和法律程序思维的发展, 都是基于法的形式化, 也就是韦伯所说的“形式理性”的法律: 这里的“形式”是指“法律判断的规则与程序均于法律体系中可以寻得, 无假外求, 只要以意义的逻辑分析, 运用高度抽象的法律概念, 即可获得法律判断”[4]41——在法律“形式理性化”的过程中, 一方面, 对于传统司法程序的严格遵循使得法律的形式性不断增强; 另一方面, 法律的形式化也令法律程序大为发展。[5]216-226法律程序思维是法律思维的基本特征, 也是近现代法治发展的重要成果。
但不应忽视的是, 作为“形式”对立面的“实质”, 在法律思维中也具有重要作用。尽管传统的实质思维, 即在法律思维中只考虑实质因素——“道德、 经济、 政治、 体制或其它社会因素”[6]1——的思维方式, 通常被认为是“轻视法律的形式、 手段和过程”、 “轻视法律活动的技术形式”、 “轻视法律内的逻辑”而在司法中受到诟病;[7]但需要明确的是, “实质思维”与“实质因素”是不同的: 前者是思维方式, 后者是思维过程所涉及的对象。前者与现代法治存在龃龉, 但后者则是法律思维过程中不可避免要考虑到的因素。更重要的是, 在现代社会的思维样态中, “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一方面是对立的关系, 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统一在“理性”这一概念之下;[8]226-227换言之, 对于法律思维来说, 无论是考虑实质因素还是程序因素, 这种考虑都是理性的——这是实质因素能够在程序思维中发挥作用的基础, 也是本文的出发点。
同时, 在我国的实践中, 随着近年来提倡“司法能动与能动司法”、 强调“人民性”等要求的提出, 司法又不得不再度注重各种实质因素。那么, 如何令这一趋势形成真正有益于法治的“否定之否定”、 避免单纯的“穿旧鞋、 走老路”, 就成为必须正视的问题。从法律思维的角度来说, 要做到这一点, 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 不回到传统的实质思维, 而应当在程序思维的框架内, 重新审视实质因素的作用。
本文集中关注实质因素在程序思维中的选择功能。这是因为: 在“程序”与“实质”的论辩中, 程序主义屡被攻击的一个软肋就是“遵循程序本身就是一个实质性的选择”;[9]但假如不将“程序”与“实质”截然对立, 那么这个被指摘的“实质性的选择”反倒能够成为沟通“程序”与“实质”的桥梁; 而对于程序思维过程来说, “实质性的选择”在许多地方都有所体现——可以说, “选择”是实质因素影响程序思维的基本途径, 因此也成为分析实质因素在程序思维中所起作用的切入点。
由于法律程序思维最初是对法律职业思维的描述, 并且司法一直是法律程序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 在司法领域中对实质因素的强调又是法官首当其冲; 所以, 本文选择法官作为考察对象, 以司法诉讼为场域, 以期进行较为深入且有针对性的探讨。
二、 实质因素在法官程序思维中的“选择—约束”形态
按照程序思维的一般过程, 以下分别从启动、 运行和结果反馈三个环节加以考察; 除了着重考察实质因素在这三个环节中不同的选择样态之外, 另一个考察重点在于各种具体的选择样态所受的约束, 以“选择—约束”的框架分析实质因素在法官程序思维中的选择功能。
(一)程序启动时的选择与约束
一般来说, 司法程序的启动有两种情况: 一是法定的, 如刑事诉讼程序, 符合法定的实质性条件即应当启动; 一是意定的, 相关主体有选择的余地, 如通过司法程序催讨债务, 债权人可以选择启动民事诉讼程序, 也可以选择启动民事调解程序。意定的司法程序的启动, 相关主体显然要考虑很多实质因素。
那么,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法官应当在程序启动环节考虑实质因素吗”?
传统上, 司法的被动性要求“不告不理”, 否则法官就会被视为因主动介入而丧失了公正的立场, 这就直接否定了法官在程序启动环节考虑实质因素的可能性。而被认为是在某些方面突破司法被动性的“司法能动”, 如美国的沃伦法院,[10]195-201也没有在“不告不理”方面有所突破; 甚至是被认为比“司法能动”更为“能动”的“能动司法”, 也仍然主张“……把被动性视为司法自身的规律, 这从‘不告不理’……来看有其一定的合理性”[11]——换言之, 法官在程序启动环节没有任何考虑实质性因素的余地, 也就无所谓选择了。
(二)程序运行时的选择与约束
司法程序运行时的法官思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其中既有传统的形式推理, 也有对各种可能冲突的因素的考虑, “逻辑的、 历史的、 习惯的、 道德的、 法律的确定性和灵活性、 法律的形式和实质等等”[12]4——这个在充满了实质因素的环境中进行取舍与平衡的过程, 就充分地体现了实质因素的选择功能。基于对司法过程“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的要求, 法官的思维可以分为认定事实和认定法律两个方向:
首先, 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思维过程也就是选择证据的过程, 而实质因素在其中所起的选择功能则与相关的证据制度有密切关联, 其中的区别主要源于规则主义和自由裁量主义的分野, 在思维上体现了“通过人的有限理性在复杂多样的社会现实中最大限度地发现案件真实”和“人的有限理性与人性弱点可能造成权力的滥用进而导致司法不公”之间的平衡。大体而言, 大陆法系国家的自由裁量主义较盛, 乃至普遍采用自由心证制度; 而英美法系国家则较注重规则主义, 发展出相对严格的证据规则[13]17-18——结合相关制度可以发现: 自由裁量主义或自由心证并不意味着实质因素可以在法官头脑中恣意驰骋, 严格的证据规则也不意味着全无实质因素的活动空间。相反, 在这两类制度中, 实质因素都在程序的约束下发挥选择功能, 只是约束的方式有所不同: 在自由心证制度下, 法官可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相对自由的判断, 但证据的收集和提取有严格的程序控制,[14]而必须“遵循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和“心证公开(尤其是心证理由公开)”的程序要求更是对法官思维中实质因素选择功能的直接约束;[15]在严格证据规则之下, 通过陪审团制度和对抗制的设置, 将实质因素的选择主体在很大程度上从法官转移到了陪审团的身上, 并且通过相关的程序对陪审团的选择过程加以直接的约束, 并通过明确的证据规则对其加以间接的约束。[13]18
其次, 在认定法律方面, 实质因素的选择作用主要表现为法律解释的过程中, 法官基于对实质因素的考虑而对法律方法的取舍。认定法律时实质因素的选择功能表现在两个层面: 第一是对于解释方法的选择; 第二是在采用某种解释方法时, 对于可能存在的多种解释结果的选择。
在第一个层面即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上, 需要明确的是: 法律解释的各种方法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考虑实质因素的空间(即存在法官进行价值判断的空间), 但不同的解释方法中存在的这种空间大小是不同的。例如, 文义解释和探究“立法者原意”的方法, 实质因素的作用空间较小; 而比较法解释和社会学解释, 实质因素的作用空间则较大。因此, 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 本身就是一种实质性的选择。不过这种选择受制于法律解释方法的适用规则, 例如文义解释(实质因素作用空间最小的解释方法)是法律解释的出发点, 只有文义解释难以奏效时才能考虑其他解释方法; 社会学解释一般只能适用于“经解释存在相互抵触之解释结果, 且各种解释结果均言之成理, 持之有据时”; 而除非出现明显不公正的情况, 否则不允许作出“反于法条文义的解释结论”。[16]245-246但是这种适用规则并不存在严格的位阶关系, 主流观点对此采取折中的立场, “不认为各种解释方法具有一种固定不变的位阶关系, 但亦不认为解释着可以任意选择一种解释方法, 以支持其论点”——[1]240换言之, 实质因素在这一层面的选择功能, 必须在这种具有一定客观性的适用规则之下展开。
在第二个层面即在同一种法律解释方法下对可能的多种解释结果的选择。这种选择尽管也受前述某些适用规则的约束, 例如解释结果原则上不得“反于法条文义”, 但总体而言, 在同一种解释方法之下, 前述适用规则可应用的范围较窄, 对于法官解释中实质因素进行选择的客观性约束也就随之较少。但既便如此, 这种选择仍然要遵循法律解释的一般思维要求, 即要明确“法律解释是一个以法律意旨为主导的思维过程”,[1]240而所谓“法律意旨”或“法律目的”, 既涉及到立法者的意志, 也涉及到法律(包括具体的法条规范)在整个法律体系中、 乃至整个社会体系中所应起到的作用。其中, “立法者意志”的客观性较强(尽管根据公共选择理论, “立法者意志”被消解在每个立法参与者各自不同的选择理由之中, 并不存在单一的“立法者意志”[17]); 而“法律的作用”则免不了混入更多的法官主观上的价值判断(即对于实质因素的选择)。但即使承认这种实质因素选择空间的存在(即“法律解释的主观性”的存在), 还是可以通过立法的科学性与民主性、 法官素质(职业技能与职业伦理)和审判制度等因素来确保法律解释最基本的客观性[16]186-188——换言之, 实质因素在这一层面的选择空间较大, 但仍然要受上述因素的约束。
(三)结果反馈时的选择与约束
司法程序的结果反馈就是用什么标准来评价司法裁判。当然, 裁判一旦公开, 社会各方都会对其作出自己的评价; 这里关注的, 是法官对自己所作裁判的评价标准的选择。
这类评价标准的具体内容有多种观点, 在实践中也不尽一致; 但在种种具体的内容中可以发现两个基本的标准类型, 即法律标准和社会标准: 前者强调裁判需要符合法律规定; 后者则强调裁判需要符合某些社会标准(如经济发展、 社会稳定、 人民满意等)——显然, 法律标准下对于实质因素的选择余地较小, 或者说, 这种选择很大程度上在法律解释环节已经完成了; 社会标准则因为其抽象性和广泛性而令实质因素的选择具有几乎无限的可能性。当然, 即使是社会标准的支持者, 也不会完全否认“裁判需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基本要求; 但是在个案中如果过于强调社会标准, 则很容易令法律标准成为次要的、 可替代的东西。
但是, 在理论上, 法律标准与社会标准并非截然分立的; 相反, 法律标准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形态的社会标准: 只要司法裁判所依据的法律是循民主程序制定的, 那么在各种社会标准自然会在法律中体现出来, 符合法律标准也就符合了这些社会标准;[注]当然也存在例外, 比较典型的两种情况是: 社会上长期处于弱势的群体难以通过选举和立法的民主程序参与法律制定, 使得法律忽视了这些群体的利益与诉求; 由于比较重大的社会环境的变化, 原先制定的法律已经难以适应新情势的要求——不过, 这些情况都可以在法律解释环节加以处理。同时, 法律所具有的明确性、 一致性、 可预见性等属性, 本身也是有益于社会秩序的——所以, 法律标准与社会标准的选择, 对于法官来说, 其实就是: 究竟是把实质因素的选择放在裁判过程中的法律解释环节、 依据一定的法律方法和法律程序作出(即选择法律标准), 还是把实质因素的选择放在裁判确定之后、 在几乎无限的具体标准中作出(即选择社会标准)?
应当说, 裁判确定之后仍然存在的对于裁判结果进行评价的过多选择对于司法而言并非好事。究其根本, 司法权只是一种判断特定行为究竟是合法还是非法的判断权,[18]这是由法治的要求、 司法的性质、 法律职业的技能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因此, 让法官不得不于裁判之后再选择法律之外的因素(甚至是法官在裁判时无法预见到的因素)对其判断再进行判断, 实在是不可承受之重——当然, 这并非否定社会标准的必要性, 而是在符合法律标准的前提下实现法律标准与社会标准的统一(这与在符合社会标准的前提下实现两者统一是完全不同的); 也就是将法官在程序反馈时对于实质因素的选择最大限度地前置于法律解释环节, 从而对其间接地加以约束。
三、 约束实质性选择的机制
前文考察了实质因素在法官程序思维各个环节中的“选择—约束”形态, 而这些不同的形态又会深刻地影响法官的思维过程乃至整个司法过程。因此, 有必要深入思维的背后, 对约束实质性选择的机制做一番考察。以下根据与思维过程的关系, 分别从三个层次对三类常见的约束机制进行考察: 首先是法官职业伦理, 这是法官思维的组成部分; 其次是司法证据规则和法律解释规则, 这是法官在个案的思维过程中需直接考虑并直接体现在思维结果(如判决书)中的因素; 再次是法官的教育、 选任和奖惩制度, 这些虽然无需法官在个案中直接考虑, 但会在更为基础的层面左右法官的思维过程。以下分别考察:
(一)法官职业伦理
这里所说的法官职业伦理, 除了一般性的内容(如“以正义感为核心的法官人格”[16]188)之外, 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例如法官不应介入政治问题、 法官应当对立法权保持最大限度的尊重等, 都直接影响了法官在思维过程中对实质因素的选择。这种约束最为典型的就是在法律解释环节, 体现为对法律解释中法官的价值判断和主观性的抑制; 但在其他环节或多或少也会有所体现。
尽管职业伦理与职业制度和职业利益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但法官职业伦理的运作过程本身是法官思维的组成部分, 所以其对于实质因素选择功能的约束作用也体现为法官思维的内在活动, 是一种受外在影响最小的机制。
(二)司法证据规则和法律解释规则
司法证据规则和法律解释规则虽然一者针对事实问题、 一者针对法律问题, 但都是在司法程序运行时对法官实质性选择进行的约束; 更重要的是, 两者都体现为一种具有客观性的规则——当然, 在不同的法律体系中, 这种客观规则的具体内容在明确性程度上会有不同, 但是它们对法官选择实质因素的约束机制是一致的, 即为法官在程序运作中提供直接的指引, 从而减少其进行实质选择的可能性、 或者对这种实质选择进行约束。
与法官职业伦理相比, 司法证据规则和法律解释规则对于法官实质选择的约束, 受外在影响较大, 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 司法证据规则和法律解释规则的制定或形成, 对于法官思维来说, 本身就是外在的; 其次, 法官在思维过程中对司法证据规则和法律解释规则的运用必须体现在司法文书中, 这使得法官对这些规则的运用较易受到来自外部的评价。
(三)法官的教育、 选任和奖惩制度
法官的教育、 选任和奖惩制度可以被视为共同约束(甚至决定)法官思维方式的三个环节: 法官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法官思维方式的基本框架, 法官的选任制度决定了具有怎样思维方式的人能够成为法官, 而法官的奖惩制度则影响到法官在具体案件中的思维方式——所以, 这些制度当然也会对法官思维中的实质选择产生约束。但是, 这种约束既非法官思维的组成部分, 也非法官思维过程的直接指引, 而是通过利益和权力的配置、 对法官行为进行调节。这对于法官思维而言是一种完全外在的约束——也正因为如此, 与前两种机制相比, 法官的教育、 选任和奖惩制度是受外在影响最大的。
正如本文一开始所强调的, 无论是考虑实质因素还是程序因素, 这种考虑都是理性的, 这也是考察相关机制的基础——当然, 在法官的思维过程中, 并不能完全排除非理性的因素, 但这种因素通常被认为是消极的, 对程序和实质都没有助益。因此, 无论是实质因素的选择还是对这种选择的约束, 都是以尽可能消除思维中的非理性因素为取向的, 这也是“选择”和“约束”这两个对立的机制能够在法官的程序思维中得以统一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 可以发现: 即使在以程序为导向的思维过程中, 也不可能完全排除实质因素的存在, 仅就“选择”一项功能而论, 就在程序的各个环节以不同的面目存在着(虽然在程序启动和程序结果反馈环节, 这种实质因素的选择未必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程序的意义在于对这些实质因素进行约束, 将其限制在既能发挥作用、 又不致被滥用的程度。
思维活动虽然是主观的, 但约束思维活动的机制却是客观的, 这是实质因素在法官程序思维中的“选择—约束”形态的基础。对思维的约束机制是多种多样的, 就法官思维而言, 这种约束可以存在于思维活动内部, 也可以完全外在于思维活动, 还可以介于两者之间——这种约束机制的多样性, 决定了对实质因素“选择—约束”形态的调节手段也是具有多样性、 不可一概而论的。因此, 只有充分尊重司法运作和思维运作的规律, 妥善地采用多种手段加以引导, 才能发挥实质因素在程序思维中的积极作用, 推动法治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泽鉴. 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 [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2] Michael H Frost.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Legal Rhetoric: A Lost Heritage [M]. Farnham, Surrey: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5.
[3] (美)P·诺内特, P·塞尔兹尼克. 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 迈向回应型法 [M]. 张志铭,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4] 陈聪富. 韦伯论形式理性之法律 [M]// 许章润. 清华法学(第2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33-61.
[5] (德)马克斯·韦伯. 韦伯作品集IX·法律社会学 [M]. 康乐, 简惠美,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6] P S Atyah, Robert Summers. Form and Substance in Anglo-American Law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7] 孙笑侠. 中国传统法官的实质思维 [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4): 5-12.
[8] 苏国勋. 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9] Laurence H Tribe. The Puzzling Persistence of Process-Based Constitutional Theories [J]. Yale Law Review, 1980(5): 1063-1080.
[10] (美)霍维茨. 沃伦法院对正义的追求 [M]. 信春鹰, 张志铭,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11] 贺小荣. 王胜俊在江苏法院调研并与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座谈时强调 能动司法是人民法院服务大局的必然选择 [N]. 人民法院报, 2009-09-01 (01).
[12] (美)本杰明·卡多佐. 司法过程的性质[M]. 苏力,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13] (美)约翰·W·斯特龙. 麦考密克论证据 [M]. 汤维建,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14] 何家弘, 姚永吉. 两大法系证据制度比较论 [J]. 比较法研究, 2003(4) : 55-68.
[15] 魏凤娟. 论自由心证的“自由”与“不自由” [J].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09(6): 16-21.
[16] 梁慧星. 民法解释学 [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17] Frank H Easterbrook. Text, History and Structure in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J].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1994(1): 61-68.
[18] 孙笑侠. 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十大区别 [J]. 法学, 1998(8) : 3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