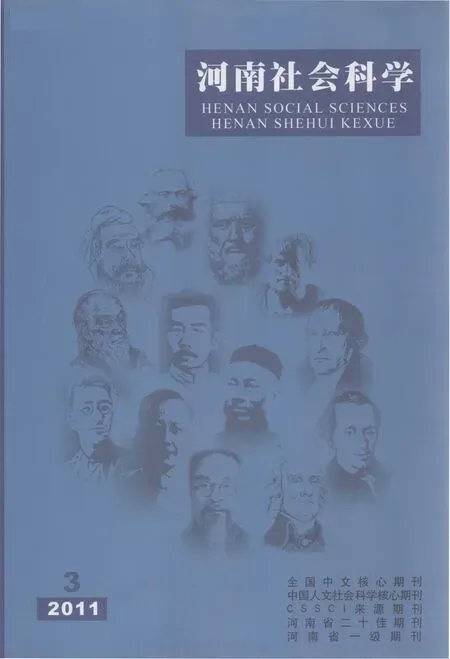列宁民族殖民地学说与中共国际战略关系解读
胡运锋
(安阳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2)
列宁民族殖民地学说与中共国际战略关系解读
胡运锋
(安阳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列宁民族殖民地学说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了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发动人民战争、联合英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独立自主地领导本国革命的国际战略,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
列宁;民族殖民地学说;中国共产党;国际战略
列宁民族殖民地学说,是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何通过民族民主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并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理论,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摆脱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思想武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国情出发,坚持把列宁民族殖民地学说同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特征相结合,制定了一条成功的国际战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一、中国共产党依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思想,做出了加入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决策
列宁曾经指出:“要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尽可能更确切地了解:可以同谁一起战斗,谁是可靠的同盟者,真正的敌人在什么地方。”[1]而“先进阶级只有客观地考虑到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到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到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据以制定正确的策略”[2]。它告诉我们,要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就必须首先对本国所处的时代特征和国际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分清敌友。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侵略扩张,在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扩张下,整个世界逐渐分成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少数几个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3]。同时,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给人类带来了不尽的战争灾难。战争必然引起革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下,被压迫民族掀起了一系列反抗侵略和压迫的民族民主革命。1917年爆发的十月革命,是人类近代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它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标志着人类开始进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因此,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当时的时代特征。
十月革命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它“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4]。从此,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东方被奴役民族之间的命运,由于反抗帝国主义这个共同的目标而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欧洲大战及其结束清楚地表明,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集中化,欧洲以外的被压迫国家的人民群众同欧洲无产阶级的运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5]。西方无产者和东方被压迫民族要完成自己的革命任务,就必须团结起来,建立巩固的联盟,相互支援,互相配合。一方面,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离不开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支持。“俄国人开创的事业,将由英国、法国或德国的无产阶级来巩固;但是我们看到,没有各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援助,首先是东方各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援助,他们是不能取得胜利的”[3]。另一方面,东方各民族革命运动的顺利发展,离不开西方无产者的帮助。“东部各民族的革命运动,目前只有和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直接联系起来,才能顺利地发展,才能有所成就”[3]。列宁认为,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按其性质来说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其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和国际资产阶级,因而不能不卷入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潮流,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都是对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支持和加强。因此,“我们应当把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同民族问题的革命纲领联系起来”[6]。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人民面临着反帝反封建的双重革命任务,要完成这个艰巨的革命任务,首要问题就是分清敌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7]。毛泽东认为,就国内来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7]。就国外来说,一切侵略奴役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以苏联为主要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社会主义的人民,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政治家、劳动者,才能真正援助;而我们的事业,没有他们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8]。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按其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8]。因此,为了完成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中国人民必须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实行一边倒。“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9]。
中国共产党关于倒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抉择,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赢得了宝贵的援助和支持,也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指明了方向。
二、中国共产党依据列宁关于唤醒民众能够创造战争奇迹的思想,成功实施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任何反动力量都是渺小的。因此,只要先进的阶级和政党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一切貌似强大的反动力量都是可以战胜的。
在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面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动分子的武装叛乱,列宁丝毫不被表面强大的敌人所吓倒,他以战略家的气魄把帝国主义称做“空架子”,把“称霸世界”的英法帝国主义视作是“泥塑巨人”。他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发动民众、组织军队,顽强抗敌,最终打败了国内外敌人,巩固了新生政权。实践证明,“革命战争如果真正吸引被压迫劳动群众参加并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使这些群众意识到自己是在同剥削者作斗争,那么,这种革命战争就会唤起创造奇迹的毅力和才能”[3]。1919年11月,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俄国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向东部各族人民表明:尽管这些民族非常弱小,尽管欧洲那些压迫民族在斗争中采用了种种奇迹般的技术装备和军事艺术,似乎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但是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革命战争如能真正唤醒千百万被剥削劳动者,就会显示巨大的力量,创造奇迹,使东部各族人民现在完全可以实现解放”[3]。列宁关于发动民众、不畏强敌的思想,极大地增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领导本国人民战胜国内外强敌的信心。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在半壁河山落入敌手、日本帝国主义气焰不可一世、国内统一战线和党内思想极度混乱的情况下,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敢于侵略中国,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处于无组织状态。因此,只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8]。他向那些视敌人为神物、视自己为草芥的亡国论者回答道: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团结统一,一致对外,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以绝对优势兵力、物力大举进攻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当时,敢不敢打和能不能取得胜利,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广大人民中间,甚至中共党内,都存在着能否打败蒋介石的疑问。一些中间派则对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抱有极大幻想,就连同情中共的苏联也担心中国内战将影响世界和平,导致新的世界大战。斯大林在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甚至指出:如果中国内战爆发,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眼光和气魄指出:“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9]1946年8月,在中国内战全面爆发后刚刚两个月,毛泽东就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豪迈地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9]。“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9]。人民的“小米加步枪”,将会比他们的飞机和坦克还要强。毛泽东镇定自若和充满必胜的态度与口气,让这位美国进步作家激动不已,当她听到“纸老虎”这个词时,更是为毛泽东傲视强敌的气魄所折服。仅仅隔了三年多的时间,毛泽东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中国人民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关于组织民众战胜帝国主义的战略思想,不仅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民战胜国内外反动派的强大精神武器,也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国际关系中确立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外交方针奠定了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依据列宁关于利用敌人之间“裂痕”的思想,建立了联合英美的抗日国际统一战线
在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革命过程中,西方无产阶级及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遇到的敌人不仅十分强大,而且,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既得利益,资本主义国家还结成了反革命联盟,这无疑增加了革命胜利的难度。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并不是铁板一块,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力量和地位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由此必然导致它们之间在瓜分世界、掠夺资源、抢占市场问题上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无产阶级必须充分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壮大革命力量。列宁指出:“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种类别之间利益上的一切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3]
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德、意、日等国上台并实行了疯狂的对外扩张政策。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扩张,不仅加深了这些国家同苏联、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矛盾,而且也使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受到侵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出现了“裂痕”。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待帝国主义的政策也进行了调整,从过去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开始转向主要反对法西斯主义。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主张无产阶级必须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倡议在全世界组织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号召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打倒法西斯的进攻。“无产阶级必须利用资本主义营垒中的一切矛盾——各帝国主义列强在国际舞台上的矛盾,各国内部各派资产阶级相互间的矛盾”[10]。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支配下。这些帝国主义国家都谋求自己在华利益的最大化,在分赃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矛盾。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矛盾,是通过各自扶持的中国封建军阀之间的矛盾表现出来的。“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7]。日本法西斯主义上台后,开始推行独霸中国的侵略政策。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步步“蚕食”,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时,日本实行独霸中国的政策,与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利益也产生了矛盾,它们在侵华问题上的“裂痕”进一步扩大。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也开始进行调整,由原来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逐步改为主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国际七大号召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后,中国共产党做了积极回应。1935年12月,毛泽东首先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7]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又把这一政策推行到全党:“中国不但应当和中国人民的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7]在党内逐步推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毛泽东还把这一政策对国外进行了宣传。1936年7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指出:“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以最小的代价赢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中国必须首先实现国内的统一战线,其次还必须努力把这条统一战线推广到包括所有与太平洋地区和平有利害关系的国家。”[11]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进一步向前发展。他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同各和平阵线国家英、美、法等进一步地靠拢,利用国际间的矛盾”[12]。“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8]。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又对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具体政策进行了阐述:“虽然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8]这样,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逐步系统化、具体化。
中国共产党联合英美抗日政策的确立及实施,不仅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后期打开对美关系的新局面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中国共产党依据列宁关于东方国家应根据自己的经验解决本国革命任务的思想,提出了独立自主地领导本国革命的基本方针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内外因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革命的胜利,都是国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本国人民和本国力量始终是革命胜利的决定因素;本国革命发展道路、斗争策略的选择,主要靠本国人民去探索、制定。对此,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3]这些任务的解决方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是找不到的……你们应当提出这种任务,并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种任务”[3]。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必要的国际援助。“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7]。苏联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国际援助,“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7]。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我们应把立足点始终放在国内,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早在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提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著名命题,标志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的初步形成。抗战时期,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能没有国际援助,但抗战的胜利最终取决于中国自己。他在1937年10月的报告提纲中明确提出,中日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中国自己的力量”[12],中国的外交政策,应该是抗日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8]。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取得抗日胜利,中国必须寻求其他国家的支援。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外国的帮助,中国就没有能力打日本!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和中国人民准备联合任何国家,以缩短这场战争的时日。但是倘若没有一个国家加入我们这一边,我们也决心单独进行下去。”[13]1939年1月,他更加明确地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帮助是有限制的,当然我们不是靠国际“吃饭”的,应该把主要点放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采取了两条不同的外交政策。国民党政府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投靠英美帝国主义,过度依赖外援,实行片面抗战路线,结果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中国共产党则相反,“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的集团”[8]。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被分隔在几个狭小的区域内,与外界联系十分困难,国外援助几乎断绝,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极其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号召全党和根据地全体军民,不等不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不仅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还为抗日战争的大反攻锻炼了军队,积蓄了力量。1945年5月,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再次指出:“我们要做国际联络工作,做外交工作,很希望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但由于各种情况的原因而没有援助,我们怎么办?还是按照过去那样,全党团结起来,独立自主,克服困难,这就是我们的方针。”[14]
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战略原则,不仅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独立自主外交方针的确立积累了经验。
总之,列宁民族殖民地学说是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国际战略的重要理论依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制定的国际战略,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而且对当前我们在新形势下全面开展对外关系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1册[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1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3][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D6
A
1007-905X(2011)03-0076-04
2011-03-07
2006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BDJ012)
胡运锋(1977— ),男,河南许昌人,安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 吕学文
(E-mail:dalishi_sohu@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