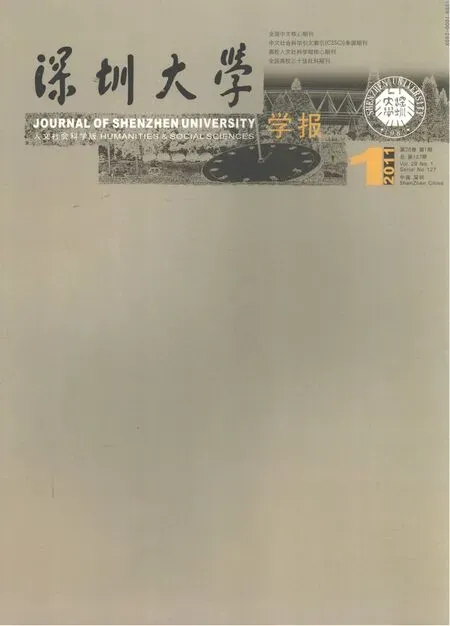泰戈尔与中国
[印]阿莫尔多·沈
泰戈尔与中国
[印]阿莫尔多·沈
文明对话与文化比较
本期栏目主持人:郁龙余
主持人语:2010年12月15至17日,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访印,和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共同宣布:2011年为中印文化交流年。而2011年,恰逢诗人泰戈尔诞辰150周年。在印度,自上至下,都十分重视泰戈尔的纪念活动,成立了由政府总理出任主席的全国委员会。在中国,隆重纪念泰戈尔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泰戈尔在中国形象可亲,与读者心贴心。
同时,通过纪念泰戈尔,弄清若干重大历史疑问,不仅对泰戈尔在中国的研究,而且对中国五四新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思想的研究,都大有助益。为此,我们在此刊出印度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莫尔多·沈和著名华人印度学家、印度国家学术奖莲花奖获得者谭中以及本人的三篇论文。这三篇论文,在国际语境下,围绕1924年泰戈尔访华引发争议,从提出问题到阐释、解答问题,互为发明,逐步深入,体现了这一课题研究的最新进展。
泰戈尔的早期欧洲崇拜者“裹挟”了西方批评者,一战中西方帝国主义的残酷暴行又对泰戈尔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得他在西方国家演讲时,要求西方多重视东方思想。可是,当泰戈尔在中国演讲也遵循这一思路的时候,那些想要改造中国的激进派面前就出现了一些传统保守派。这就势必会导致中国激进知识分子觉得与保守主义者格格不入。
泰戈尔访华;争议;原因分析
一、导言
生日是喜庆的时刻。150周年诞辰尤其应该笑颜舒展、热烈欢腾,不适合进行令人不悦的批判核查,或重开有争议的话题。泰戈尔150周年诞辰的庆祝活动大多是这样进行的,理应也该如此。然而,这样的场合也是提出疑问的适当时机,因为庆典不仅仅是怡情的时刻,也为智慧的交流和高雅品鉴提供了契机。在我们这本书中也出现相关重要的评论性文章,它们都将更具历史意义。因为就像讨论泰戈尔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包括他对中国的敬仰和中国对他的赞赏(我后面会谈到)那么重要一样,现在探讨为什么1924年被翘首以待的泰戈尔伟大中国之行会带来如此多的问题正逢其时。众所周知,这次访问引起了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批评和责难。尽管泰戈尔返回印度不久,他的在华演讲稿就被集成一书以英文形式在印度出版,但这本书并未像泰戈尔其他书籍那样被翻译成中文。而泰戈尔自己也觉得有必要停止这一版本的发行,于是第二年在作了大量的修订后重新出版。尽管如此,该书仍未翻译成中文,显然,当时泰戈尔在中国的地位仍处于某种阴影之中。原因是什么?
这种别扭的关系也许非常让人难以理解,一来泰戈尔对中国充满着敬仰和热爱,同样中国早期也曾经对泰戈尔倍加赞赏,可后来是什么引起中国对泰戈尔的热情和广泛赞誉发生改变呢?
接下来我要谈的是,我们要特别注意泰戈尔1924年伟大中国之行是发生在怎样的历史时刻。当时,欧洲惨不忍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泰戈尔被视为东方“圣人”的欧洲之旅也刚结束,在那儿他受到了极为隆重的欢迎。这些发生在1913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的事件是怎样影响泰戈尔,反过来又怎样影响中国知识界对泰戈尔的态度的?当时泰戈尔曾深信——也说服了很多人——西方世界的发展之道存在着深层次的巨大缺陷,而印度、中国或者其他东方国家中的思想可以提供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建议来弥补这一缺陷。
另一方面,泰戈尔在获得诺贝尔奖不久就接到中国的邀请,可当他1924年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知识界的氛围由于掺杂了政治因素而正在迅速地发生变化,当时的政治环境更多地聚焦于朝着激进方向发展的现实形势,而不是过去的历史文化。尽管仍然眷恋中国过去辉煌的历史,但却在某种程度上掺入了当时激进的政治需求。爆发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是一股由青年发起的重要激进的政治力量。就连最初对五四运动态度暧昧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最后也卷入这一运动。泰戈尔到达中国之时,中国正处于一场大辩论中,其中有一部分人要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另一部分新生积极分子却深切关注改造当今世界,不再留恋传统历史。泰戈尔的伟大中国之旅产生的效应是:一个激动的泰戈尔此时来到一个激动的国家,两种激动的情绪相互碰撞,然而并未能和谐共鸣。
二、泰戈尔对中国的尊崇与亲近
话分两头,在探讨上述的矛盾关系之前,我要简要地阐述一下泰戈尔是多么地尊崇和热爱中国,这一点尤为重要。泰戈尔虽然不懂中文,但他一生都对中国深感兴趣,对丰富多彩的中国文明充满着敬仰之心。对于泰戈尔家族来说,中国并不是完全陌生的国度。泰戈尔的父亲代本德罗纳特·泰戈尔和祖父达罗卡纳特·泰戈尔都曾访问过中国,他父亲还对中国哲学大感兴趣。泰戈尔从孩提时就开始受到中国文化的陶冶。
我三生有幸,从小就读于泰戈尔在孟加拉邦的圣地尼克坦创建的一所非同寻常的学校,这所学校的某些学科可以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我亲历了泰戈尔是如何认真地确保在我们的教育中融会中国文化和成就的。事实上,泰戈尔在圣地尼克坦所创建的中国学院(Cheena Bhavan)是印度第一所研究中国的学术机构。中国学院由一位伟大的学者、教育家、杰出的学术领袖谭云山教授来担任院长。谭云山教授1927年在新加坡结识了泰戈尔,1928年,他来到圣地尼克坦的国际大学拜谒泰翁,被泰戈尔挽留在圣地尼克坦主持中国研究。可以说,中国学院不仅仅为泰戈尔的教育机构锦上添花,而且还迅速成为全印度备受赞赏的中国学研究中心。
泰戈尔与中国的密切关系不仅包括他对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尊崇热爱,还包括他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1881年,20岁的泰戈尔写下一篇强烈谴责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的文章。这场鸦片贸易使得包括泰戈尔在内的众多印度人极为困扰,因为大部分的鸦片都是在英属印度生产的。泰戈尔曾著孟加拉文“Chine Maraner Byabsa”(可以译为《毒害中国人的贸易》)全面抨击英国那摧毁中国人民的可怕政策。同样,在日本入侵中国之后,过去一直对日本敬仰交加的泰戈尔,在1938年9月12日愤慨地给他的朋友、日本诗人野口米次郎致信写道,他感到“悲痛和羞耻”,“中国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痛苦的消息”使他备受煎熬。他还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能骄傲地举出一个伟大日本的范例了”。
尽管泰戈尔1924年访华引发了争论,但他仍不断地努力与他所尊敬和热爱的中国建立亲密关系。事实上,在印度圣地尼克坦,由谭云山教授所主持的具有前瞻性的中国研究正是在那次充满争议的访问之后开创出来的。正如谭中(谭云山教授的儿子)在这本书中一篇富有启示性的文章《从地缘文明透镜看“RUBI兄”与“SUSIMA”之间的心传》中谈到,泰戈尔在访华后仍然与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徐志摩,继续展开对话、保持思想交流。与此同时,谭云山教授所倡议的中印学会于1933年在南京成立,泰戈尔毫不犹豫地同意担任该学会的印方主席。可见,毫无迹象表明,泰戈尔对中国的尊敬和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有过丝毫的改变。
三、中国早期对泰戈尔的欣赏
如果说泰戈尔对中国的尊崇和热爱与他在1924年访华时所受到的批评形成一种对比的话,那么中国知识分子对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的赞誉也同样与后来的批评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宣布泰戈尔得奖之后,中国旋即出现许多表示泰戈尔实至名归的称赞言论。比如说,著名学者钱智修在一篇重要的文章里描述泰戈尔不仅是一个穷毕生精力于祖国事业的人,还是一个关心人类福祉的人。中国其他重要学者也纷纷表示对泰戈尔的崇敬——除了徐志摩(前文已提到)之外,还有郭沫若、胡适等。在郭沫若的诗歌中,不仅可以看到泰戈尔的影响,还可以清晰地感到泰戈尔的思想丰富了郭沫若的诗篇内容。
1923年12月,在泰戈尔来华前夕,徐志摩给泰戈尔写信(如谭中所引):“这里几乎所有的具有影响力的杂志都登载有关您的文章,也有出特刊介绍的。您的英文著作已大部分译成中文,有的还不止一种译本。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作家,从来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在我们这个年轻的国家的人心中,引起那么广泛真挚的兴趣。也没有几个作家(连我们的古代圣贤也不例外)像您这样把生气勃勃和浩瀚无边的鼓舞力量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让泰戈尔无法预测在中国会有任何不友好的批评,而且这封信传递了另一层重要含义。泰戈尔认为他到中国演讲是一个传播他的理想去激励中国人民的大好时机。当时他正为西方的战争和暴力所困扰,并全身心地为不完善的西方文明本体寻找药方——可以预见——他来华的言论必然将含有“东西方相抗衡”的主题。
这个话题是我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之一。在深入探讨之前,我先要谈谈两个人们已经讨论过的,而且应该弄清楚的问题。它能解释为何出现形成鲜明对照的两种不同态度:一是中国人热爱泰戈尔的背景,二是泰戈尔来华访问后所引起的论争。
四、关于矛盾的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坚决认为当时中国反对泰戈尔访问的声音来自中国左派,特别是共产主义者。这种说法认为,中国早期对泰戈尔的赞美不是来自左派,而是来自其他阵营。按照这种说法,如果共产主义者发出批评的声音与其他阵营的赞美之声相对,也是正常的。中国对泰戈尔来访议论纷纷,如果仅仅简单地说成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其他思想家的分歧是很肤浅的。这对理解中国早期对泰戈尔的赞赏(来自反左派或者至少非左派)和后期对泰戈尔的批评(被坚定地认为来自左派)之间的反差不能形成强有力的逻辑。
这种说法的缺点,从陈独秀的例子就能看出来。陈独秀是泰戈尔作品的翻译者,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事实上,他翻译了四首《吉檀迦利》的诗歌,并发表在他编辑的杂志《新青年》上。陈独秀还在注解中介绍说泰戈尔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也是印度青年的先觉。此外,还有很多属于左派的中国知识分子翻译泰戈尔作品,并对他赞美有加,还评论他的杰出作品。如果要在政治派别中去寻找解释,那就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左派的“反对”态度和来自另一方的持续“支持”态度之间的对立。
另一个说法过于简单肤浅。该说法认为邀请泰戈尔来华的组织是由一个传统保守的人所领导的,因此引起中国激进思想者的反感。这种说法必须要认真审查,它看似有理,因为邀请泰戈尔来华的是梁启超主持的北京讲学会,梁启超是一个传统思想深厚的人,他的想法时常会遭到许多激进派的尖锐批判。但是讲学会早期也邀请过许多令人敬畏的著名学者,例如伯特兰·罗素——他并不是什么典型的传统主义者——他的演讲也获得极大的成功。除此以外,还邀请过美国著名的大哲学家、激进思想权威约翰·杜威。
我们必须更加深入探讨泰戈尔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访华的目的。当时泰戈尔的思想还沉浸在野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久久不能恢复平静。除此以外,他还多少受到欧洲评论家,比如说叶芝的影响,他坚信通过著作,可以传播许多东方思想来给不完善的西方思维模式带去启示。因此,我们的分析应该集中在当时泰戈尔所关注的焦点,而不是仅仅归之于邀请他访华的学会的性质和政治见解。
五、泰戈尔对西方的批判
第一次世界大战残酷的杀戮,使得欧洲许多知识分子和文学家转向寻找来自其他地方的真知灼见,当时泰戈尔的声音似乎非同凡响地合乎时宜。比如说深受泰戈尔影响的诗人魏尔孚莱德·欧文,在作品中流露出强烈的反战情绪,可他最后却战死于沙场。有一首著名的诗,他谴责贺拉斯歌颂的为国捐躯的古老格言:“朋友,请不要激情万丈/向那些燃烧着荣耀欲火的孩子们诉说/那古老的谎言:‘为国捐躯愉快而又光荣’”。魏尔孚莱德·欧文的母亲苏珊1920年给泰戈尔写信告知,他儿子奔赴战场并战死沙场的情形。透过战争的荒凉残忍,年轻的欧文仍能看到大自然和文明的美丽。他在战场上“透过阳光闪烁的海面,看着法兰西”。苏珊·欧文告诉泰戈尔,欧文离开时说“您那动人的诗句——开头第一句是‘我现在从这儿离去,希望这儿成为我的诀别’”,当她战死的儿子那本掉在战场上的笔记本被送回给苏珊·欧文的时候,她发现(她写信告诉泰戈尔)“那些动人的诗句下面有您的名字”。
泰戈尔对这次世界大战极为震惊,其实是有原因的。然而,我们不能天真地认为残暴和战争是西方特有的痼疾,因为在东方历史上——印度、中国或者其他“东方国家”这种恶行不胜枚举。但当时欧洲的杀戮是不同寻常的,那些大屠杀的大刽子手都根植于西方,尤其是欧洲。
六、泰戈尔的政见及其多面性
泰戈尔对当时英国在印度的暴行和帝国主义在中国及其他地方的暴行越来越失望、烦恼。他在后期的作品中继续抨击在帝国主义环境下西方文明的失败。在他访问中国若干年后,在一本名为《时光流逝》的孟加拉文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译者穆罕默德·哈比布尔·拉赫曼):“欧洲文明不是为了启蒙,而是纵火。随之而来的是把枪炮和鸦片送往并燃烧中国的心脏。那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灾难。”
然而,泰戈尔对西方的不满不只是对帝国主义的谴责。在言语的交往中他深深地受到西方国家的西方文明批判者,尤其是叶芝和庞德等人的赞誉所影响。我曾在《纽约书评》(1997年6月26日)发表的和在《惯于争鸣的印度人》(2005)第五章“泰戈尔与他的印度”这两篇文章中详细探讨过。这种影响被泰戈尔内化,并使得他在西方国家演讲的时候要求西方多重视来自东方的思想。可当泰戈尔在华讲话也遵循这一思路的时候,他就必然在那些想要改造中国的激进派面前显得特别传统守旧。马克思主义也是来自西方的,泰戈尔批评西方思想体系,要求凸显东方思想的优越,这就必然会导致中国激进知识分子觉得他不近常情——甚至反动。
泰戈尔到达上海后两天,他的左派崇拜者茅盾在《民国日报·觉悟》中撰文写道:
我们敬重他是一个怜悯弱者,同情被压迫人民的诗人;我们更敬重他是一个实行帮助农民的诗人……我们绝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泰戈尔;也不欢迎创造了诗的灵的乐园,让我们的青年到里面去陶醉去冥想去慰安泰戈尔。
这就是许多泰戈尔早期的崇拜者——大部分是左派,也有其他派别——所感觉到的对立心态,这种感觉并非无中生有。
我已经在别处讨论过,特别是在《惯于争鸣的印度人》一书中,谈到了泰戈尔在西方受到的那种浮夸的赞扬误导了世界,对泰戈尔也产生了一种误导。我认为这一角度更能分析泰戈尔伟大中国之行所产生的不幸——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是一场悲剧(当然也有许多积极的成效)。与我们探讨特别有关的是:泰戈尔早期在欧洲受到的欢迎在泰戈尔心中产生了影响,他对世界大战的反思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点。有一点很重要,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指出的,这种影响对泰戈尔的整个思想体系是微乎其微的,但对他在国外演讲内容的选择却起了特别的作用。
在印度,泰戈尔绝非传统保守主义者,他甚至还因为甘地太注重传统而与之争论。他一直相信科学和科学的思维模式。他全力推广平民教育,在他访问中国后不久,他称赞苏联推动全民教育以及为广大民众分忧的做法。1931年他出版的孟加拉文著作《俄罗斯书简》,在1934年被译成英文后,立即被英属印度殖民政府禁止,直到印度独立后才重印出版。
尽管泰戈尔的许多作品中关注的是非西方的传统,但他的思想并没有转向“纯粹的传统主义者”。他常常在国外评论一些他觉得人们乐于聆听的重要问题。然而英属印度停止了他对苏联的赞美,1930年访苏期间他接受《消息报》的采访时,对苏联专制主义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批评,《消息报》没有发表他的谈话,只刊载在《曼彻斯特卫报》上。一直到58年后的1988年,苏联《消息报》才把它刊载出来。
七、结语
现在必须结束这篇文章了。前面已经讨论过,1924年泰戈尔的伟大中国之行一方面引起了论争,另一方面泰戈尔对中国的尊崇和热爱,以及中国在他访华前对他的赞誉,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需要我们更深入地探讨,同时也需要对泰戈尔信念,对他在国内国外不同的演讲内容的选择,以及他早期在西方国家所受到的赞扬和世界大战产生的巨大悲剧对他的影响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
如果茅盾在不赞成泰戈尔在华演讲的某些言论的情况下,还有可能继续崇敬泰戈尔的话,这种逻辑思维就能有助于理解上文所谈到的巨大反差。即便是我们在庆祝泰戈尔诞辰150周年,我们也可以切实地认真思考一下泰戈尔的基本观点以及他到世界各地讲演时对内容的选择所造成的对立形势。
一方面,泰戈尔的早期欧洲崇拜者有“裹挟”泰戈尔为西方批评者之嫌,并对他在国外演讲内容的选择(但非对他的基本观念和他在印度国内的演讲)起了一定影响。另一方面,西方帝国主义的残酷暴行又对泰戈尔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他1941年逝世前夕发表的最后一次主要演讲《文明的危机》中,泰戈尔执著地坚持两个方面,一方面要从西方汲取有益的知识,包括“探讨莎士比亚的戏剧,拜伦的诗歌以及最重要的……19世纪英国政治自由主义的宽大胸襟”。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些有益的东西已被“英国政府的威力重压所扼杀”,另外,“英国对那个伟大的、拥有悠久文明的中国的悲惨命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能只着眼于泰戈尔的某些作品和演讲——那些在交流中产生出一系列的复杂影响的作品与讲演——而忽略了泰戈尔宏观整体愿景中的丰富内容。泰戈尔与中国的关系不是口号式的简单概述就能说明的,它值得更深入的研究分析。当然,凡是研究伟大的人物,都是一本难念的经!
(黄蓉译谭中审校)
【责任编辑:来小乔】
Tagore and China
Amartya·Sen(India)
(Center for India Research,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Guangdong 518060,China)
The early European admirers of Tagore“swept along”Western criticizers,while in World War I, the brutality of Western imperialism exercised a great influence on Tagore’s ideology so that he demanded that the West should attach more importance to the Orient when he delivered speeches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Nevertheless,when Tagore followed the same route of thought when presenting his speeches in China,some conservative traditionalists appeared before the radicals who wanted to reform China quickly.It was inevitable that the radical Chinese intellectuals sensed amisfitbetween them and those conservatives.
Tagore’s visit to China;dispute;analysis of the reason
G 112
A
1000-260X(2011)01-0005-05
2010-12-20
阿莫尔多·沈(又译阿马蒂亚·森)(1933—),男,印度人,哈佛大学托马斯·拉蒙特校级经济学和哲学教授以及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终身理事(1998~2004年担任该学院院长);1998年因为在福利经济学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饥荒、人类发展理论、福利经济、贫穷的根本机制、性别不平等和政治自由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还获得过印度国家最高荣誉奖——“印度珍宝奖”;获得80多个荣誉博士学位,著作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曾经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印度经济学会、世界经济学会以及经济学社的主席,2010年被《时代》杂志评选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