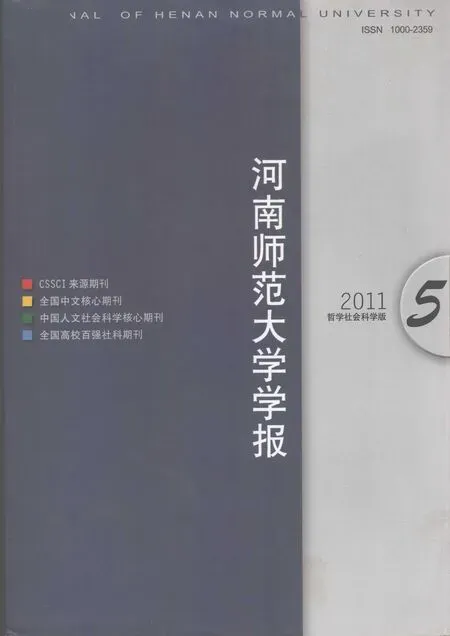章士钊逻辑思想初探
黄 海,崔文芊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300071)
章士钊逻辑思想初探
黄 海,崔文芊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300071)
作为中国近代逻辑史的代表人物,章士钊主要从逻辑思维基本规律、逻辑思维形式和基本逻辑方法三个方面,介绍了西方逻辑,对中国逻辑进行了深入的挖掘,此外他将中西逻辑进行了比较,并用大量事实批驳了“中国无逻辑”论的观点,这在学术界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章士钊;逻辑指要;中西逻辑比较
章士钊作为中国近代逻辑史上的代表人物,在近代逻辑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他的著述主要收集在《章士钊全集》中,其中与逻辑有关的著述包括章氏墨学15篇,逻辑论文25篇,包括《论翻译名义》、《名墨訾应论》、《名学他辩》、《墨议》、《原指》、《名墨方行辩》等,以及其逻辑思想的结晶——《逻辑指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章士钊的逻辑思想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逻辑指要》的逻辑价值亦未被充分发掘,这不能不说是近代逻辑思想研究的一个缺憾。本文主要对《逻辑指要》在中西逻辑比较研究方面的成就进行梳理和评价。
章士钊在《逻辑指要·自序》中说:“吾曩有志以欧洲逻辑为经,本邦名理为纬,密密排比,蔚成一学,为此科开一生面。”[1]294在《例言》中他又指出:“此学谊当融贯中西,特树一帜。”[1]295这实际上表明了贯穿全书始终的基本思想即中西逻辑比较。传统形式逻辑主要包括逻辑思维基本规律、逻辑思维形式和基本逻辑方法。章士钊的《逻辑指要》在这些方面都进行了中西逻辑的比较,做到了“融贯中西”。
一、关于逻辑思维基本规律
西方逻辑通常所说的形式逻辑基本规律包括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章士钊分别译为同一律、毋相反律、不容中律和理宜律。对于这四条规律,章士钊在《逻辑指要》中均用中国古代逻辑的相关论述、实例加以说明和解释,并力求在《墨经》中找到相似的陈述。他认为《墨辩》中包含了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并指出《墨经·经下》“合,与一,或复否,说在拒”一条是对前三律的总括。
章士钊对同一律的解释是:甲者甲也,主谓形义并同[1]310。并指出:“辞中第二甲子,无有定质。”[1]311他还认为,“律曰同一,凡两名可得并施于一物者,皆此律之所有事” ,“此律所赅,在一物之始终不变,不在二物之期于合一”[1]312。
章士钊以《墨经》中的“正无非”与同一律相比较,称同一律为无非之律。他指出:“甲为甲,此无非之律也。无非亦出《墨经》,谓真理在是,无足以非之也。”[1]312从矛盾律、排中律与同一律的本质联系来看,这种比较是有一定道理的。
章士钊认为矛盾律之名号自语相违,因此他称之为毋相反律,以“正其名而昭其实”[1]313。他对这一规律的解释为:非非甲也;又解释为:甲不能为甲,又为非甲。他还以《经说》“不俱当,必或不当”[1]319解释矛盾律,认为此语可以说明不可两可。“不可两可”即矛盾律:并非A并且非A。章士钊认为《墨经》对“次”的诠释和鲁胜《墨辩序》中所云“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无”[1]313可为矛盾律作注脚。墨经云:“次,无间而不相撄也”。譬如,启闭之次,可以无间,但决不能相撄。再如,有无之分明。他的这些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
章士钊还认为《墨经》所云“同异交得放有无”中包含了矛盾律思想。他指出,《墨经》之“同异交得,放有无”一条“最关宏旨,解之者少”[1]317。其实他本人也没有真正理解此条之含义。他认为此条在《经说》中的解释如有无、多少、去就、坚柔、死生等皆为相互否定的东西,便认为“同异交得放有无”是讲矛盾律。正如他所言:“……即墨言同异交得,其曰逻辑所不能证,尤直中本律之藩。”[1]318其实,此条并非在讲矛盾律,而是在讲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规律。
章士钊对排中律的解释为:凡物必为甲或为非甲。章士钊认为此律与毋相反律略似而实不同。他在分析和驳斥胡适混淆矛盾律与排中律的基础上指出:“毋相反律示不能同时俱存,不容中律示不能同时俱亡。”[1]319因此,《经说》中“不俱当,必或不当”为矛盾律,“不可两不可”为不容中律。他还用“必居一”释排中律。“必居一”引自孟子论兼金一事中陈臻的一段话:“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二者必居一于此矣。”[1]319章士钊认为:“以必居一释不容中,乃形式逻辑惬心贵当之义。”[1]319显然,章士钊认为《墨经》已经对矛盾律和排中律进行了西方逻辑式的论述。
在把《墨经》中的有关论述与形式逻辑的三个规律分别进行比较分析之后,章士钊在综述中指出,《墨经》关于“合与一,或复否,说在拒”一条乃“综三律而论之”。他认为:“此即墨辩之所以律思想者也。合,合同,一,重同。此明同之极诣。昭同一律也。或者正之,否者负之,既正又负,显非辞理。此明矛盾之当戒,昭毋相反律也。拒者即不容中之谓。……墨家提出拒字,意在以后律释前二律,以三律之脉络固贯通也。”[1]321由此可见,章士钊力求阐明三条逻辑规律“脉络固贯通也”,以揭示它们属于同一序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一思路是正确的。但是,他对经文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墨经》的这条经文并没有揭示出这样的内涵。
关于充足理由律。章士钊指出:“考其所谓充足,与《墨经》之宜适合。”因此,他称充足理由律为“理宜律”,以《墨经》中对“宜”的解释来阐述充足理由律。
二、关于逻辑思维形式
(一)概念
“概念”二字为concept之译语,包括内涵和外延两个基本特征。章士钊指出该词“来自东译”[1]324,“非惬心贵当之词也”[1]324。他批驳道:“谓之谓概,其先统括若干殊相而收摄之。”[1]324而私名只有内涵,没有所概之外延。他以私名“梅兰芳”为例,指出私名无内涵,从而揭示出“概念”这一译语的不当。他认为概念在“道家曰旨,墨家曰意相……《易》则曰物宜”[1]324。章士钊引用《墨经》中“知也者,以其知过物而能貌之,若见”[1]332来阐释意相,他指出:“貌之所见,意之用也,所貌之相,乃意相也。”[1]335在他那里,意相乃心官对事若物,发挥其知觉、记忆、想象诸作用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章士钊不愿使用“概念“一词,更倾向于使用“名”。他认为中国古代逻辑文献中所说的“名”相当于西方逻辑中的“concept”,并认为“名”有两个基本特征:所指事物即外延,所指事物的性状特征等即内涵。正如他所阐述的:“凡名对于物有所命,对于德有所涵。所命,示名之广狭,为横。所涵,示名之浅深,为纵。横者,汉密敦字之曰外周(extension)(即外延——笔者);纵者曰内涵(intension)。”[1]335关于这一点,章士钊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墨家虽然没有对内涵和外延进行明确的论述,但对“名”的分析与解释无疑是围绕这两方面进行的。
西方逻辑把名词分为私名与公名。根据穆勒的定义,私名指“在同一意义以内,名之只命一物以为真者也”[1]343,公名指“在同一意义以内,可于无穷物之中,标一以应焉者”[1]344。章士钊认为,这种分类在《墨经》中有相应的论述,譬如他指出:“《墨经》曰:达、类、私。达、类两名与私名对举;达、类皆公也。”[1]344这是说《墨经》从外延的角度上,将名分为“达、类、私”三类:“达名”用来概括有共同属性的最多的事物,相当于最大类概念;“类名”指具有同一属性的一个类别的名称,如马即为类名,所有具备马的属性的,都用马这个类名称呼它;“私名”反映的是某一个体的名称,如某人的姓名。“达名”与“类名”都属于西方逻辑中的普遍概念,“私名”是单独概念。
西方逻辑中对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进行了区分,章士钊也有相应的讲述。他区别了公名与从名,认为从名相当于西方逻辑中的集合概念。他指出,从名者,摄诸物而名其全;公名者,统其全而一一可名其独[1]344。他还指出,从名在《墨经》中称为“兼”,曰“体分于兼也”。
关于概念外延间的关系,他指出,西方逻辑中的种属关系在《墨经》中是指体同、类同,全同关系是指重同、合同。
(二)命题
章士钊认为西方逻辑中的“命题”相当于中国古代逻辑理论中的“辞”,正如他所言:“命题者,辞也。”[1]353他同时指出:“命题在《墨经》中曰佴。《说文》云:佴,佽也。盖凡辞,以二名相次为之,前曰主词,后曰谓词”。[1]353章士钊在整合中西逻辑思想的基础上给命题下了一个定义:命题者,离合二名而喻一意也[1]355。此定义中“二名”,一句主(subject),一谓词(predicate)。句主,《墨经》曰名;谓词,号曰实。《经曰》: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是辞的谓词,是“所以谓”,“实”是辞的主词,是“所谓”。章士钊指出,西方逻辑“言命题以三部成之”[1]358,“主谓相次,中以丽词贯之”[1]358。《荀子·正名篇》云:“累而成文,名之丽也。”章士钊认为:“丽以缀系当之,可通。”在这里,章士钊认为“名”、“实”、“丽”分别相当于西方逻辑中的“句主”(即主项)、“谓词”(即谓项)、“缀系”(即命题联项)。这是章士钊对命题(辞)的构成的对比分析。
在西方逻辑中,命题有真假。命题在《墨辩》中有二字,一曰言,一曰举。《墨经》曰:言,出举也;又曰:举,拟实也。 言之而正,墨家称为正举;不正,称为狂举。章士钊认为“正举”、“狂举”分别相当于命题的真、假。
在关于性质命题的分类及其对当关系这一问题上,章士钊也作了中西逻辑的比较分析。章士钊认为《墨经》所云“无穷不害兼”是在说全称肯定命题和特称肯定命题。他指出:“有以为不害者,即有以为害者,如或所知不敢自信,抑故欲掩去所知之一部分,斯害矣。A,兼之事也,害则退为I矣。”[1]364章士钊把《小取》中的“周”解释为“全称”。《小取》曰: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章士钊认为,“周爱人”是A命题,“不周爱”是O命题。爱人( 周爱人) 与不爱人( 不周爱) 是矛盾关系。因而这实际上是在讲性质命题之间的对当关系。
(三)推理
章士钊指出,西方逻辑有演绎归纳,演绎始于亚里士多德,归纳始于培根,而“吾之周秦名理,以墨辩言,即是内外双举,从不执一以遗其二”[1]293。《墨经》云:尽,莫不然也。尽:但止动。章士钊认为其中的“尽”为外籀之事,“止动”为内籀之事。他认为荀子已经有了演绎和归纳的思想。他的依据是《荀子·正名篇》一段话:“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2]他认为,所谓“推而共之”是归纳,所谓“推而别之”是演绎。但是他指出荀子的这些思想只是初步的,仅涉及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的基本特征而已。章士钊的这种看法,没有脱离荀子的思想实际刻意拔高其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的思想水平,是难能可贵的。
1.直接推理之比较:换质换位推理与附性推理
章士钊认为,直接推理即公孙龙子之两明之术。两明者,两物相互以明也,其无假第三物以为之介可知。章士钊认为《墨经》中也有西方逻辑中关于命题换质、换位推理的论述,认为《墨辩》的“侔”相当于西方逻辑的换质、换位法则,《墨经》 的“俱二不俱斗,二与斗也”是在说换位之规则, 意思是: 斗以二人为之, 但二人所为, 不必即斗; 即是不能随便进行简单换位。
由此,章士钊认为,“墨家之论侔,范围殆与古逻辑之言obversion or acquipollence相差不远”。这种对比解释是错误的。实际上,“侔”式推理属于现代逻辑中的二元谓词逻辑推理。譬如:
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
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
获,人也;爱获,爱人也。
臧,人也;爱臧,爱人也。
很显然,上述命题中前提和结论的命题种类不同,前提是直言命题,结论则是关系命题,它不仅比前提多了一个二元谓词(“乘”、“爱”),而且多出一个关系者[乘白马(或马)者]和量词。
在谈到换位法之直换时,章士钊说:“《墨经》所谓‘平立反’者,疑指此。立,所立之辞也。反之而平,犹言换位而无悖于法。夫是之谓正,夫是之谓合,故曰:合,平立反,……正也。”[1]382他指出了《墨经》之“平立反”相当于换位法之直换,但不确信。同时,他指出《墨经》之词条“俱二不俱斗,二与斗也”是在说换位之规则。他说:“盖斗二也可,二斗也不可,直换明明为誖矣。是之谓俱二不俱斗。”[1]383意思是说,斗以二人为之, 但二人所为, 不必即斗,也就是说,不能随便进行简单换位。
章士钊在谈到附性法时说,墨家关于辞侔的论述比西方逻辑的附性法还多了些方法。墨家于命题上所附加的不以附性法的附加形容词为限,还附加动词,或者其他一些形式。譬如,《小取》说的“白马, 马也; 乘白马, 乘马也。此乃是而然者也”是加词附益法( 即附性法)。
2.三段论与“三物”论之比较
章士钊用先秦逻辑思想和逻辑理论对西方逻辑之三段论进行了多方面的“融贯中西”的比较、分析,阐明了西方逻辑中三段论的基本结构、推理形式和基本规则早已在我国先秦逻辑理论中有所阐述。他的阐述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他批驳了严复把三段论式与中国古代的连珠体等同的观点,认为以“联珠”译三段论“于义无取”[1]391。章士钊在《逻辑指要》中对中国历史上连珠的起源、发展、兴盛、坠绪及特点进行了考察,指出连珠“始于汉,而盛于六朝,唐宋稍承坠绪”[1]392。其特点是“辞句连续,互相发明”[1]391,“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1]391。因为倘若不说事情,小前提将难以提出,由此“可知此体在逻辑别有所属,纵所穿并非鱼目,而决不能强指为三段”[1]391。因此,他认为连珠与三段论式是相悖的。后来的逻辑论著大都用“三段论式”而不用“连珠”,与章士钊的观点有很大关系。
其二,《墨经·大取》云:“语经,语经也。白马非马,执驹焉说求之。……三物必具,然后足以生。”章士钊认为这是在讲三段论式,并称之为“三物语经”[1]398。章士钊进行了具体分析:“语经”,就是言语之常经,议论说理经常采用的结构形式;“词以命物”, 三物也就是三词,即三段论的三个名词( 项);“三物必具”,就是说三段只能有三个名词( 项),不能多也不能少。曰白马,曰马,曰驹,是为三物。执白马与马以明其是非,仅两物尔,无自明理。必诉于第三物曰驹,立为说以求之,断语始萌,生之谓也。故曰“三物必具,然后足以生”。因此,他认为,三段论的结构,“包含之词亦止于三”[1]398,“此(三物)其结构,全然与逻辑三段合符;以是三段论法,亦可曰三物语经”[1]398。在这里,章士钊认为“三物必具”的“三物”即三段论式之大、中、小项。
其三,他以《小取》中对“推”和“辩”的诠释与西方逻辑中三段论的大、小、中项相比较,从而对“三物”进行了更为具体的阐述。《小取》云:“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他指出:“所取,指媒词外之两词言之,以两词俱为断案收纳,故曰所取。所不取,指媒词,媒词者,婚姻成而媒约退,故曰所不取。”“所不取”在《墨辩》为宏旨。凡三段式之命脉,全操于所不取者之一词,所取者有与之同。在这里,章士钊认为“所取者”是指大小词而言,因其在前提中出现,在结论中也出现,故称为“所取”。“所不取”则为中词,它在前提中出现而在结论中不出现,“婚姻成而媒妁退”故名之曰“所不取”。
章士钊还认为,中项在《墨辩》中可被称为“他词”或“彼词”,如他所言:“公孙龙子之他辩,他犹彼然,亦即三段论法也。”[1]400“他”源自《公孙龙子·通变篇》之“他辩”二字。章士钊指出:“他者,第三位之称,意谓备第三物以明前两物相与之谊,即逻辑之middle term也。”[1]579“彼”源自《墨经》“辩,争彼也”一语。章士钊指出:“公孙龙之他辩,在《墨经》号为争彼。彼与他同,争彼也者,争第三物之当否也。”[1]580进而指出:“彼,第三人称,不问而为中词之义。墨家以‘争彼’诂辩,可证外籀逻辑之通体结构,存乎三段,中外之理解悉同。”[1]399
对于三段论的结构的比较研究,章士钊还引用《小取》中“是犹谓他者同也,吾岂谓他者异也”来阐述。他指出:“凡媒词之见于大前提者,以第一他字表之;见于小前提者,以第二他字表之。”显然,这一解释是章士钊对《墨经》文本的一种曲解。
其四,章士钊还把西方逻辑之三段论曲全公理解释为“盈大否训”。“盈否”语出《墨经》:盈,莫不有也;否,莫不无也。进一步,他认为《经说》中“尽与大小”、《大取》中的辞“以类行”与《经下》中的“止,类以行之,说在同”是说“外籀术由全之偏”[1]387,即三段论曲全公理:如果对某类对象之全部有所断定,则对其部分亦有所断定。对于《经说》中“尽与大小”,章士钊的解释是:第一字所表者尽与大,第二字所表者大与小也。他又结合《小取》中“是犹谓他者同也,吾岂谓他者异也”一条,指出:西方逻辑之曲全公理即“物真于全者,必真于偏”与《墨经》之“尽与大既同,大与小自不得异”可谓异曲同工。
其五,章士钊认为,《墨经·小取》中的“效”是说三段论的规则。他在《名学他辩》中说,《墨辩》至少论及了如下三条规则:其一,“他词必至少尽物一次”[1]587;其二,“端词在前提中未尽物者,在断案不可尽物”[1]587,亦即在前提中不周延之大、小词,在结论中亦不得周延;其三,“他词必正”[1]587,即中词不能混指两个对象。
《逻辑指要》对中西逻辑的比较几乎涉及了传统逻辑的各个方面,以大量事实批驳了“中国无逻辑”论的观点,这在当时的学术界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但是由于时代与自身的局限,书中的比较研究还存在着一些牵强附会的因素,其“融贯中西”的原则也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它的“融贯中西”实际上是以“西”统率“中”,使“中”从属于“西”,从而也抹杀了中国逻辑思想与理论自身的特点。然而,这些并不能掩盖《逻辑指要》作为早期中西逻辑比较研究教科书的价值。
[1]章士钊全集:第7卷[M].上海:文汇出版社,1972.
[2]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1.
[责任编辑张家鹿]
B81-092
A
1000-2359(2011)05-0025-04
2011-0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