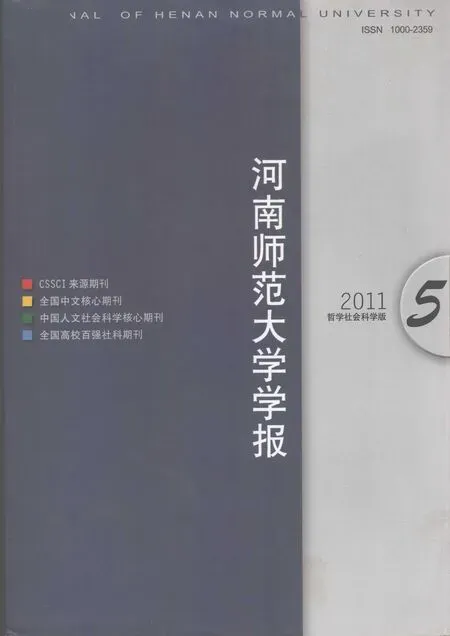本体维度下的伦理突破与亲情守护
——谭嗣同思想片论
钱 善 刚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234)
本体维度下的伦理突破与亲情守护
——谭嗣同思想片论
钱 善 刚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234)
谭嗣同以中国传统思想为基底,借西方话语,重构本体论,其本体论存在层级差别:从世界来看,以太是本体;从社会来看,仁是本体。重构本体论的目的是对传统纲伦加以批判,通过复古的方式吸纳新时代的内容,但从具体的真实的存在来看,其批判的背后难掩对亲情的守护。
本体重建;伦理突破;亲情守护
在近代思想家群体中,相较而言,谭嗣同的思想表现更具有自觉的本体意识和强烈的伦理批判精神,其本体意识体现在以中国传统思想为基底,借西方话语,重构中国的本体论上,其批判精神的特点之一是在重构后的本体维度下对传统伦常给予猛烈批判和重新思考。然而作为具体的真实的存在,其强烈的伦理批判并没有完全遮蔽其对亲情伦理的真实流露,思与在充满了紧张和冲突。
一、本体重建
本体一词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指存在的本然状态或本然的存在状态,近代以降,随西学东渐,本体一词取得了现代意义上的含义,换言之,取得了与现象相对应的实在的含义。两种含义在谭嗣同思想中都有所表现,前者如“日中天,则无朦气之障,而还其本体。日之本体,如盘者也”[1]207。但更主要的是在后一种意义即本体论意义上使用本体一词。这一意义上的本体或简称为体,与现象、功用相对应。广义的本体具有二维性,既可指时间维度上的本原,也可指空间维度上的本根、基础。谭嗣同本体论思想是通过对仁、以太等概念的疏释而得以呈现的。仁是中国传统的概念,更多地具有伦理的含义,通过重新诠释而具有本体的含义;以太是近代物理学的概念,谭嗣同将之引入自己的思想中作为宇宙自然的本体。进而言之,仁和以太两种本体是什么关系?把伦理批判建立在以太基础之上,这一思维与传统思维有什么联系?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不论是孔子的“仁者爱人”,还是孟子的“仁政”、朱熹的“仁生”,仁首先和主要具有伦理、政治的含义,谭嗣同则通过对仁、元、无三字的诠释,认为三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言仁者不可不知元,而其功用可极于无”[1]4。在传统思想中,元具有初始之义;无与有相对,在道家思想尤其是老子思想中,“有生于无”,无具有本原之义。可见,在仁、元、无的互释中,仁已不仅仅限于伦理范围,而首先指向本体之域。进一步,谭嗣同将对仁的新理解渗透到对仁的界说中,在仁学的诸种界说中,从本体论视角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命题:“仁以通为第一义”,“智慧生于仁”,“仁为天地万物之源”,“仁者,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不生不灭,仁之体”[1]7-8。仁的概念勾连和贯通自然、伦理和政治三大领域,从而建立起自己的独具特色的仁学思想。所谓“天地万物之源”、“不生不灭”等多少有道家的影子,这样界说的仁甚至可以用老子的道替代之,而道家思想的主旨是无为,这与谭嗣同欲借仁的诠释以达到言变、言通的初衷相悖离。于是,他进一步引入西学中的以太概念,为仁学找寻更加坚实的本体论根据,“学者第一当认明以太之体与用,始可与言仁”[1]11。何为以太?“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至精微,无所不胶粘、不管络而充满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声,口鼻不得而嗅味,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太”[1]10。从身、家、国至天下,依以太而存在,从极微小的生物到星云电气等同样依以太而存在,“法界由是生,虚空由是立,众生由是出。无形焉,而为万形之所丽;无心焉,而为万心之所感”[2]121。以太是万物存在的本体、本原、本因、本根,既是世界生成的原理,也是世界存在的根据。谭嗣同借近代科学的以太概念,抛弃传统的理、道、气等概念重建哲学本体论,将儒、墨、佛、耶等各家学说冶为一炉,将科学、哲学、宗教糅合为一,虽难免有博杂粗疏之讥,但其强烈的现实旨归、鲜明的人生指向、巨大的学术勇气是令人敬佩的,梁启超谓之“其尽脱旧思想之束缚,戛戛独造,则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3]。
一般而言,在一种思想体系中,最终的本体往往具有唯一性,以此观照,在谭嗣同思想中,仁是本体,以太也是本体,二者同为本体,这是否造成二元本体?关于以太与仁的关系,学界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二者等同,以太即仁,代表人物有杨正典、孙长江、谭丕模、杨一峰、郭湛波等学者;一种观点认为二者不同,以太与仁是体用关系,代表人物有杨延福、李泽厚、邱荣举等人[4]。本文认同李泽厚等人的主张,但理由和解释并不一样。以太、仁,体、用等概念必须放在复杂交错的多层面中加以理解。综观谭嗣同的思想文本,追随理一分殊的思路来看,以太是世界本体,是第一本体,一旦言说后就退居为背景;仁是社会本体,是第二本体,是其思想的焦点和立论中心之所在。仁与伦理、政治相比较具有本体地位,但与以太相比较则处于“用”的地位,“夫仁,以太之用”[1]14,以太与仁是体与用的关系。概言之,谭氏构建的是层极宇宙观,即以太——仁——伦理——政治的宇宙观,这一宇宙观是多层面的、立体的而非平面、线性的宇宙观,其范围由大到小,本性性依次递减,体与用处于动态之中。
二、伦理突破
从天道下贯至人道是中国传统的普遍思维路径,谭嗣同也没有例外,但建构本体论(天道)本身不是目的,其真实目的是要在新的本体论基础上重构中国人的伦理秩序。
从社会层面来看,既然“仁为天地万物之源”,处于本体之地位,那么,伦理、政治必须符合仁的规范和要求才能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作为本体的仁,其内在的本质规范和品性是“通”[1]7,在人世间的具体展开为四通: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通之象为平等”[1]7。至此,谭嗣同综合古今中西各家学说,建立了以太——仁——通——平等这一思维逻辑,并将之运用于伦理、政治,转化为伦理、政治的规范和要求,凡不合这一规范和要求的均在改造之列,违反这一规范和要求的都是必须加以冲决之罗网。
“仁一而已;凡对待之词,皆当破之”[1]8,“天地间亦仁而已矣”[1]14。在传统思想中,有所谓“三达德”、五常等说法,诸德目之间至少从形式上看处于并列关系中,而在谭嗣同看来,仁与其他诸德则处于包容关系中,仁可以涵摄其他德目,仁始终处于主体、本体的地位,只要认识、把握了仁,其他诸如勇、智、礼、义、信等则会随之得以认识、把握。既然“仁一而已”,何以又有勇、智、礼、义、孝、节等呢?在谭嗣同看来,其他诸德目只是圣人们随俗而设、方便俗人理解而已,他说:“故凡教主如佛,如孔,如耶,则专言仁,间有旁及,第就世俗所已立之名,借以显仁之用,使众易晓耳,夫岂更有与仁并者哉?”[1]16然而一旦有诸德目之出现,而俗人不理解其真义,往往冲击对仁的把握,造成以名乱仁的现象,“仁之乱也,则于其名”,其甚者以名为教,“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1]17在谭氏看来,仁具有唯一的实在性,而君臣、父子、夫妇等是仁体呈现于外的功用,是表现仁体的方便之名,实第一性,名第二性,作为第二性的名具有依附性和从属性。作为实的实质内涵的平等要求名之内涵也必须与之一致,否则会导致名实背离、以名乱实的后果。通过名实之辨,谭氏对传统纲伦的等级性加以改造,赋予其平等的时代意蕴。
知与行、理想与现实始终处于紧张和冲突中,从理想出发,谭氏在思想中激烈地批判传统纲伦,然而在现实中,谭氏仍然有对纲伦的维护。可以说谭氏批判的是被世俗化的纲伦,而维护的是其心目中的真正的自然的纲伦。他认为学之真际在格致,政之真际在兴民权,“教之真际,无过五伦”[1]128,五伦是人类社会中的自然存在,其具体内容或许因地域、时间的不同而不同,然其作为人与人关系的形式是不可超越的。谭氏继承王夫之的道器之辨,主张器为体,道为用,有其器则有其道,无其器则无其道,“圣人之道,果非空言而已,必有所丽而后见。丽于耳目,有视听之道;丽于心思,有仁义智信之道;丽于伦纪,有忠孝友恭之道;丽于礼乐征伐,有治国平天下之道”[1]155。观此可见,在谭看来,传统伦理虽具有一定的依附性,但同时也有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其中“丽于伦纪,有忠孝友恭之道”,从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儒家的人伦学说,“忠孝友恭”是“伦纪”的自然呈现和基本内涵,“伦纪”是“忠孝友恭”的本体论基础和前提;自社会言之,“伦纪”是自然关系,“忠孝友恭”是当然之则。进一步,在谭氏看来,伦常并不仅限于中国这一特定地域,而是具有某种普遍性。通过中外比较,谭氏发现,中外“所食”、“所饮”、“所衣”、“所需”无不相似相类,世俗之人“独于伦常,窃窃然疑其偏绝”。在谭氏看来,伦常依俗而立,是维系人类存在的根本道德,具有形式的普遍性,“夫伦常者,天道之所以生生,人道之所以存存,上下四旁亲疏远迩之所以相维相系,俾不至瓦解而土崩。无一息之或离,无一人之不然,其有节文之小异,或立法之相去甚远,要皆不妨各因其风俗,使捷于知而便于行,未有一举伦常而无之者”[1]156。中西伦常的不同表现为理一分殊、名同而实不同。从伦常对人类存在的必要性而言,中外皆然;从伦常因俗而立的差异性而言,中外异焉*谭嗣同另有《论学者不当骄人》一文,肯定“西人最讲究伦常,且更精而更实”,并举父子、夫妻等为例。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第401页。。在谭氏看来,西方无五伦之名而有五伦之实,且西方五伦之内涵无不优于中国。究其实,西方尚法而略文,中国则尚文而略法,此一说法涉及法与德的关系,中国强调德治乃至泛道德主义,导致虚伪、缺乏自主自立,人与人貌合神离,“使古今贤圣君子于父子兄弟之间,动辄有难处之事”[1]157。中西之不同,不在于有无伦常,而在伦常内涵的不同。所以,伦理重建就是要向西方大胆汲取,取彼之长改造已之所短,而据“理一分殊”之说伦理重建同时也就是取之自身,因为“在人言之,类聚群分,各因其厚薄,以为等差,则有中外之辨,所谓分殊也。若自天视之,则固皆其子也,皆俱秉彝而全畀之者也,所谓理一也”。从人性的角度看,中外则并无不同,所以“酌取乎同乎我者,是不啻自取乎我”[1]159。伦理重建必超乎伦理之囿,而达乎法律,时人有谓中国之变当从“正人心”、“正上位之人心”开始,谭氏则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西人之人心未必皆正于中国,中西不同不在伦理人心而在法之有无和良否,“亦彼之法良意美,我无法而已。法良则中人以下犹可自勉,无法则中人以上难于孤存。法良则操莽无从觊觎,无法则尧舜终于犹病”[1]171。可见,法之有无和良否关乎国之强弱和存废,法应当“与时为变”,但“法之当变,非谓变古法,直变去今之以非乱是、以伪乱真之法,蕲渐复于古耳”[1]160。谭氏借复周公之法,鼓吹重建社会秩序和人心,达到抵御外敌,强盛国家的目的。
谭氏重建传统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并未完全超越传统,而是从策略上考虑,通过恢复传统的方式吸纳新时代的内容。传统的深远影响同样表现在其对家伦的认识和实践上。
三、亲情守护
谭氏认为,网罗重重,无穷无尽,人生在世,无往而不在网罗之中。所谓网罗就是对人的种种束缚,是对人的主体性、独立性、本真性等的约束和规制,从而,所谓冲决网罗就是恢复人的自然面目即恢复人的主体性、独立性、本真性等。这里的预设是人的原初存在是完整的、独立自在的,这样的理解似乎只能是纯粹哲学意义上的,从现实之维来说,人很难说原本就是完整的、独立自在的。不仅从生理上说人刚出生谈不上独立自在,甚至尚未出生,就有各种关系先期存在了。人生在家优先于人生在世,家庭就是先于人生在世的伦理实体。正如人无法选择时代一样,人也无法选择家庭。
人的存在具有多维性,从思想上看,谭氏鼓吹“冲决伦常之网罗”,其态度坚决;从现实上看,当我们将其短暂的一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时*论者往往将谭之思想分为前后不同的时期,并且过分强调后期思想而忽视前者思想。事实上,作为真实的具体的存在,人的完整性是不容割裂的,不能因后期思想的转变而完全否定早期的思想。本文将谭氏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在思与在的统一中体会其重视亲情的一面。,则未必尽然,毋宁说,在激烈的思想背后隐藏着对家庭亲情的眷念和守护。
三纲五伦中有二纲三伦属于家庭伦理的范围,谭氏对家庭伦理的态度和理解蕴于对三纲五伦的认识和理解中。事实上,谭氏对三纲五伦的认识有一过程,从认同到怀疑到否定,大致分三个阶段。
少作《治言》倡华夏中心主义,认为华夏之国“经纬、风教、礼俗于以敦,而三纲五常于以备也”。“立乎华夏而言,自东而北而西,或左或右或后,三方环以拱者皆夷狄也”[5]232。对纲常从正面加肯定。
《酬宋燕生道长见报之作即用原韵》中对“以三五教圣长死”一句作注云:“伦而不言天人,已足杀尽忠臣孝子弟弟,于吞声饮泣莫可名言之中。乃复有纲之残酷济之,所谓流血遍地球,染大地作红色,未足洩数千年亿兆生灵之冤毒,悲夫!”[5]244-245对纲伦表达了强烈的怀疑和不满。
《仁学》认为“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5]248。鼓吹“冲决伦常之网罗”,除朋友一伦外,对三纲五伦大加挞伐。
谭氏对三纲五伦态度的变化是因应于时代的变化、认识的深化,而其中不变的是对真正的人间亲情的守护。
《仁学·自叙》:“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对于“遍遭纲伦之厄”,人们多从其“为父妾所虐”*梁启超《谭嗣同传》:“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故操心危,虑患深,而德慧术智日增长焉。”、“不得父欢”*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谭继洵素宠妾,嗣同以嫡出,因不得父欢。”见《谭嗣同全集》第31页。又,谭继洵“素宠妾,谭氏以嫡出而母又早亡,故备受虐待。而谭氏性格又发扬蹈励,反对一切守旧泥古的主张,迂陋循谨的人物,因之父子之间的意见遂成冰炭”。见杨廷福:《谭嗣同年谱·年谱前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页。等着眼,以此来诠释谭氏对传统纲伦的激烈态度之所由。这样理解似乎有简单化之嫌,没有注意到“吾自少至壮”一语。我们不妨考察一下谭氏“自少至壮”过程中家庭人员的变故。
12岁时,其二姐嗣淑、母徐五缘、大哥嗣贻相继病死。“少更多难,五日三丧,唯亲与故,岁以凋谢,营营四方,幽忧自轸。……同母五人,偶影坐吊”[2]452。其亲属在京师死亡的计六人。嗣同死去三日而苏醒,其父更其名曰复生[6]31。
25岁时,其仲兄嗣襄在台湾以疾卒,年三十三。
26岁时,“从子传简卒”[6]58。传简是其堂兄嗣棻之子,随从嗣同多年。其子幼殇,以二哥之子传炜兼祧[6]17。
“自少至壮”,母死子殇,兄亡侄故,“谁知骨肉半人鬼”[2]492,家庭的巨大变故对其思想不可能不产生特定的影响。
所以“遍遭纲伦之厄”更多是对天伦之丧的写实,其目的与其是借“纲伦之厄”从抽象意义上对普遍伦常加以否定,毋宁是在家庭的变故中更真实地体会到纲伦的切己性。特别是童年的经历对其人生观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左舜生先生所言,“这是嗣同童年期最受刺激的一事,大致也是他自己对生命不甚恋恋的原因之一”。“后来他在《仁学》一书,对中国伦常观念有不少过激的想法,和他在童年时所遭遇的,实不无关系”[7]202。
从亲情伦理的角度来看,谭氏对父、兄、妻等的关怀、思念从不曾忽略。
作为试图化传统之人,谭氏本身也有被传统所化的一面。五伦观念已深入其内心,成为其潜意识的一部分。虽说父子关系并不很融洽,但“父子有亲”、“施由亲始”等传统故训不可能不对谭氏产生任何影响。《北游访学记》透露了其内心的真实情感:“于是重发大愿,昼夜精持佛咒,不少间断:一愿老亲康健,家人平安;二愿师友平安;三知大劫将临,愿众生咸免杀戮死亡。”[1]127观此三愿的次序,仍是传统的亲亲而仁民而爱物,据血缘之远近,由近及远。但谭氏之孝亲又与传统略有不同。在谭氏的思想意识中,尊亲是一种基于自然的亲情伦理,不必经人为的提倡。他对子思“莫不尊亲”一语,分析说:“不必即尊亲,其人自由其道而莫之知也。”[1]159在谭氏看来,父子之亲源自天然,不必经过人为的倡导,而子对其父自然有尊。例如,谭氏对其父亲从不敢直称名讳,在《石菊影庐笔识》中始终用“大人”、“家大人”、“膏泽”等尊敬的称谓;在求职、做事时始终不敢违逆其父的诫命;遭捕后极力为父亲开脱*陈叔通《谭嗣同就义佚闻》:戊戌政变,大刀王五“愿挟以出亡”,但嗣同“惧罪连其父,方代父作责子书,为父解脱”。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0页。另,左舜生说:“当他在戊戌八月被捕的前夕,逻卒在门,他自己已经视死如归,但仍能从容不迫,为他父亲造出几封告诫儿子的家书,以免他的老父横被牵累,您难道可以不承认他是十足的孝子吗?”(《谭嗣同评传》,见《春风燕子楼左·舜生文史札记》,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213页。)。
对于其殇子,谭嗣同并无文字记录,其情感无从得知,但“无后为大”的孝伦理仍对其产生一定的影响,“兼祧”就是这一影响的表现。(当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是出自谭的本意。)
关于夫妇关系。嗣同19岁与李闰成婚,对自己的“婚姻也不满意”,不满意或许出自包办婚姻而非出于自主,但婚后相处得很好,“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2]495。多年来志同道合,尤其对妻子恪尽妇道,“养亲抚侄”充满感激之情。《到家二篇》:“孤岭破烟石径微,湾头细雨鸬莺飞。有人日暮倚门望,应念归人归未归。”妻子对自己的思念之情,谭氏能设身处地地理解,对妻子在家乡的安全问题也充满挂念[5]531。左舜生先生曾就此评价说:“婚姻要怎样才算满意,这是很难说的,但我们能说嗣同在夫妻之间,便没有深厚的情感吗?”[7]214
关于兄弟之爱。嗣同自幼与二哥在一起,极笃于兄弟之爱,分别后,屡有咏吟追怀之作。闻噩耗,痛苦不能自已,“创巨痛深,瞢不省事,哭踊略定,则志隳形索,清刻至骨,自顾宛如五六岁孺子也”[5]89。四五年中,哀思难寄,“吾之抒吾哀也,笔焉而中止,与不止而卒毁其草,不知其几”[5]95。
综上可见,嗣同对家始终充满着眷顾和留恋,亲情萦绕于心,不能忘怀,对家、家族从来都未忽视,《寥天一阁文卷第二》收有多篇谭氏为其先祖、族辈所立的家传。故所谓“杀身破家”[1]2、“杀身灭族”之说当辩证地看:基于个体的独立性、自主性而言,自我担当,“杀身”或有之,但如果因此而招致“破家”、“灭族”则无论在思想上或在现实层面上都不为谭氏所认同。谭氏“冲决伦常之网罗”更多地侧重于被社会化、虚伪化的伦常,而不是指出自内心的自然的真正的伦常,一如魏晋士人们表面反礼实乃内心尊礼的表现。
思与在的紧张和冲突从来就很难化解。一方面,谭嗣同在思想中鼓吹废伦常(只保留朋友一伦),另一方面,谭嗣同在实践中又忠实地践行伦常,表面上的冲突显然不能仅仅用言行不一、言不由衷等来理解,思与在的矛盾必须在深层次上加以解释。左舜生先生从谭嗣同的天性、从超越的维度进行诠释,我们认为是比较准确的,他说:“实际这种地方矛盾是完全没有的:大凡一个天性笃厚而情感真挚的人,他是无往而不表现其笃厚与真挚的。如果懂得孝之为孝才去尽孝道,懂得弟之为弟才去尽弟道,这已经落入第二义,而全不自然,更谈不到与天地同流了。‘天性’两字最为紧要,只有具有这种性格的人,才可说废伦常,因为他的笃厚与真挚已经超越伦常而行乎其所不得不行,而决不是不及伦常而必须出之以勉强哩!也只有具有这种性格的人,才真能杀身救国,才能舍身救世,以我细细体会,嗣同可当之无愧也。”[7]215
思必越位,行必素位,梁启超转述康有为的话,用在谭嗣同的身上似乎同样合适。
[1]张岱年.仁学——谭嗣同集[C].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2]谭嗣同全集[C].北京:三联书店,1954.
[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儒家哲学[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82.
[4]史华慈,等.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自由主义[C].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0:200-203.
[5]蔡尚思.谭嗣同全集:增订本[C].北京:中华书局,1981.
[6]杨廷福.谭嗣同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7]左舜生.春风燕子楼·左舜生文史札记[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张家鹿]
EthicalBreakandRelativeGuardianshipontheDimentionofNoumenon——on Tan si-tong
QIAN Shan-gang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Basing o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s,TAN Si-tong borrow the west discourse,reconstruct ontology.The ontology has differential layer.From the view of world,Ether is the noumenon; From the view of society,‘Ren’is the noumenon.Tan sitong deconstructs traditional core rules of moral,at the same time,he absorbs new era content by reliving tradition.but by the true concrete Being,He insists on the relative guardianship.
reconstruct noumenon; ethical break;relative guardianship
B82-09
A
1000-2359(2011)05-0020-05
钱善刚(1967-),男,安徽明光人,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合肥师范学院政法与管理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和伦理学研究。
2011-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