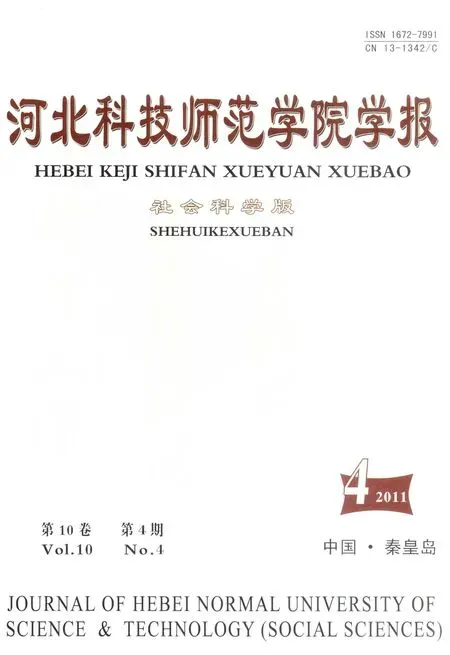林道静形象的互文性解读
李秋香,阎浩岗
(河北大学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林道静形象的互文性解读
李秋香,阎浩岗
(河北大学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青春之歌》叙述的是一个青年女性知识分子追求自我实现的奋斗历程,它的前文本是鲁迅的《伤逝》、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茅盾的《虹》。几种前文本对于女性解放问题进行了各自的思考,做出了不同的回答。《虹》与《青春之歌》的互文关系更为直接。梅行素和林道静的性格中都有不安分和为自我实现而敢作敢为、不顾流俗的一面。但梅、林二人性格和经历不同的一面给人印象更深,其中的意味也更值得分析。梅行素与林道静性格最大的区别,是梅的“疑”和林的“信”。林道静性格中的不成熟和她的理想主义激情一起,正是其独特文学魅力之所在,因为它意味着青春。
《青春之歌》;林道静;《虹》;梅行素;互文性
若抛开具体意识形态内涵,可以说,《青春之歌》实际叙述的是一个青年女性知识分子急欲摆脱平庸凡俗的生活方式、寻找理想、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奋斗历程。在《青春之歌》之前,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类似的故事早已存在,且构成一个系列。《青春之歌》的显性前文本主要有鲁迅的《伤逝》、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茅盾的《虹》。
林道静为什么会献身革命事业?虽然为了合乎主流话语,作品在一开始就特别设计了林道静沙滩上看见“华人与狗不得通过”的木牌、海边迷路遇到逃荒过来的山东女人、与余永泽同居时魏老三来借钱等情节,但从文本提供的信息及人物性格逻辑看,促使林参加革命的直接的和主要的因素,却并非“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因此上面设计的这些情节也显得有些生硬,有外加的痕迹。林道静从北平逃到北戴河是为逃婚,是因她要“做一个人”,为保持人的尊严她不惧颠沛流离,不惜冒险甚至牺牲生命,而决不愿为物质享受失去做人的尊严,不愿马马虎虎活在世上。她最怕的是平淡、平凡和平庸。在海边的杨庄当了小学教员后不久,“平淡的乡村,平淡的生活,甚至连瑰丽的大海,在道静的心目中,也渐渐变得惨淡无光”,“即使和余永泽的初恋,也没有能够冲淡这种阴暗的感觉”。这时,卢嘉川出现了。对林道静来说,卢的魅力就来自他的英俊的仪表和不凡的谈吐,来自他的“和一般人不一样”。小说里写她对国难的忧虑实际是“被煽动起来的愤懑情绪” 。
因此,国难发生后“她自己空虚的心灵”反而“也似乎充实起来了”。她还是与余永泽相爱并同居了,两人也有过甜蜜和温馨,虽然在白莉苹一类人看来他们的生活很清苦,但余在生理需要之外还给了她爱的需要的满足。不过,在低一级需要满足之后,更高的需要就占据主导了:她需要得到社会的尊重,需要自我实现,所以锅碗瓢盆的家庭生活再次使她感到了凡庸空虚,以至不能忍受。这时,卢嘉川再次出现。卢也是一见就喜欢上了林身上那种“又倔强又淳朴的美”,主动和她接近,引导她走上革命的道路。林卢的接近当然有林正在寻找出路和卢要发展事业、壮大革命队伍的因素,但他们之间相互的好感乃至爱慕,不能不说也起了重要作用。卢给林看的那些革命书籍里面提供的“预约券”(茅盾语)又应和了林的不满现状、向往理想世界的性格,使之“对于未来幸福世界的无限热情激荡着、震撼着”,“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和满足”,使她重新焕发了青春。卢准确指出了她的革命动机,尽管林辩护说自己绝非自私自利的人,但她的确不是“为了拯救人民于水火”,而是为逃避“现在平凡的生活”而革命的,这个在文本中得到了明确揭示。《青春之歌》对林这一段心理过程的描写很真实,对她后来思想转变、接受集体主义和群体观念的描写也能令人信服。不能因《青春之歌》没有像路翎《财主的儿女们》写蒋纯祖那样写出主人公内心深处个性主义与集体主义两种力量带来的矛盾痛苦而怀疑指责前者的真实性,因为林道静和蒋纯祖属于不同的性格类型。她对于群体或集体并不反感、并不抵触。在听说要参加纪念“三一八”的群众集会时,“她被一种新奇的神秘似的感觉兴奋得许久都不能安静下来”。林道静虽然希望得到社会尊重、寻求自我实现,并从“五四”精神那里得到思想资源,但自我实现并非只有个人奋斗一条途径可以达到,否则那些参加了集团斗争的非常著名的革命家也不能算是“自我实现”了。对有些人来说,集体固然会给其个性带来约束甚至压抑,但集团群体的斗争却又成为其自我实现的方式。杨沫及其笔下人物林道静就属于这一类型,20世纪中国的另外一位革命作家丁玲也属于这一类型。她们都达到了普通人难以达到的自我实现,而其实现途径却和萧红、张爱玲截然不同。不能因为丁玲、杨沫没有成为萧红、张爱玲而认为她们完全失去了个性、没有达到自我实现。她们最终成为了那样的人,是因她们本来就是那样的人!
林道静走向社会、走向革命的故事,使人联想到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几位名家的名作,即鲁迅的《伤逝》、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茅盾的《虹》。这几部名作对于女性解放进行了各自的思考,做出了不同的回答:《伤逝》强调了经济独立的重要性,而其后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虹》写到了经济以外的东西。困扰莎菲的不是离家之后的生计无着,也不是爱人的变心,而是找不到真正的精神寄托,寻不到真正让自己为之倾心的男性:苇弟乃一“萎”弟,缺乏男子汉气概,从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无法让莎菲折服;凌吉士的肉体曾打动了莎菲,但其灵魂的平庸又使莎菲厌弃。而《虹》所写梅行素的故事与《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故事具有更多可比性,两者构成直接的或显性的互文关系。笔者私下揣测,当年茅盾最先站出来肯定《青春之歌》并指出其艺术上的缺点,不是没有原因的。将它们进行比较更有益于认识《青春之歌》的特色和价值。
两部作品中可以构成两相对应的几组人物,除了梅行素对林道静,最重要的就是柳遇春对余永泽,韦玉和梁刚夫对卢嘉川和江华。此外,还可列举出其他次要人物,比如徐绮君对王晓燕,黄因明对林红,梅父对林母等。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因不能忍受世俗的平庸生活特别是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走向社会,投向革命献身“主义”,最后都是走上街头参加了“五卅”或“一二九”的游行示威;梅行素和林道静的性格中都有不安分和为自我实现而敢作敢为、不顾流俗的一面。但梅、林二人性格和经历不同的一面给人印象更深,其中的意味也更值得分析。梅行素与林道静性格最大的区别,是梅的“疑”和林的“信”。张中行在谈到他和杨沫的分歧时,就分别用“疑”和“信”来概括。可以说“信”是杨沫终生的性格特点。杨沫的“信”有时还导致“轻信”,直到晚年还因此而受骗[1]。作者的这一性格特点在小说主人公林道静身上表现得也很明显,第1部里既突出了她刚一接触“主义”便深信不疑的理想主义精神,也有多处写到她因轻信而导致失误的错误。梅行素虽然也是敢做敢闯,但她颇有心计,始终对周围男人和女人的世界保持着警惕戒备;在处理与钟情于己的韦玉、柳遇春、徐自强和李无忌的关系时,她始终掌握着主动权,除了对韦玉还有所依恋牵挂,“没有一个人能打动她的心,也没有一个人的心胸不被她看穿”(《虹》第8章)。即使最后单恋梁刚夫,她的爱也是伴随着征服欲。梁对她的冷淡,使得受惯了注意的梅觉得难堪,她还曾设想过“给他看了点利害以后就永远丢开他”。她参与政治活动,其实也是从要赢得梁的尊重的动机出发的。在参与了政治活动后,她还当心着被人利用。虽然她不是一个有意玩弄男性情感的人,但却有一种优越感存在。在梅行素身上,多少还有一些莎菲的影子。在这方面林道静全然不同。梅从小受到父亲娇宠,长大后又被不同的男性追逐;林虽然也是天生丽质,却自幼被父亲忽视、受后母虐待,加之离家后的生存困境,她似乎没有形成在异性和同性面前的优越感。按照初版,对林有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恋情的男性有5个,即余永泽、卢嘉川、许宁、赵毓青、江华。余永泽救下林道静后,“道静对这个突然闯进生活里的青年,带着最大的尊敬,很快地竟像对传奇故事中的勇士侠客一般的信任着他。”而对卢嘉川,第一次见面,“道静立刻被他那爽朗的谈吐和潇洒不羁的风姿吸引得一改平日的矜持和沉默”,第二次见面就“好像对待老朋友一样把什么都倾心告诉了他”。对江华,还没正式见面,她想象江的形象时,就“整个心灵被年轻人的狂热的幻想陶醉了”。见面后,虽然并未爱上江,但也对之推心置腹,倾诉衷肠。林道静和梅行素的差异,既是性格差异,也反映了她们各自所处时代的特点,即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不同特点。到了20世纪30年代,阶级与革命话语已取代人道主义与个性解放话语成为主流,虽然直到20世纪40年代仍有坚持“五四”启蒙话语或在接受阶级革命话语的同时仍不放弃“五四”话语的知识分子,但林道静的经历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时许多青年从接受“五四”启蒙思想到接受阶级革命思想的心路历程。这正是这一文学形象的文学史价值。现在很难用“进步”或“倒退”来评价这一时代转变,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历史事实,《青春之歌》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了这一转变,就自有其价值。
《虹》里的梅行素形象比较出色地反映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某种精神。梅行素对于“主义”尚停留在“将信将疑”阶段,林道静却已经是深信不疑了。疑而不信或将信将疑的态度是“研究”,深信不疑的是“信仰”。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疑”和“信”各有其存在的精神价值,没有“疑”就没有理性,没有科学,而没有“信”就没有精神归宿和精神支柱,没有激情。“望梅止渴”典故中曹操的兵士正是凭着对曹操所谓梅林的“信”战胜了本来无法解决的强烈的干渴思饮问题。林道静性格中的不成熟和她的理想主义激情一起,正是其独特文学魅力之所在,因为它意味着青春。毋庸讳言,这青春蕴含了昆德拉指出的可怕的东西,但更象征着强大的生命力。《青春之歌》里的爱情描写虽然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规训”,但在今天看来,就初版本的描写而言,仍有其文学价值和艺术魅力。林道静绝非在男女关系方面随便的人,这一点使她和茅盾笔下的“新女性”区别开来,也与白莉苹之流迥然不同;但她又不受世俗伦理的束缚,她在处理与余永泽和江华的性关系时体现了这一点。林与余的分手主要因处世原则和做人目标的差异乃至对立,因为“道不同”,而分手后林对和余在一起的生活仍有所怀恋,小说初版对林路过故居时内心感受的描写很动人;林道静与江华的理性型、现实型恋爱又不同于她与卢嘉川的恋爱,林与卢的关系具有彼岸性,因而在内心深处更具有不可磨灭的印痕,属于“此恨绵绵无绝期”类型。这和几十年后出现的张洁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爱情,具有同样的魅力。它写得理想而真实,因为它是以作者本人的生命体验为基础的。
杨沫动笔创作《青春之歌》时的心理状况是“被某种说不出的创作欲望推动着,每日每时都想写——一些杂乱的个人经历,革命人物的命运,各种情感的飘浮,总缭绕在脑际,冲动在心头”[2],这使得《青春之歌》里面包含着许多作者原初的生命体验与真挚情感;而初稿完成交付出版社以及初版面世引起社会反响后,编辑、读者、著名作家和批评家们的意见对这个学养不太深、创作经验不太丰富的女作家影响很大,使她情愿和不太情愿地对原稿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对照梁斌、柳青和姚雪垠创作时的高度自信自决,他们对老友和资深作家、批评家们提出的意见既虚心听取又能在关键问题上坚持己见的做法,杨沫的差距就显现出来了。《青春之歌》艺术上的不完整性既与其独特的题材及当时的语境相关,也与作者本人的性格和思想艺术修养分不开。
[1]老鬼.母亲杨沫[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250-265.
[2]杨 沫.自白——我的日记:上[C]//杨沫文集:第6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106.
Intertextuality of the Image of Lin Daojing
Li Qiuxiang,Yan Haoga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ebei University,Baoding Hebei 071002,China)
The Song of Youth illustrated the struggling process of a young female intellectual in pursuit of self-realization.Its pre-text include Lu Xun’s Sadness,Ding Ling’s Miss Sophie’s Diary and Other stories,and Mao Dun’s Rainbow.These pre-texts reflected on female’s liberation respectively and gave different answers.The intertex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ainbow and The Song of Youth is more direct.Both Mei Xingsu and Lin Daojing’s characters contain the aspects of discontentment and being afraid of no difficulties and old customs,which led them to achieve self-realization.But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se two left deeper impression on people,the meaning of which deserves analyzing.The biggest difference of Mei Xingsu and Lin Daojing’s characters lies in Mei’s“doubtfulness”and Lin’s“honesty”.The immaturity of Lin’s character,together with her idealism,leads to its special literary charm,because it means youth.
The Song of Youth;Lin Daojing;Rainbow;Mei Xingsu;intertextuality
I206.7
A
1672-7991(2011)04-0056-03
2011-09-01;
2011-10-27
李秋香(1963-),女,天津市河东区人,馆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以林道静为例
——重读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
——解析《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