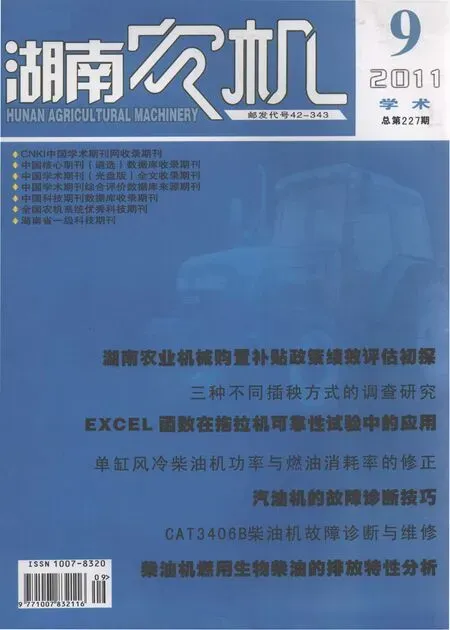武侠世界中女性的记忆力
张大圣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苏州 215104)
1 “过目不忘”母题的由来
早在魏晋时期,西域僧人的博闻强记,就引起了当时中原人极大的惊赞与钦敬。西域僧人的这种“异术”追究其根源应与古印度的文字产生和文化传承方式有着密切关联。古印度与古代中国不同,公元8世纪前的古印度还未产生文字,因而口耳相传的方式成为当时宗教经典和世俗文献的传播方式。A.L.巴沙姆在其著作中就曾指出,佛陀“为了使他的教义在听众的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也为了使他的教义便于传播,佛借助于重复关键词语和词组、列出编号的术语的方法以及其他记忆法。”可见,口耳相传的方式是当时西域僧人传布教义的主要途径,各种各样的记忆术是其传布教义的主要技巧。 谭中、耿引也曾在《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中指出过:由于“印度不同种族、血统、语言、文字的社群中都有的婆罗门阶级”,因此嘴巴“成为在没有纸张的印度实行语音统一的策略,……这样的口头文化传统促进了印度人口才和记忆的高度发达,别的民族简直无法相比”。
由此可见,“过目不忘”母题的产生与当时的佛经传译活动是有着密切关联的,“过目不忘”异术的习得应是其长期接受训练的必然结果。
在佛经文学中,这种博闻强记的奇异还从僧人延展至了普通人。百二十回本《法苑珠林》卷一百二就记载了这样一则宗教故事。文中写妒忌多瞋、不信佛法的萧铿女死后,其信乐佛法的婢女闰玉,冥游时作为一个见证人,饱览了萧氏受酷刑的情状,还被教会了用梵音诵经,用意在警醒世人。还阳后在麟德元年,西域的四个婆罗门来献佛骨,在将军薛仁轨家设斋,诸亲聚集。众人假说闰玉的诵经术是别的婆罗门教的,想密试闰玉的虚实,当闰玉以梵音诵《金刚般若》完毕:“此四婆罗门一时俱起,合掌怪叹:‘希奇!未曾有也。何因汉人能得如此?’”又诵《药师法华》,四位更加欢喜,恭敬如师,叹为非凡。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这么认为,佛教传播口耳相传的方式对“过目不忘”母题的产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佛经文学更是对这一母题的凝练给予了极大的推动。
2 女性“过目不忘”的传统
在撷取佛经故事有关神奇记忆、过目不忘传闻的片段中,我们不难发现女性避开其体力上明显的弱势,超人的记忆能力受到了比男性更多的关注,甚至于女性的相关故事隐藏着某种神奇、惊异和钦敬的意味。从而,在以男性为中心社会中,“过目不忘”的女性展现出了一种独特的魅力。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文学作品中,“过目不忘”母题的主角往往是女性。比如,《后汉书?列女传》中记载丈夫董祀获罪,蔡文姬为替丈夫脱罪辩解时,便展现出了“过目不忘”的出众才华:操因问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馀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当然,“过目不忘”的男性人物也是有的,但却常是丑陋怪异之人。比如,在《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张永年反难杨修,庞士元议取西蜀”中登场的蜀中名士张松。小说中借杨修之口指出张松其人“且无论其口似悬河,辩才无碍。适修以丞相所撰《孟德新书》示之,彼观一遍,即能暗诵,如此博闻强记,世所罕有。松言此书乃战国时无名氏所作,蜀中小儿,皆能熟记”。可见,名士杨修对张松在博闻强记方面的才能万分钦佩。但反观张松的外貌却让人大为失望,小说中记载 “其人生得额䦆头尖,鼻偃齿露,身短不满五尺,言语有若铜钟”。究其原因,这与“人们一边崇拜死了的天才,一边敌视活着的天才,所以天才要交好运就得早死。”这一“削强适弱”的无意识心态有密切的关联。
不过,在古代众多文学作品中女性与“过目不忘”的“异术”的关联也多以精神异常状态来表现。宋代《太平广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宋刘甲居江陵。元嘉中,年十四,姿色端丽。未尝读佛经,忽能暗诵《法华经》,女所住屋,寻有奇光。女云,已得正觉,宜作二七日斋。家为置高座,设宝帐,女登座,讲论词玄。又说人之灾祥,诸事皆验。远近敬礼,不可胜数。衡阳王在镇,躬率参佐观之。经十二日,有道士史玄真曰:“此怪邪也。”振褐往焉,女即已知,遣人守门,云:“魔邪寻至。凡着道服,咸勿纳之。”真变服奄入,女初犹喝骂,真便直前,以水洒之,即顿绝,良久乃苏。问以诸事,皆云不识。真曰:“此龙魅也。”自是复常,嫁为宣氏妻。
可见,当时对“过目不忘”在女性身上的体现更多是将之解释为神魔鬼怪附着于人身。这使得原先不同寻常的技艺因为神魔鬼怪的非凡能力而变成了雕虫小技。但无论何种解释,女性在“过目不忘”母题中的确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
3 金庸女性世界中的“过目不忘”
作为以男性话语为主导的武侠世界,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也作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存在。在他的武侠世界里,一群聪明可人而又身负“过目不忘”绝技的奇女子形象(比如王语嫣、黄蓉等)诞生并与男侠们并立。这或许与金庸小说整体上对于女性的人文关怀是一致的。
金庸的“射雕三部曲”就不乏对这类人物的描写,除了聪明绝顶、武艺出众的黄蓉之外,她的母亲黄夫人对研究女性在“过目不忘”母题中的表现具有更为典型的代表意义。
在 《射雕英雄传》中周伯通就曾这样描画过黄夫人的异术:周伯通告诉郭靖,说当年他从师兄王真人手中接过《九阴真经》,藏好上卷,带着下卷要到雁荡山,途中遇到黄药师和新婚的妻子,因打石弹相赌输了,不得已将经书给了不会武功的黄夫人看。“只见黄夫人一页一页的从头细读,嘴唇微微而动,我倒觉得有点好笑了。《九阴真经》中所录的都是最秘奥精深的武功,她武学一窍不通,虽说书上的字个个识得,只怕半句的意思也未能领会。她从头至尾慢慢读了一遍,足足花了一个时辰。我等得有些不耐烦了,眼见她翻到了最后一页,心想总算是瞧完了,哪知她又从头再瞧起。不过这次读得很快,只一盏茶时分,也就瞧完了。……黄夫人道:‘这部书我五岁时就读着玩,从头至尾背得出,我们江南的孩童,十九都曾熟读。你若不信,我背给你听听。’说了这几句话,便从头如流水般背将下来。我对着经书瞧去,果真一字不错。我全身都冷了,如堕冰窖。黄夫人又道:‘任你从哪一页中间抽出来问我,只要你提个头,我谅来也还背得出。这是从小读熟了的书,到老也忘不了。’我依言从中抽了几段问她,她当真背得滚瓜烂熟,更无半点窒滞。黄老邪哈哈大笑。我怒从心起,随手把那部书撕得粉碎,火折一晃,给他烧了个干干净净。”
可见,对武学一窍不通的黄夫人所拥有的“过目不忘”异术的确为人惊叹。曾有学者指出,金庸小说中“女性惊人记忆力的拥有及使用,往往会伴随着沉重代价的付出”,并以黄夫人作为典型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认为“神奇的记忆力,仿佛像一把双刃剑,其在解决了某一重大问题时,也伤害了使用者自身”。这样的案例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确能找到一些先例。比如,《太平广记》曾记载:“长女曰应贞,适弘农杨唐源。少而聪颖,经耳必诵。年十三,凡诵佛经二百馀卷,儒书子史又数百馀卷,亲族惊异之。初,应贞未读《左传》,方拟授之,而夜初眠中,忽诵《春秋》,起‘惠公元妃孟子卒’,终‘智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凡三十卷,一字无遗,天晓而毕。当诵时,若不教之者,或相酬和。其父惊骇,数呼之,都不答。……年二十四而卒。”但细数金庸小说中具有此种异术的女性人物,却未必都如此不得善终。
王语嫣是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的主要女性人物之一。她“端庄中带有稚气”,自小与母亲生长在曼陀山庄内寸步未离。她与表哥慕容复青梅竹马,因为表哥热爱武功,为他熟读各派武学秘笈,对各家武学了如指掌,是一位不谙武功的武学理论家。但王语嫣虽然丝毫不会武功,却是一部武学活词典。武林中各门各派秘传绝学,甚至失传绝学,全部装在她的心中,可以随时滔滔不绝地道出。《天龙八部》中曾有这样的记载:“这是‘清凉扇’法的打穴功夫,第三十八招‘透骨扇’,倒转扇柄,斜打肩贞。这位朱先生是昆仑旁支、三因观门下的弟子,这一派的武功,用判官笔比用扇柄更是厉害”。王语嫣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便把一位武学名家这一招的名称手法、师承来历、武学家数说得清清楚楚,可见其记忆力的惊人。
此外,从《天龙八部》的描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王语嫣的惊人记忆能力,已经到达了融会贯通的层次。她不仅熟知各门派武学的招式与路数,更对招式的实战运用技巧有着深刻的认识,甚至到达了随口点拨,便能使人武学技艺大增,反败为胜的境界。比如,她说“适才你使了青海玉树派挪一招‘大漠飞沙’之后,段公子快步而过,你若使太乙派的‘羽衣刀’第十七招,再使灵飞派的‘清风徐来’,早就将段公子打倒在地了,何必华而不实的去用山西郝家刀法?又何必行奸使诈,骗得他因关心我而分神,这才取胜?我瞧你于道家名门的刀法,全然不知”。对武学的如此认识,王语嫣足以令武侠世界中的武学名家汗颜。
《天龙八部》中王语嫣貌美、具备“过目不忘”异术和惊人的记忆力,虽然感情经历了恋情的苦涩,但最终却收获了一份可贵的真情,结局是圆满的。在枯井中,段誉以“你的表妹,却是我的了,你再也夺不去了”为宣言,宣告了王语嫣苦涩恋情的终结,打破了中国文学作品中“过目不忘”女性必定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怪圈。
4 结语
作为小说的传统母题,金庸在其武侠世界里给予了女性,特别是具有惊人记忆能力的“奇女子”们以充足的人文关怀。以《天龙八部》中王语嫣为典型代表的女性,打破了中国文学作品中“过目不忘”女性必定要付出沉重代价的禁锢,为“过目不忘”这一传统母题在武侠小说领域的进一步开拓与传承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