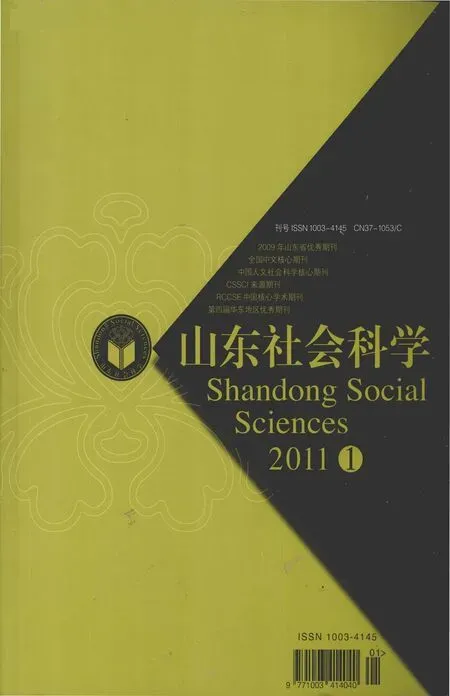翻译、期刊与文学现代性*
高志强
(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所,北京 100164)
翻译、期刊与文学现代性*
高志强
(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所,北京 100164)
翻译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建构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时,中国文学现代性所包含的复杂矛盾和内在冲突,也决定了翻译文学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现代文学期刊不仅为翻译文学提供了物质载体,更通过编者、译者、作者、读者和出版方之间的多维互动有效地建立了现代文学的公共空间。期刊、翻译与现代文学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多重对话格局,也正是在这种对话中翻译文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促进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促成了白话文学语体的成熟,培养了作家也哺育了读者,多层面地参与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
翻译文学;期刊;文学现代性
19世纪后期,列强的炮火震醒了古老中国的千年大梦,民族存亡面临危急关头,王朝统治渐至穷途末路,旧有的社会秩序和价值秩序呈现出一片混乱和瓦解态势。内忧外患之中,中国开始踏上追求现代化的艰难道路。现代性遂成为观照 20世纪中国社会图景的核心词语,渗透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每一个角落。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现代中国人社会生活和思想情感最重要的表达形式之一,自然也无可避免地体现出对现代性的追求、探索和反思。这一点可以上溯至晚清,当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改革均告失败之后,具有感时忧国的精神传统、急欲实现民族自救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把目光投向了文学。无论是梁启超倡导的小说革命和晚清启蒙思潮,还是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都是自觉地将文学作为以民族自强振兴为旨归的中国社会整体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也必然体现出后发现代化国家在追求现代性目标时所特有的文化逻辑和纽结于其中的种种复杂矛盾。例如,文学的现代性与西方文化资源和传统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和民族国家的现实危机,文艺的审美特性与社会功用性,救亡与启蒙,社会现代化追求与美学现代性批判,等等,都是中国新文学在构建其现代方案时所必然要面对的问题。
与其他领域发生的现代性变革相似,由于传统文化出现了严重危机,因此中国文学在迈向现代道路时,也是首先以外来资源作为建设新文学最重要的参照系。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语境中,这种外来资源主要被理解为西方文学和文化。这也就是人们常常说的,“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这种表述其实并不严密,因为它混淆了两个容易被人们等同起来、而实质上并不相同的概念:外国文学和翻译文学。前者是指外国作家用其本国语言(亦即源语言)完成的著述,而后者则是指翻译者用译语国语言对前者进行翻译后形成的文本。有学者指出,“无论是语言差异而导致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还是由于文学翻译过程中种种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出现的创造性叛逆现象,译作都不可能是原来意义上的外国文学作品”①谢天振、查明建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第 6页。。就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实际情形而言,由于大量的读者和作家并没有机会接触到外国文学原著或是不谙外语,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真正对现代中国的文学趣味、观念和创作方法产生巨大影响的,实际上并非“外国文学”,而是外国文学作品经由文学翻译后,以译语形式表现出来的新的存在形态:“翻译文学”。也正是在这一认识前提下,翻译之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建构的重要意义才得以彰显。
1898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指出:“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因此梁启超主张要“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于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①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 37页。这篇文章向来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最早阐明翻译文学重要性的理论文献。在这里,梁启超不仅将“小说”这种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历来被轻视的文学样式赋予了一种崭新的功能和意义:启发民智、改造社会,而且明确提出,这种功能并不存在于“不出诲淫诲盗两端”的中国传统小说中,而只能通过翻译西方小说获得,由此,他极大地肯定了翻译文学的功用。1902年,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再次强调:“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②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 54页。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对翻译小说的推崇和倡导,是基于他对小说“新民”功能的强调和“有关中国时局”的前提之上的,而对于小说本身的文学性则相对忽视。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思路似乎也预示了翻译文学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它将必然受到现实环境的制约,将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和承担启蒙的重任,同时也将面临着在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和选择。
与梁启超的理论鼓吹相呼应的,是清末民初翻译文学的高潮。据统计,晚清小说刊行的在一千五百种以上,而翻译小说又占全数的三分之二。③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年版,第 4页。其中特别是林译小说,以其数量众多、译笔优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尽管晚清翻译小说也存在着对翻译对象的选择较为随意、译者对原著删改过大等不足之处,但无论如何,正是这一时期的翻译文学,使国人对西方社会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和文学艺术有了初步的了解,激发了人们对于“现代”社会和文学最初的想象,并为日后“五四”时期的文学变革和文学翻译做好了蓄势待发的准备。
1917年,新文化运动促成了文学革命的发生。后者明确提出要建立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现代性质的中国新文学。由于“五四”峻急的反传统姿态,早期的新文学倡导呈现出鲜明的新、旧两分的思路。一方面,传统文学被认为是“旧”的和“落后”的文化产物而遭到不加辨析的激烈否定;另一方面,西方近现代文学则作为“先进”和“现代”的文学范本,成为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建构中最主要的参照和借鉴。从论证文学革新的观念开始,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就频频援引西方文学的史实经验作为论据。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造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④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 7-8页。为例论证语言革命的重要意义。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开篇则称以“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⑤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 95-96页。作为文学变革的楷模。及至新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各种文体的创作实践,则无论是观念还是技巧,无不深受西方近代以来文艺思潮和文学作品的影响。
很显然,这种“西方文学”的影响,也主要是通过翻译文学而得以实现的。正如《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讨论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文学思潮与运动时所指出的那样,大规模的文学翻译活动,实际上构成了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⑥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在“五四”之后的短短几年中,西方近现代各种文艺思潮和相关的哲学美学思潮都被介绍到中国,西方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的作品都有人进行翻译,目的就是为了大量引进外来文化、思想、语言和文学样式,以供新文学建设之借鉴。加之这一时期,新式教育的迅速发展,使得译者队伍扩大、翻译水平提高。文学社团大量涌现、期刊和出版业的发达,也从客观上为系统译介外国文学提供了有利的文学环境和物质媒介基础。当时,文学社团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如文学研究会对俄国和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译介,创造社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推重,沉钟社对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介绍,等等。很多重要的“五四”作家同时又是翻译家,如鲁迅、沈雁冰、周作人、郑振铎、徐志摩、赵景深、朱自清等,一般刊物和出版社也都积极热心地出版刊行翻译作品。由此,形成了“五四”文学翻译的高潮。正如王哲甫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指出的,当时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以资借镜”,因为“中国新文学尚在幼稚时期,没有雄宏伟大的作品可供借镜,所以翻译外国作品,成了新文学运动的一种重要工作”⑦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海书店 1982年影印版。。
以色列学者埃文 -佐哈尔曾经指出,作为文学史上一支基本的形成力量,翻译文学在某一文化内形成高潮有三种特定条件:一是当某一民族或国别文学处于发展初期;二是当该种文学觉得自己处于边缘或“弱势”阶段或二者兼而有之;三是当该种文学处于某种转折时期或危机时期或一种文学真空时期。⑧埃文 -佐哈尔:《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庄柔玉译,《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 118页。“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学,上述三种情况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整个文学正处于现代转型时期;传统文学被强烈质疑和批判;新文学则处于发展初期,亟待有效地建设和确立自己的话语规范。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翻译文学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可以说,大规模的文学翻译活动构成了新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翻译文学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参与并深刻影响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笔者在此想着重加以辨析的是,翻译参与构建新文学现代性的方式,实际上是在两个不同层面上发生的。一是以翻译的结果即译本的形式,在译语文化中对译本的读者 (从中国的实际情形来说,翻译文学的读者群中也包括大量的新文学作者)产生影响,如影响他们的文学观念、文学趣味,提供可资借鉴的技巧方法等等,并进而在译语民族自身的文学创作中体现出这种影响。这种方式通常有较为清晰的线索可辨,例如许多作家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经历时会明确声称受到外国文学 (实际上是翻译文学)的影响,或者我们通过对作家作品的分析解读,也往往能够发现其在题材、风格、技巧等方面所受到的外来影响及其变形。
翻译参与新文学现代性建构的另一种方式则要相对隐蔽,也更易被人忽视,那就是在翻译过程之中的译者行为。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认识到,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绝不仅是一种透明的、单纯的不同语言间的符号转换行为,而更是一种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化阐释。在这个过程中,翻译者的思想倾向、审美趣味、译入语的文化传统和译语文化的现实需求、接受环境等因素,都会对翻译行为 (如翻译对象的选择、翻译策略的使用等等)产生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翻译也可以视作是“译入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则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中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①谢天振:《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中国翻译》2001年第 4期。。从“五四”文学翻译的实际情况来看,当时重要的翻译家几乎同时都是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他们译介外国文学的根本目的也都十分明确,“非从事摹仿西洋而已,实将创造中国之新文艺”②《改革宣言》,《小说月报》第 12卷第 1号。。这种鲜明的现实吁求必然对翻译行为产生影响,例如,译者对翻译对象的选择偏好(选择什么样的作品来进行译介),对翻译策略的使用(是使译作更接近译语文化的“归化”翻译还是更接近源语文化的“异化”翻译),对原作有意或无意的“误读”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等等,实际上都是翻译者自身文化主张的某种隐晦表达,而他们也正是通过翻译这一特殊的文化行为,深刻地参与、推动和影响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追求中所包含的种种复杂矛盾和内在冲突,如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启蒙与救亡、文艺的审美特性与社会功用、文学自身的发展建设和民族现实危机之间的选择等等,也都同样会在那个时代翻译者的翻译行为中留下深刻的烙印。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大量文艺期刊凭借自身出版周期短、信息快③如茅盾为《小说月报》写作海外文坛消息,订阅了不少欧美的报刊,有泰晤士报的“星期文艺副刊”、纽约时报的“每周书报评论”等。、售价低廉④《小说月报》刚革新时每册 2角,六册 1.1元,十二册 2元;后来改为每册 2角,十二册 2元 4角。、持续时间长、影响巨大⑤郑振铎在 1925年 4月 25日致周作人的信中提到《小说月报》当时的印数为 14,000册。等特点,在多方面起着书籍译作无法企及的作用。许多卓有成绩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构成中,期刊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事实上,对于现代翻译文学的研究而言,期刊研究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最早都是刊登于各种期刊杂志的,期刊可以说是翻译文学重要的原生地。从期刊入手考察,更有助于我们进入翻译文学的原生文化语境,不是将文学翻译活动简单地视作不同语符之间的转换,而是将其理解为一种文化事件,这样就可以做到如叶维廉所说的“充分了解创作历史的泉源”,“掌握它们在其间全面演化生成或持续的历史意识,明白每个文化事件,每个创作行为根生的历史”⑥叶维廉:《语言的策略与历史的关联》,《中国诗学》,三联书店 1992年版,第 210页。。
中国近现代报刊的出现,最早在 19世纪初,是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华文报刊;随后,在 19世纪 50年代,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办的报刊。早期的报刊并没有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当时也很少有人意识到它在舆论宣传方面的巨大作用。至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开始明确强调报刊言论对社会思想的启蒙作用,各地报刊也随着改良运动的风起云涌而纷纷出现。康有为指出:“新报犹足以开拓心思,发越聪明,与铁路开通,实相表里。”⑦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文集》上册,中华书局 1981年版,第 132页。康有为将报刊与铁路并举,诚可谓有识之见。修建铁路带来的是现代社会在物理意义上的空间拓展和物质流通渠道的建立,而创办报刊带来的则是文化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和新的知识传播方式与信息交流渠道。对一个试图迈向现代进程的社会来说,这二者都不可或缺,而“表里”之说更表明人们已经意识到了报刊在传播思想、启蒙观念、影响社会方面的巨大作用。报刊的出现也使得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办报撰稿来发表自己的思想见解、参与社会实践,这也为知识分子突破科举“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生存方式、向具有独立地位和见解自由的现代知识分子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启蒙思想的进一步传播,新式知识分子队伍的进一步扩大,加上印刷技术和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各种报纸期刊的涌现就更如雨后春笋,蔚为大观。
在现代期刊杂志中,文艺性期刊是重要的一个部分,此外许多综合性期刊也都登载大量文艺作品。可以说,现代报纸期刊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极为密切。
首先,由于相当数量的现代文学作品和翻译作品最早都是发表于各种报纸和杂志上,所以对于现代文学以及翻译文学而言,报纸和杂志首先是与传统传播方式完全不同的重要物质载体。这也是现代期刊最基本的功能。
其次,作为现代传媒的报刊提供了连接编者、作者和读者的桥梁,并且通过这种连接有效地建立了一个公共空间,或者说,构筑了某种“想象的共同体”。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一方面,编者和作者可以通过设计栏目与创作作品来传达他们对于文学现代性的想象和追求。编者的办刊宗旨及其编辑思路,由于隐藏在物化形态的栏目和作品背后而常常容易被人忽视,而事实上,正如译者在译作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一样,编辑的文化主张和编辑思路也是决定刊物面貌的基本制约因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不同的期刊往往表现出各自对于某种文学主张和文学倾向的偏重,以及和某个文学社团的密切关系,例如《小说月报》之于文学研究会,《创造周刊》、《创造季刊》之于创造社,《新月》之于新月社,《语丝》之于语丝社等等,这正可说明现代文学期刊的编者们选择作品和建立作者群落时的倾向性。可以说,编者正是通过确定办刊方针、设置刊物栏目、甄选作品、向作者约稿以及引导读者市场等编辑行为来决定一份刊物的基本面貌,并由此表达其对文学现代性的理解和追求。另一方面,读者也并非只是被动地接受作品,他们同样可以通过其阅读反应和喜好来对文学发生影响,从而参与到现代性想象的多声部合唱中。而期刊的出版和发行特点,例如从版面上可以为读者提供发表言论和编读往来的空间、出版周期快从而反馈信息及时等,则使得期刊读者的这种能动性影响体现得更加鲜明。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原生地和物化呈现,现代文学期刊也必然带着鲜明的中国现代性烙印,前文中曾谈到的中国新文学现代性追求中所内蕴的种种矛盾和紧张,也同样会在期刊中体现出来。无论是从编辑的思路和举措,还是从编者、作者、译者、读者和出版方多重声音构成的对话中,都能折射和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复杂和丰富、冲突与选择。
此外,作为文学在现代市场运行机制下的产物,作为“一种负载精神产品的商品”①董丽敏:《想像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4页。,期刊的经济属性也必然对其所承载的文学发生一定影响。例如,由文学期刊而产生的专职报人、撰稿人、职业作家和规范的稿酬制度,使得现代知识分子可以以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和生存方式并由此实现其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这也是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内容。再如,期刊在市场运行中的发行数量、社会反响和读者的阅读趣味等,反过来也会对出版机构的办刊策略乃至编辑的选稿标准和作者的写作取向等产生一定影响。而当作品的思想性或文学追求与刊物的商业利益不能一致时,就可能出现期刊的文学性、思想性与商业运作之间的冲突。《小说月报》前后期的差异就是鲜明的例子。前期《小说月报》主要登载以迎合市民读者趣味为主的“鸳鸯蝴蝶派”小说,译作中也颇多强调故事性、情节性的言情、侦探小说,虽然其首任主编也声称以“灌输新理,增进常识”②《编辑大意》,《小说月报》创刊号。为宗旨,但显然是更偏重于商业运作的考虑;而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在实际操作中固然也不乏针对市场特点和读者心理的经营之举,例如缩小字号、增加篇幅、组织征文等,但从整体而言还是体现着茅盾在《改革宣言》中提出的“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进之方法”③《改革宣言》,《小说月报》第 12卷第 1号。的宗旨,其偏重于新文学建设的立场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当我们在启蒙思想、文学追求和商业运作等多重视角下考察现代文学期刊时,本身也暗示了文学现代性的多维向度及其内在的不确定性和矛盾性。
综上,由于期刊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密切,而现代文学的建设又以翻译外国文学作为重要的途径和内容,现代期刊对于翻译文学的重视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从现代文坛的实际情形来看,文学革命后,不仅是文学期刊,一般的报纸杂志也都多有译作刊登,可谓一时之风尚。期刊不仅像其他出版物一样可以为翻译文学提供物质载体,而且其在编、写、读之间的桥梁关系以及其周期短、传播广等特点,也使得期刊能够以多种形式对翻译文学产生影响,如通过编辑策略对翻译文学的发展动态和具体的翻译实践作出潜在的引导,期刊上同时登载译作和创作能更直观地实现翻译和创作之间的互动,从读者反应能够看出翻译和接受环境的互动,等等。特别是在新文学建设早期,很多知识分子往往是一人身兼文艺期刊的编者、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和翻译文学的译介者等多重身份,这就更直接地促进了期刊、翻译和现代文学之间的对话和互动,也正是在这种对话和互动中文学期刊及其刊载的翻译文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促进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促成了白话文学语体的成熟,培养了作家也哺育了读者,多层面地参与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I046
A
1003—4145[2011]01—0155—04
2010-10-04
高志强 (1976-),男,山东省泰安市人,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所博士。
(责任编辑:陆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