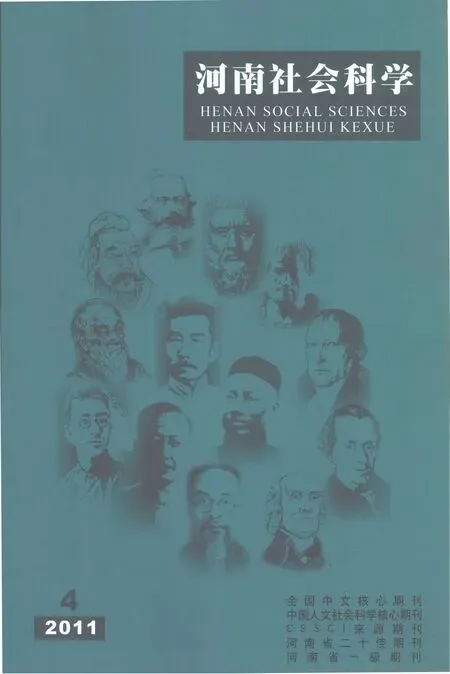嘈杂的世界,分裂的文明,女性的困境
——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解读
姚晓鸣
(中原工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7)
嘈杂的世界,分裂的文明,女性的困境
——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解读
姚晓鸣
(中原工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7)
发表于1962年的《金色笔记》在2007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作者多丽丝·莱辛常借助其作品以怀疑来思考历史的进程,以热情去谋略人类的长远命运和社会群体的处境,正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提到的:“莱辛以史诗诗人般的女性视角,饱满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以及深刻的怀疑精神,剖析了一种分裂的文明!”《金色笔记》以现实主义为基调,以心理分析为主要创作技巧,刻画了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多种主义共存并相互冲突的年代里知识女性的两难处境和选择。
一、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在柏拉图以来的欧洲哲学史中,二元对立是人们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且已深入人心。二元对立思想表现出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其直接后果是二元之间有你无我、片面排斥,如:灵魂/肉体、自然/文化、男性/女性、语言/文字、真理/谬误等[1]。这种二元项的对立并非平等并置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通过设立第一项的优先性而迫使第二项从属于它,第一项是首位的、本质的、中心的、本源的,而第二项则是次要的、非本质的、边缘的、衍生的。在《金色笔记》中,影响安娜生活的基本二元对立包括生活中的“秩序/混乱”和思维中的“理性思维/非理性思维”。安娜向往“秩序”而逃避“混乱”是因为她理性的思维方式压抑着非理性的思维方式。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禁锢了安娜的思维,使她的思维不能正确地反映生活的本质,从而导致精神分裂。
二、《金色笔记》中的嘈杂的历史真实
20世纪50年代的世界是一个伤痕累累、格局混乱的动荡世界。多丽丝·莱辛把20世纪中期整个世界的风貌的描写融入其作品《金色笔记》,外部世界的凌乱,艺术形式的混乱与主人公安娜精神的分裂杂糅在一起,勾勒出一幅嘈杂无序的全景画中画。二战后,大英帝国无奈地逐渐放弃了其帝国建造者身份,殖民主义日益弱化。主人公安娜生活的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直到1980年才赢得自治。安娜的记忆里塞满了殖民制度下的种族歧视和政治冲突,那令人不安的一幕幕在安娜的心头挥之不去,却又愈发清晰,成为游荡的梦魇,徘徊在她的精神世界,蚕食着她的生命和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国际共产主义制度的影响延伸到欧洲,安娜加入了英国共产党,但她参与的政党也是以二元对立的方式运行的,对理性的崇尚使英国共产党本身陷入了表面主义而忽略了成员的个体需求。苏共二十大以后,安娜的政治信仰起伏不定,并深深感到了民主政治生涯的艰辛与磨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就像男人们的屠宰场,无数军人流血牺牲,一去不返。驻守家园的女人们,原先的母亲、妻子、女儿、姐妹,走出家庭的狭小天地,独自面对广阔天地。她们走入工厂、农庄、铁路、煤矿,做着原先男人们做的工作。当时的许多女性欣喜于眼前的新变化和新天地,而这种变化促进了英国女权运动的萌芽。而战争结束后,她们被迫离开她们的战时工作岗位回归家庭,恢复了传统的家庭角色。因为男权社会认为女性快乐的真正源泉是相夫教子,打理家务。心理学家费迪南德·伦德伯格(Ferdinand Lundberg)和玛丽尼亚·范恩汉姆(Marynia Farnham)在1947年公开谴责女权主义:“女权主义的公式是尽可能地转变自己为男人,使举动像男人。因此得以重回到满足性本能的地位。这一公式不会起作用。”[2]这种社会观念中的安娜·沃尔夫,作为一个自由女性,不得不在作家、母亲、妻子与情妇的四重角色中苦苦挣扎……
三、分裂的文明与安娜的困境
安娜生活在一个传统观念崩溃、社会结构混乱的时代,作者把五本笔记穿插其间,目的是以此描写20世纪中期整个世界的风貌。“黑色笔记”描写主人公在非洲的经历,涉及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红色笔记”是她的政治追求,记录她对斯大林主义由憧憬到幻灭的思想过程;“黄色笔记”是她的感情轨迹,是一个题为《第三者的影子》的故事;“蓝色笔记”是她的日记,记录了主人公的精神轨迹;最后的“金色笔记”是作者对人生的哲理性总结。前四本日记所呈现的都是从深受挫败感而到困扰、精神分裂的安娜,第五本讲述了她摆脱分裂、自我整合的过程。
(一)安娜的写作障碍
在安娜的写作生活中,“秩序/混乱”的二元对立具体体现在“真实/虚假”和“确定/虚无”中。在黑色笔记中,安娜的文学理想就是“秩序/混乱”二元对立中的“秩序”,崇尚理性的安娜认为一部好的作品必须对生活做出哲理化的表述,必须“充满理智和道德的热情,足以营造秩序,提出一种新的人生观”[3],只有这样才能抓住生活的真谛,而充满“虚无主义”和“虚假怀旧”的文学作品则是“混乱”的体现。
安娜并没有意识到,她在非洲的经历本身就是混乱和虚无的。在撰写《战争边缘》的时候,她的出发点是想通过事实再现来揭露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非洲的种族问题,但人们却不约而同地认为该小说是描绘爱情题材的作品。安娜为不能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不能描述真实的体验而苦恼,她说:“我是舞弄文墨的人,希望文字的组合,哪怕是偶然的文字组合能够表达我的真实感受。……而事实上,真实的感受不能被表达。”[3]安娜对文字的表述力失去了信心,文字也变得不再可靠。她找不到自己写作障碍的真正原因,她试图消除《战争边缘》中的那种非理性、不健康的情感和那种对不加约束的放纵不羁的希冀却无济于事。在黑色笔记的末尾,她写道:“我讨厌这种口气。然而,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们就一直生活在战争之中,我相信,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这是一种自我惩罚,感情的封锁,一种对无法将相互冲突的事物糅合成一个整体的无奈和逃避。这样,不管战争多么可怕,人们就能在其中生活下去了。这种逃避意味着既不去改变什么,也不去破坏什么。这种逃避最终意味着个体的死亡和凋零。”[3]
安娜没有意识到,小说中流露出来的非理性是潜意识的,是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她无论如何都逃脱不了虚无主义与非理性。对理性的信仰和对非理性的难以逃脱增强了她的挫败感和虚无感。对身为作家的安娜而言,文字是她拥有自信、创造理性生活的唯一途径,是她克服混乱、保持自我完整的永不生锈的利器。然而,当她意识到文字已不再能够充当传达自己的真实声音的载体的时候,她的写作理想破灭,理智濒于崩溃,成为战争世界里的破碎人。受理性主义的限制,她投入到政治运动中寻求“秩序”。
(二)安娜的政治幻灭
出于受宏大的政治视角吸引,并希望能以此统摄其他较小的视角,进而建构世界中的秩序,安娜加入了英国共产党[4]。安娜把共产主义信仰当做自己生存、生活下去的全部理由,放眼全人类,塑造新世界。然而,英国共产党左翼为了维持它的“秩序”和理想主义,消除任何与“秩序”相背的东西。错误的二元划分扭曲了事实,很多党员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种错误划分加剧了安娜的精神分裂,导致了她对政治的失望。所以,安娜的政治活动并没有治愈她的分裂,反而给她带来了另一层面的分裂。安娜发现:“在过去的两三年中,这个国家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全国上下到处笼罩着一种紧张、多疑而惊惶不安的气氛,你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使它失去平衡,从而使麦卡锡主义在这里流行起来。”[3]
尽管英国共产党的模式并不能给生活带来真正的“秩序”,但是安娜他们依然不甘心放弃对它的幻想。比起这种虚伪的“秩序”,他们更害怕面对生活中的“混乱”,这是因为他们不能用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去认识“混乱”。为了保住这个避难所,他们自欺欺人,强迫自己去否认英国共产党犯错的事实。虽然安娜在笔记中的每个字都是在批判英国共产党,但在党内,她甚至情不自禁地为这个政党做辩护。安娜和她的朋友对待英国共产党的矛盾态度造成了他们性格的分裂。安娜也注意到了这点,她在红色笔记第一部分中写道:“今天回想起来,我觉得跟茉莉谈政治,简直就不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约是一个干巴巴的、聪明的、爱讽刺人的政治女性吧,要么就是个很有点疯劲的盲目的党徒。我自己也有双重性格。”[3]由于受二元对立思维习惯的压抑,她不敢面对生活的真实状态,也抓不到生活混乱的本质。经过反复犹豫、徘徊,安娜终于放弃了积极的政治活动,失望地退出了她所加入的政党,而她仍然害怕生活中的混乱,企图在爱情中寻找另一种秩序。
(三)安娜的感情危机
在黄色笔记中安娜记述了自己并不幸福的感情生活。为了抵制自己的分裂,安娜在小说《第三者的影子》中,把自己的感情危机投射在其主人公埃拉身上,把自己的情人迈克尔的形象投射在爱拉的情人保罗身上,试图通过将自我投射到虚构人物身上,从虚构人物的视角来客观冷静地、远距离地观察、分析自己和迈克尔的感情。但在这一部分中,二元对立中的“秩序”以性格定位的形式出现,“混乱”指的是对性格定位的挑战,这种错误的定位给男性和女性的关系带来了负面影响。性别定位已经深入安娜(埃拉)的思想中,她并不知晓在性格定位之外,女性和男性还可以具备其他的性格特征。就像Christopher Kilmarth在“Masculine Self”中指出的那样:“性别定位指的是那些被定义为男性或女性的一系列态度、行为和社会条件等,这一系列态度、行为和社会条件等可通过社会心理一代代遗传下去。每种文化对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定位都是建立在生理性别差异基础之上的,这两种性别定位是完全对立的。性别定位造成了性别压力,给男性和女性的性格都带来了缺陷。”[5]
一方面,因为典型的符合性别定位的男性通常被描述为强壮、独立、专断、不善表达情感等,所以,性别定位给男性的性格带来缺陷包括他们被剥夺表现脆弱和情感的机会,社会的期望使男性变得独断和贪婪,一旦男性不能达到社会期望,他们就会感到被动、空虚、失望、生气。另一方面,社会也给女性设定了一些标准,“年轻、肤浅、温柔、顺存、高高兴兴地生活在卧室、厨房、性、婴儿和家的世界里”[6]。职业女性被斥为魔鬼,稍微有一点自己想法的家庭妇女也受到排斥。就像在《第三者的影子》中,埃拉是一位职业女性,她和保罗维持了近五年的情人关系,最终保罗抛弃了她,并称她为“轻浮的婆娘”。作为一名自由女性,埃拉受到了家庭妇女的妒嫉和敌视,“而男人们在她身上所用的感情又是那样的平庸而令人失望。她的朋友把她看做藐视传统道德观的女性”[3]。但是安娜与传统家庭妇女的区别不大,她也需要男性的保护,她只是摆脱了传统家庭妇女的家务负担,她对男性和婚姻的态度和家庭妇女是一样的。安娜觉得自己虽然称不上传统妇女,但也算得循规蹈矩。她的生活始终难以纳入正轨,那是因为她觉得,或者说她有理由这样说,她至今也没有遇见真正像个男性的异性。这表明,如果安娜能找到一位真正理解她的男人,她宁愿变成一位家庭妇女。
在与保罗的关系中埃拉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但是她宁愿承受这种痛苦也不愿离开保罗。她认为:“世上没有一个女人愿意没有爱情地生活下去。”[3]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对性别的划分造成了女性对男性的依赖,虽然埃拉和保罗的关系并不能让埃拉满意,但她还在幻想着爱情的美好。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让埃拉依赖于男性,而保罗又不能按照她所希望的方式来爱她,埃拉的依赖和付出换来了保罗的背叛,这加剧了埃拉(安娜)的精神分裂,使她陷入了虚无主义。
(四)走出感情困境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秩序与混乱的冲突是贯穿《金色笔记》始终的主线,也是导致安娜精神分裂的根本原因。只有摒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接受生活多面性的合理存在,寻找认识生活本质的多极思维途径,在混乱中建构秩序,安娜才可能克服写作障碍,走出感情困境,恢复完整独立的人格。
黑、红、黄、蓝四本笔记反映了生活中个人、婚姻、感情、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分裂,以及安娜因受现实影响而人格分裂的过程,同时笔记写作也是安娜面对分裂、无序的生活现实,从不同的视角对生活展开观察和思考,在混乱中调整自我、应对矛盾的方法和策略。从不同的侧面思考生活,安娜离她的目的地越来越接近。
接连不断的梦境促使安娜领悟到人生的意义,也透视着安娜从精神崩溃到自我救赎再到重新整合的心理轨迹。她曾经梦到一个正在执行枪决任务的指挥官突然给被执行者松绑,并让这位被执行者把自己捆了起来,更换了角色。指挥官成了罪犯,罪犯当上了指挥官。这个梦突显了安娜内心深处的矛盾挣扎:世界上原本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善与恶”、“消极与积极”、“忠诚与背叛”,偶然间的一个换位就能颠倒是非。现实人生是不完美的,世界是由各种混乱的因素组合而成的一个整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现实面前寸步难行,多极思维才能冲破传统价值观的坚实壁垒。朦胧中,她听到有人说:“亲爱的安娜,我们并非如同我们想象的那样,是失败者……你和我将穷极一生地努力着,用尽我们全部的力量、全部的才智将那块圆石往山上推进哪怕一英尺。”[3]
安娜豁然开朗。人生的价值恐怕就在于这西西弗斯般坚持不懈的努力中。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推圆石的人尽管无法把圆石推上山顶,尽管他们所推的圆石甚至倒退了,但他们仍不是失败者。因为不应该苛求世界来适应人,而应该调整好自己去适应它。应该与这个完美的、混乱的世界达成妥协,与之和平共处。安娜走出了焦虑、绝望的情绪,并顿悟出生命的真谛:生活本身是支离破碎的,豁达接受毁灭的绝望;生命的意义在于抗争,始终怀有新生的希望。
《金色笔记》呈现了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的凌乱的外在面貌和一个时代的知识女性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借助西西弗斯神话传说,我们可以看到安娜最终认同了社会现实,重新开始坚持不懈地积极探索人生的本质和生命的终极意义,麻木的情感被消融,潜伏的创作力被唤醒,心理的羁绊被摆脱,失重的灵魂回到了常规。安娜所经历的一切在百折不挠苦苦挣扎之后,最终拨得云开见月明。
[1]胡鹏林.从二元对立到多元共存——走出实践美学争论的二元对立思维误区[J].烟台大学学报,2003,(3):305—309.
[2]Ferdinand Lundberg,Marynia Farnham.Modern Women:The Lost Sex[M].New York:Harper&Brothers,1947.
[3]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4]姜红.有意味的形式——莱辛的《金色笔记》中的认识主题与形式分析[J].外国文学,2003,(4):95—99.
[5]Kilmartin, Christopher.The Musculine Self[M].Boston: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2000.
[6]Friedan, Betty.The Feminine Mystique[M].New York:W.W.Norton&Company,Inc,1963.
2011-04-09
2009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2009CCJS-150)
姚晓鸣(1971— ),女,河南南阳人,中原工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