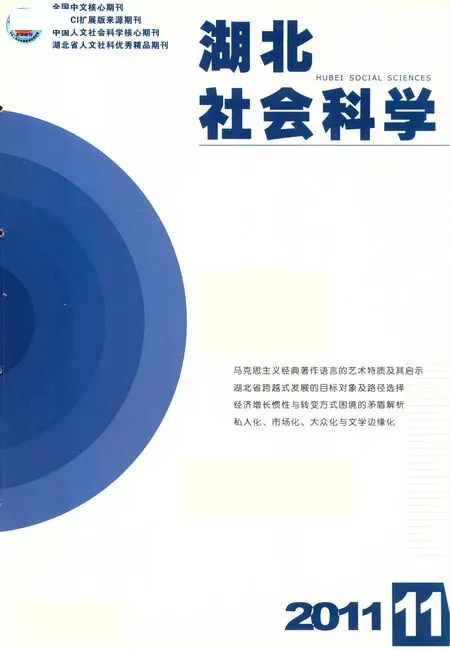老汉口市井文化对汉绣艺术的影响
冯泽民,叶洪光,万斯达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老汉口市井文化对汉绣艺术的影响
冯泽民,叶洪光,万斯达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19世纪,随着老汉口的繁荣,市井文化处于最活跃的时期,汉绣在此时也进入了兴盛期。市井文化对汉绣艺术的品种类别和艺术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这一角度看汉绣,更有利于深刻理解汉绣艺术的文化内涵。
汉绣;市井文化;品种类别;艺术风格
汉绣是以武汉为生产中心的湖北地域性刺绣品种,它的成长与发展与汉口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明清时期随着汉口镇的崛起,汉绣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清中后期,汉绣艺术从成熟进入鼎盛,成为雅俗共赏的地方名绣。此时老汉口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市井文化呈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对汉绣的绣品种类、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汉绣艺术品也成为表现当时社会生活风貌的载体。因此,我们将汉绣艺术和市井文化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汉绣艺术文化内涵的理解。
一、老汉口与市井文化
“老汉口”是武汉人对20世纪20年代前的汉口镇的旧称。当时的汉口从明成化年间的小村镇迅速发展,清初已成为长江中游有影响的贸易集散地,到清嘉庆、道光年间汉口已是各地商贾云集的“巨镇”,[1](p74)成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大多以经商为生。正如《汉口竹枝词》中所描绘的那样:“茶庵直上通桥口,后市前街屋似鳞,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2](p30)生动地记录了老汉口商业都市的繁华情景。
随着老汉口的商业愈加繁荣,规模愈加扩大,出现的商业街的专业性也愈强,就应运而生出以手工行业分工命名的许多街巷,如花布街、绣花街、打铜街、麻线巷等。老汉口商业的繁荣还表现在行当的多样性,无论是盐、当、米、木、布、药等六大行当,还是船工、搬运、卖艺等,市民的日常生活都浸染了浓厚的商业气息,从而我们可以看到老汉口繁荣的商业生活与它的市井文化密不可分。市井即街市、市场,这就决定了市井文化必定具有商业的倾向。我国的市井文化是伴随着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萌生发展而产生并成长起来的,其内容丰富庞杂,唯有商人精神一直贯穿始终。蒋和宝、俞家栋在《市井文化》一书中指出:“市井文化主要是指由市井之民创造出来的,以城市市民为主体的一种通俗性的综合文化。它不仅涉及文化的物质层面,也涉及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可以这样说:与其说它是市井生活之外的某处向市民发生影响和渗透,不如说它实际上就是市井生活本身。”[3](p19)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九分商贾一分民”中崛起的汉口镇,必然弥漫着浓厚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市井文化氛围。
市井文化也是一种市民文化,老汉口凭借“九省通衢”的地理优势,吸引了各地的商人,使得本地商业活动发达,人口急剧增加。到清嘉庆年间,人口已从明万历年间的5万人发展到13万人,成为重要的商业市镇。而且人员结构复杂,包括各省商贾和汉口周边农村破产农民、小商贩,以及手工业者,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市民文化。在这样的商业环境和市民文化的氛围中,逐步丰富和发展了汉绣艺术的品种类别和它的艺术风格。
二、市井文化对汉绣品种类型的影响
随着老汉口使用绣品的市民人数急剧增加,使得汉绣的品种更多,类型更丰富,满足了各个阶层和不同行业的市民需要,除通常的绣衣、门帘、绣鞋、头巾、围裙和荷包等生活用品外,还有以装饰欣赏为主的绣品,如壁挂、中堂、屏风和堂彩等,甚至连来往船只上标志吨位和其他事项的旗帜也是汉绣绣品。《汉口竹枝词》中记载的“数尺黄旗桅上挂”,[2](p9)在校注中解释为桅上挂黄旗是救生船的标志,黄旗上通常绣着该船所属机构的名称,及“救生”或“求安”等字样。市井文化是一种生活化、自然化的市民文化,与现实的一粥一饭、一丝一缕紧密相连。因而,从多样而丰富的汉绣绣品上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
商业的兴旺、经济的发达也让人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市民的日常生活更为丰富多彩,除衣食住行外,人们更加注重节日风俗、人生礼仪、信仰禁忌,以及娱乐游玩等社会生活内容。
在老武汉的婚俗中,常讲究“三茶六礼”,其中最具喜庆色彩也最繁琐的是“亲迎”、拜堂和闹洞房等,这离不了花轿、轿衣和绣花盖头,而女方准备的嫁妆中大多有精美的绣品,如绣花被、绣花枕头、帐帘等。据相关史料记载,辛亥革命后,一个洋行买办陈仙洲的儿子举行了轰动三镇的婚礼,其迎亲的花轿是在汉口曹锦云花轿铺特制的,富丽堂皇的花轿上盘金的红缎轿衣即是汉绣绣品。[4](p288)替长者做丧事也多有礼仪,其所使用的寿衣、寿被、奠字、棺罩和八卦衣等均为刺绣用品,甚至连棺材底层也铺上绣有“西方接引”字样的褥子。
富足后的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敬神拜佛,祈求平安,致使庙宇道观等宗教场所数量增加,最盛时达四百多所,因而需要绣制大量的宗教用品,如神像、道袍、袈裟、僧帽、佛堂桌围、龙帐和经幡等。在汉口现存的道观寺庙中,古德寺比较集中地保存了刺绣的宗教用品。武汉市博物馆藏有古德禅寺重新修建时捐出的门帘,它是完成于民国癸亥仲春,即1923年2月,门帘以红色绸缎为绣地,顶部中间用篆体刺绣了“古德禅寺”四个字。门帘上的图案以牡丹和仙鹤为主,绣品拙朴自然,庄重大方,富有装饰性,充分体现了传统汉绣的工艺特色。
城市的发展给市民带来许多娱乐方式,老汉口人们的闲暇生活中,最值得记叙的就是看戏听曲逛庙会。旧日庙会的舞台多设在大庙正殿前的露天场地上,人们在这里既敬了神又看了戏,还购了物,一举多得。相关资料曾记载,汉口开埠后,各地商贾纷纷来汉开设会馆和公所,最盛时达179处之多。这些会馆和公所每逢敬神、请客和喜庆都要请人演戏,一年数次,每次演出五六天甚至十多天。这也致使了传统戏剧服装成为汉绣的第一大宗产品并延续至今,使武汉成为全国三大戏衣生产地之一。
随着老汉口市井文化的发展,汉绣品种类型不断丰富,也使汉绣产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到19世纪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至光绪年间(1875年),汉绣绣品在汉口万寿宫亦即江西会馆周边,发展出32家绣货铺,将这一带打造成绣铺、作坊林立的刺绣一条街,汉口的绣花街也因此而得名。相关统计资料表明,当年汉口武昌两地,共有画师、绣工500多人,参与这一行业的绣女近2000余人。[5]19世纪中叶,汉口、武昌及周边地区刺绣行业的生产规模位居全国前列,仅次于苏绣。
三、市井文化对汉绣艺术风格的影响
市井文化不仅改变了汉绣的种类,而且影响了汉绣艺术风格的形成。2008年,汉绣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对它的评价中有这样的描述:“汉绣色彩浓艳、构思大胆、手法夸张、绣工细腻、专于装饰等”。我们不禁会问,汉绣的艺术风格形成于何时,又是怎样形成的。如果我们追溯到19世纪,从生活在繁华都市老汉口市民的身上,也许会对解读汉绣艺术风格有一定的启发。
当时老汉口繁华的商业生活,刺激了人们的牟利欲望,产生了趋利的市民心态,这是商业生活的必然产物,是商业社会中人的正常心态。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汉口市井文化明显地呈现出一种落俗的审美情趣。当时的人们在行业选择上,主要追求金钱利润;婚嫁生活上,更看重财富。[6]而在绣品选择上,也更加地注重强烈的视觉冲击,追求色彩的艳丽、浓烈,绣品常用高明度的正五色绣线在深色绣地上绣制图案纹样,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因而在汉绣中形成了很少使用浅色而多用重色做底的习惯。“远看颜色近看花”,色彩是一种最大众化的感觉,汉绣艺术在它的实践中,用浓艳的色彩迎合了商业环境下老汉口市民的某种心态。虽然落入俗套,但是却营造了一种热烈张扬的氛围,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地域性绣种的艺术特色。当它们保留在今天的汉绣中时,我们看到的是火一样的热情,就像地处“火炉”中的武汉人的性格一样。如一些表现喜庆吉祥的绣品,在大红的缎面上绣出五彩的“福”字或“喜”字,似有一种炽热的激情迸发,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般来说,趋利与避害两者互为补充,当趋利无法满足时,避害就成为人们最基本的心理追求。市井文化是一种最实在的生存文化,因而驱邪避灾就成为汉口市民中最普遍的心态,他们用生活中的各种形式来表达纳吉和祈福的美好向往。由于绣品上精美的图案、纹样有着丰富的意义,因此汉绣绣品广受市民们的喜爱。我们从今天汉绣老艺人仅存下来的清代汉绣残片中可以看到寓意着生活富足、婚姻美满、家庭和睦、健康长寿的龙凤、鸳鸯、牡丹、莲花、蝙蝠、寿桃、仙鹤等的吉祥图案,被五色丝线绣制在枕套、帐帘、被面、衣裙和头巾上。它们和当时充满商业竞争的社会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新的都市民俗风情画。在激烈紧张的经商谋利潮流中,这些人们最熟悉、最亲切的物品,带给他们人性的温暖。因而,这些传统的图案纹样连同它们朴实的价值一直保留在汉绣艺术的作品中,并且延续发展下来。
在老汉口的历史上,汉口镇作为一个重商业、轻农工的消费性市镇,涂饰行为遍布,虚荣之心炽热,大富商们争奢斗富,小商贩们追奢求富,市民们羡奢慕富,多种因素交织产生了奢靡、拜金之风,反映了当时汉口市井文化中一部分富有市民的社会心态。刺绣艺术品作为一种典型的奢侈品,自然受到了他们的追捧,然而由于拜金主义的影响,使得人们普遍对知识采取轻视态度,因此他们不欣赏如闺阁绣、文人画绣等,而喜欢用金银线绣制的刺绣艺术品,这些耀眼的绣线暗喻了生活中的黄金白银,满足了他们追求虚荣的心态。为了迎合这样的审美趣味,汉绣艺人在绣品中大面积地使用光亮的金银色绣线,表现出金碧辉煌、富丽堂皇的艺术氛围。用金银线所堆积的龙凤花卉,给人以奢华绚烂、耀眼夺目的感觉,充分体现了汉口市井文化中炫富拜金的社会心态。在针法上为达到这种艺术效果,艺人们大量使用了“平金夹绣”的工艺技法,久而久之,这种针法就成为汉绣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针法。
汉口商业经济的兴盛和外域文化的传入,冲击了旧礼教,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开放性特点。商业的发展也带来了城市人口的增长,使汉口成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市镇,并且形成了不同的阶层。迁入汉口的各地移民,带来了各区域独特的文化,这些不同区域的文化在汉口的市井生活中相互碰撞、交融,进而形成了融九州于一流的大众化的市井文化生活方式。汉绣艺术也开始朝着大众化的方向发展,满足了不同阶层的审美需求,通过汉绣艺人的加工创造,在针法上下针果断,图案边缘齐整,多从外围启绣,然后层层向内走针,进而铺满绣面;在色彩上采取的是块面式的分层破色,层次分明,绣面浑厚凸起,立体感强;在造型构图上,采用抽象的条纹、圆格组合构图,对画面中的山水花鸟、瑞兽祥云进行夸张变形,即使是有人物情节的绣画也常在周围绣制装饰性的角隅图案,更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汉剧戏衣上也使用了这种装饰手法,因此,它逐渐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地域性绣种的艺术特色,被业内的同行称之为“专于装饰”。汉绣绣品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受到了从达官显赫、富家子弟到文人墨客、商贾僧道、百工仆役各色人等的认可,使得汉绣艺术成为既可供上层精英欣赏,也可为市民大众享用的雅俗共赏的绣品。
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文化,每个城市的文化又有其历史的传承关系。19世纪,老汉口浓厚的商业气息使它的市井文化带上了浓重的商业色彩,并因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市井文化不仅影响了当时武汉的政治、经济,而且影响了生长在这个城市中的汉绣艺术。经过百年历史变迁,我们依然可以解读出市井文化深刻在汉绣艺术独特风格上的印迹。一座曾经充满活力的城市,滋养和培育出一个受大众喜爱的地域性的绣种,并赋予它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也是汉绣与其他地方绣种相区别的主要因素。今天,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的进程中,传统手工技艺离我们渐行渐远。我们回顾老汉口与汉绣艺术的这段历史,以期探寻传承和保护文化遗产更有效的方法与途径。
[1]范锴.汉口丛谈校释[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2]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校注[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3]蒋和宝,俞家栋.市井文化[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4]方明,陈章华.武汉旧日风情[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
[5]武汉市第二轻工业局,手工业合作联社编制办公室.武汉手工业精英集[C].武汉:武汉市档案馆,1984.
[6]周霞,扬薇.从叶调元《汉口竹枝词》看清中后期汉口市井文化[J].鄂州大学学报,2005,(1).
TS941.11
A
1003-8477(2011)11-0196-03
冯泽民(1951—),男,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叶洪光(1971—),男,博士,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副教授。万斯达(1989—),男,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在读研究生。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09YJA760034
责任编辑 高思新
——汉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