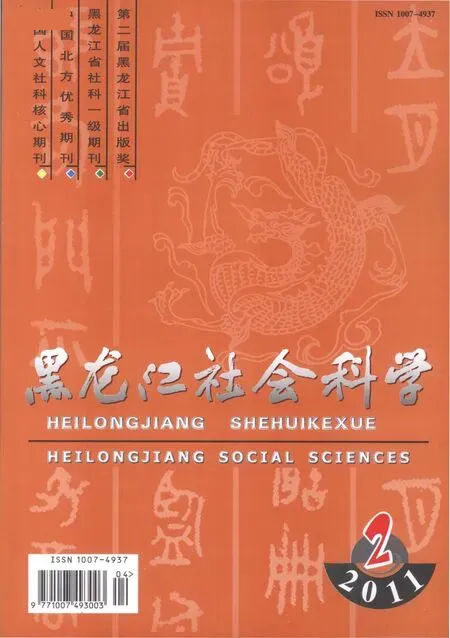后苏联俄国最初十年的历史文学:苏联作为被否定性再叙述的生活
林精华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037)
后苏联俄国最初十年的历史文学:苏联作为被否定性再叙述的生活
林精华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037)
后苏联到来过程,伴随着对苏联的批判、否定。这种潮流,既是文学的产物,也推动着文学的发展,由此推动了后苏联重新书写苏联文学的潮流。这种文学,包括回忆录、人物传记、苏联历史题材的小说等文类,成就了后苏联看来属于历史文学的潮流。这种历史文学潮流,在 1990年代,其作者多为苏联的亲历者,苏联也就成了被否定性的叙述对象。历史文学潮流的这种否定性叙述持续到 1990年代末,此后被对苏联的怀旧性叙述所替代。
后苏联;历史文学;否定苏联
一
对历史的文学性追忆,是俄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重要叙事传统,例如流亡中的著名思想家赫尔岑所写的鸿篇巨制《往事与随想》,给读者留下来的不仅仅是从十二月党人到 186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历史,更有作为知识分子的作者参与这段历史的现场感和独特理解。由此,卢纳察尔斯基主编的《文学百科全书》,甚至收录有“回忆录文学”条目,称这种文学是对历史的追忆性叙述和文学性描写相融合。不过,后苏联对历史的追忆还是不同于过往的回忆录,按批评家巴辛斯基《回忆录——一种复杂而崇高的文体》的说法,是全体俄国人都遇到了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我们无处躲藏”,对历史的追忆成为栖身之所和理解现在问题的通道。所以,早在 1993年著名批评家涅姆泽尔《未曾发生的事件:文学家视野中的悖论性历史》就敏锐指出,后苏联出现了思想观点各不相同的史学家、作家和政客等共同关注历史的现象,过去 (无论是真实的还是神化的)被证明是一个棱镜,经由它可以看见不确定的现在和模糊的未来,俄国人尤其感兴趣对俄国历史上转折点的讨论,并带来两种不同反应,或者抱怨过去的一切是一错再误,或者世故地认为不可能是别的,只能如此。
这种判断是有根据的,自苏联末期就开始重新叙述苏联的热潮:1986年流行艾布拉德泽导演的幻想性历史题材《悔恨》(反斯大林主题)、1988年出版地下作家鲍里斯·亚姆波里斯基的《莫斯科大街》,以及畅销多时的谢尔曼·阿拉诺维奇执导的影片《我当斯大林贴身警卫》、《我担任斯大林的机要秘书》和《人民的大型音乐会》等,促成了激烈否定斯大林和苏共其他领导人、拒斥苏联体制和苏联的历史文学艺术,在苏俄迅速畅销起来。并且,阅读历史文学不是临时性现象,不是部分读者的兴趣所为,而是一种社会潮流,是广泛的公共现象,按彼得堡公共图书馆和马雅可夫斯基城市图书馆数据,“最近十年来,读者对阅读历史文学远甚于此前的苏联时期读者”;2001年阅读调查显示,对 21世纪俄国读者而言,历史尤其是关于苏联的历史仍然是流行的读物,虽然这种趋势正如期间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那样——文献类的影视片日益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群,但俄国读者却经历了对自己历史的复杂变化。而且,历史文学艺术的这种广泛流行之情景,在表面上似乎是延续苏联时代对历史小说热衷的余热,也符合重新发现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复杂性的叙述,还契合俄国文学和历史关系本来就很模糊的情形,如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彼得大帝》和阿克肖诺夫《莫斯科传奇》等经典作品分别是对俄国不同时期历史的再叙述,而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肖洛霍夫、邦达列夫等则热衷于把自己时代的现实置入不同时段的历史语境下理解;但是实际上,后苏联的历史文学潮流和苏联时代对历史题材的文学艺术之热衷有很大不同,因为苏共意识形态掩盖了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公开性就是要寻求历史真相,这种政治变革行为却因文学在苏联的巨大能量,导致价值观和审美观念变化,即揭示历史性真理,走向重建历史。换句话说,这种历史文学潮流并非作家个人的一厢情愿,而是后苏联国家得以产生的重要动力、建构的重要方式:后苏联诞生于不断重新解释历史,尤其是重建苏联历史的过程中,即 1987年 2月戈尔巴乔夫在全苏宣传工作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如是主张——俄苏历史和文学不应该有被忘却的名字和空白点,应该有其真相,开始引发还原俄国原貌的历史文学;后苏联诸多变化,在很多方面是因对历史尤其是苏联历史的解释方式和立场有了变动。相应的,反复叙述历史,尤其是苏联历史,成为后苏联文学重要内容;后苏联文学变化过程,许多方面就是通过叙述苏联的立场或叙述方式的变化所标示的,并随时间延伸,“苏联人”、“苏联文化”和“苏联文学”等不仅是作为专门的历史概念,而且成为文学的内容,“苏联”之于后苏联人不只是历史,还是一种切肤之痛的记忆。这些情形,成就了这样的具体文学事实:在后苏联的文学产业中,仅次于大众文学规模的是历史文学;历史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类,包括回忆录、历史演义、历史小说等不同文体;后苏联的苏联历史文学的作者,不单单是历史小说家,也可能包括其他经历苏联的人。
二
在历史文学中,规模最大、经常引起社会关注的话题,是对执掌苏俄 24年 (1929-1953)之久的斯大林,以及被涂抹了浓厚的斯大林色彩的这期间并延及到苏联末期的苏俄体制和文化。1920年代末以来的苏俄,无论历史如何变革,包括文学艺术在内,斯大林总是挥之不去的形象,甚至是 1930年代后期以来的苏俄文学最热衷描写的人物,无论是正面塑造,还是反面讽刺批评,持续的斯大林热,甚至刺激了西方和东方的文坛。这种情势,自然刺激了历史文学中关于否定斯大林题材的文学繁荣。其中,曾亲历这场战争创作的两卷本小说《该诅咒的和该杀的》,是最应该被提及的。第一部《鬼坑》有题辞“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它从第 21步兵团的一个士兵视角生动描写卫国战争中的许多疯狂、恐怖景象,和苏联红军中不公正的死刑和威吓;第二部《登陆场》用日记体叙述红军解放基辅的一次战役,指挥混乱、官兵贪生怕死、政工干部虚伪并专横,尤其是讽刺性描写斯大林 1942年 11月 7日红场讲话——鼓励将士英勇抗战,但鼓励的对象是他怀疑的人民,并虚假通报战事进展的消息。
阿斯塔菲耶夫对苏联和斯大林的否定性描写,却没有妨碍他两次获得俄联邦国家奖 (1996年首次获得,2003年去世后又被追加一次),这是意味深长的文学社会学事件!远不只是阿斯塔菲耶夫在后苏联如此投身于批判斯大林及其体制的热潮,并激烈否定苏联津津乐道且引以自豪的卫国战争,实际上,这是 1950年代中后期解冻思潮所开启的描写卫国战争残酷性之先河的延续,许多作家先后发生了这种转变,如著名的犹太族裔苏联作家格罗斯曼,曾以《人民是不朽的》和《为了正义的事业》而赢得声誉,解冻思潮之后,耗时八年创作成功的 70万字巨著《生存与命运》严重疑惑这场战争的伟大性——以战壕真实派笔触披露苏军在战争中许多令人恐怖的事件,当时没能发表并殃及作家命运;该作直到 1988年才得以出版,这属于讨论苏联问题的正常升级;1990年代大量出现这类作品,是自然不过的接续。于是,继《阿尔巴特街上的孩子们》之后,雷巴科夫发表进一步强烈反斯大林的小说《灰尘与灰烬》。在此叙述中,1939年 8月 23日,在斯大林—希特勒操纵下签署的苏德外长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协约,实际上已对苏联构成严重伤害,是战争的一部分,而且这份《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仅是临时的军事撤退,还是有意识的选择;被苏联官方打扮成卫国战争功勋、地位仅次于斯大林的伏罗希洛夫,实际上是缺乏军事指挥能力的,他和斯大林等军事领袖对战争进程的延误,是卫国战争变得艰难起来的最主要原因。
同样,著名的老作家列昂诺夫在后苏联创作的长篇巨著《金字塔》,自动放弃苏联时代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獾》、《小偷》、《俄罗斯森林》等现实主义诗学,改用幻想形式,叙述“大战爆发前一年”的苏联,天使德姆科夫来地球探访,作为撒旦化身的撒旦尼茨基教授设下陷阱,让天使逐渐丧失创造奇迹的本领,无法回到自己的世界,若不是东正教神甫女儿杜尼娅相助,天使几乎离不开地球。陀思妥耶夫斯基、但丁、歌德等著名文学家影响下的俄国,在斯大林时代变成了魔鬼控制的世界,斯大林甚至试图征募杜姆科夫这位来自另一个星球、地球人视为天使的人物帮助,用其神奇力量帮助他建立类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所写的阴郁人物什加列夫所构想的新社会,这个方案第一步就是从肉体和精神上镇压导致人类不平等的异己分子;由此,斯大林被描写成一个十足的魔鬼,他自认为是比伊凡雷帝更为坚忍不拔的绝对统治者,是建造金字塔的埃及法老的后裔。叙述者认为这个计划要遭到后代人诅咒的,因而杜姆科夫选择离开地球,因为他明白自己不可能战胜当时控制着俄国的邪恶力量。这种把传说中的特异功能大师犹太人梅辛格,变成了对斯大林相信超能力的讽刺。这种把否定斯大林和末世论关联起来的叙述,显示出后苏联历史文学和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的本质性不同,即苏联时期否定斯大林多是基于和官方意识形态对抗,充满着火药味,很少从被禁止的基督教角度进入,因而哲学韵味不足,而后苏联多元化地叙述苏联历史和斯大林,经由基督教去看苏联体制和斯大林成为其中重要方式之一,有助于唤起东正教复兴中的读者的热忱。
尤其是后苏联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以新时代人的眼光重建斯大林和苏联形象。1990年代通过题为《论 17世纪恐怖年代的俄国》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弗拉基米尔·沙洛夫,其小说《此前与期间》提前使用了别列文《恰巴耶夫和普斯托塔》与马卡宁《地下人》后来才使用的手段——把俄国和苏联比喻为精神病院,叙述者阿廖沙作为精神病院的患者,在这儿人的经验被其记忆所操控,他就这样断言自己是真实历史的叙述者,叙述了法国作家、著名沙龙主人、最受 18—19世纪之交俄国作家尊敬的斯达尔夫人,曾和俄国乌托邦思想家尼古拉·费多洛夫生了一个名叫约瑟夫·斯大林的儿子,这个儿子后来做了许多令人恐怖的事情。由此,作品引发了文学如何表达历史的激烈争论,批评界严厉斥责其歪曲和嘲弄俄国历史,以及制造这类耸人听闻的乱伦主题。然而,作家自认为该作很少变动历史,变动的只是斯大林、费多托夫、作曲家斯科里亚宾等名字,但他们都是可能潜在地破坏科学和理性主义的乌托邦人士,无论每个人实际做了什么,皆曾打算参与或倡导乌托邦。的确,作品展示了当代人希望重新发现俄国的非理性、神秘哲学之类传统,描写马克思主义目的论史学观和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的理性、逻辑、原因、结果等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
而安纳托里·阿佐利斯基这位苏联海军,在苏联时代称不上是作家,后苏联以幻想性手法叙述历史人物的小说《柏林—莫斯科—柏林》而一举成名。作品叙述一位曾参与 1944年试图暗杀斯大林事件的人物,多年后匿名在新西兰向听众讲述当年的情形,特别描写了斯大林那令人恐怖的眼睛、不离身的烟斗、军人短上衣和靴子;他最为重要的长篇小说,即 1997年获得布克奖的《笼子》,主人公巴里诺夫作为数学家、生物学家,一生中一次次身陷囹圄、多次面对死亡,又一次次侥幸逃脱牢笼,用各种假名和假身份证逃生于林海或人海,过着悲惨生活,继续从事着深奥的遗传学、染色体的研究工作。叙述中传达出作家以主人公的经验去个性化地理解苏联历史,即斯大林秘密警察制度,使普通人宛如被禁锢在笼子里,并且写实性地描写了秘密警察行动的细节。与《笼子》相当,瓦列里·伊萨耶夫文献小说《斯大林的老战友》立足于克格勃新公布的新材料,叙述斯大林表面上相信的乌克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波斯迪舍夫,1938年被逮捕并死于狱中的历史,凸显斯大林的阴险、波斯迪舍夫的忠诚和正直,但叙述过程回避后者作为苏共乌克兰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清除异己和残酷对待农民的历史。至于后苏联最被争议的观念主义小说家索罗金,其《蔚蓝色的油脂》甚至写斯大林和希特勒 1954年还活着,他们曾经密切合作过,但希特勒却强奸了斯大林的女儿微拉;就是这样没有原则的斯大林,居然和赫鲁晓夫是同性恋伙伴。诸如此类的荒诞不羁描写,实际上满足了后苏联读者批评斯大林对二战的责任、罪行,同时暗示赫鲁晓夫和斯大林是同类。
可以说,否定性叙述斯大林,是历史文学潮流中最为壮观的现象,比起解冻思潮以来苏联时代多从政治上反对斯大林,要丰富复杂得多。
三
实际上,1990年代的作家变成了文学生产者,他们对斯大林的否定性叙述,不单是个人对苏联的记忆性表达,也是适应于当时全社会性地批判、否定、颠覆苏联之潮流。而苏联远不只是斯大林的苏联,因而负面叙述苏联,自然也就会延及到其他领域。
其中,涉及对列宁和苏维埃历史之关系的书写,同样是令人瞩目的文学景观。女作家托尔斯泰雅的《情节》叙述普希金决斗没有死,而是击中了一个叫瓦洛佳·乌里扬诺夫的青年人 (列宁的小名),这个人是激进的沙皇爱国主义者,1918年战胜德国后当上了内政部长,长期敌视普希金所讴歌的自由精神,甚至反对诗人所描写的国家和人民;乌里扬诺夫去世之后,德·朱加什维里 (斯大林)替代其位置,俄国历史的这种状况也没有完全改变,甚至更严厉地限制臣民的思想、言论和意志等自由。而以苏联尚健在就问世《追悼苏联文学》而名噪一时的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其小说《与傻瓜一道生活》着力描写长相如列宁般的沃瓦——一个内涵复杂的红头发的狂人 (沃瓦乃弗拉基米尔的小名)。该作英译者雷诺兹认为,沃瓦使俄国神圣傻瓜形象得到了讽刺性表达,颠覆了普希金《鲍里斯·戈东诺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等人物形象塑造的传统,沃瓦暗中破坏了传统俄国观念——神圣傻瓜被赋予了精神智慧并总是口说真理,在此变成了对知识分子炫耀俄国人智慧的嘲弄。尤其是,后苏联成长起来的作家别列文《奥蒙拉》也写到苏联人对列宁的崇拜,苏联人的正常生活,因为列宁的无所不在而被打乱,甚至无论列宁的话是多么陈腐或莫名其妙,总是被引用或作为根据,以至于造成有人假冒列宁之口说话的现象,如一个中尉引用假托列宁 1918年的话“在所有星球和天体中,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月球”,但这种冒用实际上讽刺性模拟列宁“在所有艺术中,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电影”;同样,有人说,“从那时 (1918年)以后许多年过去了,世界已发生了多方面变化,但列宁评估:时间已证实其正确的,列宁这些话的火光仍在照耀今天的日历。的确,月亮在人类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则是讽刺苏联人把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列宁形象发生的这种变异,类似于侨民艺术家亚历山大·科索拉波夫的“社会主义艺术”反宣传画《可口可乐——它真正的事情》——无所不在的苏共党旗,变成了商业化的可口可乐广告的底色,也随处可见。米哈伊尔·库拉耶夫《遇见列宁:来自档案的真实故事》,叙述者意外有了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手稿,这份手稿不能说出 1967年纪念列宁 1917年在彼得格勒的芬兰火车站会见几千工人失败的故事,老布尔什维克试图创造一个宏大的纪念列宁场面,却被许多因素破坏:这给理解苏共失败试验提供了隐喻,显示列宁不可能重回那个历史瞬间,俄国人不可能回到苏联历史,“现在许多人不再相信列宁,人开始相信基督并期待着其第二次降临”,叙述者明白复活历史是不可能的,哪怕他坦白存在着一块历史幕布,从而质疑何谓真实的历史。而且,正是在再造斯大林和列宁形象变化基础上,后苏联扩展了重新叙述苏维埃历史的范围,并用戏谑态度代之。其中,对十月革命后持续多年的内战,苏联官方史学称之为反对白军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临时政府军和孟什维克被描述为凶恶的敌人——红色作家富尔曼诺夫的历史文献小说《恰巴耶夫》和瓦西里耶夫兄弟执导的同名电影就是这样描写这场战争的。但是,在别列文《恰巴耶夫和普斯托塔》中,不仅内战,甚至关于内战的这种文学,变成了被讽刺性模拟的题材:恰巴耶夫不再是内战中成长起来的著名红军指挥员、富尔曼诺夫笔下的传奇式英雄,而是另类人物,如他战前动员令如此干涩,“小伙子们!你们聚集在这里干啥,你们知道。没什么好磨蹭的。你们会遇到各种情况,经受各种考验。不这样行吗?到了前线,要给那帮狗娘养的颜色瞧瞧。想什么呢——上前线可不是躺在摇篮里玩啊……前方没有后方不行,后方没有前方也不行……我们应该到前线去——这就是我向你们说的,别忘了,我这个指挥员会给你们撑腰的”。作为军事指挥员如此拙嘴,作为一个人却是诡辩论者:有一次拿起两个葱头,一个红皮剥光了只剩下白色葱肉,另一个紫红色的厚皮还留着,向“我”论述道,同一个葱头可以被脱去红皮显出白的肉体,但人不会这样从红的变成白的。
可以说,后苏联历史文学中对苏联的否定性描写,由再造斯大林形象开始,扩展到对列宁形象、苏联红色经典所塑造正面形象的颠覆性描写,而且这些描写远不限于苏联仅仅从反主流意识形态出发,而是多元复杂的。
总之,1980年代末以来的历史文学,对苏联和斯大林、列宁的批评、否定、反对、贬斥成为主流,正如久尔克夫斯基的《斯大林主义的文学伏魔:俄国作家和苏联过去》所总结的,后苏联文学是整个后苏联社会情绪化排斥苏联的感性表达,并且排斥主要集中于斯大林主义问题上来,虽然并未搞清楚斯大林主义乃俄罗斯帝国问题的表达。可是,这种持续十年之久的对苏联的否定性描写,无助于后苏联问题的解决,甚至会加剧后苏联重建的紧张,并意识到长期负面评价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联历史,实际上已经和批评本身的正面意义越来越远,以至于“1990年代以来,悔恨过去成为俄国的一种奖赏。十年来一致拒绝斯大林暴君是越来越不真诚了。否定的浪潮已经转向,并且有足够多的人为斯大林的共产主义终结而遗憾”。因为苏联问题不仅仅是俄罗斯帝国的苏联时期的问题,而是帝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俄国学习西方,目的不是要把自己变成现代欧洲文明的民族国家,而是经由学西方的途径而强盛俄罗斯帝国,使欧亚大陆许多被强制性地纳入俄国的其他族裔人口,经由帝国官方意识形态压力,承认各种假定的宏大话语,包括 1920年代末以来所设计出来苏联共产主义——对外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和资本主义等,对内牺牲非俄罗斯族裔的诉求。这种不以建立民族认同为基础的帝国行为,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1960—1980年代农村题材的兴起就是基于此,但终究因其对俄国民众伤害过于严重,成为其解体的最基本原因;并且,某种程度上还在俄联邦延续,普京对此批评道,“这个国家在一党垄断权力之下存续了 70多年。这几乎是整整一代人的时光,许多人看到他们自己的生存和列宁名字的关系。对他们而言,埋葬列宁就意味着他们曾为之献身的价值失败和那个目标的失败,他们曾经的生活是徒劳无益的”,并撤出了护卫列宁墓的守卫、恢复列宁墓附近的无名战士墓守护仪式。然而,苏联式的帝国意识始终植根于民众意识中,2005年普京助手波尔塔夫琴科重提迁移列宁墓问题,仍旧引起社会公众舆论反弹 (1990年代杜马选举俄共支持率为 20%~25%,到 2003年仍维持 12.6%),希望通过政治强势、历史手段去消除俄共影响力是很难的。由此,历史文学无法再持续否定苏联的潮流——否则,文化产业难以为继,这正是卢卡奇《历史小说》所说的,历史小说应“创造过去的生活”,应“使过去接近我们,并使我们能在它的真正现实中体验它”。1990年代末,十余年的改革带来了俄国西方化历程的挫败,市场经济的收效远非人们所期待的那样美好,民主政治的实施结果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由此,对苏联的批判被代之以对苏联时期俄罗斯帝国的缅怀,历史文学在对苏联的描写上面临着对苏联重新追述的转化问题,否则无法满足具有帝国意识的俄国社会苏联的怀旧情绪。当然,1990年代末以来的俄国历史文学感伤性怀旧苏联,是另一个需要专门论述的话题。
J4
A
1007-4937(2011)02-0081-04
2011-01-08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关于 90年代俄国文学发展与俄罗斯民族主义关系问题研究”(02BWW006)
林精华 (1965-),男,安徽黄山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苏俄后现代主义文学和后苏联文化转型问题研究。
〔责任编辑:王晓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