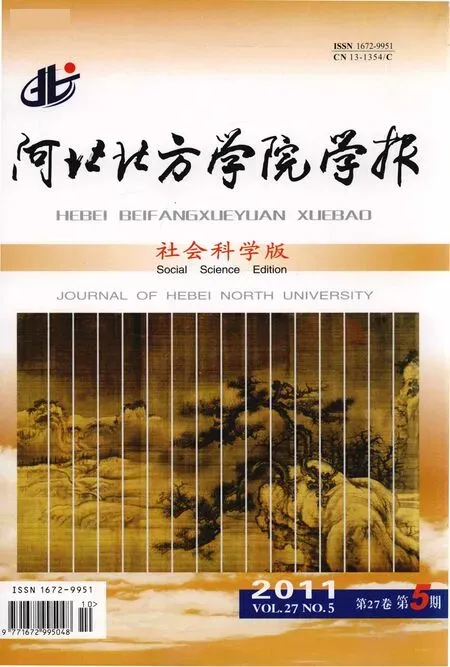浅析巴金家庭题材小说隐指作者的转变
李向东
(河北北方学院 文学院,河北 张家口075000)
对于巴金的系列家庭题材小说而言(这里用作分析的文本主要包括《激流三部曲》、《憩园》、《寒夜》5部作品),作家的创作意图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制度批判是贯穿这5部作品的最主要的创作意图①。但是,这些小说隐指作者的人格特征却发生了显著转变,《激流三部曲》中的隐指作者主要还是一个启蒙主义者(当然,《家》、《春》、《秋》创作于不同时期,隐指作者的人格特征是有不小差异的,但它们毕竟还是一个整体,有着更大的共通点),其核心观念是青年人要获得自由、幸福,就要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接受新思想、新思潮的洗礼。可是这种观念被此后的小说逐步颠覆了,其所呈现的隐指作者也逐渐转变为感伤主义者。
这里谈到的隐指作者是从叙述学引入的一个概念。隐指作者是从文本叙述中归纳、推定出来的一个人格,是文本体现出的道德、习俗、心理、审美的价值与观念的集合体,是真实作者的“第二自我”[1](P10)。一方面,隐指作者肯定会受到作家本人情感意志的影响,另一方面,隐指作者又会与作家本人保持疏离,或者可以说隐指作者是进入高度投入创作状态的作家表现,这与真实的、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作者是有分别的,同一作家的多部作品可以呈现不同的隐指作者。鉴于巴金主观创作意图与文本实际思想内蕴间的显著差异,笔者认为,借助隐指作者这个概念可以更好地阐释文本间思想内蕴的转变。
隐指作者的感伤首先源自对“家”与“家中人”的失望。
这种失望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脱去了封建礼教束缚的现代家庭并未获得真正的和谐、幸福。
在《激流三部曲》中,挣脱以大家族为代表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对于青年人重获新生是至关重要的。1931年完成的《家》矛头直指封建礼教的罪恶,到了1940年完成的《秋》,这个大家族终于分崩离析,公馆被出卖,各房平分家产开始独立生活,小说彻底否定了封建家族制度,对此,隐指作者是深感欣慰的。从《秋》的《尾声》大哥觉新写给离家出走的觉慧和淑英的信中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这一点:首先,觉新一房的生存状态有了改善——“我们搬出老宅以后,生活倒比从前愉快,起居饮食,都有改革……一家人过得和和睦睦,简直听不到一点吵闹。”其次,以前在大家族中一些很难得到解决的事有了圆满的结局——“三妹自进学校后,非常用功,考试成绩也很好……现在开了课,她每日都是高高兴兴地夹着书包来去。”觉民和琴“他们已于前月订婚,仪式非常简单,这种订婚在我们高家算是一件破天荒的事”。而且,大哥觉新的生活也有了新的生机——“我搬出老家以后,我倒有得安静日子过了”,“说起翠环……我上个月已遵照三叔遗命将她收房了,我很喜欢她,她对我也很好,我不会错待她的”[2](P654)。似乎脱离了封建礼教束缚的小家庭肯定会使人的生存境遇获得极大的改观。
1944年完成的小说《憩园》也是以两个家庭作为表现对象的。小说批判了“长宜子孙”的封建思想,以及养尊处优的封建家族制度对人性的侵蚀,这是《激流三部曲》制度批判观念的延续。但是,这部小说的关注点已主要不是制度问题和伦理道德问题,它开始更多关注具有普遍性的人性问题。
小说中杨梦痴的家庭,同样是一个从溃败的封建大家族分离出去的小家。在这个小家庭里,封建礼教几乎荡然无存,儿子甚至还可以对父亲的行为不端严加指斥。可即使如此,这个家庭还是没能拥有《秋》中觉新一房的平静与温馨,它依然充满了不宁与苦痛。导致这种后果的根本原因是杨梦痴执迷不悟的婚外恋情——一种源自人性深处的情欲诱惑。
《憩园》中“憩园”的新主人姚家,表面看来是一个和谐、温馨的三口之家,但脉脉温情掩盖着的却是一个受伤的灵魂。继室万韶华虽然温柔、善良,但这些美好的品质既无法化解她和丈夫姚国栋间严重的心灵隔膜,也无法抵御姚国栋前妻之子小虎对她的冷漠、敌意以及前妻家人对她的侮辱、蔑视。
完成于1946年的小说《寒夜》中汪文宣的家庭已经完全是一个现代家庭,那里没有了封建礼教的羁绊,汪文宣和妻子曾树生通过自由恋爱结合,且一直是未婚同居的关系——他们连组成一个家庭的合法形式都舍弃了。在《春》里,面对大家庭夫妻的不睦,琴曾说过:“这有什么稀奇?不自由的婚姻都是如此。”[3](P164)可是在这个自由结合的小家庭中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极其痛苦压抑的,小说中的一切都令人窒息。
“《寒夜》写出了人与人无法沟通的悲剧……它植根在文化中,植根在人的存在中”[5](P301)这段话准确揭示了《寒夜》家庭悲剧产生的本体性根源。母亲对儿子汪文宣深沉而自私的爱,对儿媳曾树生的妒忌和刻薄;儿子面对无休止的争吵而穷于应付的精神煎熬;儿媳在爱与恨、走与留之间的挣扎与徘徊。小说对这些特定伦理关系制约下的人性弱点给予了集中呈现,也体现了隐指作者的观念——即使没有封建礼教的束缚,人存在本身的局限性依然会使“家”陷入到痛苦的泥淖。
其二,即使接受了现代教育,也并不一定就会改善“家中人”的精神境况和生存处境。在《激流三部曲》中,小说提示了青年接受新思想、新思潮的路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接受现代教育的洗礼。
小说《家》在第三章就写出了青年人对现代教育的向往:觉民的表妹琴虽然很早就上过学,但她依然无法忍受学校里传统观念的束缚,当琴听说另外一所较为开明的学校要招生时,感到异常兴奋,“我恨不得你们底学校马上就开放,我好进去”[5](P21)。
在《春》里,当淑贞对琴诉说她的母亲不让她再去书房读书的苦闷时,
琴不等她说完就接口说道:“那也不要紧。横竖在书房里跟着那个冬烘先生读书也得不到什么有益的知识。你高兴读书你二哥、二姐和我,我们都可以教你。这比在书房里读《女四书》,《烈女传》之类强得多了。”
“那是再好没有的了,”淑贞到这时才破涕而笑,她欣喜地说。[3](P60)
在《秋》中,当继母支持了女儿淑华到琴就读过的学校念书的请求时,淑华“差不多欢喜得跳起来”[2](P548)。
在这些青年人眼中,接受现代教育是一件多么神圣的事情,仿佛这真的能够使人脱胎换骨,重获新生。
然而对于《憩园》中“憩园”的新主人姚国栋而言,虽然“大学毕业又留过洋”,“做了三年教授,两年官”,可他最后还是“回到家里靠他父亲遗下的一千亩的田过安闲日子”[6](P4)。不仅接受了完整的现代教育,还曾添为人师的姚国栋依然回到了传统文化为知识分子设置的老路上来。
姚国栋的儿子小虎虽然从小就有着优越的接受新式教育的条件,可是他却不爱去学校读书,时常旷课到外婆家赌钱,小小年纪就表现出跋扈和势利。这是脱离了传统影响的一代,但所谓的“新文化”也只是教会了他如何享乐,这又是在精神上垮掉的一代。
接受现代教育的启蒙主张,在《寒夜》中更是无情地破碎了。汪文宣夫妇都是教育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汪母还曾是云南昆明的才女。可是,当他们面临生活的煎迫时,受教育的经历不仅没能改善他们卑微的社会地位、困窘的物质生活,反而因不善钻营,成为导致其贫困的重要原因。小说中母亲曾痛苦地对汪文宣说:“我只后悔当初不该读书,更不该让你也读书。我害了你一辈子,也害了我自己。老实说,我连做老妈子的资格也没有!”[7](P375)
其实,这种趋势在《家》中就已经显现了:由于城内败兵流窜,高家的女眷可能面临遭受凌辱的危险。对此,琴深深感到了自己的软弱无能,“这时候什么新的思潮,新的书报,什么易卜生,什么谢野晶子,对于她都不存在了”。面对比自己大得多的异己力量,生命本身的脆弱就裸露了出来,“她疲倦了,她绝望了,她这时候才开始觉得她和梅,瑞珏这些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她实际上是和他们一样无力的”。[5](P216)
曾几何时,《激流三部曲》中那些冲破封建牢笼,争取新生的青年人是何等兴奋、激昂。《家》中的觉慧最终脱离封建大家庭的束缚去了上海,在出走前,觉慧的朋友就对他说:“你到下面去,在学识与见闻两方面,都会有大的进步……在上海新文化运动比较这里更热烈得多。”[5](P614)
《春》中的淑英也离开高家,投奔了在上海的觉慧。她在给琴的信中以轻松的笔调记述了与觉慧在一起的愉快心情:“姐姐,我真高兴,我想告诉你:春天是我们的。”[3](P510)这完全是一个找到了精神皈依的人的精神状态,似乎一旦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就会彻底告别阴晦的生活。
可是《憩园》、《寒夜》中的那些挣扎于新的苦痛中的小人物难道不就是《激流》中青年人后来的人生写照吗?毕竟,我们在三部曲之后的小说中没能看到这些走到广阔天地中的青年人更为辉煌的身影(其实,也不大可能再见到他们的更大作为。在三部曲中,与作家对大家族坚实、细致的描写和对封建制度充满气势的批判相比,小说里青年人的所谓革命运动始终被写得虚浮、空泛,他们“有的只是一点勇气,一点义愤,一点含糊的概念”,“只知道应该做,却还不知道怎样做”[3](P246),在自己至为熟悉的环境中描述青年人具有启蒙意味的活动尚且如此,如何能将笔触延伸到远离家庭的他们的生活中间呢),取而代之的是那些重又回到家中,面临着种种难以克服的精神与现实困境的小人物和他们更为卑琐、苦痛的生活。
隐指作者感伤情绪的形成还有赖于失望过后的宽容。
极度的失望很可能导致义愤,义愤的后果往往是讽刺的锋芒毕露。后期家庭题材小说中的隐指作者对“家”与“家中人”是十分失望的——尤其是对人性缺陷的失望(到了《寒夜》或许应该叫做绝望)。但是,面对这些,小说还是呈现了他们生命中些许的亮色,表现出隐指作者极大的宽容。这种宽容避开了讥刺所可能带来的单薄,增加了小说情感的厚度和诗的韵味,使感伤的情绪更加深沉。
《憩园》中不同身份人物对杨梦痴的介绍、评价构成了价值判断各异的“复调”。从这些不同的声音可以看到,隐指作者对杨梦痴身上体现出的人性弱点的态度是复杂的。放弃家庭责任,一味追求情欲的满足当然是不可取的,但同时隐指作者对杨梦痴又给予了巨大的同情。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小说的叙述者没有从道德层面对他的出轨过多指责,相反,还从人性的角度特意凸显了体现人物真挚情感的细节。当杨梦痴深爱的四川女子不辞而别,他“就像害过一场大病一样,背驼得多,脸黄得多,眼睛落进去,一嘴短胡子。走路没有气力,说话唉声叹气”[6](P77),只在家里呆了几天就又背着家人出去寻找那个四川女子。当杨梦痴一无所获回到家时,天正下大雨,“他一身都泡胀了……人比从前更瘦,一件绸衫又脏又烂,身上一股怪味”[6](P81)。后来那个离开杨梦痴的女子托人给他送来了一大笔钱,表达自己的无奈、愧疚与思念。可见她当初和杨梦痴在一起并非为骗取钱财,同样是出于真心。
面对出轨的父亲,杨梦痴的小儿子寒儿不仅处处关心已被赶出家门、潦倒落魄的他,还对父亲的婚外情感持宽容、理解的态度。他对那个四川女子做了这样的评价:“我觉得她还是个好女人,她现在还没有把爹忘记……倘使她知道爹在哪儿,那是多么好,她一定不会让爹流落在外头的。”[6](P85)
姚国栋的浅薄粗疏、刚愎自用使他无法真正体贴继室万韶华的心灵,但小说同时也为人们呈现了他性格中不失可爱的一面:大度、率真、善良;他的继室万韶华虽然忍受着的心灵的苦痛,但是小说一再描写她可以照亮人心灵,让人感到温暖的眼睛。
《寒夜》中,婆媳关系是尖锐对立的,小说除了表现这不可克服的人性弱点,还用了大量篇幅描写夫与妻、母与子单独在一起的场景。在这些场景中,婆媳间的矛盾暂时隐退,文本凸显的是母子、夫妻间的深挚情感。
从这两部小说的可靠叙述者(可靠叙述者就是文本中与隐指作者价值立场较为一致的叙述者)对故事的剪裁、遴选、评价和小说人物的次级叙述,我们可以推定隐指作者虽依然葆有思想启蒙的观念,但对人性、人生已经有了更为自觉、深入的体察并由此生发出浓浓的感伤——既然生活中的很多裂痕我们无法弥合,人性当中的一些缺陷我们无法改善,那就不如用一颗善良的心去包容,当然这种包容是满含着的苦涩与无奈的。
在《激流三部曲》中,不论是反抗封建礼教还是接受现代新思想、新思潮的洗礼,都主要是抽象的理论主张。《秋》结尾处所体现出的启蒙主义的胜利很大程度上仅是一种思想原则的胜利,这是建立在一种相对盲目的人生信念基础上的——小说中的青年自信比大多数人更有思想,更有学识,更有力量。因此,人们总能感受到隐指作者那不懈的激情。但是,必须看到在《激流三部曲》中启蒙思想原则出现的大的文化语境,即在家庭外部整个社会还是被封建势力占据着的,还同以往的社会现实没有任何根本差别;在家庭之内,处于特定伦理情境中的人性困境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就连第一个挣脱“家”的牢笼的觉慧也曾无奈地感到自身的软弱和渺小:
我也许是太自私了,也许是被别的东西迷了眼睛,我自己不愿牺牲,却把她(指鸣凤)牺牲了。
我,卑怯的我。我没有胆量……我从前责备大哥和你(指觉民)没有胆量,现在我才知道我和你们一样,我们是一个父母生的,在一个家庭里长大的,我们都没有胆量……我恨一切的人,我也恨我自
己
充其量,《激流三部曲》中的那些青年人只是在碎裂、涌荡的现实的缝隙中暂时找到了一个看似美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一旦历史的机缘不再眷顾他们,这个新的空间立刻会被汪洋大海般来自各个方面的习惯势力扭曲,吞噬。正如周作人所言:“中国虽然也曾努力想学好,可是新的影响质与量都微少,混到旧东西里面便有如杯水车薪,看不出来了……”[8](P178)因此,我们看到,随着巴金创作的延续,在《憩园》、《寒夜》中新的人生观念不但没能给那些人物带来更大幸福,反而使他们陷入到现实与人性的沼泽,最后毁灭了他们的人生。这直接导致了隐指作者感伤情绪的出现。
隐指作者的宽容来自作家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巴金不止一次说过:“我爱一切的生物,我讨好所有的人。我愿意揩干每张脸上的眼泪,我希望看见幸福的微笑挂在每个人的嘴边。”[9](P515)贯注于文本间博大的爱包容了小说呈现的诸多不幸与苦痛,也丰富和强化了感伤的内蕴。
巴金曾说过:“我可以说是有着两个‘自己’”,一个自己是“革命者巴金”,另一个自己“却鼓舞我在文字上消磨生命。我服从了它,我写下一本、一本的小说”[10](P204)。上述小说的隐指作者体现了那个将生命消磨在创作中的巴金。他有着诗人般的忧郁、敏感、犹疑和悲悯,越到其创作后期,越表现出对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的失望乃至绝望。
但是,不要忘记“革命者巴金”。这是一个有信仰的巴金——“旧的要灭亡,新的要壮大;旧社会要完蛋,新社会要到来;光明要把黑暗驱逐干净。这就是我的坚强的信仰”[9](P520)。他目标明确、态度决绝、立场坚定,文学创作不过是其干预现实人生的一种无奈却必需采取的方式,破旧立新当然是其文学创作的自觉要求。当新的时代来临,革命者的巴金又唱起了时代的颂歌。他在1950年上海首届“文代会”上真诚地说:“会,是我的,我们的家,一个甜蜜的家。”然而,正如黄子平先生质疑的,在这样新的笼罩着更大空间的“家”中,还会不会有迫害、倾扎、阴谋、牺牲和梦魇呢?[11](P439)巴金的“文革”经历为人们做出了回答。于是有了后来的《随想录》,虽然是散文作品,虽然还在重申着制度批判的主张,但是人们分明又感受到了《憩园》、《寒夜》中隐指作者的无奈与感伤。
作家在20世纪30年代就说过:“我的生活里是充满了矛盾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爱与憎的冲突,这些织成了一个网,把我盖在里面。”“我时时都想从那里爬出来。然而我始终不能够冲破矛盾的网,那张网把我缚得太紧了。”[12](P91)被这两个矛盾纠结着的巴金或许是先生一生的痛吧?
注 释:
① “我一直把我的笔当做攻击旧制度、旧社会的武器来使用。倘使不是为了向不合理的制度进攻,我绝不会写小说……倘使我对剥削人、压迫人的制度并不深恶痛恨,对真诚纯洁的男女青年并无热爱,那么我绝不会写《家》、《春》、《秋》那样的书。”(《谈〈春〉》)“财富并不能‘长宜子孙’……‘家’这个小圈子只能摧毁年轻心灵的发育成长。”(《谈〈憩园〉》)“我要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受苦来谴责旧社会、旧制度。”(《谈〈寒夜〉》)当然,巴金在不同时期对这些小说创作意图的阐释文字在表达方式(“描述性”文字还是“理论性”文字)以及与文本间的契合程度等方面还是不尽相同的,这里选择的是我认为较有代表性的文字。注①中的引文均见:李小林 李国煣.巴金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1] 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 巴金.秋[A].巴金全集(第3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3] 巴金.春[A].巴金全集(第2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4] 王富仁.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A].王富仁自选集[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5] 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七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6] 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第七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7] 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第九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8] 周作人.《过去的工作》跋[A].钟叔河.知堂序跋[C].长沙:岳麓书社,1987.
[9] 巴金.我的幼年[A].李济生,李小林.巴金六十年文选[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10] 陈思和.巴金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11] 黄子平.命运三重奏:《家》与“家”与“家中人”[A].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C].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
[12] 巴金.《爱情三部曲》总序[A].李小林 李国煣.巴金论创作[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