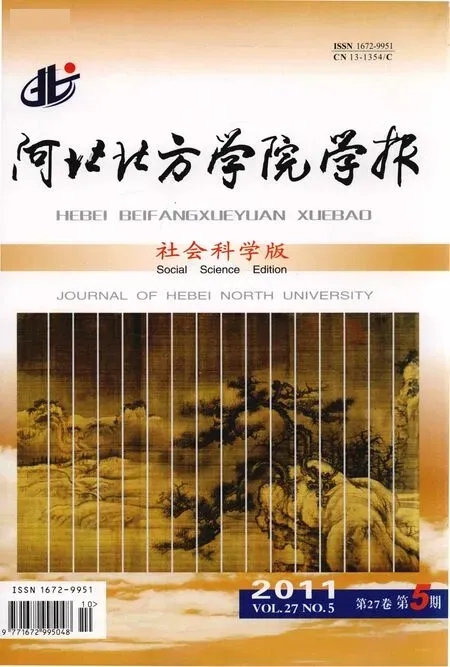论曹植文学创作风格中的二元对立
邢培顺
(滨州学院 中文系,山东 滨州356603)
曹植是邺下作家中的晚辈,他身为公子王侯,又主要生活于社会环境已相对安定的建安时代后期,总体而言,生活是比较安逸的,但他的文学创作在基本风格上能与曹操及“七子”等人保持一致,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人们深入探讨。粗看起来,曹植的生活比较单调,生命后期又受到人为的拘限,生活的接触面比较狭窄,但由于他生活于社会思想观念大转变的时代,加上他文学家的天赋以及特殊的生活遭际,他的人格结构具有明显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而且这些构成他人格特征的因素,彼此之间往往形成对立和冲突,而这正是他之所以成为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大家的根本原因。正如荣格所说:“事实上所有的人格理论家,不管他抱有什么样的信念,坚持什么样的主张,都认为人格同时容纳着可以导致相互冲突的两极倾向。”[1](P66)作为能代表一个时代的伟大作家的曹植,自然更是如此。曹植经历了社会政治的动荡变幻,思想观念的分合变迁,以及人生的得失悲欢,在遍历了层层的生命境界之后,他把种种的外部冲突转化为心灵世界的内在激情,并把这种激情外化为艺术。因此,曹植文学创作的艺术特征体现出极为鲜明的深刻性和多面性,从而以有别于曹操及“建安七子”的独特形式呈现了建安风骨。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中和与慷慨
在《赠丁仪王粲》中,曹植针对王粲和丁仪的情感表现,规劝他们说:“欢怨非贞则,中和诚可经。”而在《前录自序》中,他又说自己“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中和”与“慷慨”这两种看似冲突的美学原则共存于曹植的审美观念和文学创作中,正是曹植思想观念中既守持儒家传统精神又放纵个体情感的精神状态在文学创作中的反映,而这两种美学思想又各有所承。“中和”的美学原则主要继承了儒家的传统美学思想。儒家诗教反对情感表达的直露与偏激,讲求“温柔敦厚”,“主文而谲谏”,“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曹植在他的诗歌创作中的确遵循了这一创作原则和美学风格。如他两次被曹丕及其爪牙诬陷打击后所作的《责躬诗》,一味地自怨自责,痛哭流涕,却没有流露出些许的怨恨皇兄的意思。再如著名的《赠白马王彪》,面对手足相残相抑的人间悲剧,他怨天地,怨小人,却始终不愿把怨愤的矛头指向幕后的元凶,自己的兄长,当今的皇帝。在他生命的后期,备受拘禁和压抑,他把这难以名状的悲苦通过咏史、游仙以及用美女等比兴寄托的方式表达出来,使他的诗歌创作真正达到了情感真挚深沉、表达蕴藉华美的美学境界。“慷慨”的美学原则主要继承了楚辞与汉赋的美学风格。本来,自东汉中叶产生的抒情小赋,就是楚辞与汉代散体赋相结合的结果,这种赋既继承了楚辞“发愤抒情”的特点,又继承了汉代散体赋铺陈扬厉的手法,到汉末建安时期,这种抒情小赋成为辞赋的主流,成为文人们喜爱的咏物、抒情的工具。曹植的文学创作便是从辞赋开始的,而且他的赋大都是体制短小、情感浓郁的骚体赋。他的辞赋创作,虽然前后在内容和格调上有所变化,但在表达上蹈扬发露却是一致的。如创作于前期的《感婚赋》、《愍志赋》、《静思赋》等,表达对真挚爱情的追求以及求而不得的痛苦,炽热大胆,明白发露;而后期创作的《九愁赋》、《秋思赋》等,表达人生的失意和生命的不自由,沉郁苍凉,悲情慷慨。前后表现虽有所差异,但都具有激扬慷慨的特点。
二、载道与抒情
曹植十分重视文艺对国家政治和百姓教化的作用,在《画赞序》中,他表达了这方面的文艺思想。他说:“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节死难,莫不抗首;见忠臣孝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 者 何 如 也。”[2](P67-68)这 是 对 儒 家 传 统 文 艺观念的继承。在文学创作中,他也自觉地贯彻了这一文艺主张。如《七启》便热烈赞扬了其父曹操的政治功业和用人政策,赵幼文在《曹植集校注》中评此文说:“曹操消灭袁绍,统治冀州,复取荆州。为了进一步发展统一事业,必需争取士族与之合作。针对这一客观现实,便在建安十五年宣布《求贤令》,提出‘唯才是举’的征用原则,借以网罗散居在野的士族,充实曹魏政权的统治力量。曹植以统治集团成员立场,热烈歌颂求贤措施的必要性,而且极力阐述国家对此的决心。并借献帝刘协的号召,期求鼓舞在野士族参加政治之积极情绪,从而创建国富民康的理想社会。通过玄微、镜机问答,更深刻指出不愿为当前政治服务的思想是错误的,这就配合曹操政治意图做了有力的宣传,显示文学与政治具着密切的联系性。”[2](P28)此说可从。东汉王朝在黄巾农民大起义的沉重打击下衰微,曹操乘机建立起自己的霸业,因此他对道教势力心存戒心,采用笼络的政策,将各地的道教领袖召集到邺下,以免他们宣传鼓动,形成自己的实力。为此,曹植创作了《辨道论》,一方面揭露道教方士的虚假,一方面为曹操召集方士的行为辩护,因此,本文也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性。再如《魏德论》、《鼙舞歌》等诗文,证明曹氏代汉的合理性,为曹魏政权唱赞歌,也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创作的。此外,像《丹霞蔽日行》、《辅臣论》、《陈审举表》、《谏取诸国士息表》、《谏伐辽东表》等,也是为议论朝政、批评朝政、为朝廷提出施政建议而创作的。一方面是承自传统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一方面是他本人的强烈的政治热情和功名事业心,使得曹植以文艺的形式,表达自己对社会政治的关心以及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政治情感。
汉末建安时期,随着人的觉醒和文学的自觉,文艺已经成为人们抒写自我情感的工具,抒情性的增强是建安文学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在这一点上,曹植无论在思想观念还是创作实践上,都有明确的意识,他创作辞赋,“雅好慷慨”;在《卞太后诔表》中他说:“铭以述徳,诔尚及哀。”[2](P417)正因为如此,他的诗歌、辞赋情感强烈浓郁自不必说,就是章、表、颂、赞、诔、铭这些实用性和规范性很强的文体,通过他的改造,也成为抒情意味很强的文学作品。很多实用文体,就是经过了曹植的改造,才彻底改变了原先枯燥、呆板的面貌,成为颇具形象性和情感性的文学作品,影响了整个魏晋南北朝乃至此后的整个古代文学创作。这些在曹植笔下获得新生的文体,往往被刘勰批评为“讹体”。如诔这种文体,在曹植以前,主要是用描述性和评价性语言,用较短的篇幅颂扬诔主的美好德行,曹植将其进行改造,运用叙述性和描写性的语言,再现诔主生前的行迹,借以表达作者的哀痛之情,不仅文章篇幅加长,形象性和抒情性也大为增强,使诔这种礼仪性和程式性很强的文体成为作者充分表达情感的文体形式之一。曹植对诔的这种改造,受到了刘勰的批评,他在《文心雕龙·诔碑》中说:“陈思叨名,而体实繁缓,文皇诔末,百言自陈,其乖甚矣。”[3](P155)曹植的《文帝诔》有一千二百余字,叙事委曲,辞采华美,充分表达了他对胞兄的复杂而深沉的感情,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刘勰对他的批评,正可以反映出曹植对文章的改造之功。
三、端实与空灵
一方面,曹植继承了《诗经》、汉乐府所代表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用文艺的形式,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人们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变迁和思想演变,内容端实厚重,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很强的感人力量,如他的《送应氏》、《泰山粱甫行》。其《泰山梁甫行》说:
八方各异气,干里殊风雨。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4](P426)
叙写了边地百姓历经战乱后的极度穷苦生活,形象鲜明,情景真切,情感深沉,催人泪下,表现了曹植对广大不幸百姓的关心和同情,成为他现实主义创作的名篇。
另一方面,他又继承了《庄子》、《楚辞》所代表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用比兴寄托、虚拟想象的手法,表达他对社会现实的感受和隐微的内心情感。如他的著名的《洛神赋》,用华美的语言,浪漫主义的手法,营造了一个亦真亦幻、迷离恍惚的艺术境界,用以表达他复杂隐微的情感。又如他生命后期创作的咏史诗、游仙诗、大部分的女性题材作品,就都是这种创作方法的体现。这部分作品,内容和风格空灵飞动,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如《杂诗·南国有佳人》:
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北海岸,夕宿潇湘沚。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俛仰岁将暮,荣曜难久恃。[4](P457)
很明显这是虚设的形象,用以寄寓自己才志不为统治者所知赏、希冀能为世所用的心情。刘履解此诗说:“此亦自言才美足以有用,今但游息闲散之地,不见顾重于当世,将恐时移岁改,功业未建,遂湮没而无闻焉。故借佳人为喻以自伤也。”[5](P121)此说大体不错。
一般而言,曹植前期的创作偏重于写实,后期的创作多用虚拟和比兴寄托,这既与建安文学总体的发展变化趋势一致,也有曹植自己的特殊情况。曹植后期的创作,之所以写得空灵变幻、微婉含蓄,除了免触忌讳的考虑以外,还与他随着阅历的加深,思想情感更加深沉,艺术表现手法越来越成熟高超有关。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担负起集建安文学之大成、开魏晋文学之新局面的历史任务。
四、雅正与俗化
曹植的文学创作,在内容上讲求雅正,在形式上讲求工练华美,特别是对表达技巧和语言形式的讲求,甚至达到有些苛刻的地步,他曾说自己“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他总是能够根据内容的特点和表达的需要,选择恰当的表现形式,做到“应物制巧,随变生趣”。胡应麟称赞说:“子建《名都》、《白马》、《美女》诸篇,辞极赡丽,然句颇尚工,语多致饰。视东西京乐府,天然古质,殊自不同。”[6](P27-28)如他写于早期的《公燕诗》:
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阪,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跃高枝。神飚接丹毂,轻辇随风移。飘飖放志意,千秋长若斯。[4](P449-450)
这种以叙事开头,中间用整饬的对句写景,最后用抒情或议论作结的诗歌结构模式,在篇章结构上被认为是徒诗的先导。这种结构严谨、情景事理俱备、艺术技巧高超的诗歌,在古诗中尚未发现,它由王粲首创,而在曹植作品中有较多表现。而诗中炼字炼句的功夫,更是受到后人的赞叹,王世贞说:“‘东风摇百草’,‘摇’字稍露峥嵘,便是句法为人所窥。‘朱华冒绿池’‘冒’字更捩眼耳。”[7](P978)曹植的这种练字技巧,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范晞文说:“子建诗‘朱华冒绿池。’古人虽不于字面上著工,然‘冒’字殆妙。陆士衡云:‘飞阁缨虹带,层台冒云冠。’潘安仁云:‘川气冒山岭,惊湍激岩阿。’颜延年云:‘松风遵路急,山烟冒垅生。’江文通云:‘凉叶照沙屿,秋华冒水浔。’谢灵运云:‘蘋藻泛沉深,菰蒲冒清浅。’皆祖子健。”[7](P411)曹植在文章的章法、句法、用词、用字及音韵上的追求及其卓越成就,受到后人的高度赞扬,以至于有人责备他开了两晋南北朝形式主义的先河。
曹植又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将文学生活化、世俗化的人,他认识到文学不仅有教化百姓、翼赞政治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摹写生命、彰显生命、完善生命,进而延续生命,因此,文学的本质就是生命的清澈和生命意识的张扬。在曹植的笔下,大到天地宇宙、军国机务,小到童儿夭逝、鸟雀伤亡,都一样写得充满深情,都是他生命意识的显现。在文学形式上,曹植也是雅俗并赏,在《与杨德祖书》中他说:“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2](P154)曹植十分尊重和喜爱民间文学,并从民间文学中吸取创作养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都知道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创作五言诗的人,而五言诗在魏晋南北朝是公认的流俗之体,如挚虞说:“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8](P820)刘勰也说:“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3](P65)在魏晋南北朝,人们用四言诗表达严肃庄重的内容,而用五言诗表达个人隐微缠绵的情感。曹植改造、发展了五言诗这种刚刚出于民间的文学形式,并将其发展到“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高度,他也成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诗圣”。
总之,从曹植开始,文学才真正从政治和学术中解放出来,成为它自身,获取了自己的本质和功能。它不再是传统意义的高雅品,而成为人们世俗生活的展现和一个个独具个性的生命的呈示,正因为如此,曹植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美文的创造者。
五、壮阔与柔婉
曹植是卞太后的少子,又天性聪颖孝友,深得父母的喜爱和娇宠,所以他性格中有娇柔软弱、缺乏自立精神的一面,这从他的日常行为和文学创作中也可以明显看出来。同时,他又“生乎乱,长乎军”,看惯了征战厮杀。此外,他也沾染了当时贵介公子大都具有的任侠放荡的习气,所以他性格中又有尚武任气的一面,这从他的《鹖赋》、《名都篇》、《白马篇》等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再从他的思想观念和人生志向上来说,他想安济苍生,立功当时,扬名后世;却又深爱文学,不护细行,放纵自己的行为和情感。他的济世大志既不为客观环境所允许,他的主观条件也不具备实现政治抱负的起码前提,这样,在曹植的心灵深处,存在着产生于自身而难以解决的人生冲突,这种矛盾冲突表现于文学之中时,便必然表现出雄壮和哀婉两种文学风格。当他用文学的形式表达他的人生志趣时,所表现的是他人格中积极主动的一面,那么此时的文学风格往往是奋发昂扬、壮阔雄奇的;而当他抒写人生失意的情感时,他便发现在他面前有一股阻碍自己作为甚至控制自己命运的强大力量。他不满,又不敢反抗;想超越,又没有力量,于是他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了被动的臣妾的位置。曹植的文学创作,这种心态特点和风格特征的表现相当明显。
一方面,他的文学创作有沉雄壮放的风格特征,他用雄奇的形象,壮阔的意境,表达他“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的雄心和壮气,以及“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的英雄气概。如他的《盘石篇》:
盘盘山巅石,飘飖涧底蓬。我本泰山人,何为客淮东?蒹葭弥斥土,林木无芬重。岸岩若崩缺,湖水何汹汹!蚌蛤被滨涯,光采如锦虹。高波陵云霄,浮气象螭龙。鲸脊若丘陵,须若山上松。呼吸吞船欐,澎濞戏中鸿。方舟寻高价,珍宝丽以通。一举必千里,乘飔举帆幢。经危履险阻,未知命所钟。常恐沉黄垆,下与鼋鳖同。南极苍梧野,游盼穷九江。中夜指参辰,欲师当定从。仰天长叹息,思想怀故邦。乘桴何所志,吁嗟我孔公。[2](P260-261)
此是曹植徙封雍丘时所作,他营造了一个辽阔然而凶险的意境,表现自己蹈危履险,一举千里,却又无所定止的生活处境。意象丰富壮丽,意境雄奇开阔,风格雄放扬厉。他写桂树之大,充满宇宙,“日出登东干,既夕没西枝”。他的《鰕鳣篇》,通过营造开阔的意境和雄壮的气势,表现自己非凡的志向和豪气。他的许多游仙诗,境界阔大,意象神奇,表现了他开阔的胸襟和远大的目光。他的《五游咏》,以九州为狭,表示要“逍遥八纮外,游目历遐荒”。其《远游篇》通过壮阔意境的营造,表达自己蔑弃世俗富贵、超越时空、齐年天地的伟大气概。
另一方面,曹植的文学创作又有柔婉的文学特征,他用纤小柔弱的意象,凄婉的意境,表达弱者的不幸遭遇和对强大而恶劣的外在现实的无可奈何。从前期的写实性作品如《感婚赋》、《愍志赋》、《静思赋》、《出妇赋》等表现爱情的不得意和婚姻的不幸,以及《蝉赋》、《龟赋》、《离缴雁赋》等表现弱小生命横遭不幸,到后期虚拟性的作品如《七哀》、《种葛篇》、《美女篇》等,用貌美才高、柔弱多情的悲悲戚戚的女子形象,象征自己的人生不幸、美好事物被漠视和遗弃,都显示了曹植的这种创作风格。
曹植是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文学创作风格自可作为建安文学风格的代表,可是,曹操、七子及蔡琰等人历经战乱,备受动荡流离之苦,他们的文学创作具有慷慨悲凉之风格特点,自是容易理解,曹植作为邺下作家的晚辈,身为公子王侯,生活在相对安逸的环境中,其悲凉之气自何而来?有人把其中的原因归结为他生命后期备受迫害和压抑,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曹植除黄初初年两次受到曹丕的爪牙的诬陷而差点被杀外,其余时间的生活还是相对安逸的,这些迫害还不足以让他成为能代表一个时代并影响深远的大作家。所以,不仅仅是生活的不幸,更重要的是文化的转型及由此而引起的文人心态的转变磨砺并成就了曹植。处在文化转型时期的曹植,内心深处充满各种观念的矛盾和冲突,而最基本的冲突便是守持传统与放纵个性的冲突,正是这些矛盾和冲突激发出来的艺术之花成就了曹植。有人说曹植的人格是儒道互补的人格,恐未必然,因为从根本上说,曹植的思想观念并未通透,人格结构并未圆融,他的观念结构正是汉魏之交文化转型时期各种思想观念杂糅状态的投影。不过,在相当程度上我们仍然可以说,曹植确立了后世文人的人格模式和创作模式,这就是在思想观念上存在着守持传统与张扬个性的冲突,具体表现为践履士人责任与放纵个体情欲的冲突,由此而在创作内容上体现为言志与抒情的对立,在创作风格上表现为壮美与优美并存的状态。
[1] 霍尔,诺德贝.荣格心理学入门[M].冯川,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2]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 黄叔琳,李详,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4]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 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三曹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 胡应麟.诗薮[M].北京:中华书局,1958.
[7]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 严可均.全晋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