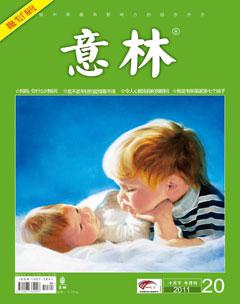张越:胖亦能立
我天生就胖,刚刚十来岁时,走在街上,就有人窃窃私语:“嘿,那姑娘真够胖的呀!”习惯了那些灼热的目光后,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所有的人都看不见我,于是专门穿黑色和灰色的衣服,想把自己隐藏起来。
从首都师大中文系毕业后,我做了中学老师。我对异性的吸引力接近于零。有位老大姐劝我:“你该减肥了,要不都成老姑娘了。”我决定好好减肥。
我的减肥是一场闹剧。十个胖人里,有九个都是贪吃的。
也不知道减肥产品遇上美食后发生了何种奇妙的化学变化,过了一个月,我胖了两斤。
据说烟民多半胖不了,我连咳嗽带喷嚏地学会了抽烟。抽了一个月,又胖了三斤,我的月开支多出几百元。
听说喝红酒有助于减肥,我开始喝。一个月十瓶红酒都打不住,我酒量见长。
我紧急叫停了减肥计划,不得不想办法赚外快来支付那些额外的账单。电视台的朋友让我写点小品本子试试,这一试,就试出了名堂。我的第一个小品在《艺苑风景线》播出,导演、制片觉得还行,于是春节晚会的小品也让我写起来。
一次跟朋友去歌厅小坐,我见到一个女歌手在唱一首叫《雪域光芒》的歌,歌喉很美妙,可看看她本人,比我还胖。朋友说,那个歌手叫韩红,因为肥胖,没有歌舞团要她,只好在歌厅唱歌。那一刻,我觉得什么东西触动了我的某根神经。她唱完,我点了个花篮送给她。不一会儿,韩红拿着一瓶啤酒过来谢我,说这是她唱歌以来收到的第一个花篮。我说:“我们都是重量级人物,迟早有一天,会在万众瞩目之下面对面……”
回家后,我觉得自己不能在中学里混吃等死了。胖,怎么了?我的斗志第一次熊熊燃烧起来!
那时,《半边天》栏目有个小板块叫《梦想成真》,拍摄一些女性在一天内实现梦想的过程。那些女性不是想当歌星就是想当模特儿。有人推荐说:“有个叫张越的胖女人想当厨子。”导演乐坏了,与我一拍即合。
我对美食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含情脉脉,让我的表演出尽风头。导演夸我的表演松弛且有灵性,问我是否愿意转行做主持人,愿意,当然愿意!胖怎么了?我就要做一个最好的胖主持人!
第一期节目,我就把韩红作为嘉宾请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录播间。我要让所有人看看,除了那些卖相好的歌手和主持人,还有我跟韩红这样卖相不佳但内秀的人物存在。
很多人说我主持节目有“江湖气”,但是效果非常不错。就这样,我在央视坐稳了位置。
事业上的成就给了我很足的底气。
我不再惧怕和别人在一起,穿大红大绿的衣服,做各种夸张的手势,用大嗓门说话。我一度醉心于此:在电视上到处露脸,今天谈做饭、明天说香水、后天侃就业、大后天聊女权主义……我觉得我有无穷的精力和创造力,無穷的体力。
后来,《三联生活周刊》的文章对我形象的混乱和四处露面表示了严重的质疑和批评。
我承认我那段时间是晕眩了——我以前是那么自卑的一个人,突然之间得意了,就觉得特别美。
有了这记警醒,我发现了自己的无聊与无趣,发现了从众的盲目与空虚。我开始远离喧哗浮躁的场景,用批评的眼光反省自己,审视声名与事业、人情与爱情、男人和女人,试着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自己的内心感受与意见,慢慢地把性格锻炼成个性。
在流俗之后,我终于把自己立了起来!
(潇湘雨摘自《女士》2011年第7期图/周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