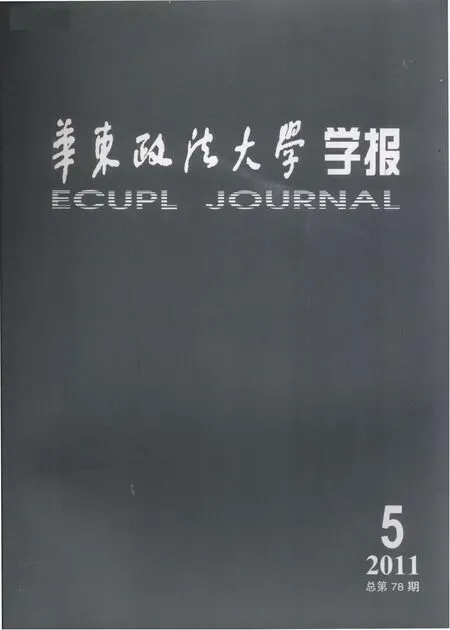民事权利本质论
张 驰
民事权利本质论
张 驰*
对民事权利本质之争的三学说中,“利益说”体现了保护的目的,“法力说”则在明确保护目的的同时,强化了法律的实际应用,均不能揭示权利的固有属性,唯有“意思说或自由说”涉及主体意志的实现资格反映了权利本质。但权利创设离开法律这一媒介则与现实不符。而探究权利本质的目的主要在于准确理解法律与权利的关系,以及明确法律设置权利及其赋予权利主体享有权利的价值所在。
权利本质 意思 自由 利益 法力
近代以来,民法以人为本位,并围绕着人这一主体确定权利义务等基本内容和有关制度。其中,权利已成为民法的核心概念,可以说民法的一切制度均是以权利为中心而构建的。但对于权利这一法律构造物,学界至今依然在如何界定、能否类型化以及如何保护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莫衷一是。其实,这些争论的存在或多或少都与对权利本质的认识相关。
一、民事权利本质的定位
我国古代汉语中,“权”和“利”为两个独立词汇,偶然也有权利并用,但其涵义均与现代权利概念相去甚远。〔1〕参见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现代汉语“权利”一词,移译自日本,日文中权利一词又移译自欧洲。最初译作“权理”,取其事理、道理之意,后译作“权利”。西语中的权利,拉丁文的jus、德语的Recht、法语的droit和英语的right均蕴涵正义和合理,〔2〕参见郑玉波:《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指正当而得有所主张而言,非“争权夺利”。〔3〕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页。除英语外,法语、德语和拉丁语的权利一词均同时兼有法律的涵义,权利为主观化的法律,法律为客观化的权利,〔4〕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足见权利与法律存在密切关系。但理论界对于权利的态度却并非一致,甚至存在权利否认说的观点,如法国学者狄骥认为人们只有依据法律从事社会互助的社会任务,绝无权利可言。〔5〕[法]狄骥:《宪法论》(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08页。如此观点因过于极端而难以符合现今社会的发展需要,故对民法确定权利未形成影响。相反,鉴于权利机能在确定保障个人自由活动范围,自主决定组织和安排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价值,〔6〕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近现代民事立法均肯定权利存在的合理性。无疑,对权利本质的分析和揭示也是在肯定权利存在的基础上展开的。
(一)民事权利本质主要学说简介
自19世纪以来学者们致力于探究权利的本质,学说纷呈,其中有代表性的流派主要包括意思说、利益说和法力说三种。〔7〕除这三种主要学说外,还有权力说、申诉说、期望说、折衷说等。参见王利明等:《民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页。
1.意思说。意思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德国学者萨维尼(Savigny)和温德夏特(Windscheid),〔8〕萨维尼是系统阐述权利本质者,温德夏特在学术上是萨维尼的衣钵传人,全面继承了萨维尼的学说观点。该说基本观点是权利本质乃意思自由或意思支配。亦即权利为个人意思能自由活动或任意支配的范围。故意思为权利基础,无意思即无权利,权利的本质应归着于意思。〔9〕参见郑玉波:《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萨维尼之所以毫不掩饰地重视意思,关键在于他将意思支配与法律关系相联系,并且认为法律关系的本质就是被确定的个人意志独立支配的领域。个人意志除作用于当事人自己外还可包括外部事物,由此决定意志支配主要可涉及三个对象,即本人、无意思自由的自然以及他人。〔10〕参见[德]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第1卷),朱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60页。显然涉及对象不同,所呈现的法律关系的种类也有异。与意思说相似的是自由说。该说主张权利本质为自由行为的范围,但其影响力较为逊色。〔11〕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书中虽提到“自由说”,但解释甚为简陋,亦未能指出此说由谁人所倡及如何变化发展等。其实,自由说与意思说本质相同,都强调了意志或意思在权利中的地位。只是自由说更明确地指出权利乃是意志实现的自由,而非单纯意志自由。因任何人意志均为自由不言而喻,故只有将个人能自由实现的意志定为权利,才具有法律价值。
2.利益说。利益说的创始人为德国学者耶林(Jhring)。此说基本观点是,权利本质为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凡依法律归属于个人生活之利益(精神的或物质的)即为权利。〔12〕参见郑玉波:《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耶林曾明确主张“法权是信法加以保障的利益”,更有学者对此进一步说明:“其实主观法权的根本就是一种利益,法权只当利益经法权的享有人或另一人用意思表示在外部证实时,才真正地表现出来。”〔13〕参见[法]莱昂·狄骥:《〈拿破仑法典〉以来私法的普通变迁》,徐砥平译,徐菲勘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按照该观点,权利主体与受益主体同一。利益说将社会生活关系中包含的各种利益作为权利,更为直接和客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我国大陆众多学者认可。
3.法力说。法力说由德国法学家梅克尔(Merkel)首创,此说基本观点是,权利本质乃享受特定利益的法律上之力。〔14〕参见郑玉波:《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也就是说,权利由内容和外形两要素组成,前者为法律上的特定利益,是人类为求生存不得不发生的人类与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后者为法律上之力,即法律因充实其所认许的利益不能不赋予的一种力量。〔15〕参见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该说立足于实证角度研究法学对象,成为近世有力之说,尤受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推崇。我国台湾学者郑玉波先生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强调法律赋予的法律上之力因受法律支持和保障,而不同于一般实力(私人腕力)。同时,法律以力予人,目的在于使人享受特定利益(包括财产和非财产利益)。〔16〕参见郑玉波:《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2、63页。因此,不同权利意味着利益和法律上之力也不同。
(二)民事权利本质主要学说评析
关于权利本质的不同学说,学界至今见仁见智,难以完全达成一致。
对于“意思说”(或自由说),否定者通常认为该说根本缺陷在于,不强调权利与法律的关系,不能解释道德规范和不依当事人意思的法定权利现象。〔17〕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也就是说,“意思说”不能合理说明权利与法律谁先存在,无意思能力者是否仍然可作为权利主体,权利得丧是否均须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等问题。这是因为,按意思说,只要存在意志就应有权利,但事实上权利的出现晚于法律,在法制史上早期的法律是以义务为本位而非以权利为本位。此外,权利若归结于意思,则未成年人或精神病患者因无意思能力而不应享有权利。但现代民法均以人格平等相标榜,无论权利人精神状态如何,都无例外地为权利主体。固然,为补正无意思能力人的缺陷,可设法定代理人制度。但以法定代理人意思为被代理人意思,可解决权利行使的问题,却终难证实无意思能力人有意思的自由。〔18〕参见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对于“利益说”,否定者一般认为其主要不足在于易将权利与权利所保护的利益混淆。〔19〕也有观点认为“利益”本身难以界定,在法律领域利益是否仅指财产?如李锡鹤先生认为:利益为身外之物,不属于人身。利益如需法律保护,只能是财产。参见李锡鹤:《民法原理论稿》,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9页。这是因为,一方面法律保护的利益并不都体现为权利,如交通安全作为一种法律保护的重大利益并未表现为权利,却反映为要求人人遵守交通规则的义务;〔20〕参见郑玉波:《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另一方面权利也不总是反映为利益,有时仅反映一种自由,如人们为赠与或捐助行为,以及舍己救人行为等,仅仅表明行为资格而与利益无关。〔21〕参见李锡鹤:《民法原理论稿》,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亦即权利与利益无必然联系。何况,民事法律作为行为规范通常仅规定主体能否为何种行为的界限,而不顾及主体行为的动机和结果等。此外,如不言明该利益是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则与“意思说”相同,该说亦以权利先存为基础,而不能合理解释法律与权利的关系。
“法力说”以法律先存为基础,强调先有法律后有权利,明确了法律与权利的关系,成为当今通说,但仍然有难以回避的缺陷存在。这是因为,作为权利要素的内容和外形均非权利的本质。即特定利益本身是权利所要达到的目的,法律上之力系达到目的的手段和担保。“目的”仅是行为的结果,而非对“行为”本身的注解,手段是法律的强制作用体现,仅表现为一种现象,同样也不能揭示事物的固有属性。而且,法律上之力只是法律制度对权利人的授权,体现为法律上“可以作为”的某种可能,而非指各种具体权利,且不同法律关系也无法概括出一种具体的权利。〔22〕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79页。
比较而言,“意思说或自由说”关注主观层面的意志自由,着眼于权利动态;“利益说”侧重于客观层面存在的利益,重视法律保护的对象;“法力说”立足于应用层面,强调法律是权利的发生依据和前提,注重法律上之力的作用。可见,各种学说虽因侧重不同而利弊并存,但仍可根据其基本内容推导出存在价值。三学说中“意思说或自由说”基本反映了权利本质,“利益说”体现了保护的目的,“法力说”则在明确保护目的的同时,强化了法律的实际应用。因此,唯在关注“法力说”的基础上强调意志自由是权利本质,才能对权利进行准确定位且使之更具实际意义。对此,尚有两点需要进一步说明。
第一,之所以认可“意思说或自由说”揭示了权利本质,是因为民事法律作为授权性规范,主要是界定行为人“可以作为”的范围,而特定行为的可能性或资格必然反映特定意志的实现自由,且众多具体权利行使与实现也体现为特定主体意志的实践,本质上与“意思说或自由说”如出一辙。但将“意思说或自由说”作为权利本质,并非置法律作用不理。事实上,无论是“意思说”(含自由说)还是“利益说”均未脱离法律框架。具体而言,强调思想层面任何人皆享有自由者,也充分意识到史上几乎没有以约束、规范思想为目的的法律。单纯意思自由不能被称为权利,仅是思维上的活动不能导致法律关系变动,无法影响权利得丧。法律上能产生法律效果的各种事实包括行为和事件,所启动的权利得丧离不开具体法律关系。因此,法律需规范的内容只有行为的范围、可能性或者自由,也只有这种外在表现意思的客观状态,才能被法律调整和规制。这也是持“意思说”者在确定意志支配领域时,要将之与法律关系相联系的原因所在。同样,持“利益说”者虽也认为权利是法律确认的一种行为可能性,但因法律保护的利益作为一种形式无法显示事物的根本属性,〔23〕拉伦茨教授指出,权利是为了保护权利人的某种利益的,但它本身并不是利益,只是一种法律形式,可以依此形式主张利益。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79页。更为关键的是,根据生命人人格平等的理念,任何意志天然地享有相对于实现资格的表现资格,法律不应过问意志后面的因素,即意志的动机,而“利益说”与“意思说”不同,明确行为的目的是行为人自己的利益,意味着任何不以利己为目的的意志不具有表现资格,由此与现代法学根本原则相悖而无法揭示权利的本质。〔24〕参见李锡鹤:《民法原理论稿》,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页。
第二,“意思说或自由说”虽认为法律是确认权利的依据,但对法律的具体作用即法律上之力的认识仍显不足,或者说较为模糊。这是因为,即使从正面界定权利本质为自由时,也须强调自由为权利行使的客观界限,而不能只顾权利的主观状态;即使明确权利取得的依据及其范围,也得关注权利能否实现的法律保障措施,否则法律确定权利将失去意义。无疑,“法力说”作为一种手段和措施,仅反映了事物的现象,却无法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但从实证角度而言,充分关注法律的强制作用对全面把握法律确定权利的意义,似乎比单纯了解权利本质更为重要,这也是法力说成为当今通说的最好注解。然而,对于“法力”,既不能仅简单将其理解为各种法律关系的具体之力,认为不同法律关系的“法力”含义不同,如“直接支配、排他性”就是物权的“法律之力”,“请求”就是债权的“法律之力”;也不能过于扩大“法力”的涉及范围,如将“支配力”解释为既可支配标的物,也可支配他人。〔25〕参见郑玉波:《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3、64页。理由是,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法律关系纷繁复杂,意志作用的对象难以一一明了,不同法律关系涉及的各种权利所显示的“法力”应当不同,债权与物权如此,其他权利如形成权等亦复如此。何况,有些权利如人格权,依现代民法所倡导的主体地位平等的精神,意味着任何人不得支配其他人。〔26〕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78页。由此说明在明确不同法律关系可体现不同“法力”的同时,似还应从权利实现角度来理解“法力”。事实上,法律授予主体享有权利,并不意味着权利人就可亲自去实现与权利相适应的状态,如仅有请求权,未必导致债权实现。可见,对于权利人而言,不仅需要关注权利的有无及其界限,而且更应重视权利能否在法律的保障下得以实现。不过,请求之力(权利)以诉讼方式实现,并非将权利与诉权划等号。诉讼保护不是权利的目的,仅是权利实现的一种手段。因此,法律赋予权利之“法力”应体现为具体和抽象之力的结合:具体之力源自法律规定或意思自治,主要指权利主体对权利客体基于其意志为自由行使和处分的可能或资格,取决于不同法律关系内在效力的表现;抽象之力来自法律规定,为任何权利所共有,表现为权利的外在效果即法律的担保力。唯如此理解“法力”的独特价值,才能准确地体现法律与权利的关系。
二、研究民事权利本质的意义
探究权利本质,并非单纯解释或揭示其根本属性。重要的是,通过分析权利本质各观点之争,寻找各学说存在的合理内核,充分理解法律设置权利及其赋予权利主体享有权利的价值所在。据此可将研究权利本质的意义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界定权利及其特性的需要
大陆法系素来主张体系完整、概念清晰。故对民法核心内容的权利加以界定理所当然。的确,在现有的法学教科书或辞书中不乏权利定义,但因受权利本质不同学说的影响,迄今为止尚未出现一个能充分概括权利全部内涵和外延并为学界真正接受的定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利不可定义。根据前文对权利本质各说的分析,权利的本质乃意志自由,而自由既应受到法律的约束,又应得到法律之力的保障,故应得到法律的确认。同时,被法律确认和保障的自由在法律层面仅是一种资格或可能性,而非主体意志的现实体现或实现。鉴于此,权利基本可定义为民法赋予并保障民事主体特定范围的行为资格。
应指出的是,从民法体系层面为权利定义,只能是一个抽象概念,不能与具体权利相提并论。正如德国学者拉伦茨教授所言,权利形式上的概念,只是根据法律逻辑形成,而非“权利”的内在意义(法律伦理和法律目的)及其内容,进而他认为权利概念只能是一个“开放式的概念”,或者一个“框架概念”,这个概念应能适用于不同种类或者不同类型的权利,并且是我们现行法律中所认识的。〔27〕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76页。而要探求权利的具体内涵,只有结合业已发生的各种具体法律关系加以理解。唯有如此,权利概念才具有兼容性和适应性,能名副其实地被称为私法上的重要工具。简言之,法律保护的对象非抽象性权利,而是各种法律关系中的具体权利,其必然是主体意志作用于客观现实利益的反映。
然而,这并不意味权利体系层面的抽象定义可有可无。框架性定义虽不能直接显示存在于具体法律关系中各种权利的内涵,但完整权利体系的形成需要一个可统帅各种具体权利的上位概念存在,更重要的是抽象定义可充分揭示各种权利的共性。
不可否认,权利概念的存在和使用,易与权力、权能和权限等近似概念混淆,故有必要加以区别。权力同样被作为法律确认的特定范围行为资格,最易与权利混为一谈,如有学者将代理权作为权力,或直接将权利定义为权力,〔28〕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但权力的支配或保护对象均不像权利那样归属于市民成员,故而权力概念应限用于公法领域。至于权能与权限,前者为权利效力的具体表现形式;后者是权利效力的具体范围。〔29〕参见李锡鹤:《民法原理论稿》,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页。但无论是权能还是权限,必然与各种具体法律关系紧密关联,而非停留于抽象的框架层面。同时,一个单个权利往往包含着不同权能,如权能尚未与权利分离,不能独立地被转让时,就不能作为“权利”。〔30〕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63页。当然,也无法确定其效力具体涉及范围。换言之,作为法律关系要素的权利,只能是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权能。也只有如此,权利才有可能被转让,或者成为救济的对象。
(二)明确权利构建基础和机能的需要
权利与法律应结合不容置疑,但具体到权利与法律谁先存在的问题,学界却说法不一,不同答案形成了对权利构建基础的不同态度。学界观点主要有三种。〔31〕参见郑玉波:《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6、77页。一是权利先存说,立足“天赋人权”,认为权利与生俱来,有保护权利之目的始有法律之创设。〔32〕参见张宏生、谷春德主编:《西洋法律思想史》,汉兴书局1993年版,第173、174页。该说关注权利的应然状态和神圣性,对于反对封建专制和培育法治精神意义深远。但其仅为法律理想状态,与现实不符。二是权利与法律同时存在,该说认为权利与法律乃一事物的两面,法律依主观方面观察为权利,权利依客观方面观察为法律。尽管罗马法以来众多语言如拉丁语、德语、法语等均用同一词汇表达权利与法律,但仅凭此不能有力证明权利和法律同时产生,更不能解释某些由法律直接创设权利的现象。三是法律先存说,该说源自“实证法学派”强调“法外无权”,〔33〕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是约翰·奥斯汀。该派主张法学研究的对象仅限于实在法,即由立法者创制的法律,以实在法作为一切法律现象发生的根据和渊源。参见张宏生、谷春德主编:《西洋法律思想史》,汉兴书局1993年版,第326页。认为权利由法律创造并以其强制力担保。但此说在如实描述实然法律的同时,也尽显消极因素,无意中为“恶法亦法”提供了论据,且可能抑制人民为权利斗争的积极性。不同观点虽各有利弊,但在大陆法系语境下,法律先存说最具现实说服力,故受众多学者赞成。
根据法律先存说,我们知道权利是由法律创造并类型化的。在大陆法系立法模式和理论体系中,权利可根据不同标准进行分类,组成体系,以认识各种权利特征及其区别与关联。〔34〕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标准不同权利类型也不同,但将不同权利类型形成体系的基本思路是,先基于“法力说”考虑的权利两要素即“特定利益”和“法律上之力”着眼:前者属权利标的区分为静的观察;后者属权利作用区分为动的考察,后复可依其他种种标准加以区分明确私权的分类,〔35〕参见郑玉波:《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以最终构建权利类型化的体系。但因受立法技术和立法者认识能力所限,或出于公共政策和利益衡量的考虑,任何立法都不可能也无法将民事主体应享有的全部特定利益纳入其中,这说明法律确定权利应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不仅需将某种有保护必要的行为自由或利益及时赋予法律之力,而且也应及时调整那些因社会变迁或法律发展而偏离主流伦理的权利内容。同时也说明民事权利体系构建应呈开放状态,权利种类应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权利类型的扩展并非不受限制,通常只有既具备权利共性特征也符合某种权利类型个性要素的“特定利益”,才可正式被命名并归入相应权利类型。
根据法律先存说,我们应意识到法律确定权利的同时也限定了主体享有权利及其行使的范围。法律赋予主体的权利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为保障个人得共存共荣、和谐的社会生活,凡权利皆应受限制。〔36〕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48页。也就是说,权利的行使或保护应以法律合理和有度赋权为前提,而权利的边界则需在兼顾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基础上确定。
根据法律先存说,我们还应明确在为权利斗争亦即为法律而斗争,维护权利的同时,也在维护法律尊严。德国法学家耶林指出,为权利而斗争,是权利者对自己的义务。为权利而斗争,也是权利者对社会的义务。质言之,权利人主张或行使权利,既关乎法律的尊严,又蕴含着伦理的意义。〔37〕参见[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胡宝海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因此,在制定和完善法律制度的同时,充分关注对人民法感情和法意识(尤指权利意识)的培育,对于法律赋权的实现有着重大意义。
(三)完善权益保护模式的需要
权利确定及其类型化,是权利体系化的要求,是制定法的产物。但一个完整权利体系的形成,当不可缺少权益保护这一重要组成部分。亦即法律赋予主体权益,就应以法力予以保障。这意味着无论何种权益均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以及任何权力的侵犯,一旦主体的权益被侵害,都应有救济途径。按照法律制度体系化的思维,民法通常区分不同“特定利益”而定权利类型,并赋予不同的法力和救济手段,将权利类型与保护方式直接衔接。单纯靠有限权利类型调整近乎无限的利益冲突,必对那些被法律确认“遗漏”的应保护利益有救济不能或保护不周之虞。因此,大陆法系各国立法不仅关注各种具体权利特性及其体系构建,以明确权利的特定内容和法力作用,而且针对权利类型化的弊端以探寻和完善权益救济路径和保护机制,其中对法定权利外某些利益的保护模式设计尤为关注。
理论上,对未被法律作为权利确认的“特定利益”,有学者主张采广义理解权利概念的方式,将那些仅仅通过个别强行规定得到法律保护的法律状态也视作权利,以扩大侵权法上的损害赔偿范围,〔38〕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即求助于“权利推定原则”以济其穷。但这种略带浪漫色彩的推定做法有两点值得推敲:一是权利推定时是否应按现有的权利类型进行推定并归类?二是推定的权利与法定权利应否得到同等保护?如果对此都能得到肯定回答,想必无需推定,只要通过解释就可弥补保护不周的弊端,否则仍然会因欠缺可操作性而使之流于形式。更为关键的是,如不加区分地将人类一切应当且能够受保护的利益给予同等救济,则将过度限制他人自由。为此,大陆法系的主要代表德国在立法上提出了“法益”概念。其实,正是因为利益内容多元性,才有权利形态的多样性;也正是因为利益范畴的复杂性,才使现有权利体系难以涵盖各种法律须保护利益并将之类型化。因此,不同权利应体现不同的法力,权利与法益应有不同的保护力度,应是民事权益保护模式设计时不可忽视的内容。
基于此,立法和司法对权益保护机制设计的具体思路原则上由三个层次构成。第一层次是将由法律认可的具体和有名权利类型化作为权利保护的第一道防线,与现有权利保护体系所确定的相关保护手段等直接挂钩,按照不同法律关系所生的请求权基础赋予不同的救济路径。这一任务主要通过立法完成。第二层次是针对法定权利外存在效力较弱的“法益”或“框架权利”,民事立法可通过设置一般条款等方式将保护范围扩大至“法益”,为“法益”的保护提供适用依据。如此设计与侵权法规范采取何种模式无必然关系,关键须依托于司法活动的具体落实。换言之,在司法具体适用一般条款时,应区别对待“法益”和法定权利,对“法益”的保护手段与程度应视具体情况并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而定。第三层次的设计是在前两个层次均无法为主体提供足够救济达到保护目的时,可考虑赋予法官一定程度的自由心证将某些正当合理诉求径行确认为保护对象,以达法律救济之目的。但是,应要求法官根据民法及其原则体现的精神或理念,参酌衡平、正义观念判断有关诉求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并结合诉求的可主张和保护性以定保护方式和力度。另外,也应强调判例等间接渊源可作为适用依据,以引导并限制法官自由心证适度而为。为使法律应保护的权益得到全面和合理的保护,保护机制设计的三个层次应有适用的顺序,任何跳跃顺序的做法都不具有法律效力。
三、结语
综上,认可主体具有独立意志并为鼓励其追求和实现自身价值,意味着权利的本质应体现为自由或意思,但全面满足或迎合“应然”状态的需求显然与现实不符。人们任意过度地追求自我,必然会损及他人的利益,由此主体行为资格理应受到法律约束,亦即权利或自由只能经法律这一媒介赋予和限定范围。但法律创设权利不仅仅是为了确定意志自由的范围,使之在法律的担保下能得到实现,在遇到侵害时能受到充分保护,也应是其题中之义。因此,唯有充分关注人类发展各种合理需求,将自由或意思与法律规定紧密结合,使“应然”与“实然”有机对接并赋予合理的法律之力,才能充分体现私法的功能和价值,真正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
*张驰,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本文系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第五期)“民法与知识产权”(项目号J511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李秀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