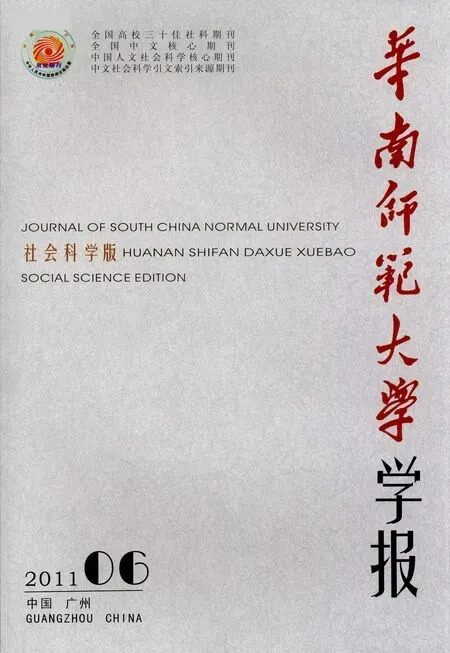论宏观历史研究借用二手材料的界限及风险防范
代继华,彭 莘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论宏观历史研究借用二手材料的界限及风险防范
代继华,彭 莘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历史研究中,原始材料的评价标准具有唯一性,而使用二手材料又是一个普遍的做法,尤其是单个史学家在社会需要、在全球史编撰等的相互作用下,面对无限的材料,必需借用二手材料进行宏观历史研究。要解决这一矛盾,要明确必需不是随意,更不是滥用;其界限是适用于历史理论和历史思想的探索、宏观历史比较研究和大型综合史书编撰三大领域。唯有如此,宏观历史研究才能在历史理论和历史比较以及历史多样化解释等方面有所创新和贡献,充分展现其史学意义,促进实现史学社会功能。宏观历史研究借用二手材料存在风险,借用必须以新意为依归。通过坚持研究目标服从材料的原则,坚守学术规范等,防范风险还是有希望的。
宏观历史研究 二手材料 借用 界限 风险
历史材料是史学家的“为炊”之“米”。史料有原始材料与二手材料①汪荣祖认为:“照西方的概念,史料分原手(primary sources)与二手(secondary sources),像二十四史绝非原手史料,而是二手史书。评价二十四史须以史书的标准,若以史料的标准,只能算是次料。中国所具备的第一手史料,并不充沛,更不能说是完整的记录。现代中国学者在西方的影响下,遂欲扩充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包括地下出土的考古资料。”见《史学九章》,第100页,三联书店2006年版。中国史学界基本上是把“二十四史”视为“原始材料”的。本文依据这一取向来区分原始材料和二手材料,作为立论的出发点。之别,原始材料又成为判别史学家和历史著作的唯一标准。这一标准,严重妨碍了对宏观历史研究②历史学通常可以划分为宏观史学与微观史学两大类型。宏观史学研究,就是从大范围的、或整体的或贯通的对历史现象进行高度概括性的综合研究,“勾画当日社会的整体面貌”是其基本要求。(参见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第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微观史学研究,一般来说,“是指这样一种历史研究:从事这种研究的史学家,不把注意力集中在涵盖辽阔地域、长时段和大量民众的宏观过程,而是注意个别的、具体的事实,一个或几个事实,或地方性事件。这种研究取得的结果往往是局部的,不可能推广到围绕某个被研究的事实的各种历史现象的所有层面,但它却有可能对整个背景提供某种补充性说明。也就是说,微观史学家的结论记录的或确定的虽只是一个局部现象,但这个看似孤立现象却可以为深入研究整体结构提供帮助”。(参见陈启能主编:《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第21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宏观历史研究的实现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通过史学家的合作研究来实施。比如,前苏联史学家集体编写的十卷本《世界通史》、由阿克顿爵士支持而编写的《剑桥近代史》、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等;第二,单个史学家所进行的宏观历史研究。比如,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周谷城的《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合作撰写宏观历史著作可以更多地凭借第一手材料来完成,而单个史学家主要是通过借用二手材料来实现的。为避免节外生枝,本文只以单个史学家所做的宏观历史研究为分析对象。、尤其是对单个史学家的宏观历史研究活动和成果的理性认识和中肯评价。其成果要么被不屑一顾,要么被另眼相看,要么被大加贬损。如何减少这些误会、误解和偏见呢?本文拟从五个方面(即历史研究使用二手材料是一个普遍现象,宏观历史研究借用二手材料的必要性、界限、史学意义、风险防范)加以论述,或许有助于史学界善待单个史学家的宏观历史研究活动和成果。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历史研究使用二手材料的四种做法
历史记载是人类知识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怎样记载历史,以接近或逼近历史真实,以取信于时人和后人呢?尊重历史,忠实记录,成为史学家长期坚守的主要信条之一。事实上,要做到历史记载接近或逼近历史真实,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是取决于原始材料的有无及多寡,取决于其是否具有足够的复原价值。原始材料作为历史研究的最基本出发点,具有唯一重要性。
近代专业史学的形成,使得使用原始材料成为历史研究的不二法则。“18世纪晚期,史学家开始采行如今念过历史书籍的人都熟悉的读史方法,他们阅读古旧文件记录,从中找寻有关撰写者的事实。他们也开始考订后来专业史学者所谓的第一手或原始的资料。”①乔伊斯·阿普尔比,等:《历史的真相》,第23页,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被称为“德国理性主义之父”的新教神学家泽姆勒(1725—1791)强调方法论,特别是把当代和第二手的证据材料的价值和使用之间的界限、原始资料和间接资料之间的界限加以区分。②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第169-170页,孙秉莹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法国史学家奴马·登尼斯·浮斯退尔·得·库朗日(1830—1889)认为,“最好的史学家是密切靠拢材料的人,他仅仅根据材料进行写作和思考”。有一回,他“偶然遇到一位引证第二手文献的作家,他气得就像要吞食一切的一团大火。无论任何种类的第二手著作他都很少使用”③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四分册,第509-510、712 页。。实证史学大师兰克更是档案材料的极力主张者和实际工作的集大成者,影响深远。
史学家是否使用原始史料、是否将原始史料一网打尽,成为衡量史学家和历史著作的唯一标准。“我们在判断任何一部历史著作的价值时总是首先检查它是否使用了原始史料,其次才是检查它是否考虑了已经获得的全部史料。”④杨豫、胡成:《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第23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因此,那些借用⑤借用,就是指宏观史学家主要地或部分地借助已有研究成果(如恩格斯之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周谷城之于《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剑桥近代史》、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黄宗智和杜赞奇之于“满铁”《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等)作为进行历史研究和著述的材料来源。此外,翻译材料可以划归二手材料的范围,只是情况更为复杂,讨论的空间更大。二手材料撰写的历史著作的声誉大受影响。麦考莱(1800—1859)的《英国史》“是一种二手资料,它的声誉被现代研究大加贬损”⑥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第53页,吴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但是,无论怎样申明与坚持,无论怎样反对或抵制,在历史研究与史书编纂中,古往今来的史学家使用二手材料始终是一个较为常见的现象。归结起来,大致有如下四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史学家“对某些部分的问题认知不足时,就采取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或以弥补孤陋,或以加强论证”⑦韦政通:《中国文化概论》,“自序”第3页,岳麓书社2003年版。。“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专业或领域,例如一位外国的自然科学家,就得依靠权威的、严肃的介绍。”⑧葛剑雄、周筱赟:《历史学是什么》,第12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二种做法,史学家因为资料的有限与时代的制约,依赖于二手材料进行研究和写作。
“英国历史之父”比德(673—735)的《教会史》,是蛮族时期写出的一部最伟大的著作。“从公元597年到731年,无论就世俗或就教会事件说来,这部书都是唯一的一部可靠的史料,尔后所有作家都是从他这部书中摘取材料的。”⑨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第229 页,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英国史学家乔治·芬利(1799—1875)的《从罗马征服到现在的希腊史,公元前146年至公元1864年》,“从头至尾都表现着创造性的研究和对这个题目透辟的了解”。“他写这部书时并未使用任何档案材料;到这个世纪末尾,第尔就把他这部书扔到一边,说它肤浅。然而,研究东罗马帝国全部11个世纪的历史的英国人,却仍然只有吉本和芬利的书可供参考。”⑩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四分册,第509-510、712 页。
在19世纪兰克的史学革命之前,历史学家倾向于依赖这种原始资料。要了解罗马历史,他们会求助于恺撒(Caesar)、塔西佗(Tacitus)和苏托尼厄斯(Suetonius)的历史著述;而研究中世纪的史学家会利用盎格鲁-萨克森编年史提供的资料,借鉴诸如13世纪的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和14世纪的让·傅华萨(Jean Froissart)等人的著述。现代历史学家并未轻视这些叙事资料。他们将这种资料的持久重要性归因于这样一种事实,即创作它们的那个时代仅留下的有限资料。⑪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第55页。
“本尼迪克特是在日美交战的情况下研究日本的,她只能凭借间接资料进行‘遥研’。”①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译者序言”第3页,吕万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与学术环境的转变,海外人类学家只能通过在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社区的田野调查,或凭借仅有的文献资料来研究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封闭的大陆使海外的学者无法亲临现场来研究中国,只能通过对华侨社区的调查间接地研究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文化观念,或借助以往的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来把握他们难以认识的汉人乡村社会。”②胡鸿保:《中国人类学史》,第210、21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从1950年代到70年代,西方学者的“大多数的研究或凭借传媒所报告的官方资料,或通过采访在香港的大陆移民进行”③胡鸿保:《中国人类学史》,第210、21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三种做法,史学家因为语言的阻隔,依靠已有的翻译作品进行研究。
莱布尼兹(1646—1716)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阅读了几乎当时在欧洲出版的所有有关中国的书籍。“因为白晋不来信解释莱布尼兹已收到的16卷汉文资料”,他抱怨自己“看不懂这些著作”。“只有后来在1715年收到龙华民和利安当的论文和大量汉文经典的摘录之后,莱布尼兹才受到激励,开始写他的关于中国的最有哲学价值的著作——《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④孟德卫:《莱布尼兹和儒学》,第63页,张学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自然神学”系莱布尼兹用以指中国“儒家哲学”的词。美国著名的思想史家和史学史家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说:“尽管不幸的是,我不能阅读中文而必须依靠翻译。过去五年内,我积极参与了一项《中国文学与比较史学》的国际项目。”⑤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中文版序言”第1页,何兆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王晴佳的《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虽然引用了不少西方史家的著作,但基本上依靠的是已有的翻译,自己并没有做多少努力。我只是在自己的写作中,不故弄玄虚,而是力求深入浅出,将意思表达得清楚、流畅”⑥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第269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四种做法,史学家有意识地将已有研究成果作为历史研究和著述的基本材料。如果不借用,其研究无法开展,要获得最终成果也就无从谈起。如,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是根据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林惠海和‘满铁’调查部门对长江三角洲八个村庄的研究,结合江南地区的文献资料,追溯明初以来的一些主要变化撰写的”⑦胡大泽:《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第1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韦政通的《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一文,共六节,分节叙述了中国文化对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英国、法国、德国的影响。作者在其“附言”中说:“这一篇附录,大部分是根据第二手资料,或节录或改写而成,只能包括用中文写成的对这一问题研究的部分成果。”⑧韦政通:《中国文化概论》,“附录”第355页。
以上四种做法都是使用二手材料。但是,使用还应当作引用与借用的区分。第一种做法属于引用,即较少数量地在较小范围内使用二手材料,而且是局部的、次要的。后三种做法属于借用的范畴,即数量较多和范围较大地使用二手材料,而且是基本的、主要的和自觉的。这可以视为引用和借用的主要区别。但是,还需要对借用作进一步辨别:第二种做法,是没有选择的,是不得不借用,并同时适用于宏观与微观历史研究,因此,不在本文讨论之列;而第三、第四种做法主要适用于单个史学家进行的宏观历史研究。
这就出现一个明显的矛盾:在强调原始材料标准的唯一性的同时,借用二手材料又是史学界的一种普遍做法。尤其是不少宏观历史研究成果具有历史理论、历史方法、历史观念、历史解释等新颖性和启发性,长期在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由此可见,是否使用原始材料、是否全部使用的评价标准也是相对的。对于单个史学家的宏观研究成果,需要将材料(原始的与二手的)与理论、思想和方法的贡献,与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等加以综合考虑,从而使其历史成果评价的材料标准更具有包容性,使借用二手材料更规范更有效,取得推进宏观历史研究的良好效果。
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单个史学家进行宏观历史研究为什么必需借用二手材料、借用的界限在哪里、借用的史学意义是什么、如何预防借用的风险等诸多问题。
二、宏观历史研究借用二手材料的必要性
在史学实践中,长期强调原始材料的唯一性,制约了宏观历史研究的发展,直接的后果就是“见树木”的成果太多,而“见森林”的成果寥寥,难以有效地发挥史学影响社会的应有作用。“如何确定对个体现象的研究和对群体现象的研究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如何结合对历史的微观研究方法和宏观研究方法。……可以说,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和作出的种种努力,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决定西方史学今后的主要走向。”①陈启能主编:《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第16-17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史学其实也不例外。事实上,微观历史研究成果,好比一块一块的砖,体现的是学术价值;宏观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借用这些砖(即二手材料)搭建成各种各样的漂亮房子,集中展现历史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这就是宏观历史研究必需借用微观历史研究成果的客观现实。具体来看,宏观历史研究之借用二手材料受到以下原因的直接影响。
第一,历史需要实现其社会作用,社会需要史学家提供宏观历史成果。
宏观历史研究是全球的、地区的、民族的、国家的,综合性、整体性和贯通性是其主要特点,面向社会进行释疑解惑是其主要意图。微观研究成果是个别的、局部的,难以面向社会。宏观历史研究通过整合微观研究成果,形成历史的整体结构。这对于提高历史理论水平、开阔历史视野、提供多样化的历史解释、实现史学社会功能等,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任何对宏观历史研究的轻视、否定都是片面的,都无助于宏观与微观历史研究的良性互动,无助于历史与社会的紧密联系。
1864年,古朗冶“出版了《古代城市》(La Cite Antique)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力求通过比较希腊、罗马城市,概括城市的发展和宗教的影响。但以后,他就放弃了这种宏观的比较,而强调历史学是一门事实的科学,必须禁绝一切抽象概括、形而上学和爱国主义等主观因素,让历史事实说话。②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第149页。“科学派史学家却很少注意大规模往事间的相互关系,更不去解释历史的变动,特别是大规模的变动,也不愿写作以大规模往事为题材的史著。小规模事实的确定对于史学研究本身以及有关科学研究,虽有重大的意义,但对于整个社会的直接用途却微不足道。事实搜求派的史学家显然取消了一些问题,并规避了对社会大众直接服务的责任。”③王尔敏:《史学方法》,第228页“许冠三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禁绝一切抽象概括”和对宏观历史研究不以为然的态度,显然是无益的。“拒斥所有宏大叙事不可能有意义,因为叙事和宏大叙事只是叙事的不同种类,没有这样的叙事就不可能有世间的行为实践。”④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第173页。“就逃避宏大著作的行为而言,更为合法的反对意见就是,如果不尝试将近代历史的方方面面视为某种整体,如果不形成一个故事或者一种综合,那么,问题(它们需要答案,它们的解答能够促进对整体的真正理解)就不会彰显出来。这种观点完全正确,并且证明了‘未成熟的’宏观研究的写作是正当的——如果牢记这种研究的主要目的应当是界定有待完成的进一步的研究工作的话。”⑤G·R·埃尔顿:《历史学的实践》,第61页,刘耀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为了贡献社会,史学不可能“拒斥所有宏大叙事”,满足于“小规模事实的确定”与一隅之见。宏观历史研究成果是人类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历史学不可能规避“对社会大众直接服务的责任”。
第二,宏观历史研究的全球性、区域性等新特点,与单个史学家存在的语言难通和专业分工过细的局限,必然导致宏观历史研究借用二手材料。
拓展视野、探索未知世界始终是人类最基本的追求之一。新航路的开辟使世界史的编写提上了议事日程。德国史学家施罗塞(1735—1809)编写了一部《世界史》。“他说,世界史应包括‘一切已知的时期、国家和重要事件’。只有当‘它通过许多事例讲解人类的起源、进步、改进、衰落,从而给心理学、政治学、自然科学以及其他学科带来使人心明眼亮的例证’的时候,才算‘真正的人类史’。”⑥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第167页。在黑格尔(1770—1831)的工作以后,“历史学不得不谈世界史。而且世界史必须注意,已经变成众所公认的了;虽然抽象性的及建构性的形式还不是合宜的(世界史研究方式)。”⑦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第106页,胡昌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史学家的观点愈富有世界性,愈能摆脱民族或地区的偏见,愈接近获得有效于当代的历史概念。”⑧杜维运:《史学方法论》,第2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原始材料的观点,要用全球视野来编撰和阐释历史,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它超越了单独的民族国家、地理区域或文化群体的范围。全球史是宏观历史研究必需借用二手材料的集中体现之一。
首先,没有哪位史学家能掌握世界上主要的民族语言,更不用说全部。就是熟练地掌握一种其他民族的语言,能够听说读写,能够自由交流,能够从容研究,已殊非易事。
“欧洲汉学成果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大量的、必要的中国哲学、文学和史学典籍的西文译本。它们既是各种课题研究的基础、引文的来源,也是初入汉学的必读书,即便是中文非常优秀的学者或学生也要借助译文迅速进入某一课题的语境,了解较多的背景材料。进入论文、论著的写作过程以后,有了好的译文,就不必在引用原文时重新翻译一遍。因此,译者的贡献非常重要,在汉学产生初年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尤其重要。”①胡志宏:《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第6页,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研究17世纪英国革命的专家会自然地对西欧其他一些国家——像法国和荷兰——感兴趣,这些国家在同期也经历着自身的危机,但他或她有关这些国家的知识或许仅凭借对二手文献的阅读——令人遗憾的是,在许多情况下,仅包括英语和其他一种欧洲语言的文献。仅有少数历史学家能对一个以上国家或时期有直接的研究。”②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第98、103页。可以说,语言成为跨文化、跨地区、跨国家、跨民族等宏观历史研究的障碍之一,除去使用翻译材料(应当属于二手材料),很难寻找到更好的解决之道。
其次,史学家的专业分工过细,研究范围过窄,只能借用二手材料编写全球史,乃至编写地区史、国别史,一些专题史等的情况也相同。“一位史家往往终生集中于一个时段和一个国度,甚至一个国度中的一个专题。”③郭小凌:《西方史学史》,第311、312、34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位史家精通近代就不能精通古代,精通古代某个国家便不能精通一个地区,甚至精通某个国家的一个局部就难以精通这个国家的历史情况也出现了。”④郭小凌:《西方史学史》,第311、312、34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专业史学家(professional historians)群趋于选择极小的研究范围,作细致深入的研究,研究范围以外的世界,不去闻问;欧洲以外的历史,视为洪荒未开,不加理睬,以致历史研究呈现猵狭与见树不见林的现象。历史的贯通与宽广不见。”⑤杜维运:《史学方法论》,第291页。就这点而言,区域史、国别史的编写也不例外。
事实上,单个史学家要弥补以上两大或其中之一的局限都是困难重重的。借用二手材料编写全球史、区域史、国别史等是明智之举和当然选项。
第三,宏观历史研究面对的历史材料,甚至只是原始材料都极大地超出了史学家的掌控能力。不借用,宏观历史研究只好纸上谈兵。
自北宋的毕昇创造了泥活字印刷术、尤其是德国人谷登堡开发了铅活字印刷术、为人类文明史的记载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技术支持后,历史材料的增长速度令人瞠目结舌,巨大数量使人目眩头晕。无限的材料变成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给历史研究提供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材料;另一方面,也给史学家带来收集和把握材料的巨大困难。
表现之一就是,史学家已经无法掌握稍大一些研究课题的全部材料,甚至只是原始材料。“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来说,很难有一部令人满意的传记,原因在于:他们的早期经历和他们作为教皇的多方面影响经常遍及整个欧洲,记录他们的档案资料之多是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无望全部掌握的。”⑥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第98、103页。“对于英国史的相当长的时期而言,探究者所得到的文献名单和目录他一辈子都不可能看完。”⑦G.R.埃尔顿:《历史学的实践》,第57页。史学家汤象龙主张历史研究要尽全力搜求史料,以使研究能得到最“充分的史料”。他以“中国近代经济史为例,说明史料搜集的范围除了一部二十四史和几千部地方志以外,最起码还应该包括明清两代中央政府档案、各地方政府卷宗档册、以及农民或家庭的流水账、店铺的生意账和公司的营业账等各种不同的账簿。汤氏以为只有透过这类型的资料,才可以如实地考察出当时各地的农民经济、物值、生活程度、工商发达的情形和社会组织等实况”⑧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第243页,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阿克顿爵士(1834—1902)是公认的英国近代史家中最渊博的学者。“他在个人治史实践中竭尽全力收集原始文献材料,《自由史》没有动笔的一个原因是他认为史料不全,而别的史家在他已经收集的史料上也许可以写出十几部书了。”⑨郭小凌:《西方史学史》,第311、312、34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仅仅只是一位教皇的传记或英国史的相当长的时期、仅仅只是中国近代经济史,史学家试图掌握全部材料或者原始材料的做法,在史学实践中,已经难以做到。因此,阿克顿爵士坚持收集全部材料的完美主义倾向,注定无法动笔。
表现之二就是,史料种类的扩展,数量的巨大,增大了史料鉴别技术的难度,史学家必需掌握十分严格的专业技术甄别。“历史资料包括人类在过去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各种证据——文字资料和口述资料,地貌和相关的人工制品,美术作品及照片和电影。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历史学的原始资料种类是最繁多的,每种资料都要求专门技能予以鉴别。……单个历史学家不可能掌握对所有这些资料进行分析的技术。”①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第50-51页。“在史料整理的实践中,史学的辅助学科碑铭学、考据学、纸草学、钱币学、校勘学、版本目录学等得到进一步发展。到19世纪末,欧美各大学的史学专业中已将辅助学科作为常设的课程。”②郭小凌:《西方史学史》,第311页。“19世纪以后,西方盛行利用语言学与文字学、古文字学、古文书学、印章学、徽章学、泉币学、族谱学(即氏族学)、年代学、地理学等历史辅助科学,以进行历史研究。”③杜维运:《史学方法论》,第139、84页。实际情况是,这些辅助学科及其专门技能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成为一位史学家的毕生事业。
表现之三,史学家面对大量的二手著作已是手忙脚乱,无暇顾及原始材料。19世纪以来所出版的历史著作与历史论文,比兰克那个时代“多出不知多少倍。如果在兰克的年代,人们还能仅仅根据原始材料写作历史,那么到了现在如果人们还照此办理,那么观点雷同、史料重复之处就无法避免。如此这般写出的著作非但了无新意,而且还有抄袭、侵犯别人知识产权之嫌疑。……史学家在大量的著作面前无所适从,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所谓注重第一手史料的运用,也就成了一纸空文。每个史学家都是在前人研究已经构成的论述上,稍稍发挥,略作补充或者修正,以形成尚可以称为是自己的看法。换言之,虽然历史学家以追求历史的真相为自己的崇高责任,但其实,他们忙于应付那些二手著作还来不及,没有多少时间去亲近历史的‘真相’。只是不断提出新的论述和解释,以求不与已有的观点相雷同”④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第18-19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每一史学家必须接受大量的第二手的判断(second-hand judgment),不管他如何力求富有批判性(critical),因为他不可能为自己鉴定历史上的每一单独‘事实’。”⑤杜维运:《史学方法论》,第139、84页。费正清每次修订《美国与中国》一书时,总是“深感新的学术成就如潮水般地涌现,以致在我试图利用它们来充实本书内容时,有时感到应接不暇”⑥胡大泽:《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第156页。。
从现实层面看,人类社会总是需要宏观历史研究成果来适时地实现史学的社会功能,并且不大在意史学界准备得如何;从学术层面看,单个史学家难以弥补语言阻隔和专业分工太细的局限;面对巨量的原始资料和专门的鉴别技能已经无法掌控,面对时人与前人的大量研究著作也是读不胜读。现实与学术的交集,意味着单个史学家借用二手材料进行宏观历史研究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必须的做法。形势强于人。完全依据原始材料的历史研究,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尽管其基础性、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马克·布洛赫曾强调说:“人的能力有限,不可能就过于广泛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的史实进行第一手的科研工作。严格意义上的比较工作最终将成为一小部分历史学家的专职。”⑦转引自范达人、易孟醇:《比较史学》,第278-279页,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面对此情此境,宏观历史研究要么选择借用二手材料,要么选择放弃研究。既然如此,还是着力解决怎样借用二手材料以及如何借用得当为宜。
三、宏观历史研究借用二手材料的界限
宏观历史研究借用二手材料是必需的,并不是说这种借用是随意的。需要严格限定其借用范围,明确其界限,才能讲借用得当的问题。
随着时代变迁,每一时代都会面对新的社会环境和问题。宏观史学家总会在新材料、新理论、新思维、新方法、新观念等的指导下,重新解读历史,获得新的历史认识成果,表现出良好的历史修养,站得高、看得宽、想得深。史学实践表明,单个史学家借用二手材料,主要适合于三个宏观领域:宏观历史理论和历史思想探索、宏观历史比较研究和大型综合类史书的编撰。超出这一界限,借用不但适得其反,而且将极大损害历史学求真求实的根本原则。
第一个领域:宏观历史理论和历史思想的探索。
历史学是一门材料与理论相交融的学科。“史学家必须寻求通则,不然,历史将流于枯燥的编年史。……离开通则,无法工作。”①杜维运:《史学方法论》,第171页。历史理论和历史思想的探索需要对大范围的历史研究成果进行抽象,寻求通则。这就需要有效地借用二手材料,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借用有助于一些擅长理论思维的历史思想家和史学家不必受困于原始材料,以便节省时间和精力,从事高屋建瓴式的理论研究,获得历史思想成果。这类事例并不鲜见。
“孟德斯鸠(1689—1775)利用的史料规模极为庞大,其中大半出自古希腊和罗马史家、哲学家的作品,小半来自当时已知的世界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积累的有关知识,包括阿拉伯、印度、土耳其以及欧洲人刚有皮毛了解的中国、日本、美洲等国家和地区。这种重古代的作法并不是出于崇古好古,而是由于当时积累的不同时代的材料状况。比如,《论法的精神》讨论的重点是政体与法的关系,由于古希腊和罗马曾是政体的共时性实验场,各种政体应有尽有,并且古希腊罗马人对不同政体进行过深入、细致、全面地比较研究和理论总结,积累起其他时代、其他地区以及其他民族无可比拟的大量现成论据和论点。孟德斯鸠广泛运用古典史料就不足为奇了。其书中几乎援引了所有幸存的著名古典作家的作品。古典著作不仅是他的主要史料来源,而且是他的观点的重要借鉴。”②郭小凌:《西方史学史》,第221-222页。
伏尔泰(1694—1778)《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是一部从古代世界延伸到伏尔泰时代的世界史,突破了基督教的世界史体系和政治史传统,独具创建。作者在书中努力要表述这样一个有意义的主题: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已逐步摆脱了偏见、迷信和奴役,尽管他们遇到无数次的错误和失败,但总是向着理性、公正,向着物质和精神不断改善的方向前进的”③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第15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是一部历史理论名著,主要材料来源于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和马克思对《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详细笔记。该书揭示了原始公社制度解体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的形成过程、国家的起源和形成,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私有制、阶级、国家都是经济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阶级国家最后不可避免地要消失,至今仍然具有指导历史研究的积极理论意义。
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以较大篇幅分析研究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又重点研究了建立在这种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中国正统文化——儒教伦理,同时还考察了道教。他对儒教与西方的清教加以比较,得出了一个结论:“儒家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④韦伯:《儒教与道教》,“出版说明”第2页,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韦伯自己说,“在写这些论文时,使用的资料都是翻译过来的”⑤韦伯:《儒教与道教》,“作者说明”第1页。。
周谷城的《世界通史》强调,世界是一个多元的有机整体,“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需要“特别着重世界各地相互之关联”。此书另外两个值得重视的史学观点是,“打破了先前世界通史几乎一以贯之的‘欧洲中心论’思想”,“而是以相当大的篇幅叙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力求从世界历史总体的研究中揭示历史发展进步的内在规律”⑥姜义华、姜玢:《世界通史》,见《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第264-26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引用了十几位专门研究古代中国的美国汉学家的成果,但总的目的是由此论证他自己的观点,即‘今天的中国革命和国共两党的战争,是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直接的产物’”⑦胡志宏:《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第35-36页。。
黄宗智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使用的史料,主要出自20世纪30年代人类学家实地调查的资料,尤以‘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研究人员,在华北平原33个自然村实地调查的资料为主。该书作者又于20世纪80年代亲自去访问了两个村庄,通过实地调查来核对和补充了一些资料。作者并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了有关资料。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对近数百年来华北(重点是冀—鲁西北)农村的演变模式的一些看法”⑧胡大泽:《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第175页。。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从社会史的角度谈及村落与国家的关系,并向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范式和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发起冲击,其最为重要的资料来源便是满铁”《中国农村惯行调查》。①胡鸿保:《中国人类学史》,第93页。
以上诸位历史思想家或史学家通过或主要通过借用二手材料,得出了富有启发性的宏观历史结论、观点和见解,无疑是值得肯定和赞许的,更需要认真总结其示范性经验。
第二个领域:宏观历史比较。
历史比较研究,指运用某种理论和方法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现象进行异同及原因的实证辨别。它是认识历史的最重要最普遍的手段之一。“纷纭庞杂的史料,归纳在一起,不经过比较,无法看出每一种史料所代表的特殊性质以及史料与史料间详略异同的所在;历史上林林总总的现象,上自整个学术文化的变迁,下至林泉牧夫樵叟的咏歌,不经过比较,无法看出每一种现象所具有的真正意义,历史的变动性,将不可见,古今的融合,中外的沟通,也不可能。”②杜维运:《史学方法论》,第64页。按照历史比较范围的大小,可以划分为宏观历史比较和微观历史比较。宏观历史比较,“就是指站在历史整体的角度,对不同的历史现象进行贯通的或者高度概括性的比较研究”③赵吉惠:《历史学概论》,第277页,三秦出版社1986年版。。
宏观历史比较古已有之,在启蒙时期取得了较大进展。伏尔泰试图建立普遍的历史图景,“同号称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决裂了,他不仅叙述了欧洲史,而且叙述了亚洲各民族的历史,中国、印度、波斯和阿拉伯人的历史。……孟德斯鸠对古代希腊、罗马、叙利亚、埃及、中国及欧洲各国的历史具有深湛的知识,并对它们作了比较研究,因而能够就地理环境对世界历史过程及不同文化类型各自的历史特点所产生的影响作出最广泛的概括”④麦尔高尼扬:《社会科学中比较研究的发展阶段》,见项观奇:《历史比较研究法》,第6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随着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的交流活动日益增强,那种自我封闭、自我孤立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20世纪以来,史学家为了获得系统的历史认识,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因素或规则等,更加需要全球视野,对世界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进行宏观比较研究成为研究重点之一。
无论比较的地域广度还是比较的问题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世界文明体系的比较。它基本上是通过借用二手材料来进行的。因为,史学家要熟悉任何一种文明都是困难的,遑论对世界上7种、8种乃至更多的主要文明进行比较了。
奥斯瓦尔德·史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提出,“人类历史不外是诸种文化自行生长、衰亡的舞台。这些文化被史本格勒分成八种,即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希腊罗马)文化、玛雅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欧文化。它们自成体系,‘同时’演进,经历大致相似的从乡村到城市、从文化到文明的过程。这就是以后风行一时的‘文化形态史观’。这种观点从内容上来说,体现了一种宏观的研究历史的态度,打破了以西欧为中心的理论框架,反映了西方文化从中世纪走向现代,从一元走向多元的发展”⑤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第167页。。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共12卷,于1934—1961年出版。本书“少诗意的幻想,更多对实际材料的阐明。他认为历史学研究的最小单位是‘文明’,6000年文明史被他分为26个文明。他据此提出了一套以分析文明循环、发展、衰落为基础的历史哲学,以及一套与之相应的观念,如环境的‘挑战’与人类的‘应战’等等”⑥何兆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67页。。亨廷顿认为,冷战后,全球政治成为多极和多文明的。冷战后的世界是由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所构成的。它们是: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对多文明的比较,“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⑦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第3页,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此外,史学家还通过借用,取得了众多的其他宏观比较研究成果。
艾森斯塔德的《帝国的政治体制》,区分了“帝国体制的两个类型——一种是世袭制王国,如古埃及王国、印加、阿兹台克或众多的南亚王国;另一种是很大程度上已中央集权化的官僚制帝国,其最为重要的例证是中国、罗马、拜占廷、萨桑和伊斯兰教哈里发诸帝国;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印度的孔雀帝国和芨多帝国,以及欧洲早期的绝对专制主义政权。”①艾森斯塔德:《帝国的政治体制》,“中文版导言”第1页,沈原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艾森斯塔德所赖以比较的材料就来源于众多学者的提供。“下列诸君在有关不同历史素材的问题上对我有所助益:J.普罗维尔教授(关于拜占廷历史)、W.埃伯哈尔德、A.赖特、E.巴莱兹诸教授和D.蒂维凯特博士(关于中国历史)以及W.布里哈教授(关于西属美洲的历史)。我还愿向那些在搜集和准备作为分析基础的素材方面给予帮助的诸君谨致诚挚的感激之情——尤其是准备关于英格兰素材的O.夏皮罗先生、准备中国唐代素材的R.巴雅塞夫人、准备中国素材表格的Z.施伏林博士以及准备法兰西素材的J.米勒夫人。我应犹为感谢埃立克·柯亨先生,他组织并督促了对表格中所表述的历史素材的准备与分析,他本人则分析了印度帝国的素材……”②艾森斯塔德:《帝国的政治体制》,“序言”第5-6页。
巴林顿·穆尔的《前工业世界向现代世界过渡的主要历史途径》,艾里克·沃尔夫的《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都是“建立在第二手资料以及有关专题论著的基础上的”③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79页,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小巴林顿·穆尔的《独裁与民主的社会根源》、萨达·斯哥克波尔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弗兰西斯·V.莫尔德的《日本·中国与现代世界经济》、罗伯特·布伦尼尔的《工业革命前欧洲的农村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以及加里·G.汉密尔顿的《国外商品中的中国消费:一种比较观》”④萨达·斯哥克波尔、玛格丽特·萨默斯:《历史比较在宏观社会研究中的作用》,见项观奇:《历史比较研究法》,第169-170页。等,也是借用二手材料的结果。
由此可见,不借用二手材料,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宏观历史比较研究。没有宏观历史比较研究,人类的视野将会何等的短浅、窄小与猵狭。“惟有比较方法可以减少史学家间种族的、政治的与国家的偏见。史学家局限于国家民族史的狭小范围内,其种族的、政治的与国家的偏见,不可避免的使其陷于泥淖之中,无法真正了解所研究的历史,因他无法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相会通。”⑤杜维运:《史学方法论》,第245页。
第三个领域:大型综合类史书的编撰。
历史研究总是处于一个个别、部分和整体的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形成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研究成果。史书是这些成果最为集中和常见的表现形式之一。在众多史书中,大型综合类史书(在历史理论的指导下,将分门别类的历史内容组合成一个整体)最能引起学界和社会大众的共同关注,其中通史、断代史与专门史是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形式。
史学家编撰通史、断代史与专门史,都面临着无穷的原始资料、跨度大的历史时间和复杂的历史内容。重起炉灶的做法不仅割断了史学的联系,还否定了史学的积累,更有轻视前人和时人劳动之嫌。只有全面、充分、合理地借用二手材料,才能进行大型综合类史书的编撰。这在史学实践中被证明是可行的和有效的。
“《四洲志》系根据英人慕瑞《世界地理大全》译出,叙述了世界三十多个地区和国家的历史、地理概况,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较有系统介绍世界史地的译作。”⑥吴泽:《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册,第119、124、14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魏源于1843年编成《海国图志》。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纂的世界史地志。“书中所征引的资料虽达近百种之多,其中外人著述仅有二十种左右,但在介绍各国史地情况,用的最多的正是这些书。尤其是英人马礼逊《外国史略》、葡萄牙人马吉斯《地理备考》,几乎是每卷都引用的。在介绍美国时,高理文之《美理哥国志略》差不多大部分被采用了,且特别冠于篇前。本书百卷本末之世界各国地图也是采自香港‘英夷公司’所呈之大宪图。”⑦吴泽:《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册,第119、124、14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徐继畲的《赢环志略》,“全书四十二幅地图,除日本与琉球一幅取自中国有关资料外,其余都是从西方地图册中钩摹的。在当时中国刊印的外国地图中,可以说是最好的。书中所征引的资料除以西方各国资料为主外,还引用了二十多种中国著作”⑧吴泽:《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册,第119、124、14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柳诒徵编写的《历代史略》,由江楚书局1903年印行,为中国近代第一部章节体历史教科书。全书共6卷8册,上起唐虞三代,下迄明末。从上古至宋代,以日本学者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为蓝本,稍加增易而成,有的只是改动了标题。……元朝和明朝两卷,为柳诒徵所增辑”⑨吴泽:《中国近代史学史》,下册,第155页。。
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史》(1585年,用西班牙文出版)是16世纪欧洲人研究中国集大成之作。“其资料来源不仅有巴洛斯的《亚洲史》、拉达带回的中国书籍和拉达的长篇使华报告,还有两部欧洲研究中国的重要书籍,艾斯卡兰蒂的《葡萄牙人航行世界东方记》和克鲁兹的《中国情况记》等均是其利用的资料。”①潘玉山、陈永刚:《中西文献交流史》,第3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吉本(1737—94)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震惊18世纪史学界的杰作,但是他在政治上、道德上与宗教上的主要观点,是来自伏尔泰的。”他将十七八世纪的博学者所做的极多精湛的专题研究,“一一综合以后(他遍读前人的学术论文,极少十七八世纪博学者的大名,从其附注中消失),于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历史巨著,便幡然问世了”②杜维运:《史学方法论》,第88页。。日本学者那珂通世(1851—1908年)的《支那通史》(1888年出版),选用材料,不限于中国古籍,而且兼用西洋人所录资料,值得注意的是它打破了中国史书的传统体例,而采用西方“通史”的体例,开始脱出以帝王为中心的王朝事件的叙述,而试图描绘历史的演进和发展,这在中国史研究上是一次重大革新,对此后的中国史研究有很大影响并备受好评。③何寅许光华:《国外汉学史》,第325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剑桥插图中国史》的作者自己说:“本书的大多数思想都得自他人。”“我也依赖了一些并非为一般读者所写的专业性研究成果。”④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致谢”,赵世瑜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
从周谷城为其《世界通史》所列的书目中可以看出,“作者广泛地利用了12卷本《剑桥古代史》、8卷本《剑桥中古史》、14卷本《剑桥近代史》,汤因比的12卷本《历史研究》、斯密兹的25卷本《史家世界史》。威尔斯及海斯的著作也在利用之列。作者还使用了一大批原始文献,相当一批断代史及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及国际关系史方面的专门研究著作。这就使本书能够广泛吸取世界通史及断代研究、专史研究的已有成果,具有相当高的起点”⑤姜义华、姜玢:《世界通史》,见《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第264-265页。。
屠寄(1856—1921),花费26年之精力撰成《蒙兀儿史记》,“其广征博引,排比中西史料,取众家之说熔于一炉,为后人研究蒙元历史提供了条件”。该书的史料来源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广泛搜集中国史料,特别是对元人文集运用得较充分。第二,在前人(以洪钧为代表)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外国蒙元史研究资料。……参考征引的前人从未引用的西文书籍主要有四本:一本是美人乞米西亚·可丁《蒙古史》三册,“命第三子孝实译出。”“另一本国人所英著《史家之历史》,由第四子孝宦译出”。“第三本为俄国人著《蒙兀泉谱》。”还有一本是德国人著《元代疆域图》,系日本人重野安译出。”此外,还采用多种国外资料。“第三,吸取了当代史地学家的研究成果。”⑥吴泽:《中国近代史学史》,下册,第313-315页。
类似实例甚多,不再赘引。通过以上三个领域借用二手材料的简单叙说,至少可以明确这样一个事实:在宏观历史研究中,单个史学家不但必需借用二手材料,而且可以做到很好,并取得积极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是值得重视和尊重的。正如“沃尔夫、帕尔墨和前面提到的历史学家所进行的全面完整的世界史研究,以及托因比的著作,……大致代表了这样一类学术水平,即既有能力进行历史综合,同时又不至于降低学术性,更不会遭致谴责而被斥之为肤浅或抽象的系统化”⑦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80页。。
四、宏观历史研究借用二手材料的史学意义
在史学实践中,缺少宏观理论、思想、概括和比较的历史研究,缺少宏大叙事,很难得出具有广泛意义的历史结论,这肯定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如果不允许借用二手材料,我们的历史研究、历史著作与历史思想将会是如何地贫乏和无趣。
宏观历史研究借用二手材料既是必需的,又有三个适用领域,并取得了积极的研究成果。那么,其史学意义又何在呢?
第一,宏观史学家通过借用二手材料,归纳并抽象出历史理论和方法,有助于综合性地观照历史,深刻理解历史过程以及重大变迁,探索历史的潜在因素以及背后的奥秘等。
孟德斯鸠、伏尔泰、恩格斯、韦伯、斯宾格勒、汤因比、亨廷顿等均是借用二手材料的成功者。就此而言,二手材料功不可没。
韦伯“虽不懂汉语,在中国研究资料方面依赖于精通汉语的汉学家,但他以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这种新型文化认知法阐述中国社会,使人们深刻理解中国社会中的文化特殊性”①何寅、许光华:《国外汉学史》,第228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韦伯虽然不懂中文,但是他通过西方资料研究过中国的宗教和官僚政治的实质,在文官制度主题方面,他从组织和宗教宣传及其相互关系揭示了中国皇帝制度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本质。”②胡志宏:《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第129、93页。“虽然韦伯不懂中文,但是汉学家常引用他的研究和结论。”③胡志宏:《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第129、93页。“托因比拓宽了历史学家的视野,使他们看到了使用比较方法的潜在前景。……实际上,这为解决世界历史中的问题也为探索历史的意义和规律提供了当前普遍适用的方法,而且正是在这个领域中,完成了一些最富有推动意义的工作,即使这样的推动有时仅仅是批判和抵制,而不是赞许和承认。”④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68、278页。“艾里克·沃尔夫用墨西哥、俄国、中国、越南、阿尔及利亚和古巴的事实为基础对20世纪的农民战争所作的研究”,“因为使用了社会科学的工具,因而造成了研究方法和观点上的重大进展”⑤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68、278页。。“魏源的《海国图志》标志着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质的飞跃。传统学术的格局开始被突破。在史书内容、著书旨趣和哲学指导思想上都灌注进具有近代意义的新东西。”⑥鲍绍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第28页,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正是借用二手材料所取得的理论突破与方法创新,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为探索历史的意义和法则提供了更加开放性的理论与方法。
第二,历史需要解释,尤其需要多样性解释。开放性的理论与方法使历史多样性解释变为现实,极大地增强了宏观历史研究解释历史的能力,为历史服务于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历史解释,就是阐明历史发展的轨迹、含义、原因、理由及其意义何在等,“究其实际,则是对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所作的疏通陈述”⑦杜维运:《史学方法论》,第164页。。“解释是将呈现在眼前的事赋予意义(Deutung);是把呈现在眼前的资料,将它所蕴涵的丰富的因素,无限的、打成了结的线索,松开、拆清。经过解释的工作,这些交杂在一起的资料、因素,会重新变得活生生,而且能向我们倾述。”⑧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第33页。
“伏尔泰受启于入华耶稣会士的著作,从儒家思想中找到了世俗的理性精神,并以此作为反对宗教愚昧的根据和理由。莱布尼茨是《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的忠实读者,白晋给他的《康熙皇传》深深地打动了他,使他认为康熙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帝王,并从白晋所寄的有关《易经》的材料中,找到了可以证实自己所发现的二进制的内容。孟德斯鸠则从这些文献中得出了另一个相反的传论,认为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尽管是专制政体中最好的国家。”⑨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第344页,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
周谷城的《世界通史》“广泛地运用了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正如他在论述这一方法的优点时所说:“比较研究,将彼此不同的事物进行参照对比。这样做,可以使我们不致产生一些不应有的偏见。通过比较研究,较易看到:从古代到中世纪,亚、欧、非三洲有些政治势力的发展,存在着由分区并立向往来交叉发展的趋势。比较研究,还有助于认识各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文明的特征,哪些大体相似,哪些极不相同。此外,历史的发展虽有阶段可循,但中外发展仍旧存在着许多地区、时段的不平衡,把不同国家对比起来看,就较易看清楚这些特点。”⑩姜义华、姜玢:《世界通史》,见《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第270-271页。
《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没有声言自己采用了什么研究方法,但实际上他对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多种方法,如文明模式理论、地缘政治理论、文明交流理论、长时段和宏观历史理论等,都了如指掌,应用娴熟,从而为读者构建起一幕幕雄伟的历史画卷。不同领域的读者可以从《全球通史》的不同侧面,汲取不同的知识、观点和方法,这就是一本历史学的巨著应该做到的”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第7版推荐序”第5页,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布莱恩的《世界简史》是来自南洋的世界史书,既不同于东洋的也不同于西洋的,“在学术上无疑是有意义的”。“本书从结构到内容,在克服上述两种倾向方面,都做了很大努力,对大洋洲文明的重视就是一例。”⑫杰弗里·布莱恩:《世界简史》,“译序”,何顺果等译,国际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
《剑桥插图中国史》“为了避免外国学者阐释中国历史的局限性,作者尽可能地参考了中国各界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走向的阐释”①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封2”、“译者后记”。。此书“是为英语世界的普通读者写的,因此它并不是一部学术性很强的历史学著作,但是它却是在大量学术著作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概括而成的,因此明眼人可以从书中发现,它的观点使人耳目一新。读完本书后的感受是:它与我们从小就熟读的历史教科书有许多不同,与我们今天在大学历史系的课堂上讲的东西也有许多不同”②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封2”、“译者后记”。。
我们可以质疑,可以商榷,可以反驳以上的观点和结论;但是,没有宏观史学家的积极探索,历史解释要么严重缺失,要么僵化单调;没有多样化的历史解释,历史的固有魅力被消解,史学社会功能又从何谈起呢?
第三,因为历史理论的抽象、史学方法的创新、历史解释的多样化,不少宏观历史著作在一定时期内受到了学界与社会的欢迎,甚至是热烈的欢迎。
历史学是一门自觉服从和服务于社会的学科。“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③罗银胜:《顾准传》,第556页,团结出版社1999年版。“历史的研究,除了当作一门客观独立的学问研究以外,是有着巨大的实用价值的。不只鉴往以知来是人类学习的一个最大的泉源,而且客观地了解别人的历史以及自己的历史,才能训练我们自己培养成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不把自己的行为建筑在主观的空想、情感的反应与错误的估计之上,这样当然会产生比较好的效果。”④刘述先:《研究中国史学与哲学的方法与态度》,见韦政通:《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第172页,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最早于1585年用西班牙文在罗马出版,随后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而且每一种文字都有好几个版本。比如西班牙文有11种版本,意大利文有19种版本,英、法、德分别也都有多种版本。总之,到16世纪末,《中华大帝国史》以7种不同的欧洲文字重印46次之多,风靡整个欧洲汉学界。”⑤何寅、许光华:《国外汉学史》,第50、84 -85、623 页。基歇尔是17世纪著名的学者,是一个从未去过亚洲的神父。他的《中国图说》于1667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是书1986年英文版译者查尔斯·范图尔说,在“该书出版后的200多年内,在形成西方人对中国及其邻国的认识上,基歇尔的《中国图说》可能是有着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著作”⑥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第297页。。1735年,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尔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在巴黎出版,“第二年在海牙出第二版,不久,英、德、俄译本相继问世”。“对当时文化界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是欧洲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了解中国的主要资料来源。”⑦何寅、许光华:《国外汉学史》,第50、84 -85、623 页。伏尔泰《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从内容和方法都属全新的作品一问世,即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欢迎。仅在1756—1768年这短短的10多年中就再版过16次”⑧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第150页。。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汤因比的声誉“自英伦三岛,洋溢寰宇。在美国,他变成大众人物(a public figure)。在中国,史学界人人知晓其人(纵使不知其学)。其书畅销世界各地,为出版商的营利保障。英国、美国、加拿大较具规模的新旧书店里,《历史研究》一书横陈”⑨杜维运:《史学方法论》,第290-291页。。20世纪50年代后期,汤因比的声名仍如日中天,“是台湾岛上五十年来知名度最高的外国史家。汤因比在台湾受到重视,主要是由于这位史学家从50到60年代间先后在美国和日本走红,影响及于岛上,奉为大师,尊礼有加”⑩汪荣祖:《史学九章》,第39页,三联书店2006年版。。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自1970年初版问世以来,赞誉如潮,被译成多种语言流传于世,可谓经典之中的经典”。“本书享誉世界几十年,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齐名,但比《历史研究》通俗易懂。与《梦的解析》、《广义相对论的基础》、《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时间简史》等并列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封4”。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已被翻译成22种不同的文字,并具有相应的影响”⑫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第1页。。
日本著名学者贝冢茂树(1904—87年)在中国通史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是《中国历史》上中下三卷。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基础教育读本,在日本有很大影响。这部通史,从“三皇五帝”一直写到孙中山、毛泽东,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⑬何寅、许光华:《国外汉学史》,第50、84 -85、623 页。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到1947年,已经印行到第十版。50年代与80年代都曾一再重印,至今在台湾、香港、东南亚、日本和美国都常被列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参考书。”①姜义华、姜玢:《世界通史》,见《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第262页。
“梅则雷(1610—83)是当时法国最受欢迎的历史家。他的《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第1卷于1643年问世,不久之后就再版两次(1646,1651年);全部著作三大卷完成后,1685年又需要出第2版了。……迟至1830年还出了一版。”“他是一位编纂家,他的资料主要是第二手的。”②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第44页。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于1946年发表《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运用文化与人格理论对日本的国民性作了独特的分析,是一部对民族性与文化间关系作具体研究的名著。“1951年此书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至1963年已重印三十六次”,影响至今不衰。③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译者序言”第2页。
当这些宏观史书出现了流行、风靡、受欢迎、多次重印等情况,说明它们发挥了较好的社会作用。这是值得继承并发扬光大的好事。
五、宏观历史研究借用二手材料的风险及防范
历史材料的使用,受到时代的、政治的、民族的、阶级的、史学家个人等诸多因素影响,呈现异常复杂的情况。宏观历史研究借用二手材料尽管是必需的,并将持续下去;但是,按照现代史学的要求,二手材料终归是间接的、次要的,借用必然具有较大风险。所谓风险,即借用二手材料潜在着损害宏观历史研究的诱因。单个史学家如能在以下三个方面积极努力,还是有希望减少这种损害的。
第一,宏观史学家更需要建立起研究目标服从于史料的自觉意识,其他的做法都只能是南辕北辙。
历史学家“至少必须自觉自愿地根据源于资料的问题来修正最初的目标。没有这种灵活性,历史学家就会冒欺骗性地使用证据资料以及未能充分挖掘资料潜力的风险。真正掌握这门技能的是这样的人,他们认为,所能提出的问题会由于以后在研究中遇到的各种资料而改进”④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第78页。。
“在方法上,吉本则常以史料为我用,胜于史料的考定。他在叙述波斯贵族的那章中,引用了不少古今资料,认为人性是一样的,所以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人与公元后3世纪的波斯人,没有两样。吉本于此断不同时代之章,假古道今,不免有违历史的特殊性格,而‘时间错乱’(anarchronism)乃史家大忌。公元3世纪中叶史料尤少,……然而这一段历史,却是自罗马帝国转到拜占庭时代的关键时刻,吉本处理史料短缺的方法乃是:环顾断片残简,都很简短,往往语焉不详,有时矛盾抵触,作史者惟有取之,比而观之,而后猜测;猜测固不能视为事实,然有时只好以人性知识,以及强烈而难以驾驭的热情,来弥补史料之不足。由此吉本以人性与热情,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和事件。”⑤汪荣祖:《史学九章》,第9、44页。汤因比“生在英国,受到完整的西方教育,而完全没有中国学问的根底,连汉字都不识。他要研究世界文明,不能不涉及中华文明。而这一方面的知识,只能依赖欧美汉学家的一些著作,以及胡适等中国学者的少数英文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西方汉学尚未真正的学院化,可依赖的研究成果实在不多,因而汤氏写《历史研究》时,所能掌握的中国历史文化资源十分有限。他只能捡取可资利用的二手材料,来适应他的理论,根本不能掌握不利于其理论的资料,以至于挂一漏万,顾此失彼,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情况,所在多有;‘以论带史’(he forces the facts to fit his theory)的情况,亦颇显著。”⑥汪荣祖:《史学九章》,第9、44页。“人性知识”无法弥补史料之不足,“为我所用”和“以论带史”更是触犯了历史研究必须尊重史料的大忌。
第二,历史材料愈全面,犯错误的机率就愈小。单个史学家进行宏观历史研究必须坚持掌握和运用全部材料的史学基本原则,尽管难以做到。这始终是保证宏观历史研究成果学术可靠性与发挥社会作用的根本所在。
“单个的工作者绝不可能把握比较分析必须立足于其上的一切社会的全部原始资料。因此,该工作者必须主要地依赖第二手资料。他必须充分地熟谙这些领域内的史学研究,并且知晓史学家之间的不同争执,以便能够评估这些争执,谨防过于轻率地使用任何材料或观点,并且明了按照他所分析的问题和所使用的范畴而能够对这些资料加以分析的范围。”⑦艾森斯塔德:《帝国的政治体制》,“序言”第2页。
例如,法国历史家路易·阿道夫·梯也尔(1797—1877)用了20年的时间撰写了《执政府和帝国史》,“拿破仑时期的历史虽说就是全欧史,但梯也尔却未曾使用任何外国资料”。因此其书“受到严厉批判。他了解德国很少,了解英国就更少。……外国档案和印刷史料,他一无所知。像马姆斯伯里、福克斯、卡斯尔累、韦林顿这样一些著名的英国人已经出版的回忆录、日记、急件和书信,他一点都没使用;反而从法国官方杂志《导报》中去搜罗一鳞半爪情况;而这份《导报》刊登的东西都是拿破仑批准刊登的。难怪英国人对梯也尔这部历史著作的批判是无情的。‘他对我国政府的误解与对我国文献的无知一无二致’”①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第339-341、111 页。。梯也尔不能全面审视材料,“未曾使用任何外国资料”,没有“立足于其上的一切社会的全部原始资料”,不仅未能达到编写全欧史的目的,反而招致严厉批判。这是足以让宏观史学家引以为戒的。
第三,宏观历史研究借用二手材料,必须严格遵守历史学术规范,标示出处。
历史学术规范是史学界从事研究工作的基本规则。宏观历史研究非但不能例外,还因其所存在的风险而更应严格要求。宏观历史研究只能借用经过时间的和学术的严格检验后的二手材料,说明借用的充分理由,指明来源,标明出处,才能取信于学界,才能在历史研究中立于不败之地。
吉本曾说:“在我未能得到机会参阅原始材料的少数情况下,我便采用我信得过的近代先行者提供的证据;但在这些情况下,我并不把提厄蒙或拉德纳那些光彩夺目的美羽搬来装饰自己的门面,而是非常谨慎而准确地标出我所参阅的范围和材料来源。”②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第339-341、111 页。周谷城的《中国通史》重版时,对于“新发现的文物、文献、以及史学研究的新成果,限于本书的体例,修订时未能采用。将来如有机会重新改写,当设法弥补这一缺憾。……引用资料,一律注明出处,以便读者复核和进一步的钻研。”③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第二次修订重版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本尼迪克特是在日美交战的情况下,“利用文化人类学家最倚重的方法——与被研究的人民直接接触。在我们国家中,有许多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我可以询问他们亲身经历的许多具体事例,发现他们如何进行判断的方法,根据他们的叙述来填补我们知识上的许多空白”。此外,她继承了许多研究日本的学者的遗产。“在嗜古好奇的文献中充满了生活细节的描述。欧美人士详细记载了他们的生动经历,日本人自己也撰写了许多不寻常的自我记录。”“还看了不少在日本编写、摄制的电影——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描写东京及农村现代生活的影片,然后再和一些在日本看过同样影片的日本人一起仔细讨论。”④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第4-6页。“诚实”地交代和标识所借用二手材料的来源,是宏观历史研究得到应有尊重的基本前提之一。
宏观历史研究借用二手材料必须有助于新理论的提炼、新方法的建树和新见解的提出。没有新意的借用,就是滥用。宏观史学家只有坚持研究目标服从于史料的指导思想,坚持“重新来一遍”材料的史学基本原则,“一天的综合需要有多年的分析”⑤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四分册,第509页。,坚持规范地标示所有史料和思想出处,才能有效地防范风险。这对宏观历史研究的合理运用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宏观历史研究是因应社会的需要,史学家主动寻求史学出路的选择之一,而全球史等的兴起与无限的材料均极大地超出了史学家的掌控能力。三者交集,借用二手材料也就在情理之中。史学实践表明,借用应当严格限制在以上所论的三个领域中,才可能取得相应的创新性成果。这些成果,取得了整合微观历史研究成果的效果,具有开放性和多样性的特点,有助于增强整体把握历史的能力,有助于加强史学与时代的互动。
宏观历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借用二手材料所得出的结论必须是有新意的;借用是有界限的,不能滥用。只有坚守新意与界限,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宏观历史研究用活用好二手材料。宏观历史研究的主旨在于是否能提供激活宏观历史思维的新思想,这是其获得尊重的理由,也是对其进行评价的根本标准。
时代呼唤既受学界欢迎又受社会欢迎的宏观历史研究成果,史学家有责任、也有能力来回应时代的呼唤。
The Confines and Risk Prevention Pertaining to the Adoption of Second-hand Materials in Macroscopic Historical Studies
(by DAI Ji-hua,PENG Shen)
Original materials are the unique evaluation criterion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research.The adoption of second-hand materials is,however,a common practice.Under the interrelated factors of social demand and world history compilation,facing unlimited materials available,it is especially necessary for an individual historian to borrow from second-hand materials in macro history research.It is“essential”to resolve this contradiction not unequivocally and also not indiscriminately.This is only applicable within the confine of three domains,namely,the historical theory and historical thinking exploration,comparative study of macroscopic history,and large-scale history compilation.Only under such condition can macro historical study provide innovation and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comparison and diversified explanation of history,sufficiently demonstra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historiography and its social function.The intrinsic risk of adopting second-hand materials in macroscopic historical research is that“new idea”is being“borrowed”.By means of strict adherence to the research objective,compliance with the original material's principle,and maintenance of academic standard,there is hope to safeguard against risks.
macroscopic historical study;second-hand material;adoption;limitation;risks.
代继华(1952—)男,重庆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2011-07-20
K061
A
1000-5455(2011)06-0051-14
【责任编辑:赵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