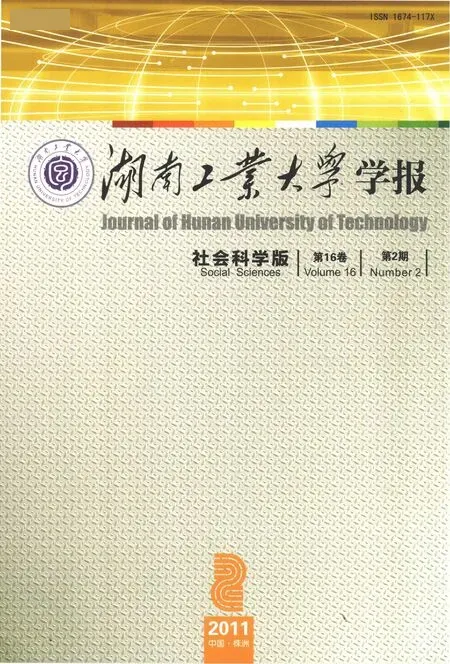走向圆融:“以禅喻诗”的演进历程*
田 琼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 长沙410081)
走向圆融:“以禅喻诗”的演进历程*
田 琼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 长沙410081)
作为古代重要诗学范畴之一的“以禅喻诗”,它所走的是一条批评家的诗禅体验交融之路,历经了佛自佛,诗自诗,诗禅之间终有一层隔阂的初涉期;“尚在形似意想间,犹未显然分明”、“仅见其形质”的交融期及游刃有余地出入禅学和诗学维度的圆融期三个阶段,最终发展成为宋代的一种重要的批评模式。
“以禅喻诗”;诗禅交涉;诗禅交融;诗禅圆融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type of ancient poetry,“Buddhist Poetry”has been walking on a way of blending poetry criticism and Buddhist meditation.Having experienced the primary period of“Buddhism is Buddhism,poetry is poetry,and there always be an estrangement between poetry and Buddhism”,the blending period of“similar in the form and no distinction between form and spirit”,and the harmony period of“freely getting into and out of the dimension of Buddhism and poetry”,it had finally developed into an important criticism mode in Song Dynasty.
Key words:Buddhist poetry;communication between poetry and Buddhism,blending between poetry and Buddhism,harmony between poetry and Buddhism
作为古代重要诗学范畴之一的“以禅喻诗”,自严羽明确提出后,就成为了中国古典诗学中的一桩公案。学术界在探讨“以禅喻诗”过程中,歧见迭出,分歧之一表现在对“以禅喻诗”的源头追溯上。“以禅喻诗”一词首先明确地出现在严羽的《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且《诗辨》篇中贯穿着“借禅以为喻”的论诗方法,因此人多以为“以禅喻诗”始于严羽。而随着人们对“以禅喻诗”认识的加深,有学者质疑“以禅喻诗”说起源于严羽的说法。经郭绍虞先生的提示,“以禅喻诗,人皆谓始于严羽,实则严羽以前亦早已有人论之,不过零星琐屑,不成系统,直至严氏《沧浪诗话》,始专从这方面发挥,于是论旨始畅耳。”[1]192后来的学者受此启示,纷纷地追溯起“以禅喻诗”的起源来。唐代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孟浩然、王昌龄、皎然、刘禹锡、齐己等被列入关注的对象;更有将晋代的支遁、慧远也纳入了追溯的范围。究竟如何看待“以禅喻诗”的起源呢?
罗宗强先生曾说过,“我常常想,一种新的诗歌思想、诗歌理论的出现,必有一个环境、一个过程,绝非孤立现象……”。[2]作为古代诗学范畴之一的“以禅喻诗”是否也能依寻出一条发展形成的轨迹?它所经历的又是怎样的一个环境与过程?佛禅思想为“以禅喻诗”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适宜的发展环境。“以禅喻诗”所走的是一条批评家的诗禅体验圆融之路,历经了初涉期、交融期、圆融期三个阶段,最终成为宋代的一种重要的批评模式。
一 初涉期:终隔一层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佛教般若学以其与玄学相似的命题和思辨方式,援玄入佛,格义叠出,成功地切入中国文化。禅僧谈玄,文人论禅,禅玄双修。禅僧入乎玄而出乎禅,文人则入乎禅而出乎玄,各取所需,互不妨碍。禅玄合流,为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内容,开了诗禅交涉的先河。
晋代,禅诗始出现。支遁、慧远等开始用诗歌来表现佛教义理。支遁《咏怀诗》之一“踟蹰观象物,未始见牛全。毛鳞有所贵,所贵在忘筌”[3]1080描写了探玄求道,了悟即色空义的过程;《咏怀诗》之二“道会贵冥想,罔象掇玄珠。怅怏浊水际,几忘映清渠。反鉴归澄漠,容与含道符”[3]1080-1081则依附玄学以阐说般若修习的要义。慧远冥游山间,于山水中体悟佛理,《庐山东林杂诗》之“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3]1085是对全诗所阐述的佛学思想的总结。从上可以看出,诗僧的诗歌创作更多是借诗歌来宣扬佛教义理。
敏感的文人也嗅到了来自佛学的这股新鲜之气,玄言诗中出现了一些表现佛禅思想的内容,如《续晋阳秋》就点出了一些玄言诗中有“三世之辞”的内容,“询及太原孙绰转相和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4]219继之,佛学的影响逐渐扩大,诗人的诗歌中表现佛教义理的内容逐渐增多,谢灵运是以诗篇唱诵佛教义理的佼佼者。他擅长于将观照山水的悟道情怀引入佛理,《过白岸亭诗歌》、《从斤涧越岭溪行诗》、《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此外,佛教典籍中的一些佛理及修禅经验也很值得我们注意。僧肇的“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涅盘无名论》卷四),拈出“妙悟”,成为“以禅喻诗”的语源;“境界”一词也多出现于当时的汉译佛典之中,对后来诗歌的境界理论有重要影响。慧远在《念佛三昧诗集序》中提出念佛“三昧”,有学者认为慧远开了诗禅交涉的先河,把“专思寂想”视为念佛与作诗的“三昧”。
总之,支遁、慧远、谢灵运的诗歌创作,僧肇的“妙悟”,汉译佛典的“境界”,慧远的念佛“三昧”,为以后的“以禅喻诗”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但由于此期尚属诗禅相涉之初,诗僧、诗人各自的禅学修养与诗创能力没能完美地融合,诗僧更多是借诗歌来宣扬佛教义理;而在诗人这端,“佛禅影响于诗还限于形迹”。[5]68佛自佛,诗自诗,诗禅之间终有一层隔阂,禅的体验与诗的体验终隔一层。
二 交融期:见其形质
唐以后,随着禅宗的兴盛,诗人与诗僧交往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一大批诗人如王维、柳宗元、白居易、杜甫等或修习佛禅或深受禅宗影响。白居易《自咏》云:“白衣居士紫芝仙,半醉行歌半坐禅。”[6]5140王维《终南别业》云:“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佛禅对于一些诗人来说,已不是一种外在的追求,而成为了一种更为自觉的内心需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等都达到了一种诗禅圆融无碍,诗即禅,禅即诗的和谐状态。
禅学的内心化,使得诗人的诗的体验与禅的体验更为融洽。诗人开始意识到禅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意义。刘禹锡诗云:“释子以诗闻于世者相踵。因定而得境,故翕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秋日过鸿举法师院便送归江陵引》)[6]4015同时,诗僧的诗学修为大进,有着深刻的诗歌创作的体验。由于长期的修禅实践,诗僧们更擅长于诗歌创作中的心理机制、思维问题,他们常常将禅学术语“玄”、“魔”、“灵”等直接引来论诗歌创作的心理机制,这可以视为诗僧对“以禅喻诗”所作出的贡献之一。
真正把诗与禅相比附,是在中唐以后。此期援禅入诗、援禅论诗比较流行,诗人、诗僧打通了诗与禅的隔阂,徐寅:“诗者,儒中之禅也。”(《雅道机要》)[7]527尚颜:“诗为儒者禅,此格的惟仙。”(《读齐己上人集》,一作栖蟾)[6]2082他们或诗禅对举,或诗禅比附,或诗禅互证,尝试着用禅学体验来表达和还原他们对诗的体验。
孟浩然:“弃象玄应悟,忘言理必该。静中何所得,吟咏也徒哉。”(《本阇黎新亭作》)[6]379
元 稹:“轻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禅。”(《见人咏韩舍人新律诗因有戏赠》)[6]1005
皎 然:“诗情缘境发,法性寄筌空。”(《秋日遥和卢使君游何山寺宿扬上人房论涅盘经义》)[6]1996
戴叔伦:“律仪通外学,诗思入禅关。”(《送道虔上人游方》,一作灵澈)[6]1988
齐 己:“诗心何以传,所证自同禅。”(《寄郑谷郎中》)[6]2057
以上诸说已经含有“以禅喻诗”的成分,虽然有些只是只言片语,比较零散,但难得的是诗人、诗僧们开始思考诗禅关系,并看到二者的相通性,且有意识地援引禅学语言来丰富古代诗学。
诗歌理论方面,刘勰的《文心雕龙》在诗学体系的建构上大受佛学影响,但准确地说,佛学还没有广泛地深入到文学批评和创作实际中。自唐代始,《诗格》、《诗式》等诗学著作中出现了佛禅思想影响的痕迹。批评家在评论诗歌之时,引入了禅语。王昌龄的《诗格》已有禅语,“如此之人,终不长进,为无自性”[8]163,“诗有三境”[8]172;皎然的《诗议》有“本性”[8]163、“中道”[8]209之说,他的《诗式》有“空王”[8]229之说。式、宗、门等更是被直接套用来论诗。由于诗格、诗法多注意于诗歌外部形式的繁琐分类及修辞造句的方法,诗学理论更为细致地引入禅语来探讨诗歌的形式技巧方面的问题。
虽然在诗学理论的探讨中,诗僧慧远、皎然、贯休、齐己、尚颜及诗人孟浩然、刘禹锡、戴叔伦、元稹、白居易等的援禅论诗还有些盲目、偶合性,用叶燮的话来说,“尚在形似意想间,犹未显然分明”、[9]61“仅见其形质”。[9]34这一时期具有交融期的特点,用禅宗术语来讲还是一种不自觉的尝试,具有一定的模糊、含混性,“以禅喻诗”的理论也缺乏系统性。但是这些援禅论诗的尝试皆可看作唐人为“以禅喻诗”在宋代形成气候所作出的有力铺垫。
三、圆融期:游刃有余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时期,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0]245自北宋中叶特别是熙宁以后,出现了“不读禅,无以言”的状况,促成了诗禅的进一步融会贯通。“以禅喻诗”已达到一种圆融无碍的境界,批评家游刃有余地“出”、“入”禅学与诗学两个维度。
“学诗浑似学参禅”是“以禅喻诗”中的一个很有特色的话语模式。在宋代,“学诗浑似学参禅”成为论诗的话头,大有“论诗不谈禅,无以言”的势头。
吴 可:“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学诗浑似学参禅,头上安头不足传,跳出少陵窠臼外,丈夫志气本冲天。”“学诗浑似学参禅,自古圆成有几联?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学诗诗》三首)[11]451
龚 相:“学诗浑似学参禅,悟了方知岁是年。点铁成金犹是妄,高山流水自依然。”“学诗浑似学参禅,语可安排意莫传,会意即超声律外,不须炼石补青天。”“学诗浑似学参禅,几许搜肠觅句联欲识少陵奇绝处,初无言传与人传。”(《学诗诗》三首)[11]331
赵 蕃:“学诗浑似学参禅,识取初年与暮年。巧匠曷能雕朽木,燎原宁复死灰然。”“学诗浑似学参禅,要保心传与耳传。秋菊春兰宁易地,清风明月本同天。”“学诗浑似学参禅,束缚宁论句与联。四海九州何历历,千秋万岁永传传。”(《学诗诗》三首)[11]
陈师道:“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次韵答秦少章》)[12]12652
韩 驹:“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赠赵伯鱼》)[12]16588
曾 几:“学诗如参禅,慎勿参死句。”(《读吕居仁旧诗有怀》,《前贤小集拾遗》卷四)
李处权:“学诗如学佛,教外别有传。”(《戏赠巽
老》)[12]20379
李 衡:“学诗如参禅,初不在言句。”(《乐庵语录》卷三)
葛天民:“参禅学诗无两法,死蛇解弄活泼泼。”(《寄杨诚斋》)[12]32062
戴复古:“欲参诗律似参禅,妙趣不由文字传。”(《论诗十绝》之七)[12]33608
林希逸:“学诗如学禅,小悟必小得。”(《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十三)
萧立之:“后山诗法似参禅,参到无言意已传。”(《题东畈陈上舍吟稿二首》之一)[12]39163
徐 瑞:“文章有皮有骨髓,欲参此语如参禅。”(《雪中夜坐杂咏》)[12]44666
还有李之仪的“得句如得仙,悟笔如悟禅”(《赠祥瑛上人》,《姑溪居士后集》卷一),批评家们直接道出诗与禅之间的“如”、“似”、“浑似”的关系,用禅学系统的概念来类比诗学系统的概念,挑明了诗禅之相似、相通处。“学诗浑似学参禅”这种论诗方式是批评家在面对“言不达意”、“言不尽意”的“言”、“意”难题时,所采用的一种巧妙而智慧的处理策略,不可不说是“以禅喻诗”成熟的表现之一。它一改唐以前的“以禅喻诗”的实践的盲目、偶合性,实践起来也比较系统。
如果说,“以禅喻诗”在魏晋、唐代更偏重于诗的体验、禅的体验,致力于两者的融洽的话,那么宋代及以后的禅的体验则相对来说是浅薄的,后来发展为一种流行的说法,正象在春秋时期的“以诗观志”,禅宗术语成为一种范式,也可以说是诗论的“潜规则”。
“以禅喻诗”成熟的另一表现是经由佛禅的催发,诗学中出现了追求纯形式、审美的鲜明特色。程亚林在他的《诗与禅》一书曾指出,“有重视与知性、功利密切相关的‘美’的概念,经由佛学的刺激和庄、玄、庄玄化佛学、禅学的启发,向总是纯形式和依存性审美转化,就可能是实现审美自觉的一条逻辑路线。”[13]190大量的禅宗语言进入诗学体系,初步建构了审美倾向的禅学诗学。
就影响来看,可以说江西诗派是宋代诗坛、诗歌理论批评的代表。江西诗派几乎无人在论诗时不用禅宗术语的,曾季狸曾作出过总结,“后山论诗说换骨,东湖论诗说中的,东莱论诗说活法,子苍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然其实皆一关捩,要知非悟入不可。”(《艇斋诗话》)[14]296江西诗派中人的“以禅喻诗”说代表了宋代诗歌理论批评重视作诗的形式技巧的特色。
江西诗派之外的人士也多有说禅作诗的风气,而大抵逃不出对诗歌形式探讨的窠臼。范温的《潜溪诗眼》谈到更多的是形式的问题,“句法以一字为工,自然颖异不凡,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14]333“盖古人之学,各有所得,如禅宗之悟入也。山谷之悟入在韵,故开辟此妙,成一家之学,宜乎取捷径而径造也。”[14]374杨万里诗云:“句法天难秘,工夫子但加。参时且柏树,悟罢岂桃花。”(《和李天麟》)[12]26112
由于江西诗派的形式追求存在局限性,反江西诗派的诗论于是应运而生。陆游提出:“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12]24789到了南宋末,严羽则更是明确地表示自己对江西诗派诗论的排斥,思考诗道,提出“以禅喻诗,莫此亲切”。[15]251但他的诗论也正如郭绍虞先生所支持的,“他不能摆脱当时纯艺术论风气,知宋诗之弊而不知其弊之所自生,依旧欲在纯艺术论上攻击当时纯艺术的倾向”。[15]41可以说,此期的“以禅喻诗”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对艺术性的重视,诗学趋于审美化。
在宋代诸家的努力下,大量的禅宗术语涌入宋代的诗歌创作、诗歌理论中,严羽的“以禅喻诗”说之提出及其在《诗辨》篇中的“以禅喻诗”法之实践,标志着“以禅喻诗”的走向圆融即最后完成。“以禅喻诗”成为了宋代的一种重要的批评模式。
“以禅喻诗”这种论诗方式正体现着中国诗学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它或许可以成为古代诗学通向现代诗学的一条甬道。
[1]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92.
[2]吴文治.宋诗话全编[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3]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219.
[5]孙昌武.禅思与诗情[M].北京:中华书局,1997:68.
[6]曹 寅,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7]陈应行.吟窗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7:527.
[8]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9]叶 燮.原诗[M].霍松林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10]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45.
[11]诗人玉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2]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1999.
[13]程亚林.诗与禅[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190.
[14]郭绍虞.宋诗话辑佚[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5]严 羽.沧浪诗话校释[M].郭绍虞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41.
责任编辑:李 珂
Heading for Harmony-On the Evolution of Buddhist Poetry
TIAN Qi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
I206.2/4
A
1674-117X(2011)02-0100-04
2010-10-10
田 琼(1982-),女,湖北黄冈人,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代文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