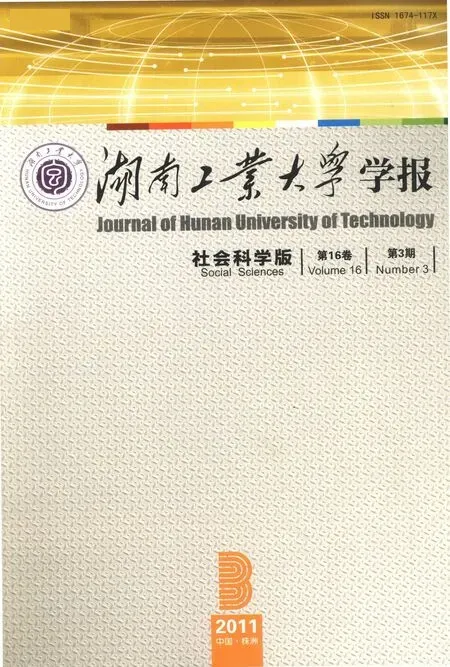结构主义理论视域下的年鉴学派发展阶段划分*
康建伟
(甘肃政法学院人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结构主义理论视域下的年鉴学派发展阶段划分*
康建伟
(甘肃政法学院人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结构主义是一种把所有文化现象都视为符号结构加以分析的文化和文论思潮,年鉴学派是20世纪法国乃至世界史学发展的主流。借鉴结构主义的理论视域,并结合福柯、斯特劳斯与年鉴学派的关系,可以将年鉴学派发展阶段划分为:结构主义年鉴学派与后结构主义年鉴学派。
年鉴学派;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主要指发端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并在1960年达到高潮的一种把所有文化现象都视为符号结构加以分析的文化和文论思潮,根据结构主义理论,透过作为表意系统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可以剖析出一个文化意义的产生与再现。结构主义者就是通过研究这类符号,来找出一个文化意义是如何被制造与再制造的深层结构。泛化来讲,结构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学说,而是一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家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共同应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其目的就是试图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能像自然科学一样达到精确化、科学化的水平。年鉴学派则是20世纪法国乃至世界史学发展的主流,在20世纪的历史学中占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特别在布罗代尔时代,此派获得巨大的国际声誉,几成一个史学王国。通过借鉴结构主义的广义理论视域,并结合斯特劳斯、福柯与年鉴学派的关系,我们可以将年鉴学派划分为:结构主义年鉴学派与后结构主义年鉴学派两个发展阶段。
一 从地窖到阁楼:结构主义年鉴学派时期
年鉴学派以吕西安·费弗尔与马克·布洛赫为代表的第一代和费尔南·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第二代在理论精神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两代的重要著作都充分体现了整个学派的主导符码——总体史。他们倡导研究人类活动的总体史,包括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情感、政治等因素。这些因素互相联系,形成多层次的结构。总体史研究是年鉴学派甚至是法国史学家的共同准则,法国各代历史学家对总体史都是情有独钟的,保罗·利科甚至概括为“从这一意义上说,法国没有其他历史学派,只有一个‘总体史学派’”。[1]5
年鉴学派的创始人费弗尔和布洛赫是以对兰克学派的批判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兰克学派及其兰克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现代史学,这一学派在实证主义的指导下,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在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及个人传记。而年鉴学派不再满足于对政治等专门史的研究,而要对影响和左右政治行为的更深层次的经济和心理等诸多因素进行深入的探究。保罗·利科认为“年鉴学派一方面抛弃了具有编年意义的事件,另一方面反对把个人当作历史分析的最后单位……年鉴学派发现,他们所认为实证主义史学的主要特点,与政治史的统治地位之间隐藏着某种密切关系。所以,批判‘事件史’和‘战争史’,构成了呼吁研究人类总体史的前哨战……”[1]38-39这一思想到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巨擘布罗代尔时被系统化并开始占据法国史学主流地位。布罗代尔提出的历史时段理论:“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以及与之对应的“事件”、“情势”、“结构”,表现了年鉴学派用恒定模式来把握历史,从而达到对历史发展背后的深层结构进行探究的企图。
总体史的追求,对政治和个人的扬弃,恒定模式的探究和对深层结构的追踪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基本上是关于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新的观念,即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由事物构成的观念,就成为可以确切地称为‘结构主义者’的那种思维方式的第一条原则。简言之,这条原则认为,在任何既定的情境里、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总之,任何实体或经验的完整意义除非它被结合到结构(它是其中组成部分)中去,否则便不能被人们感觉到。”[2]8-9因此,结构主义者的最终目标是永恒的结构:“个人的行为、感觉和状态都纳入其中,并由此得到它们最终的本质。最后就象F·詹姆森所描绘的那样,是‘明确地寻找心灵本身的永恒的结构,寻找心灵赖以体验世界的,或把本身没有意义的东西组成具有意义的东西所需要的那种组织类别和形式’”。[2]9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勒罗瓦·拉杜里为何把年鉴学派的第一个阶段表述为“定性结构史学”阶段。按照拉杜里的观点,年鉴学派的历史以1945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1945年前也即上述第一代可谓“定性结构史”,第二阶段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年鉴学派进入新的时代:“定量势态史”时代。这两个时代尽管特征不同,但方向是一致的。[3]
我们还可从布罗代尔对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理论的借鉴中找到佐证。彼得·伯克指出:“少数人类学家很早就对年鉴派感兴趣,尤其是列维-斯特劳斯与伊文斯-普里查德。布罗代尔与列维-斯特劳斯是圣保罗大学的同事,此后一直继续他们的对话。”[4]98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此时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与社会科学主导思潮保持良好的关系。列维-斯特劳斯的工作地点就是在赫赫有名的第六部里,因而这时的年鉴学派(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第二代)与当时社会科学主导思潮可以说是一致的。列维-斯特劳斯借鉴普罗普的童话研究,将注意力集中于神话结构之上。在人类学领域的创造性实践使得他成为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从而取代萨特成为思想界的领袖。然而他与结构主义的其他巨子不一样,他始终没有转向后结构主义,而坚持了思想的一贯性。
有论者认为,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结构的概念基本上是静止的、主观先验的,它是超越于时间性之外的史学结构方法,是产生与结构主义平行发展与相互影响之中的;但单纯把史学结构方法看作是结构主义对新史学的影响与渗透,并非正确。[5]可打破学科壁垒,不把结构主义单纯看作一个文论流派,而是从广义结构主义的视域下审视年鉴学派,年鉴学派的第一、二代可称之为年鉴学派的结构主义阶段。已有论者指出了布罗代尔对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理论的借鉴,认为二者都受到涂尔干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保持良好的私交。布罗代尔借鉴了结构人类学的结构整体观与结构分析法、历史时间理论与跨学科研究。[6]
70年代之后,特别是布罗代尔退休之后,年鉴学派进入新的时代,年鉴范式在外部甚至是内部都遭到广泛的怀疑,趋于“衰微”,濒临“解体”,面对这一态势,对年鉴学派的后期又如何称呼呢?
二 从阁楼到地窖:后结构主义年鉴学派时期
年鉴学派的第三代以独立后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为基地,打出了“新史学”的旗帜,所以人们一般称他们为“年鉴——新史学派”。他们虽然继承了长时段理论和对总体史的追求,但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历史人类学和精神状态史上。当今这一流派呈多元化甚至零碎化趋势,很难用某种主导名词来概括其倾向。参照结构主义的继承者和叛逆者后结构主义命名方式,我们可以把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及以后命名为后结构主义年鉴学派。
“年鉴——新史学派”对年鉴学派的一贯主张,尤其是对社会史和结构史的支配地位发动了全面的挑战。彼得·伯克把这种反动,概括为三种趋势:人类学的转向、政治的回归与叙事的复兴。[4]74勒高夫认为当前“问题的症结是必须超越‘结构——情势的困境,尤其是结构——事件的困境’”。[1]90而他在1993年6月10日与中山大学同行座谈时指出:“我们理应努力地更新自己的史学思考。我们要采取行动,来一个我们所说的‘关键性的转折’。这种转折乃是西方史学的的回归‘即史学研究中一些或多或少已消失的老方式被重新采用,可归纳为政治史回归、事件史的回归、叙述史的回归、人物传记的回归和主体的回归’。”[7]年鉴学派的第四代则在这条自我反省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也更为决绝:雅克·勒韦尔承认历史学“陷入了一个无法掩饰的认同危机”;担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长的弗雷声称年鉴学派现在只代表一种“影响和声望的权威,而不再代表一个有思想的学派了”;如果换个角度,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论调理解为年鉴学派的自绝宣言。1987年乔治·杜比、弗雷、勒胡瓦拉杜里、阿居隆合编的5卷本《法国史》出版,在该书的前言中,明确宣布他们的目的就是写一部政治史;贝尔纳·勒佩蒂推出“批判转折论”,声言“重新洗牌”,建立了新的参考概念框架,提出了新的社会史的研究方法;1994年《年鉴》杂志改名为《历史与社会科学年鉴》,这次更名反映出年鉴学派对西方史学变化的回应和对自身的重新定位,试图把文化因素摆在重要地位,从文化人类学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中吸取理论。
所有这些调整甚至自我反叛,确证着在后现代思潮的席卷之下,反抗理性,解构权威的巨浪已经横扫了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门类。年鉴学派这个昔日的灰姑娘在成为白雪公主后好景不长,又要从阁楼被赶进地窖,虽然这次下台更加类似于自我放逐,但毕竟阁楼上的风光已经成了昨日黄花。
这一判断,也可从与结构主义关系紧密而又与年鉴学派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福柯处得到支持。福柯曾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工作,受布罗代尔的领导,这位当时法国最杰出的史学耆宿也对福柯充满敬意,称他为“他的时代最辉煌的思想家之一。”[8]146
福柯“特别关注历史上一些不大引人注目的事物或缓慢的发展过程,比如人们对癫狂、死亡、性爱、罪犯的态度的演变,以及学术界思维方式的变化等等。知晓当代西方史学思潮的人都不难看出,这种史学路数基本点和法国年鉴派如出一辙……年鉴派史学家都轻视政治事件而注重中长时段的研究,而且在中长时段的研究方面,他们的注意力明显地倾向于向长时段集中,划出了一条相当清晰的由经济史到社会史再到文化史的演进轨迹。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文化史的基本内容的‘心态史’一天天凸显,逐渐演成年鉴派特有的看家功夫:即使是对政治事件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的第三代年鉴学派,在重新研究事件时也都无一例外地要到心态史上去作文章,以至于‘心态史学’竟已成为当今年鉴派史学的代名词”。[8]150从以上文字中,我们明显看到,作者在这里企图强调福柯与年鉴学派的共同点,即福柯的“超现实主义”的史学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与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特别是与第三代强调的“心态史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按前文把年鉴学派分为结构主义时期和后结构主义时期的话,福柯与年鉴运动的第三代即后年鉴学派有更多的相似点,而在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占据史学理论主流时,他则“处于边缘甚或边缘之外的位置”。[4]2在“米歇尔·福柯的学术发展中,法国‘新史学’扮演了富有意义的角色。福柯与年鉴学派的第三代有共通之处……福柯喜欢称之为‘考古学’或是‘系谱学’的东西,与心态史至少在亲缘关系上具有类同性。两者都对长时段的趋势表现出很大的关注,相比之下,对个体的思想家则关注不多……福柯与心态史学家最为不同的地方,恰恰在于福柯乐于大胆地抓住棘手的问题,并讨论世界观如何变迁。”[4]96在这里,彼得·伯克明确地说明了福柯与年鉴学派第三代以后的相同之处。同样的肯定性的断语也可见于中国史学家的笔下:“实际上,西方史学的最新变化似乎就是‘政治史的复归’,它是在福柯和布迪厄的影响下出现的”。[9]
年鉴学派与福柯史观有某种近似点,然而就福柯主流思想而言,其史学观强调颠覆历史理性,放逐历史主体,瓦解历史客观性,终止历史进步,拒绝历史总体化。所以人们一般把福柯的史观纳入后现代主义历史观,与年鉴学派第一、二代大不相同。如果按照本文对年鉴学派的划分来确证福柯与年鉴学派第三代的关系,我们可以把福柯与年鉴学派后期都归类为后结构主义史学。因为福柯虽然与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和拉康奉为“结构主义前四子”,但“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个结构主义者……或许唯有后结构主义这个含义太为广泛的概念,才是毋庸置疑适用于福柯的标签”。[10]当前年鉴学派的改革方向之一便是积极学习文化人类学,而在文化人类学中,对年鉴学派影响最大的就是福柯。当然这种学习并不是完全一致,福柯认为文明化过程的实质是社会纪律不断加强的过程,而历史需要研究的是一种权力知识的关系如何被另一种权力知识的关系所取代。历史研究不存在想当然的思想对象,也没有结构,更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年鉴学派不可能走得这么远,但从方法论而言,福柯对年鉴学派的总体史研究提出的严峻挑战与第三、四代年鉴学派有相似之处。
撮要论之,虽然年鉴学派与结构主义都各有其理论分野。但是,如果打破学科壁垒,以跨学科的眼光,把结构主义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共同应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再结合福柯、斯特劳斯与年鉴学派的关系,可以将年鉴学派发展阶段划分为:结构主义年鉴学派与后结构主义年鉴学派。
[1]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2]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罗凤礼.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251.
[4]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M].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孙晶.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及其评价[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
[6]王作成.试论布罗代尔对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理论的借鉴[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7]雅克·勒高夫.年鉴运动及西方史学的回归[J].史学理论研究,1999(1).
[8]高毅.福柯史学刍议[J].历史研究,1994(6).
[9]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002:420.
[10]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35.
The Division of Developmental Phases of the Annals Schoo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ism
KANG Jianwei
(School of Human and Literature,Gansu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Gansu,730070,China)
The structuralism is a culture and literature trend which regards all cultural phenomenons as symbols.The Annals is school the mainstream in 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even the world history.The division of developmental phases of the ann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ism is explored.From the angle of structuralism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ucault,Strauss and the Annals school,the developmental phases of the Annals school can be divided as structuralism Annals and post-structuralism Annals.
Annals School;structuralism;post structuralism
K0
A
1674-117X(2011)03-0070-04
2011-03-09
甘肃政法学院青年科研资助项目(GZF2010XQNLW52)
康建伟(1980-),男,甘肃会宁人,甘肃政法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文艺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骆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