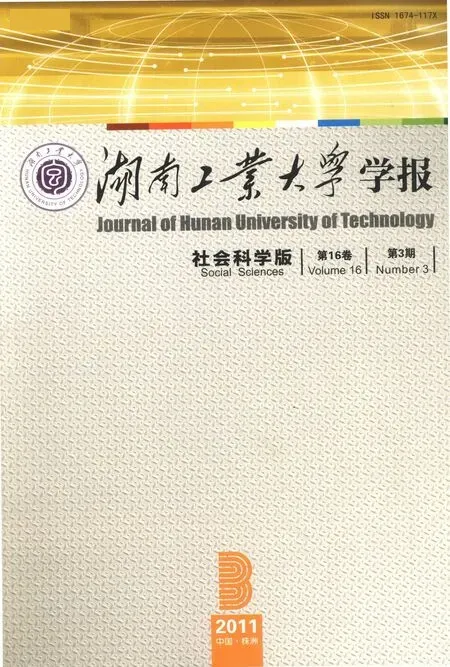李渔叙事结构思想试探*
赵炎秋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李渔叙事结构思想试探*
赵炎秋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李渔重视叙事作品的结构。李渔的“结构”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整体构思意义上的结构,二是主题意义上的结构,三是谋篇布局意义上的结构。李渔对结构的讨论主要是从戏曲的角度进行的,但其思想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可以运用到整个叙事文学的创作中去。
李渔;叙事作品;结构;戏曲
李渔是明清时期与金圣叹齐名的文学批评家。李渔的小说、戏曲在结构上很有特点,他在自己的理论著作《闲情偶寄》中比较集中地阐述了自己关于叙事结构的思想。本文主要根据《闲情偶寄》和李渔的小说与戏曲创作,对其叙事结构思想做一初步的探讨。
一 李渔对叙事结构的重视
李渔的一生都是以叙事文学为主轴进行活动的。他兴趣广泛,诗词歌赋、花卉园艺、饮食养生门门涉猎,样样精通,但其成就最大的还是戏曲与小说。李渔是一个当行的演出实践家,自称为“曲中之老奴,歌中之黠婢”。[1]114但在他的戏曲活动中,占主导的仍是剧本创作,他终生都在创作剧本,而演出实践只有短短的5年。戏曲是一种复杂的文艺活动,既有舞台演出,又有剧本创作。作为一个当行的批评家,李渔不轻视舞台演出,但相对而言,他更重视剧本的创作。在《闲情偶寄·演习部》中,李渔提出“选剧第一”,认为,“演习之工而首重选剧”,如果所选剧本不佳,“则主人之心血,歌者之精神,皆施于无用之地。使观者口虽赞叹,心实咨嗟,何如择术务精,使人心口皆之为得也。”他批评“方今贵戚通侯,恶谈杂技,单重声音,可谓雅入深致,崇尚得宜者矣。所可惜者:演剧之人美,而所演之剧难称尽美;崇雅之念真,而所崇之雅未必果真。”[1]100剧本为一剧之本,戏曲演出的依据,戏曲中的其他要素如演员的唱念做打做得再好,如果所表现的内容缺乏价值,演员的演出也就没有,至少是减损了价值。因此,戏曲演出首先要选择好剧本。而好剧本不是从天而降的,需要剧作家艰辛的努力。这样,剧本的创作便提到了重要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重视剧本,无疑是重视戏曲活动中的文学因素(在汤显祖、李渔等人的努力下,当时剧坛的主要剧种——昆曲中文学因素十分浓重,形成了以剧作家为中心的戏曲活动体系,有些剧作家甚至创作出一些只能阅读不能演出的“案头之曲”。京剧兴起后,戏曲活动中的作家中心逐渐过度到演员中心,剧本的重要性削弱,戏曲中的文学因素逐渐淡薄。从某种角度看,这实际上是一种退步)。
而在剧本中,李渔则将结构放在第一位。他的《闲情偶寄》,“词曲部”摆在最前面,而在“词曲部”中,“结构”又放在首位。他宣称:
填词首重音律,而予独先结构……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工匠之建宅亦然。基址初平,间架未立,先筹何处建厅,何方开户,栋需何木,梁需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挥斤运斧。倘造成一架而后再筹一架,则便于前者,不便于后,势必改而就之,未成先毁,犹之筑舍道旁,兼数宅之匠资,不足供一厅一堂之用矣。故作传奇者,不宜卒急拈毫,袖手于前,始能疾书于后。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题不佳,而能出其锦心、扬为绣口者也。尝读时髦所撰,惜其惨淡经营,用心良苦,而不得被管弦、副优孟者,非审音协律之难,而结构全部规模之未善也。[1]7
戏曲剧本,即是戏曲演出的蓝本,同时本身亦可作为文学作品供人阅读。音律与结构,则是戏曲剧本的两大要素,相对而言,结构更多地属于叙事文学的范围,音律则更多地属于舞台演出的范围。李渔将戏曲结构放在首位,认为结构是决定戏曲成败的关键,比音律等其他要素更为重要。结构不好,即使用心良苦地将剧本创作出来,也不一定能够在舞台上演出。这样,李渔就把结构放在了戏曲活动的首要位置。
二 整体构思意义上的“结构”
粗略地说,李渔的结构就是广义的构架,是作品其他要素依附的基础。结构立起来了,作品的其他因素才有取舍的标准,也才能各就其位。具体地说,李渔的结构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层含义指叙事作品的整体构思、全盘规划。李渔认为,文学创作之先,要先把握、构思全局。“如造物之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倘先无成局,而由顶及踵,逐段滋生,则人之一身,当有无数断续之痕,而血气为之中阻矣。”[1]7也就是说,文学创作之前,作者就应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全面的规划和整体的把握,这样,动笔之后,才能各方协调,思路不致阻滞,不做无用之工。正是在此意义上,他强调创作剧本时“不宜卒急拈毫,袖手于前,始能疾书于后”。所谓“袖手于前”,也就是说在创作之前,先应构思,对整部作品成竹在胸之后,写起来才能得心应手。这就像工匠建宅,必须对房屋有了整体规划之后,才能开始工作,否则,必然边建边改,事半功倍。
李渔对剧本的构思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
其一是“戒讽刺”。李渔的“讽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讽刺,而是指借文学作品“报仇泄怨”,达到个人不正当的目的。“心之所喜者,处以生旦之位,意之所怒者,变以净丑之形,且举千百年未闻之丑行,幻设而加于一人之身”。李渔看到了文学巨大的社会作用,认为笔与刀一样,“皆杀人之具”,[1]15而且以笔杀人之痛,比刀更为持久,且可延之后世。因此要求作者修养文德,创作之时持心以正,扬善惩恶,对观众读者施以正面、积极的影响;而不要将文学作品作为泄私愤的工具,对观众读者施以负面的影响。
其二是“脱窠臼”。李渔主张创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而文章一道,较之他物,尤加倍焉。戛戛呼陈言务去,求新之谓也。”“窠臼不脱,难语填词。”李渔的“新”,指的是已存的作品中没有的情节、事件。“是以填词之家,务解‘传奇’二字。欲为此剧,先问古今院本中,曾有此等情节与否,如其未有,则急急传之,否则枉费辛勤,徒作效颦之妇。”[1]17-18自然,李渔要求“脱窠臼”,也不是不要传统。在《格局第六》中,李渔批评“近日传奇,一味趋新,无论可变者变,即断断当仍者,亦加改窜,以示新奇。”[1]90他认为这种作法是不好的。不过在《格局第六》中,李渔所说的格局指的是戏曲的结构程式。在这方面,李渔比较尊重传统,有一定的保守性。而在《脱窠臼》中,李渔要求创新的主要是情节与事件。细细品味,这里仍有一定的区别,需要辩证地看。总的来说,李渔强调的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创新,但在情节、事件方面,他更强调创新的一面;而在结构程式方面,他更强调继承的一面,戏曲小说皆然。
其三是“戒荒唐”。“戒荒唐”与“脱窠臼”是相辅相成的。“脱窠臼”强调创新,道前人所未道。“戒荒唐”则指出,这种创新并不是要写一些“荒唐怪异”、“魑魅魍魎”等荒诞的东西,而是要在“人情物理”“家常日用之事”中发掘所未见的内容。他批评“家常日用之事,已被前人做尽”的观点,指出“世间奇事无多,常事为多;物理易尽,人情难尽”。[1]25认为“前人已见之事,尽有摹写未尽之情,描画不全之态。若能设身处地,伐隐攻微,彼泉下之人,自能效灵于我,授以生花之笔,假以蕴绣之肠,制为杂剧,使人但赏极新极艳之词,而意忘其为极腐极陈之事者。”[1]25也就是说,已有的事件,即便曾被人写过,也仍有一些未曾披露的内涵,只要善于发掘,仍能写出新意。结合《脱窠臼》中的主张一起理解,李渔的观点是比较全面、辩证的。
其四是“审虚实”。文学需要虚构,但中国古代文学又有崇真的传统。文学作品是写实还是虚构,这也是构思时就需要考虑的问题。李渔提出“传奇无实,大半皆寓言”,[1]27认为文学创作应以虚构为主,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此问题笔者已在另一篇文章中做了详细探讨,此处不再展开。[2]
应该注意的是,李渔的上述主张虽然主要是针对整体构思与全盘规划而言的,但也牵涉到具体的创作过程。换句话说,只有在整体构思与创作过程中都遵循了这些主张,这些主张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三 作品主题意义上的“结构”
结构的第二层含义指作品的主题,也即李渔说的“主脑”。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品的主旨,一是作品的题材。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主旨决定着题材的选择,而题材的选择又体现着作品的主旨。
李渔认为:“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1]15这里的“本意”,也就是作者的意图、主旨。主旨是作家创作想要达到的目的,希望表达的思想和情感,是作品成功的关键之一。一部作品如果主旨不好,其他方面写得再好,也很难成为优秀作品。因此李渔认为:“未有命题不佳,而能出其锦心、扬为绣口者也。”[1]7这里的“命题”,也即主旨之意。主旨不佳,作品的价值就大打折扣,其他方面如文字、情节再好,作品也很难成功。
另一方面,李渔认为,一部剧本要涉及很多人物,一个人物有许多事迹。但在这些人物中,只能有一个主要人物,而在这个人物身上,又只能有一件事是为主的。“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其他人、事,都是从属、服务于这一人一事的。“如一部《琵琶》,止为蔡伯喈一人,而蔡伯喈一人又止为‘重婚牛府’一事,其余枝节皆从此一事而生。”[1]15蔡伯喈的“重婚牛府”在剧中的矛盾冲突中起着枢纽的作用,从结构上看,是全剧的关键性事件,剧中的其他事件都通过它联系或引申出来的。李渔的“一人一事”实际上也就是作品的主要题材,是主题另一层次上的含义。立定了主旨,确定了题材,作品的“主脑”也就确定了。
为了做到“一人一事”,李渔提出“减头绪”的主张。所谓“减头绪”,有剧本表达的思想要简练、集中的意思,但主要强调的还是围绕主旨,突出重点,去掉与主线无关的枝节。李渔认为:“头绪繁多,传奇之大病也。《荆》《刘》《拜》《杀》之得传于后,止为一线到底,并无旁见侧出之情。”(《荆》《刘》《拜》《杀》分别指《荆钗记》《刘知远》《拜月亭》《杀狗记》等四剧)一根主线贯穿到底,不仅便于剧情的组织安排,更重要的是,便于观众把握剧情,理解剧意。“三尺童子观演此剧,皆能了了于心,便便于口,以其始终无二事,贯串只一人也。”戏曲是一次性的艺术,不能像小说一样反复翻看。而当时的观众大多不识字,即便识字,也不一定能在演出前看到剧本,把握动辄几十出的传奇主要只能靠观看演出。头绪太繁,观众很难把握。另一方面,当时戏场的角色有限,“便换千百个姓名,也只此数人装扮。”人物设置太多,反而增加混乱,使观众无法把握。不如少设一点人物,使角色只扮数人,“使之频上频下,易其事而不易其人”,[1]23这样反而能够收到好的效果。
由此可见,李渔“一人一事”的主张与当时舞台演出的条件与特点是有关系的,主要是针对戏曲剧本而言的。但这种创作主张一旦形成,便不仅影响着他的戏曲创作,也影响着他的小说创作。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李渔实际上也是严格遵循着“一人一事”的原则的。《无声戏》《十二楼》中的小说自不必说,即便其长篇小说也是如此。如《合锦回文传》主要写梁栋材与桑梦兰爱情上的悲欢离合,主要人物是梁栋材,主要事件则是分为两半的一幅回文锦。据信为李渔所写的《肉蒲团》的主要人物是未央生,主要事件则是他从追求男女欢情到看破红尘出家为僧。
“一人一事”使叙事作品线索清晰,结构严谨。但也影响了李渔作品表达的生活面,使李渔无法创作出视野宏阔、结构复杂的史诗性作品。
四 谋篇布局意义上的“结构”
李渔的结构的第三层含义指作品的谋篇布局。中国古代作家与批评家一直重视作品的谋篇布局,这也是“结构”一词在古代批评中通常的含义。李渔认为,“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剪碎易,凑成难”。[1]20文学创作不能照搬生活,必然打乱生活,对其进行选择、补充、变更,然后再将这些“剪碎”的材料构成一部新的作品。这部作品必须是有机完整的,具有内在自足性。这就对作品的结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好的文学作品,结构应该具有整体性与严谨性。
整体性一方面指作品结构的完整,一方面指部分与整体的相谐,部分服从整体。古代戏文一般很长,因为时间的原因,人们有时只演出其中的一部分,李渔不赞成这种做法:
予尝谓好戏若逢贵客,必受腰斩之刑。虽属谑言,然实事也。与其长而不终,无宁短而有尾,故作传奇付优人,必先示以可长可短之法:取其情节可省之数折,另作暗号记之,遇清闲无事之人,则增人全演,否则拔而去之。此法是人皆知,在梨园亦乐于为此。但不知减省之中又有增益之法,使所省数折,虽去若存,而无断文截角之患者,则在秉笔之人略加之意而已。[1]106-107
或者,干脆在原本的基础上,
另编十折一本,或十二折一本之新剧,以备应付忙人之用。[1]106-107
李渔宁愿删去剧中不重要的部分,甚至重编新剧,也不愿“腰斩”剧本或者只演出其中几折,主要原因就在于“腰斩”或“选折”破坏了剧本的整体性,从而不能完整地表达出作者的整体构思,达不到应有的艺术效果(李渔的这一主张与后来中国剧坛盛行的折子戏似乎相反。但李渔强调的是剧本的完整,而折子戏突出的则是演艺,观众欣赏的主要是演员的演出,而且,由于经常演出,折子戏前后的剧情,一般观众也大都了解。相比而言,李渔的主张更偏重文学方面)。
同时,在去掉剧中的部分内容之后,李渔又要求创作者做一定的加工,使去掉的部分“虽去若存”,不影响剧本的完整性,不给人不连贯的感觉。这仍是从整体性的角度考虑。李渔认为:
文章一道,结构全体难,敷陈零段易。唐宋八大家之文,全以气魄胜人,不必句栉字篦,一望而知名作。以其先有成局,而后修饰词华,故粗览细观同一致也。若夫间架未立,才自笔生,由前幅而生中幅,由中幅而生后幅,是谓以文作文,亦是水到渠成之妙境;然但可近视,不耐远观,远观则襞祯缝纫之痕出矣。[1]207
以文作文之文就部分看,也可能出精妙之作,但就整体看,却不可能成为好文章,原因就在于文章缺乏整体性,部分之间不相协调,流露出斧凿之痕。
部分效果再好,整体效果不行,仍不能成为好的文章。上面这段引文,已经含有部分服从整体的思想。部分应该成为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是李渔一贯坚持的观点。另一方面,整体没有确定,部分也很难写好。比如传奇中的“家门”,“虽云为字不多,然非结构已完、胸有成竹者,不能措手。”这是因为,“家门”怎样写,是由整个剧本的内容决定的。犹如画龙点睛,龙画到最后,才把睛点上去。“非故迟之,欲俟全像告成,其身向左则目宜左视,其身向右则目宜右观,俯仰低徊,皆从身转,非可预为计也。”[1]91整体出来了,部分才能最终确定。这是部分服从整体的另一层意思(金圣叹也强调作品结构的整体性,但含义与李渔的有所不同。金圣叹主要是从有机整一的角度谈结构的整体性的,相比而言,李渔的整体性的内涵要丰富一些)。
严谨性指作品结构严密整一,各个部分互相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严谨性的最低要求是作品没有自相矛盾之处。李渔认为,传奇由于篇幅长,容易出现“前是后非,有呼不应,自相矛盾之病”。作家应该尽力避免,要像《水浒传》那样,虽然篇幅长大,却“寻不出纤毫渗漏者”。[1]85严谨性的最高要求是整部作品一气呵成,浑然天成。李渔赞扬《三国演义》“行文如九曲黄河,一泻直下,起结虽有不齐,而章法居然井秩。”[3]341他曾替朋友修改文章,但修改之后,很不满意,认为是“索瘢西子之面,着粪如来之顶,无益本来,徒自增其罪过,惟听材择可耳。以渔视之,即使补缀有当,终不若仍旧贯之为一气呵成。”[3]447李渔这样说也许有自谦的成分,但在本质上是他自己的真实想法,修改别人的文章很难在各个方面都与原作协调一致,即使是修改成功,也很难达到“一气呵成”这种结构上的最高境界。
要使作品结构严谨,整体的构思、“立主脑”等都是必不可少的方面。在具体的结构方法上,李渔则提出了“密针线”的主张:“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一节偶疏,全篇之破绽出矣。”[1]20要想结构严谨,全在针线紧密。“密针线”主要指情节、事件、人物之间的照应、联系。“每编一折,必须前顾数折,后顾数折。顾前者,欲其照映,顾后者,便于埋伏。照映埋伏,不止照映一人、埋伏一事,凡是此剧中有名之人、关涉之事,与前此后此所说之话,节节俱要想到,宁使想到而不用,勿使有用而忽之。”[1]20李渔的“照映埋伏”有现在结构论中伏笔照应的含义。如《巧团圆》一剧,姚克承与曹小姐的婚姻由一把玉尺相联系。在剧本开始,姚克承曾梦登一小楼,一老人谓此玉尺与他的婚姻有关。后来姚克承将此玉尺赠给姚小姐,后又凭此玉尺将被乱军装在麻袋中出卖的曹小姐买回,最后两人又终因玉尺而结为夫妻。剧本虽然充满巧合,但由于有玉尺前后照应,并不使人觉得牵强。不过,李渔的“照映埋伏”又不仅仅指结构上的伏笔照应,它还含有情节、事件、人物之间相互协调、互相照应的意思。李渔曾批评《琵琶记》中赵五娘剪发一事,认为没有顾及到张大公这一人物,有关文字,“并无一字照管大公,且若有心讥刺者。”[1]20这有损急公好义的张大公的形象,也不符合五娘的性格,是剧本的一个瑕疵。因此,李渔要求作者创作时要瞻前顾后,把每一细节都考虑清楚,以免出现结构上的疏漏。
此外,李渔提倡与运用的结构方法还有线索的清晰、结构的紧凑和构架的匀称。
线索清晰、结构紧凑与李渔“立主脑”“一人一事”的结构原则有着密切的关系,是这一原则在结构上的具体体现。线索清晰故事便能井然有序,即使内容丰富也能杂而不乱,结构紧凑则使事件、人物联系紧密,少出漏洞。李渔的剧本、小说大都以一组人物和一条矛盾冲突线索贯穿始终,结构紧凑集中。如《无声戏》中的《美男子避惑反生疑》。整篇小说以赵玉吾与儿媳何氏,蒋瑜与未婚妻陆小姐以及知府一组人物为核心,以一个扇坠为贯穿线索结构故事。赵玉吾送给儿媳一个扇坠,扇坠被老鼠拖到隔壁的蒋瑜家,知府以此断定蒋瑜与何氏有私情。赵玉吾让儿子与何氏离婚,并为了报复,故意将因嫌蒋瑜贫穷早有悔婚之意的蒋瑜的未婚妻陆小姐娶为儿媳。后真相大白,知府还了蒋瑜清白,并把已经离婚的何氏配给蒋瑜。整篇小说一环套一环,线索清楚,结构紧凑。
构架匀称指结构的均衡、对称。但匀称、对称又不意味死板,而是匀称中有变化,对称中有灵动。李渔不仅是一个文学家,也是一个建筑师、园艺家,深谙艺术中的均衡、对称与变化原则。李渔吸收建筑、园艺的美学原则,运用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使自己的作品在谋篇布局上均衡、匀称而又富于变化。如他的剧本《风筝误》,写了戚友先的放风筝,又写韩世勋的放风筝;写了詹烈侯与掀天大王的交战,又写韩世勋与掀天大王的交战;写了韩世勋假冒戚友先题诗,又写詹爱娟假冒詹淑娟相会;写了戚友先的大闹洞房,又写韩世勋的大闹洞房。但这些情节虽然相似,却不雷同。在这些相似的重复之中,情节得到了推进,人物性格在对比中得到了更加鲜明的表现。再如小说《丑郎君怕娇偏得艳》,写阙里侯连娶三妻,但三妻都因嫌他丑陋,身有恶臭,不肯与他同房。最后第三个妻子吴氏想出三人轮流陪睡,同房不同床,只在要紧的一刻在一起的主意,大家才相安无事。最后儿子中举,阙里侯活到80岁。作者刻意在重复中求变化,在相似的情景中写出不同的情由,写出人物的不同的性格,表达出自己美妻配丑夫,是理之常,处常则应相安的思想(这一思想是否值得肯定姑且不论)。
应该指出的是,李渔对于结构的讨论主要是从戏曲创作的角度进行的,但实际上,李渔的结构思想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不仅适用于戏曲创作,也适用整个叙事文学的创作,李渔的小说创作就贯彻了他的这些思想。现在看来,李渔的叙事结构思想有其不完善的、片面的地方,但在当时,却代表了叙事结构特别是戏曲结构思想的最高成就,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值得重视的。
[1]李渔.闲情偶寄·演习部·授曲第三[M].杜书瀛,评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
[2]赵炎秋.李渔文学创作观试探[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0(6).
[3]李渔.李渔随笔全集[M].艾舒仁,编.冉云飞,校点.成都:巴蜀书社,2003.
On Li Yu's thought of Narrative Structure
ZHAO Yanqiu
(School of the Literatur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410081,China)
Li Yu thinks highly of the narrative works structure.The nanative structure of Li Yu has three meanings.The first is the structure on the meaning of design of the whole work;the second is the structure on the meaning of subject;the third is the structure on the meaning of composition.From the point of Chinese Opera,Li Yu's discussion on structure reflects his thought has universality and can apply to the creation of literary works.
Li Yu;narrative works;structure;Chinese opera
I206
A
1674-117X(2011)03-0049-05
2011-03-21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03BZW004)
赵炎秋(1953-),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比较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