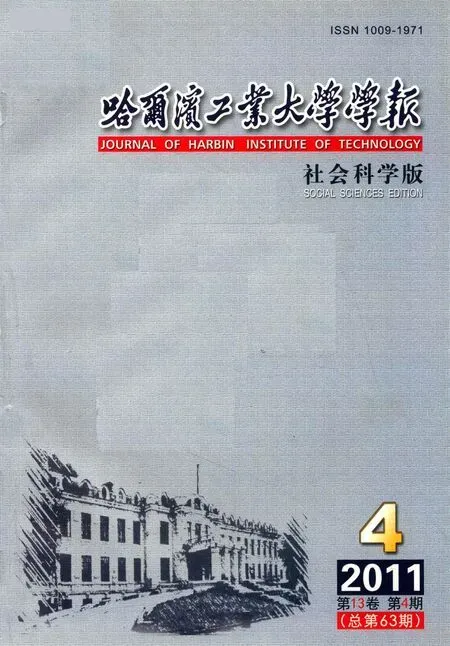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中的鲁迅
张德旺
(哈尔滨工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哈尔滨 15000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中的鲁迅
张德旺
(哈尔滨工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哈尔滨 150001)
鲁迅通过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明确了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方向,确立了唯物史观的阶级观点,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鲁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一是全面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提出对其主导精神线索专制主义的原则;二是对外国文化放手实行“拿来主义”,分别采取占有、使用、存放、毁灭等政策;三是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构成了中共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雏形;四是提出应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他们必须实行与工农大众革命实践结合。鲁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活动有三个特点:自觉的主体意识、彻底的求实精神、毫无顾忌的原则性。
鲁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个文化现象引起笔者的关注:一方面,毛泽东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对鲁迅有中国新文化的“主将”、“旗手”,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共产主义者”,其“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其“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结晶”等崇高评价;①见《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168页;《进一步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载《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169页。另一方面,迄今为止国内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诸多论著,却毫不言及鲁迅。②有代表性的论著如唐宝林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庄福龄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课题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上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宋士农等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笔者浅见,后者不符合历史实际,本文进行初步探讨,请学术界指正。
一、鲁迅是否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海内外很多学者持肯定态度;③有代表性的论著如林志浩:《鲁迅研究》(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张宁:《无数人们与无穷远方:鲁迅与左翼》,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孙晨:《鲁迅与马克思主义》,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李欧梵著,尹慧珉译:《铁屋中的呐喊》,岳麓书社,1999年等。一些学者持否定观点,如美籍华裔学者周策纵说:“50年代中期胡适先生曾告诉我:‘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今言犹在耳,恍如昨日也。”[1];还有的说鲁迅由“全盘性反传统”走向“虚无主义”,实际也完全否定鲁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④原话是,鲁迅“全盘性反传统立场与他选择性地接受了一些中国传统道德价值的事实,两者之间存有无可疏解的基本矛盾”,“这种彻底的绝望之感很轻易地使他走向‘虚无主义’……没有什么是可信赖的、可相信的”。林毓生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263页。笔者陋见,否定观点不符合历史实际。
所谓一个人是某某主义者,主要是指其以那一种理论学说为自己的政治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指导思想。所以强调“指导”,因为在各种文化学说思潮交会撞击激烈、新陈代谢迅速的近现代世界,特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存在诸多矛盾现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立物的学说如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却在中国还有某种程度的反对封建主义甚至反对帝国主义的积极作用,与马克思主义有反封建的同盟关系。这决定了近代中国以一种学说为指导思想,成为某种主义者,而丝毫不受其他思想学说影响者少见。鲁迅就是如此,他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现实斗争中,吸收了中国古代、近代和西方近现代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成果,并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与改造,形成了自己博大深邃的思想。
正如瞿秋白1933年指出的,鲁迅“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2]。这里的“战斗”、“经验”、“观察”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鲁迅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解决了他在革命实践中遇到的一系列重大根本问题。
这首先是中国革命、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前途问题。鲁迅是在紧密结合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的不断了解和认识中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这表现在前期鲁迅虽然有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坚定信念,有即使不能胜利,牺牲一切包括宝贵生命也要不懈战斗的钢铁意志;也对中国前途光明、革命胜利充满希望,在小说《药》的结尾,革命者夏瑜的坟上出现了“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尖的坟顶”[3]447-448,表现出后继者正在不懈奋斗;但对于革命斗争的最终奋斗目标并不清晰:《野草》中屡屡描述战士无私无畏,一往无前奋勇进击,可是“好的故事”等展现的未来却是朦胧的,就都表明了作者的这种思想状态。这同李大钊在1918年发表的《Bolshevism(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文中热烈拥护十月革命,宣布“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是有明显差别的。但随着对俄国十月革命的了解,鲁迅态度日益明朗。1927年4月10日在广州发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一文,称赞“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深知道历来革命成败的原因,自己又积有许多经验”,毫不“因胜利而使脑筋混乱”,看清“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这实际是鲁迅向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阵营明确提出了学习俄国革命先进经验,警惕作为“革命的策源地”和“后方”的广州发生严重危机的积极建议[4]162-163。
同时,鲁迅也关注有关苏联的反面介绍和评价。1928年,他购买了拉姆斯著《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和“国际政治囚犯救济委员会”发行的《苏俄の牢狱》,后者收入了被流放的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等反对派成员的书信。30年代初,鲁迅又购买了几种观点不同的苏联游记[5]。1936年2月,鲁迅婉拒了胡愈之转达的莫斯科的赴苏联休养的邀请,最后说:“苏联国内情况怎么样,我也有些担心,是不是也是自己人发生问题?”[6]胡愈之说,鲁迅这“是指当时斯大林扩大肃反,西方报刊大事宣传,他有些不放心。这也是他不想去苏联的原因之一。”[6]这有力证明,鲁迅对苏联迫害政治异见者是有一定了解,也有一定看法的。
但是,鲁迅对苏联总体上肯定态度是坚决、鲜明的。他1932年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明确指出,苏联“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3]462,“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的命运的人”[3]462,其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3]430;但他这期间又明确指出:“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3]233。这表明,鲁迅是从人类发展的历史高度,肯定了苏联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从而表明了鲁迅对于共产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坚定信念;同时对这个进程必然有曲折有清醒估计。今天,苏联已经成为历史,其30年代后期“大肃反”等严重问题也为人们知晓,但是,苏联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很长时期内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心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是一切实事求是的人们应承认的。有人以此为由,否定鲁迅是“一个真正的独立思想者”,实际否定鲁迅向马克思主义转变,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
鲁迅还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克服了进化论的偏颇,确立了唯物史观的阶级观点。从严复发表《天演论》之后,进化论就成了中国先进分子救亡图强的思想武器。但其局限性也逐渐暴露,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关注。鲁迅则是被四一二政变中反革命势力的极端残暴所震动,开始全面审视这一问题的:“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4]362,“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7]。他深刻感受到了阶级斗争的严峻残酷,“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3]5从此,鲁迅认清,任何人“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会去种兰花”[3]204。这构成鲁迅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同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中,鲁迅进一步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文艺理论。他后来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3]6。鲁迅特别强调,“我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3]209。联系鲁迅同创造社、太阳社奋斗目标一致,不难看出,鲁迅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期盼整个革命文艺队伍,都能通过论战和学习,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进而推进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健康发展的深刻用心。
可见,鲁迅是在积极参与现实反帝反封建的激烈斗争中,在不断解剖别人更不断解剖自己的思想斗争中,实现了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所说的,从进化论走向唯物论,从个性主义走向集体主义的伟大思想转变,实际从激进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化为共产主义者。
鲁迅本人实际承认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这集中体现于他对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对自己“从进化论进到唯物论,从封建绅士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战士”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转化过程的评价的赞同。他赠瞿秋白录清人何瓦琴句的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病重期间坚持编辑出版瞿秋白的译作,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他对这个评价的认同。鲁迅还多次谈到自己思想的转变过程:“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唯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3]191;“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更好。待到十月革命以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现在苏联的存在与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产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并且增加许多勇气了”[8]18。这些话含义丰富深刻,实际是鲁迅简略勾画出了自己从激进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政治立场的心路历程。
鲁迅的这些转变,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获得了广泛认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以鲁迅为文化战线的杰出代表和领袖。1930年5月,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约见鲁迅,请他发表公开声明支持中共中央;瞿秋白、冯雪峰同鲁迅一起直接领导了左联的反国民党文化“围剿”斗争;身陷国民党政府狱中的方志敏把《可爱的中国》等文稿托鲁迅转交中共中央,处境困顿的成仿吾请鲁迅帮助找中共中央建立联系。鲁迅逝世后,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对鲁迅作出了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新文化旗手、共产主义者等崇高评价。国际无产阶级文化界也视鲁迅为自己的杰出代表。1931年8月10日,《文艺新闻》第2号刊登一则纽约通讯,报道有一百三十多个团体的二百多位代表参加的纽约工人文化同盟代表大会推选鲁迅和高尔基、巴比塞、辛克莱等为大会名誉主席,宣布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拥护国际文学会,援助矿工罢工等[9]37。鲁迅逝世,法捷耶夫、富尔曼诺夫、肖洛霍夫等苏联作家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到参加世界反侵略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住处,对鲁迅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法捷耶夫说:“我们不久前失去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人高尔基,今天又失去了同样伟大的作家鲁迅,这是全世界劳动人民不可弥补的损失。鲁迅对于人物的刻画,对于事物的剖析,其深刻性几乎是无可比拟的,俄国作家中只有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匹敌。但是,鲁迅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对人民的深刻信任,特别是对新生力量的信任,只有高尔基可以同他相比。”[9]48相反,国民党政府则一再通缉鲁迅,严厉查禁其论著。鲁迅逝世后,一个以共产主义为敌的中国青年女作家公开提出“取缔鲁迅宗教”,声称“左派利用之为偶像,极力宣传,想将这个左翼巨头的印象,深深打入青年脑筋,刺激国人对共产主义之注意”[10],也从反面有力证明了这一点。
已故日本学者竹内好提出了一个极为深刻的问题:鲁迅“怎样地不变”,①参见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原话是:“我所关心的不是鲁迅怎样变,而是怎样地不变。他变了,然而他没变。”对于本文来讲,当是鲁迅以什么始终如一的思想基点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追问。个人浅见,鲁迅是以为中华民族和人类彻底解放、特别是为中国新文化建设贡献一切的精神为基点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这是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动力之源,是他一生不变的根本所在。这不但同鲁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毫不矛盾,而且有力表明了鲁迅这个转变的历史合理性与基础坚实性。
二、鲁迅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迅速兴起,实际构成了中国革命一个成就显赫并首先取得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倒性优势的重要领域。鲁迅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化的旗手,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上海文艺之一瞥》、《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等重要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化作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贡献,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系形成发展史的一个特色鲜明不可或缺的突出发展环节和重要组成部分,②参见张德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形成过程探析》,载《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6期。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四点:
其一,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主导精神线索专制主义全面分析,并提出如何对待它们的原则和策略。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居主导地位的专制主义进行了前无古人、迄今仍无人超越的深刻批判。他用“吃人”揭示专制主义制度及其思想的本质,用“瞒和骗”、“卑怯”、“懒惰”、“无特操”、“精神胜利法”等准确形象地概括出了专制主义思想、制度造成的国民性或民族性格的痼疾。他明确指出这些影响已经内化成中国社会的“习惯和风俗”,“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土建塔,顷刻倒坏”[3]224。至今仍可谓振聋发聩,启人深思。
鲁迅深刻指出了专制主义痼弊及其影响的严重性、长期性、顽固性,“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3]235;中国常常是“改革一两,反动十斤”[3]224。
为此,鲁迅明确提出:“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3]235他具体说明,这个实力首先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改造,“文化的大众化”,“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11]350;还必须根本改造经济制度,如男女平等,首先就要使女子“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3]598;而在文化战线更特别要有“韧”,强调“要在文化上要有成绩,则非韧不可”[3]237。
鲁迅敏锐地抓住封建专制主义在革命队伍中的影响指出,“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革命的大人物”[12]1000,“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势,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8]529-530。鲁迅非常清楚,这些是革命队伍的内部问题。他拒绝参加“国防文学”提倡者发起的文艺家研究会,尖锐批评它有“非常浓厚的含有宗派主义和行帮情形”,但仍明确肯定该会“是抗日的作家团体”[8]530。鲁迅如此严肃地提出问题,绝非个人意气,而是因为这是革命文艺队伍中“代表着某一群”[12]1028的严重问题的苗头,实际是向革命文化战线乃至全国人民提出了高度警惕封建专制主义腐蚀革命队伍的问题。1936年4月,冯雪峰从陕北到达上海,鲁迅用幽默的语言对中国革命胜利后这些问题可能恶性发展表示了深切担忧。①李霽野1936年12月在《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说:“讽刺着‘革命文学家’对于自己的攻击,先生故作庄重的向F君(指冯雪峰——引者)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F君连忙摇头摆手的说:那弗会,那弗会!”刘运峰编:《鲁迅先生纪念集》(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366-367页。鲁迅郑重强调,把这些事实记录下来,“其实也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②见《致曹靖华》,《鲁迅书信集》(下卷)1003页,整句话是,“我真想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这其实也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历史的发展不幸为鲁迅所言中。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那些极左人士让人抹煞个性自由而屈从团体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反倒是鲁迅的将个人的自由与团体的利益打成一片的追求,更切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是其他一切人自由的条件’的那个‘联合体’”[13],个人浅见,这个论断符合历史实际。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绝非如一些学者断言的“全盘否定”。鲁迅指出,“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苦,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12]1064,“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8]118。对孔子,鲁迅在批判其作为儒家学说消极面总代表的同时,仍肯定他的入世思想、进取精神,称之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8]521。鲁迅热烈赞扬这些宝贵精神正在一二九运动中发扬光大:“刚刚接到本日的《大美晚报》,有‘北平特约通讯’,记学生游行,被警察水龙喷射,棍击刀砍,一部分则被闭于城外,使受冻馁,‘此时燕冀中学师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纷纷组织慰劳队,送水烧饼馒头等食物,学生略解饥肠……’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鲁迅充满信心地断言:“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8]435
鲁迅批判传统文化弊端是为了建设新文化。他指出,“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建设却是麻烦的事”[3]233-234;新的阶级及其“创业的雄主”,“自然也有破坏,这是为了未来的新的建设。新的建设的理想,是一切言动的南针,倘没有这而言破坏”,“不过是破坏的同路人”,“而言保存,则全然是旧秩序的维护者”[11]356。鲁迅指出,“左翼文艺,只靠发宣言是压不倒敌人的,要靠我们的作家写出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来”[14];“我们是要有东西的,因为这于我们有用”,“如果我们文学或科学上有东西拿得出去给别人,则甚至于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政治运动上也有帮助”[3]237。
其二,对外国文化实行“拿来主义”。
鲁迅明确提出对外国文化要实行“拿来主义”,就是“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如同一个穷青年得到了一所大宅子,既不能采取“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清白”的全面排斥;也不能“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烟”,而是自觉地“占有,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变成新宅子”[8]39-40。
怎样占有、挑选,使用、存放、毁灭呢?鲁迅说,“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就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西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烟枪和烟灯“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可以请她们各自走散”[8]39-40。显而易见,鲁迅用鱼翅、鸦片、烟具、姨太太等各界民众耳熟能详的名词指陈外国文化中有益、有益同时有毒、毫无益处并且有害等各类成分,应分别采取大胆吸收使用、弃糟粕取精华、正当有序消灭的政策。鲁迅还提出剜“烂苹果”,“这苹果有着烂疤了”,“倘不是穿心烂”,就要善于“剜烂苹果”,吸收其有益因素加以利用[15]。这实际是最早明确提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对待一切剥削阶级、特别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理论原则,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正确处理中外文化关系指导思想的重要理论先导。
鲁迅指出,实行这种“拿来主义”首先要划清我们主动“拿来”和外国任意“送来”的界限,终结西方列强给中国“送来”“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对中国进行敲骨吸髓的经济掠夺和精神奴化的现状。这实际是明确指出了国家政治、文化主权是对外国文化实行“拿来主义”的前提。这个问题的真正全面解决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等,“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16],才有对外国文化的真正的“拿来主义”。
鲁迅强调说明,中国人民要“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发扬“汉唐气魄”,高度自信独立自主地对待外国文化,而绝不照搬任何外国。他热情肯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及其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重大意义,但在回答美国记者斯诺“你认为俄国的政府形式更加适合中国吗?”的问题时,仍坚定回答:“没有疑问,我们可以向苏联学习。此外,我们也可以向美国学习。但是,对中国来说,只能有一种革命——中国的革命。我们也要向我们的历史学习。”[17]这是何等深刻全面的文化自觉!
其三,提出了动员全国文化界奋起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纲领性口号,直接推进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理论的发展和成熟。
鲁迅指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大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其首要之义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8]590。他说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主要是对前进的一向称左翼的作家们提倡的、希望这些作家们努力向前进”,“也可以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们也来努力向前进”;“但这不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标准”,它应该也可以与包括“国防文学”等在内的抗日口号“并存”[8]533。
鲁迅指出新文化必须是“民族”的、“大众”的,把两者都提到了文化革命纲领的政治高度和理论高度。他认为新文化必须是“民族”的,就是在政治上要反对帝国主义,当前就是使“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8]530。鲁迅强调,坚持“民族”的新文化原则,还要珍惜中国的优良传统文化,他指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传承,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11]355,“唯有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我们的文学的发展才有希望”[3]301,在学习借鉴外国的“新法”同时,还要“加以中国旧日之所长,还有开出一条新的路径来的希望”[3]6019;因为“古文化裨助着后来,也束缚着后来”[8]339;当然“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品中”,“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8]23,从而使我们的新文化“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11]185。
鲁迅大力倡导新文化必须是“大众”的。他深刻指出,是劳动人民创造了文化:“我们祖先”,“那时大家抬木头,其中一个叫道‘杭育杭育’”,“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记下来,这就是文学”;劳动人民口口相传的文学创作是新文化的一个重要来源,摄取民间文学的营养“而起一个新的转变”的事例,“常见于文学史上”[8]94。鲁迅号召:“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做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11]349。鲁迅强调,新文化创作应采用大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如连环图画所以能早已坐进“艺术之宫”,“在艺术史上发光”,根本原因就在于“大众是要看的,大众是感激的”[3]448-449。鲁迅这些论断,不仅是对五四以来文化大众化问题一系列讨论的科学总结,也为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系统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实际构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雏形,至今对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重大指导作用。
其四,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
鲁迅多次大力呼吁“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3]236。联系他是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讲这些话的,可以看出他强调的是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文化队伍。他指出,这支队伍新的战士应该有较高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水平,“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有一切“目的都在工农大众”的革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特别应该积极参加革命实践,“和革命共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最近左联提出了‘作家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就是对于这一点的很正确的理解)”[3]236,“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勇于承担“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经受革命不可避免的“痛苦”、“污秽和血”等考验[3]233-238。
鲁迅尖锐指出,当前左翼文化队伍中存在的不适应革命事业发展需要的缺点,“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12]663,“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出卖朋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这大约是各国都有的事。但我看中国较甚”[12]685。鲁迅特别反对“分裂,高谈,故作激烈等等”[12]685,因为“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3]233-234。这些观点,同后来毛泽东指出的,知识分子“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等著名论断的思想内涵基本内在一致[18]。这表明,实际是鲁迅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早提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必须与革命斗争实际密切结合的理论原则,不仅当时有力推动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健康成长,至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有直接根本的指导作用。
三、鲁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活动的突出特点
一是自觉的主体意识。鲁迅接受、运用马克思主义,是基于他始终如一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切为人民大众的彻底献身精神;基于他自觉集中身体力行并不断升华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特别是“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人格力量;基于他对为中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不懈奋斗的历史经验及其发展规律的全面冷静考量。鲁迅在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在《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论文中深刻阐释的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对个性独立、思想自由的执著坚持,就已经大大突破了激进民主主义革命派的思想界限,接近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所以,鲁迅成为近代以来空前的中华民族主体意识的杰出代表,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任何思想学说,都不是顶礼膜拜,而是“放手拿来”,为中国人民所用,在实践中吸收、检验、改造,使其成为中国人民推进中国民族解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武器。他既同形形色色的封建地主阶级复古倒退、资产阶级崇洋迷外等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展开了坚决斗争,也对革命阵营内部各种错误思潮、特别是有封建专制主义底色的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进行了严厉批判。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价值观解剖别人,同时更严格更高标准地解剖自己。在鲁迅身上,极为全面深刻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代表西方最先进文化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的交会融合,表现出中国人民一方面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革命、建设、改革的指导思想,一方面以独特的精神力量、政治智慧等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文化底蕴。
二是彻底的求实精神。鲁迅接受、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推进其中国化,是在对中国国情不断深刻认识、全面把握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这个关系中国革命全局的基础性问题上,鲁迅的认识达到了当时包括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胡适、梁启超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未能达到的思想深度,瞿秋白称之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无论是中国“最黑暗的压迫和剥削制度”及“政治经济关系”;来自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的“刽子手主义和僵尸主义的黑暗”,还是来自“满清士大夫、老新党、陈西滢们”种种错误甚至反动思想,“小私有者的庸俗、自欺、自私、愚笨,流浪赖皮的冒充虚无主义,无耻、卑劣、虚伪的戏子们的把戏”等等,都“不能逃过他的锐利的眼光”。鲁迅坦承自己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不多,而主要是通过实践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发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的事实”[19]。他尖锐指出,要特别警惕“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3]480的危险。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鲁迅言行一致,用自己不懈奋斗、忘我牺牲的实际行动及其杰出文化成就,树立了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巨匠的辉煌丰碑。如有学者指出的:“鲁迅所以有别于那些善变的人物,正因为他的思想力量是以伟大的人格力量作为基础。没有人格力量印证和血肉融化的思想,那思想也就变得苍白无力。”[20]鲁迅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特别是中国文化革命实际的结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
三是毫无顾忌的原则性。这集中体现在鲁迅坚持真正做到了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坚持原则,在重大问题上绝不妥协的“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21]。这源自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政治立场和坚持真理的科学态度,是他深刻认识中国历史和现状的文化自觉。他始终对中国各个政党都认真分析、采取不同态度。对国民党的反动腐朽政策,鲁迅针锋相对,坚决反抗,彻底揭露。对中国共产党,他坚决拥护其理论纲领、政治理想,自觉地为其纲领路线忘我奋斗,公开宣布,“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8]529;他还积极承担了替国民党监狱中的著名共产党人方志敏转送重要文稿给中共中央,帮成仿吾接上党组织关系等本属于党内人员的重要事务。但对中共某些组织及其领导人存在的来自苏联斯大林模式和中国政治、文化痼疾的种种错误影响,鲁迅坚持原则进行了不懈斗争,如前述“两个口号”中的论战等。在这一点上,他不参加党组织无形中构成了自由发挥斗争意志的独特优势。因为如果参加了党组织,其成员就必须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就会出现个人无条件服从组织,即使坚信自己的意见正确,也要按照组织原则行动的情况。鲁迅这个特点主要是用实际行动体现出来。
鲁迅曾在1935年9月12日就萧军是否参加“左联”的问题答复胡风说:“现在不必进去”,“近几年,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22]211。有些人以此说明鲁迅反对别人参加共产党,证明鲁迅对共产党的否定态度,如胡适断言:仅凭此信,20世纪50年代“鲁迅若不死,也会斫头的”[23]。笔者认为这些判断不符合历史实际,因为鲁迅讲的“不必进去”是“指萧军参加‘左联’事”[22]212,希望他不要搅进各种纠纷,集中力量搞出创作实绩,而不是反对萧军加入中国共产党;鲁迅表述的是对当时周扬等“左联”领导者的宗派主义等错误言行强烈反感,但鲁迅同时又清醒地肯定,这种反感是革命阵营内部矛盾,是革命同志之间的不同意见。他在同一封信接着说明;“我的意见,在元帅(指周扬等——引者)看来,一定是罪状(但他和我的感情一定仍旧很好的),但我确信我是对的。将来通盘筹算起来,一定还是我的计划成绩好”[22]211。所以,这封信绝不是鲁迅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自己同共产党关系的证据,而是鲁迅真正站在党的路线和中国革命事业长远根本利益的立场处理问题的表现。
综上所述,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所面临的诸多基本问题,如前进方向、发展方针、主体构建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独具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开掘、消化和运用,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当代化的宏伟事业。
[1]谢泳.胡适还是鲁迅[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35.
[2]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G]//鲁迅杂感选集.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9:15.
[3]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4]鲁迅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5]姚锡佩.鲁迅力求了解苏联的真相——鲁迅藏书研究[J].鲁迅研究月刊,1995,(12):53-55.
[6]严家炎.鲁迅晚年思想寻踪[J].香港:明报月刊,2002,(9).
[7]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8]鲁迅全集:第 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9]葛涛.鲁迅文化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329.
[11]鲁迅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12]鲁迅书信集:下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13]高旭东.高旭东讲鲁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58-159.
[14]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78.
[15]鲁迅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298-299.
[16]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4.
[17]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583.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41-642.
[19]鲁迅书信集:上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444.
[20]王元化.思辨短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91.
[21]黎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55.
[22]鲁迅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23]耿云志,等.胡适书信集(1950—1962):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262.
[责任编辑 王 春]
Lu Xu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 in China
ZHANG De-w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arbin 150001,China)
Through the study of Marxism,Lu Xun found the direct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and established a class point of 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and he had realized his conversion into the Marxist.Lu Xun made contributions to Marxism in China as follows:1.After his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he proposed the principles of absolutism of leading spirit clue;2.He perform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taking-in foreign culture,such as possession,use,storage,destruction and other policies;3.He proposed"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national revolutionary war,"which constituted a prototype of the CPC program of new democratic culture;4.He suggested that a new large group of soldiers should be created who should be implemented with the practice of revolutionary workers and peasants.Lu Xun's promoting the activities of Marxism in China had three significant features:subjective consciousness,thorough and realistic spirit and principles of boldness.
Lu Xun;Marxism;sinicization
D231
A
1009-1971(2011)04-0061-09
2011-05-09
张德旺(1946-),男,河北景县人,教授,从事五四运动史、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