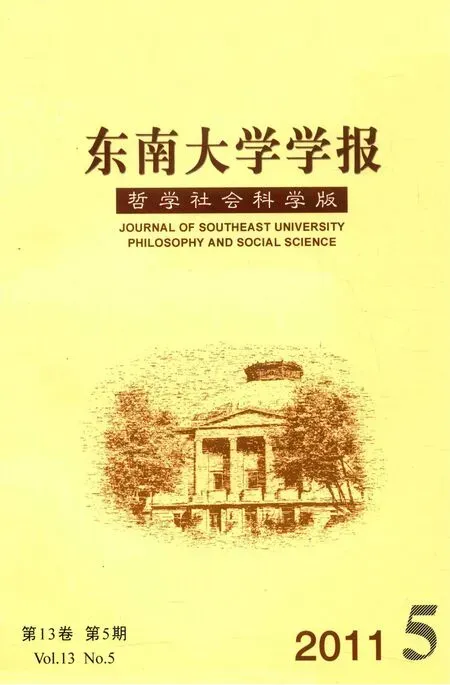巴洛克科学中缺席的观察者:从开普勒光学到笛卡尔怀疑论
Ofer Gal ,Raz ChenMorris著
郭 飞3,吕乃基4译
(1澳大利亚 悉尼大学;2以色列 巴伊兰大学;3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310018;4东南大学STS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96)
巴洛克科学中缺席的观察者:从开普勒光学到笛卡尔怀疑论
Ofer Gal1,Raz Chen-Morris2著
郭 飞3,吕乃基4译
(1澳大利亚 悉尼大学;2以色列 巴伊兰大学;3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310018;4东南大学STS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96)
历史上光学与视觉理论的分离是个矛盾过程,它反映的不是人的眼睛从视觉对象中解放出来,而是由于对眼睛作为自然物质的光学工具的认识不断加深而观察者从光学中消失。17世纪,人类观察者逐渐从光学文献中消失。开普勒信任来自遥远的图像而怀疑直接的感觉,这是一个视觉悖论。科学的观察使得观察者从光学中消失成为必然。笛卡尔怀疑论是这一悖论的认识论阐释。
观察者;光学;开普勒;笛卡尔
人类观察者在17世纪逐渐从光学文献中消失。光学与视觉理论的分离是个矛盾过程,它反映的不是人的眼睛从其对象中获得解放,而是观察者从光学中消失,其缘于对眼睛作为自然物质的光学工具的认识的不断加深。眼睛的同化(naturalization)导致人类观察者从自然中脱离。被同化的眼睛不再为观察者提供可见对象的真实呈现,眼睛仅仅是个屏幕,无任何认识论意义。因此,需要思维把纯粹的自然现象——平面图像——解释为无内在关联的、对象的模糊颠倒的反映。已有研究关注了观察者脱离的意义,但是对其视觉悖论的源头知之甚少,本文即关注于此。
一、开普勒:人工观察
当开普勒的《天文光学》(Paralipomena Ad Vitellionem)转向人工观察时,人类观察者退出光学。开普勒通过证明由暗箱获得的图像正是被观察对象的图像,确立了人工观察的主要工具——暗箱——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继而阐述了其基本原则,即通过物理模拟在小孔后面的屏幕上成像:从书的各个角出发的线穿过多边形孔的边缘,以孔的形状投射图像——对于书的每个角都是孔型图像。书的四个角产生的图像以颠倒的顺序排列在地上;从书的每个角(理想地)重复此过程,许多孔型的图像被投射到地上,以书的(颠倒的)样式排列。
开普勒光学的新意不是基于暗箱的小孔像现象,也不是以交线方式的叙述。然而,这是开普勒从透视主义者那里获得的好处。对于透视主义者,小孔像不仅仅是其光源的可靠投射,也是太阳的独特呈现。圆形图像不是由太阳或光所致,而是太阳的真实形状或光的恰当散播;图像的圆形是其真实性的象征。博切姆(Pecham)解释说,球形与光有关,光因此自然地向这个形状移动。[1]70-71
光源与图像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及这种联系所保证的呈现的精确性,完全在开普勒的叙述中消失。小孔像的圆形并不独特:如书的实验所示,矩形物体产生矩形图像。小孔像不呈现光:用穿过孔的线模拟光,但是投射在路面上的图像具有任何对象的性质,而不一定是发光体(例如书)。对开普勒而言,投射的可靠性不依赖于完全信任被投射物,而依赖于对投射物理过程的理解。开普勒发现,不能期待这样的信任:地面上书的形状由部分重叠的“图形”的“窄行”构成,不仅是倒立的图像而且其边界模糊。另外,这些光斑是缝隙的投射。随着屏幕与缝隙的距离以及光源图像与屏幕的距离分别增加,它们被合并在一起。开普勒的“图像”与光源无相似之处,路面上书的完整、光滑、直立的感觉是头脑中的构想。
二、天文学的挑战
开普勒的兴趣是工具的合法化而非工具的消失,其《天文光学》要保持天文学的尊严,征服恶意的怀疑,他在这里表达了一个真实的忧虑。16世纪末,Zabarella、Carbone、Ursus和Frischlin等人攻击天文学知识合法性的要求,指出“上帝把天体放在远离感觉的地方,使我们无法找到原则去证明它们……无法发现……特定现象的原因”[2]。
天空太远而无法观察,这一观念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对于亚里士多德,这个距离意味着感觉不足以提供关于天体的证据。创新的天文学家迈克尔·迈斯特林(Micheal Maestlin)和第谷(Tycho Brahe)不得不承认没有人能够上到天空看到一切。
关于天的“原理”或“原因”的论断在天文学知识之外,但是不在开普勒的追求之外。开普勒在《新天文学》(Astronomia Nova)中宣称“物理学家,请侧耳倾听”,并提出一种侵入式的思考。眼睛对这一新的冒险所需的事实尤为不足,因为眼睛附属于头,通过头,眼睛附属于身体;通过身体,眼睛附属于船或房子,或附属于整个区域及可见的范围。开普勒认为,视觉在可移动物体方面的观点是错的,难以被具体化和情境化。既然没有人能带我们到达月亮或其他星星,开普勒就需要新的中介(agent)连接认识论的断裂,把图像从遥远的地方带回。
三、光和光学的转变
开普勒的中介是光。光弹离“不透明的媒介”落在“不透明的屏幕”上产生图像。若屏幕是眼睛,则视觉产生;但是眼睛并不独特,任何屏幕都可以。当光成为所有光学现象唯一的中介时,观察天体现象距离面临的认识论难题得以解决:光的数学性质,光线不腐烂而只传播,距离转化为观察的一个几何学分析要素。有了光,人工观察的认识论困境消失。路面上的图像倒立模糊,视网膜上的图像也如此。工具的可信不在于它不影响视觉,而在于它不比眼睛更糟。这一认识论成果促使光学从视觉科学转向图像生成的数学—物理研究。
传统光学的主题是人的视觉。[3]视觉是对可见物体的直接认识,这些对象与眼睛之间的交流——光学过程——显然是目的论的,它旨在为思维提供对象足够的图像。目的论在文艺复兴时期存在下来,总结了繁琐的光学。
光有兴趣成为视觉的必要条件,然而它不是主要的视觉中介。眼睛的分析提供了同一的意向性的确证和视觉的真实性。正如博切姆指出:视觉通过冰状液体中万物的排列发生,正如对象的许多部分在外面排列一样;这是因为除非如此,否则眼睛不能清晰看到对象。博切姆认为,光学是关于视知觉的理论;任何理论如果不能充分解释被看到的图像,都是错误的。
开普勒摒弃此推理路线,认为光学过程是严格的光效应:当眼睛的瞳孔暴露在与到达的光线距离最近时,视觉产生。开普勒反对可见光线的做法对于光很重要:开普勒光学没有为意向性的中介提供空间。有了意向性的中介,眼睛的特殊地位消失。眼睛与任何仪器一样被动地接受“照亮”,眼睛不能仅仅比作“封闭的室”:角膜仅仅是透镜;视网膜仅仅是屏幕,本质上与纸或人行道相同;瞳孔仅仅是另外的孔,瞳孔替代窗户。
四、后 果
很难夸大开普勒光学变革的意义。图像由光产生仅仅是因果效应;偶尔弹离对象并落在屏幕上的光斑;没有形状或可见光线的参与。由此,视觉的意向性和目的论消失,光学作为其他所有科学的认识论根基也随之消失。
开普勒光学与传统光学都是认识论主导的,但在总体上不保证视觉知识的正确性,而旨在支持其新天文学的经验基础,尤其支持远距离的仪器观测;更为关键的是,通过传统光学提供的一般性的认识上的确证性,完成这一任务。毛罗里科(Maurolyco)为暗箱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开普勒为暗箱的使用取得合法性。既然光是所有图像的制造者,那么太阳与其投影之间的形状相似不再意味着连接它们的过程具有任何内在的认识论意义。信任图像是因为它们是纯粹自然因果过程的结果,此过程可通过实验和理论去考察。这意味着,观察星体与观察书一样可信,仪器的人工观察与眼睛观察一样可信。
然而,这种信任中的认识难题在于:若仪器不比眼睛更易于错误,那么眼睛对于错误与工具一样敏感。若“视觉的激情与照亮行为相伴”,那么视网膜上的图像与路面纸上的图像一样,不是对象的正确反映。开普勒拒绝繁琐的假定——万物的安排恰好与物体在外面的安排的一样,对他而言,视觉的真正结构清晰地表明视觉会经常发生错误。
视觉错误不是新内容,开普勒的新意在于新的错误概念。[4]在亚里士多德的范式中,错误由人的想象介入所致,视觉数据不容置疑。有了新光学,怀疑被引向被感知的图像。模糊不清是光学现象的一个特征,错误是“视觉真正结构”的结果。
开普勒不是怀疑论者,其光学要征服敌对的怀疑而不是加强这种怀疑。《天文光学》重视对视网膜像可靠性的解释。书的实验应用到眼睛上,证明屏幕的形状与投射对象相符。真正的怀疑不是来自错误的可能性,而是来自那些需要证明的事实。开普勒光学的主要分歧在于:眼睛能提供的所有对象是这些视网膜像,图像是与它们的原因无本质联系的结果,思维需要把光斑的自然对象解释为不同对象的印记。思维如何面临挑战完全是个谜。
这是一个视觉悖论:眼睛的同化使观察者脱离,对光学的深刻理解把视觉引向神秘。多年之后,开普勒在《宇宙和谐论》(Harmonices Mundi)中通过信任自然和人类智力两者之中被神圣赋予的数学基础,提出解决这一悖论的形而上学方案。然而,此悖论不能通过光学理论解决,开普勒把解决方案留给“自然哲学家”,在《天文光学》之外。
五、忧虑、办法和妥协:实践者
镜子、透镜和暗箱是通常的光学仪器。这些仪器在光学传统中的运用非常有趣:基亚姆巴蒂斯塔·戴拉·波尔塔(Giambattista della Porta)描述了一些实验“产生心灵的想象虚构”,自诩“常常用这些眼镜与最漂亮的美女一起戏谑”[5]355,356。德拉·波尔塔对光学装置的有趣使用基于仪器歪曲(distort)的能力,然而是眼睛在歪曲,这是其仪器产生的“心灵的想象虚构”,美女们的眼睛恰好接收到德拉·波尔塔的透镜和镜子传递的“形状”。眼镜等仪器对弱视有帮助,但是视力本身不能被虚构。落在视野中的图像正是思维获得的图像。
对开普勒而言,没有“思维的虚构”就没有视觉。视网膜上的画面是一个自然的对象,是瞳孔形状的光斑部分重叠的集合;思维觉察到它,构造出三维、光滑等高、直立的视觉呈现。视觉对象的独立存在先于被“灵魂法庭或视觉能力法庭”认为的存在,这种分离与德拉·波尔塔的观点完全不同。[6]虽然图像应该在表面出现、在空中摇晃,但是德拉·波尔塔从不认为图像在半空中。图像不存在而只是被感知,智力不能觉察到图像,观察对象可能是恰当或歪曲地感知,这种感知即图像。
开普勒把视觉呈现理解为构想,把自己置于德拉·波特的文化环境和光学魔术师之外,这很接近荷兰学派或“北方”学派中画家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7])——他们努力捕捉无修饰的视觉现象(技术处理之前的视网膜像)。文艺复兴时期高超的绘画工具如阿尔伯蒂风格(Alberti-style)的透视法,把理想的数学结构强加给本质上扩散的视觉现实。开普勒光学并不意味着使用这些工具是不诚实的或仅仅是风格上的一时兴致,它意味着他们的成功不是来自捕捉独立的现实或完美的视觉,而是来自呈现“视觉精神”的操作,这把倒立模糊的视网膜像转化为被感知并被很好描绘的对象。[8]44
从凡·爱克(Van Eyck)到贝利(Bailly)以及维米尔(Vermeer)的绘画作品中,都很信任纯粹视觉图像,然而要么导致透视错误(如《官员与大笑的女孩》[Officer and a Laughing Girl]中人物的相对大小),要么导致光线错误(如《代尔夫特印象》[View of Delft]中光的点缀和模糊的轮廓),要么两者兼有(如《倒牛奶的女佣》[Milkmaid])。[9]如“维米尔似乎对透镜的光学效应很满意,试图把它们在画布上再造出来”[10]58。对于德拉·波尔塔,暗箱仅仅是个仪器,最多比作眼睛;对于维米尔,它是再造图像的方式,这种图像由光在“视网膜的白色”上描绘出来;对于开普勒,眼睛和暗箱是同一回事。
六、图画和图像
眼睛的同化意味着图像产生与视觉感知之间的分离,光学不再是视觉理论。尽管承认“留给自然哲学家讨论”这种分离的后果,开普勒仍然尽力避免认为所有视觉经验都是人类思维的建构(fabrication)和歪曲。传统认为,“图像”的定义错误因为透镜或镜子的干扰。然而,开普勒认识到所有人的视觉都包含仪器般的干扰。因此,对比错误的“图像”,他必须建立一个先于所有视觉能力干扰的纯粹的物质实体。然而,图像至今都被看作理性的实体,现在物体在纸上或其他屏幕上的图形都被称为图画。
图像是个“理性的实体”,因为它是大脑“想象中的建构”。图画是真正的物理效应,能够在视网膜“或其他屏幕”上——最重要的不是未被仪器干扰,而是不经过任何思维加工。[11]
然而,本体论的不同并没减轻认识论的忧虑——所有视觉都在歪曲中并且其自身也是歪曲的。一个无干扰、无歪曲物理图像的现实存在,并不能提供无干扰无歪曲的视觉。开普勒的分析使我们再也接触不到无建构的视网膜图象,再也得不到对象或屏幕(除了视网膜)上无干扰的图像。开普勒认为,精神(mind)总是由被建构的图像所致。
七、席奈尔和耶稣会信徒的妥协
对于耶稣会信徒(Jesuit)的数学家克里斯托弗·席奈尔(Christoph Scheiner)而言,干扰及其认识论分歧值得注意。席奈尔在其著作《眼睛》(Oculus)中反对通过光把光学退化为图像生成理论,并尽力保持亚里士多德的视觉目的论:“为了能够看见,上帝创造了动物的眼睛,眼睛能释放一种获知可见对象存在的功能。事物被创造出来呈现给眼睛,不是通过眼睛发出到达对象的光线,而是通过来自对象进入眼睛的光线”。[12]2席奈尔的眼睛维持了(或回归到)眼睛的传统角色:视觉过程的目标,完成“获知可见对象出现”的任务。眼睛与“对象”的关系回归直接和自明,事物被创造出来呈现给眼睛。
席奈尔希望维持新光学经验性的成就,尤其在眼睛的心理学方面;但是他忽视了新光学关键的新意及其暗含的认识论困境。因此,他承认视网膜是眼睛的视觉敏感部分,承认晶状体具有透镜的功能,同时在视觉光线和万物的传统术语中解释了这些发现。他的第三本书解释了新光学——视觉光线如何刺激视网膜以及眼睛结构的原因。
像开普勒而又不同透视主义者传统,席奈尔的图画“被呈现在视网膜上”;晶状体折射而不吸收图像。这种观点折中了视觉的真实性:图画是物体折射的二维呈现。但是,席奈尔尽力使其最后的妥协加入新光学。《眼睛》中的视觉依然来自“可见对象”的“视觉光线”创造,其“好处”是确保清晰明确的视知觉。席舍尔在实验中用透镜和屏幕模仿晶状体和视网膜,光惟有在“万物”中才能被发现。更为重要的是,席舍尔的图画非常有序,远处事物的边缘落在眼睛的边缘;左边的出现在左边,右边的出现在右边,上面的出现在上面。
耶稣会信徒的认识论胜利来之不易。席舍尔想保持开普勒把晶状体看作透镜的分析,但是这暗含了视网膜像的倒置。于是,为了视网膜像右边的出现在眼睛的右边,左边的出现在眼睛的左边,他不得不假定当图像穿过晶状体时已经翻转,即,视觉光线在通过瞳孔进入眼睛之前穿过。席舍尔被开普勒的成就深深地影响,被他们的自然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暗示所困扰;席舍尔声称在《眼睛》的整个第二部分经验性地展示了光线在视角之前的穿过过程。
在融合新科学的过程中,努力保持亚里士多德认识论的心物一致是大约17世纪之交耶稣会关注的重点。[13]42-66席舍尔努力挽救视觉目的论,保持开普勒的视觉经验和几何基础:光线折射,图像倒转,但是眼睛在实现“由上帝安排好的”功能方面依然完全成功。然而,避开开普勒最冒险的转变——光学由视觉光线转变为光——需要付出代价。席舍尔未能从开普勒的成就中获得益处。
八、笛卡尔:彩虹的颜色
一些开普勒主义者的成功使耶稣会信徒的妥协落空。更好地解释新光学的一个光学现象是彩虹。[14]134,150天空彩虹的颜色对亚里士多德的视觉理论和光理论提出挑战。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颜色是可见的、有边界的物体的性质。因此,彩虹既不是透明空气的性质,也不是光的性质;因为光不是物体,没有边界。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光学家和亚里士多德的注释者。直到1619年,席舍尔的基督教同会霍雷肖·格拉西(Horatio Grassi)仍然认为“空气不能被照亮”。
开普勒早就意识到把光看作物质流,通过假定折射角度的比例使颜色是绿色、蓝色等,展示了解决彩虹之谜的一种方法。这种考虑使笛卡尔向开普勒宣布了自己“主要的光学”,并把光学作为其模型以支持数学的物理学。彩虹看起来像被太阳照亮的水滴,笛卡尔能够通过对着那些水滴的光线折射和来自那里并朝向我们眼睛的光线折射,运用开普勒光学解释彩虹的颜色。这成为笛卡尔数学分析的范式,提供了物理现象的因果理解。笛卡尔的分析与传统光学的启发关系不大。在其描述中,各种颜色都是折射的恰好角度的直接结果,不依赖于媒介。尽管数学地表达,但是这是一个物理假设,具体细节——哪个角度产生哪种颜色——可以通过实验完成。
沿着开普勒的做法,笛卡尔把光学转变为自然哲学的一个分支,保留了其数学语言和方法。因此,他把自己的任务定为解释物理细节——如彩虹的颜色在“连续带”中如何被组织起来,某种角度为何产生某种颜色。笛卡尔试图通过实验方式回答这些问题。尽管他有新的计划,但是其早期实验仍然植根于传统光学,不仅在水球的使用方面,而且更根本地,强调眼睛作为光学过程的关键场所:光线“朝向眼睛运动”,角度来自眼睛。
然而,一旦数学问题获得因果—物理的重要性,眼睛就失去了重要性:彩虹的角度与眼睛无关;光线落在不同屏幕上,从不同视角看起来相同。与眼睛一起消失的是水球,不再竭力模拟水滴和眼睛,笛卡尔用棱镜构造一个抽象的折射和投影的物理—实验模型。水球和水滴都成为折射面的特殊例子,一般由棱镜呈现;(屏幕的)视网膜通过“布或纸”呈现。因此,彩虹的颜色由光线的折射精确地产生,眼睛是纯粹偶然现象;颜色出现时的角度不需要特定大小,因为它们之中没有任何变化能够被改变。
笛卡尔把眼睛驱逐在外,完成开普勒传统光学的重新运用——视线的数学考察——落脚于光的行为。他的光学成了真正实验—数学的自然哲学,由此能够考察颜色的真正性质。但是,如果颜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视觉现象、不是对“通向眼睛”的视觉光线的修改,也不是物体形式的部分反射,那么颜色是什么?颜色如何产生?我们在颜色中感知到什么?笛卡尔以机械的术语对此做了回答:光粒子的运动,光的同质粒子直线匀速运动。折射和反射传递到粒子旋转运动,旋转的速度依赖于光线中粒子的位置;它与折射面之间的距离。旋转即颜色。这解释了折射的相同角度为何产生相同的颜色,以及相同的颜色为何总是位于相同的序列。
若颜色是光的修改而不是对象的性质,那么无法在真实与表面之间作出区分:真实的是它们的外观。只有在智慧的观察者那里,颜色、图像和其他光学现象才能既真又假;否则,它们只不过是因果效应。若光学不再研究认识论过程而仅仅研究光的传输及其效应,那么观察者则无立身之地。
九、开普勒主义者光学及其阵痛
开普勒彩虹理论的成功把人类观察者从光学中逐出。光学易于忽略真假之间的区分,因此被剥夺了认识论根基的地位。视觉呈现成为认识论忧虑的一个根源,这是开普勒企图回避的忧虑。笛卡尔声称,构成感官知觉的任何事物都不能要求它们与其呈现对象之间相像。亚里士多德主义—透视主义者传统的基本假定认为,感官承载着真实的标准。“哲学家”想当然地以为感官真实地呈现对象,以为它们把相像提供给思维。
笛卡尔努力克服开普勒尽力避免的怀疑论倾向。视网膜图象与原对象无相似之处。笛卡尔在《规则》(Regulae)中通过转向亚里士多德“视觉在头上”的隐喻,教读者如何在无相像的情况下想到感觉的呈现。他指出“感知的发生与蜡从印章中产生印记的方式相同”,这解释了我们感觉到的不仅仅是真实的对象,感觉同时与对象不可分割(即使对象很遥远),显然直接暗指亚里士多德《论灵魂》(De Anima)中的“类比”。但是亚里士多德没有使用印章和蜡的隐喻简单地“通过触觉去解释感知”。
对于亚里士多德,蜡的隐喻强调通过中介,物体与感官之间的直接接触,强化了感知的目的论、即时性和真实性。对于笛卡尔,这个隐喻传递了相反的观点:接触“不透明膜”的不是可见物质实体的性质,而是“光的多种颜色”。所有感觉都是真实的,它们提供被感知对象的非直接呈现。各种感知的一致性——对亚里士多德意味着视觉中远的对象与直接接触的对象一样被真实地呈现——对笛卡尔意味着视觉提供的图像与对象之间不相像,而至多是嗅觉和味觉。
笛卡尔在《规则》中表达了感知与其对象之间关系的不透明。感觉的对象与它们要呈现的对象无内在的对应,不同对象类型之间的关系既不透明也不自明,感觉需要解释。后来,笛卡尔强调感觉呈现的非透明性以及从感觉中解释和推断对象的必要性,用语法上的类比代替蜡的隐喻:“如果语言——通过人们的约定表示事物——对我们思考无相似之处的事物是足够的,为什么大自然不能形成某些迹象使我们有光的感觉,即使那种迹象与感觉无任何相像?”[15]276-290
蜡的隐喻暗示了对象与感觉之间是因果的和被干扰的,而不是本质的;几何的分析强调感觉与对象不相像;言语的隐喻使对象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完全随机:它不是本质的联系,也不是连接言语与事物之间的“人们的约定”。笛卡尔再次运用亚里士多德的比喻仅仅为了颠覆其意义。
亚里士多德指出,口头言语是心智体验的记号,书面语言是口头言语的记号,心智经验对所有对象相同。亚里士多德尤其把语言表达的情境性放在声音和书面文字上:对象在思维中呈现,精神意象对所有人相同。在亚里士多德的传统里,感觉的呈现是对象性质在媒介、感觉器官、心智和语言中一系列再造,再现的过程纯粹偶然,在词语命名精神意象的阶段——同一对象可以用不同言语来指称。笛卡尔认为图像与对象的关系像言语与概念的关系一样偶然。笛卡尔回到言语问题上再次指出这种偶然性与其几何学、语言学类比的“对象与其图像”之间的分离,旨在说明“我们的精神能够被其他很多不同于图像的对象(如符号和言语)所刺激,它们与指代的对象不完全相像,甚至在任何情况下图像必须在所有方面相似于呈现的对象,否则对象与其图像之间则无区别”[16]165。
这些是开普勒光学全部的认识论后果,笛卡尔对此做了阐释。产生图像的过程属于光。它本质上既不归因于眼睛也不归因于对象;它们两者仅仅都是偶然。这不是一个随机或随意的过程:视网膜上的同一图像可以被看作同一过程的结果,因此呈现同一对象,正如一个词语总是指称同一对象。但是,这种一致性是我们感觉中信任的唯一基础;就其本身而言,它只不过是原因与结果的一致性。从所有科学的认识论基础来看,视觉已经依赖于科学,作为其有限可靠性的保证。[17]
十、笛卡尔的怀疑
对笛卡尔的怀疑论有三种竞争性的解释。[18]第一种解释发现:我们可能完全错误的忧虑正是“现代状况”的真正核心。笛卡尔是这一传统激进的创新者[19]。在这种解释中,笛卡尔的怀疑是“追求确定性”失败的结果。笛卡尔为正确的知识设定的标准不低于数学的确定性;笛卡尔开始担忧我们是否能够知道一切。这完全不同于古代怀疑论——认为我们通常是错的,它来自笛卡尔关于精神的观点:封闭的内在空间,独特的实体通过“思想之幕”,在封闭的内在空间中“呈现”一种完全来自不同实体的世界。[20]
在第二种解释中,笛卡尔把其怀疑归因于古代怀疑论文本的重新发现和后来皮浪主义(Pyrrhonianism)的复兴。[21]超越对笛卡尔怀疑困境的争论,这种解释反对传统地强调笛卡尔的革命性的现代性(revolutionary modernity)。
第三种解释关注笛卡尔的怀疑论与其科学之间的关系,对感觉呈现现实所产生的失败到忧虑,这种忧虑暗含了其科学中的机械论哲学思想:物质对象的性质仅仅包括广延、形状和运动,完全不同于头脑中的想法。因此,“人类……系统不断地在日常感觉经验中被蒙蔽”[22]。其他解释展示了笛卡尔怀疑论对亚里士多德主义基于感觉的科学批判。这为他(经验的、假设—演绎的)“方法”扫清道路,与追求确定性很少相关。
从开普勒到笛卡尔,光学的发展表明:正是科学——光学和观察——产生了哲学的怀疑论。[23]光学视角为笛卡尔怀疑论的各种解释提供了清晰的回答。即使有时在传统术语中被阐述,这仍然是新的忧虑。它奠定于感觉分析之上,这种感觉对古代和中世纪完全陌生;它奠定于笛卡尔主义科学之上,在开普勒光学之后成型,领先于并促进了形而上学的反思。这种怀疑源于这种科学的成功。
笛卡尔的怀疑论体现在其“科学的”文本中,认为观察世界就像被对象被投射到眼睛视网膜上一样。但是,这是新光学成功的一个象征和这种成功令人不安的分歧。观察者而不是眼睛从光学中消失。眼睛与观察者分离被重新纳入视觉过程;刚去世的人或其他大型动物的眼睛与活人的眼睛一样,提供很多光学过程。这是对亚里士多德立场的公然反对,亚里士多德认为视力是眼睛的物质,当视觉移走,眼睛就不再是眼睛。
在区分了眼睛与视力之后,笛卡尔开始抛弃“薄膜”。他用日光能穿过的一些薄的白体(white body)替代死的眼睛,观察出现在表面的图像。“暗室中白布上的图像紧挨着眼睛,以相同的方式、同样的原因在那里产生”。笛卡尔以“赞赏和高兴”结束,但是其意蕴令人忧虑:眼睛不再是窗口而是屏幕,不再穿过观察的事物而在事物之中。[24]91-93,97
笛卡尔的怀疑论不是关于视力而是关于视觉的怀疑论。笛卡尔没有重新发现自古被关注的问题——视力不值得信任。相反,他发明了心灵之目,以肉体的眼睛为模型而完全独立于肉体,颠倒了视觉的认识论地位。从知识的获得和直接认识来看,视力成为介入的象征。这是一个悖论:如果认为知道就是看见和理解,那么笛卡尔如何确信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
(译者注:限于文章篇幅,本译文对原文的正文、参考文献和注释有删减,深表遗憾。)
[1] John Pecham.John Pecham and the Science of Optics[M].ed.and trans.David Lindberg,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0.
[2] Nicholas Jardine.The Birth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3] A.Mark Smith.Getting the Big Picture in Perspectivist Optics[J].Isis,1981(72):568-589;What is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Optics Really About?[J].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2004(148):180-194.
[4] Giora Hon.On Kepler’s Awareness of the Problem of Experimental Error[J].Annals of Science,1987(44):545-591;Putting Error to(Historical)Work[J].Centaurus,2004(46):58-81.
[5] Giambattista della Porta.Natural Magick[M].London,1658.
[6] Sven Dupre'.Inside the Camera Obscura:Kepler’s Experiment and Theory of Optical Imagery[J].Early Science and Medicine,2008(13):219-244.
[7] David Summers.The Judgment of Sense:Renaissance Naturalism and the Rise of Aesthet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8] Svetlana Alpers.The Art of Describing:Dutch Ar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
[9] Philip Steadman.Vermeer’s Camera:Uncovering the Truth behind the Masterpiece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10] David Hockney.Secret Knowledge:Rediscovering the Lost Techniques of the Old Masters[M].New York:Viking Studio,2001.
[11] A.Mark Smith.Ptolemy,Alhazen,and Kepler and the Problem of Optical Images[J].Arabic Sciences and Philosophy,1998(8):9-44.
[12] Christoph Scheiner.Oculus[M].Innsbruck,1619.
[13] Peter Dear.Discipline &Experience:The Mathematical Way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esp.Chapter 2;and Rivka Feldhay,“Mathematical Entities in Scientific Discourse”in Biographies of Scientific Objects,ed.Lorraine Dast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14] Carl Boyer.The Rainbow[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
[15] Descartes.The World,4;C.f.Stephen Gaukroger,Descartes: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5.
[16] Rene'Descartes.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M].trans.John Cottingham,Robert Stoothoff,and Dugald Murdoc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17] Alison Simmons.Are Cartesian Sensations Representational[J].Nou^s 33(1999):347-369.
[18] Jose'Luis Bermu'dez.Scepticism and Science in Descartes[J].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1997(57):743-772.
[19] Paul Edwards.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M].London,1967.
[20] 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M].Princeton,1979.
[21] Richard H.Popkin.The History of Scepticism from Erasmus to Spinoza[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
[22] Margaret Wilson.Skepticism without Indubitability[J].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1984(81):538-539.
[23] A.Mark Smith.What is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Optics Really About[J].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2004(148):194.
[24] Rene'Descartes.Discourse on Method[M].trans.P.J.Olscamp,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65.
N02;B565.21
A
1671-511X(2011)05-0022-06
2010-10-02
本文是“巴洛克科学”项目的一部分,受到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的资助。
Ofer Gal,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副教授;Raz Chen-Morris,以色列巴伊兰大学(Bar Ilan University)讲师。
[译者简介]郭飞(1980-),男,安徽涡阳人,博士,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STS、工程哲学。
吕乃基(1945-),男,上海市人,东南大学STS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STS、科技知识论。
-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科学主义与超现实主义“合谋”下的“游戏”
——对“影像时代”中艺术与技术相糅合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