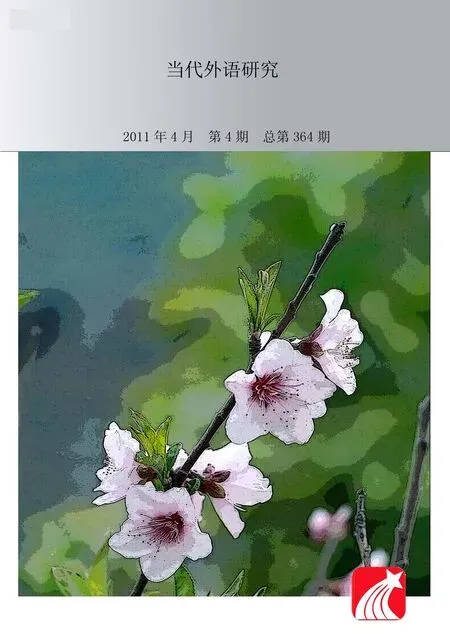“理据”作为语言学术语的几种涵义
李二占 王艾录
(盐城师范学院,盐城,224002)
1.引言
理据一词古已有之,南朝齐僧岩的《重与刘刺史书》曰:“纡辱还诲,优旨仍降,徵庄援释,理据皎然”;《南齐书·礼志上》有:“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禮次天地,故朝以二分,差有理据,则融玄之言得其义矣”。这里的理据都意为论据或道理之所在。近年来,“理据”这一术语的使用频率非常高,百度和谷歌(Google)里的检索数分别达到2,430,000和205,000(截止日期为2011年1月1日),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主题”、“篇名”和“关键词”三项里的检索数分别是3560,1032和2044(从1980年到2010年)。《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ABC汉英大词典》也都收录了它。《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将理据释义为“理由,根据”,并提供了一个例句:这篇论文观点明确,理据充足。《ABC汉英大词典》把理据翻译成motivation,并将之标注为语言学研究范畴。
现在,理据一词既频现于语言学领域,又常用于日常生活,但由于汉语词汇双音节特征和词义组合上的浓缩化倾向①,它往往有不同的内涵:当用来描述语言符号的属性时,它指理据性;当用来解释语言现象时,它指理据论;当用来谈论理据词典、理据记载等情况时,它指理据的语言表述;它既是motivation一词的汉译,又与认知语言学里的iconicity同义。由于它雅俗共用,常用于不同的场合和领域,故而本文认为有必要对其多种涵义进行归纳、分类和阐释,尤其是厘清作为语言学术语的它在实际使用中所引发的一些含混现象,因为“一种学问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有一套术语来描述其研究对象、目的、方法、规律、定理的基本概念”(方梦之等2004:ⅰ-ⅱ),这对语言学来说更是如此,而语言学发展史也已证明:“如果语言学所做的可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对范畴的研究”(同上)。
2.“理据”的五种具体涵义
理据一词虽然在南北朝时期已出现,但在现当代语言学研究的影响下,它既成为日常语言生活中的重要词语,又正在形成语言理据学这门崭新的学科。语言理据学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也叫音义学(phonosemantics),旨在考察词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可论证性联系。广义的则研究语言自组织系统中激发某一语言现象产生、发展或消亡的动因,涉及范围包括语言各单位及各层面。语言理据学是当代认知语言学和解释语言学日渐成熟的产物,也与中西方两大语言研究范式密切关联。中西方语言研究都关注语源探求和名实关系(俞允海、潘国英2007:197-198),都曾有过与约定论和本质论类似的观点。约定论和本质论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任意性理论和理据性理论。任意性理论认为语言的音义之间无自然的联系,不可论证;理据性理论则认为二者之间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可以论证。任意性理论的集大成者是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在他的巨大影响下,任意性理论成为语言学中的基本常识。相反,中国从先秦到清末民初,探求词语的理据和语源始终是语言研究的主要脉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西学东渐以来,人们全面接受了索绪尔的任意性理论,于是我国现代语言学同他国现代语言学一起,被任意论统治近百年。
不过上世纪60年代起,语言研究中的认知科学和功能主义范式指引着人们认识到,语言符号除任意性还具有象似性和理据性。象似性思想源于美国哲学家珀斯(Peirce),他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着一种表面结构上相似的符号即象似符。象似符通过写实或模仿来表征其对象,分为意象符、图表符和隐喻符。珀斯符号学着重研究人类的认知和思维,因此现在被用于语言的认知研究(郭鸿2008:22)。语言象似性指语言符号的外形、长度、复杂性及其构件之间的关系总是平行于被其所编码的概念、经验和交际策略(Newmeyer 1998:114-115)。象似性与理据性这对术语并不完全相同,但一起作为任意性的对立物,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多于不同点,因此无妨把象似性涵盖于理据性。
从上述简要的文献叙述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当代语言学重要术语之一的理据其实处于古今中外四视角的交叉点之上,这一特点决定了它承载着不同的、因而往往也是不甚明晰的信息内涵。下文,我们将其细分为五种具体的涵义,并配以详细的解释。
2.1 一般意义上的理由或根据
理据一词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属于生僻词汇,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后来,随着语言理据研究的深入发展,它才逐渐传播开来,渗透到通用领域。《现代汉语词典》就是把理据当作普通词汇而收录的。作“理由”或“根据”解时,理据只是一个流通于日常语言生活领域里的词语。例如,“董事会全体团结一致,并相信这一行为是单一股东个人利益驱动,缺乏正当理据”;“中国风水有科学理据吗”;“广州物业管理收费混乱由来已久,高收费理据何在”;“港报指中美军机碰撞事件美欠理据”;“社会言论使用的理据标准内容有变,但其‘高度政治化’的形式继续”,等等。
从语域(register)角度看,“理据”显然要比其同义词“理由、根据、缘由……”等更加正式,因它能够彰显某一概念或事物的新颖性与专业性,从而引起受众注意。有趣的是,现在有资格和理据形成同义词并彼此竞争的却是“动因”一词。二者的英语表达都是“motivation”,而且都是先流通于专业领域,之后才逐渐应用到大众语言生活中的。理据一词的使用也与地域有关,比如它较早在港台地区使用,可能是那里的居民比大陆人更倾向于使用文言词汇的缘故。作为普通词语的理据有时也被叫做“有缘性”,主要流行于我国台湾地区。
2.2 语言自组织过程中促动和激发语言生成、发展与变化的动因(广义理据)
广义理据的涉及范围包括语言各单位以及篇章、文字等各层面(王艾录、司富珍2002:2)。例如,“语法的形式和理据”;“多义词词形与词义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还是有理据的”;“寻找语言产生和发展的理据性,揭示语言演变与人类认知之间的象似性规律”;“汉字构形理据的历史演变”,等等。
从某种程度上说,语言研究的历史就是一条思考语言理据的道路史(王艾录、司富珍2002:ⅰ),如从柏拉图问题的提出,到康德的图式理论的产生;从洪堡特“有限的手段,无限的使用”,到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机制及其解释充分性。石毓智(2008:409)认为,认知语言学从人的生理条件、社会自然环境、交际活动中寻找理据,而生成语言学则从人类的生物基础上寻找理据。司富珍(2008:89)也认为生成语言学追问语言研究中的“为什么”问题,而“为什么”就属于语言理据学的范畴。当代语言学似乎更赞成这样的研究,即语言“在其出现和变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现象总体来说是有理据的,虽然不一定能预测,但是我们有可能通过反溯来对它们做出解释”(徐盛桓2008:25)。总之,广义语言理据研究致力于探求语言自组织过程的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期望对语言现象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但这种研究目前尚缺少统一的理论框架。
2.3 语言系统的子理据(狭义理据)
狭义理据或子理据指语言系统某一层面的理据,如音位理据、词语理据、句法理据、语义理据、形态理据、文字理据等。这里以文字理据为例谈谈语言的子理据问题。汉字是象形表意文字系统,其“大多数都是象似性符号”,而这正构成了“汉字与其他的语言文字的又一重大区别,即象似性对任意性”(潘文国2002:230)。作为一种主要由象似性符号构成的文字,汉字独特的由来在于首先“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依类象形,创造了一大批最古老的文字,而后在此基础上“孳乳以浸多”,逐步形成富有理据的文字系统。
汉字象似性的特点使它从产生之日起就与理据建立了不解之缘。我国第一部完备的字书《说文解字》里,对字的理据的思考就既表现在文字的构形方面又表现在文字的音义联系方面,而宋代学者提出的“右文说”重在通过对同源字的联系来说明文字的理据。当然,传统的文字学过于注意对汉字形体理据的研究,以至走上了重形轻音的道路。这种囿于文字字形束缚的藩篱直到清代学者提出“因声求义”的理据研究范式时才被冲破。从以形求义到因声求义不止是方法论的突破,更说明了文字理据与语言理据的关联性和一致性。语言理据是因,文字理据是果,即语言声义理据是基础,文字形义理据则属次生。徐通锵(2005:108)指出,汉字“据义构形造字”的体系使文字的“字”与语言的“字”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因此可以通过对具有理据性的汉字的研究来透视汉语的结构原理。可见,以汉字为例对语言系统子理据之一的文字理据的分析表明,理据视角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语言的各个层面。
2.4 词语的理据性和理据义
词语是最基本的语言符号,所以语言理据主要指词语的理据性质。语言的理据性与任意性相对,例如彭润泽(2003:77)等编著的《语言理论》就把二者并列为“语言基本的符号实体单位——词”的重要属性,并认为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具体而言,理据性对任意性形成制约关系,简称“理据管约”。作为前提的任意性和作为动力的理据性在语言符号生成时共同发挥着作用——任意性给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和多样的机会,理据性则给这种结合以现实的范畴和稳定的秩序。任意性关心的是潜在符号,即语言符号如何成为可能;理据性关心的是现实符号,即语言符号如何具体生成。任意性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变量,它支持着语言的变异性、选择性和多样性,而理据性是一个普遍潜在的动因,它支持着语言的有序性、机制性和可证性。
语言里的“一物多名”和“一音多义”现象可以充分证明理据性对任意性的管约关系。一物多名指同一概念或所指可以与多个音响形象或能指结合,从而生成不同的语言符号。“手机”这一概念(所指)在英语中既可以和声音序列“/selfun/”又可以和“/mublfun/”结合,生成“cell phone(蜂窝电话)”和“mobile phone(移动电话)”两个不同的语言符号,这体现了语言生成的任意性。但这两个符号同时也是理据驱动的结果。“cell phone”的理据是“电话运营商将一个区域(如一个城市)划分为一个一个的小区,每个小区一般是25平方公里,通常将这些小区看作一张大的六边形网格中的一个个的六边形,而这些小区则犹如蜂窝(cell)”。“mobile phone”的理据是“这种电话可以自由移动(mobile),与固定电话相对”。一音多义则指同一音响形象或能指可以与多个概念或所指结合,从而生成不同的语言符号,它涵盖了一词多义、同音词、同形词、同源词等。“/bid/”这一声音序列可与“祷告”、“念珠”、“有孔小珠”、“准星”、“瞄准”、“以索取……为目标”等多个概念形成一词多义的“bead1”、“bead2”、“bead3”等。它们的产生以任意性为前提,否则一个能指只能和一个所指形成必然的联系,从而无法参与更多符号的编码工作。但这些符号又有“同”的一面,“同”指的是理据管约。例如“bead1(祷告)”变化为“bead2(念珠)”的理据的语言表述是“一个人在睡觉前祈祷时数着一粒粒念珠”。这些事实证明,作为语言符号的两个支撑面,任意性与理据性对立统一、相反相成。
作为造词动因,理据只在能指与所指结合的一剎那起作用,但这是决定语言命运的作用。它之后便淡出语言世界,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成为一个失而难得的非物质遗产。因此就性质而言,理据是认知的,它只有在语言的表述下才能成为被我们所直接认识到的、具有一定物质性的记录或记载。理据的语言表述的汇集就是理据词典。作为理据大国,中国的理据词典古已有之,如《尔雅》、《说文》、《释名》等,但它们主要是关于单纯词的,复合词的内容并不多,而且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对理据的语言解释自然未上升到科学设计的高度。现代辞书如《现代汉语词典》、《新华词典》、《辞海》、《现代汉语学习词典》等对理据问题的处理也不尽如人意,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绝大多数辞书都以解释词义为目的,都属于词义词典,因此对于词语的理据未能照顾到。其中虽然有许多词条的释文涉及理据内容,但是大都融合在词义解释里;其二、对词语理据的处理尚缺少系统规划与明确目的,还处于不自觉的阶段。例如《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在“红”字下的“红榜”、“红包”、“红蛋”、“红马甲”等都涉及到理据,但“红筹股”“红灯区”等却没有给予相应的理据解释。至于像“红契”等词语,其词义解释(旧时指买田地房产时经过纳税而由官厅盖印的契约)距离理据(官厅盖印用了红色的印泥,因此叫做红契)仅一步之遥,却最终未能跨越出去。但这也说明,理据问题一不小心即可触碰到,理据遍及语言。
专门的语言理据词典迄今只有《中文有理有据三千词》(王艾录2010)②。它的出版标志着汉语理据语料的积累和研究已初具规模。在语言理据学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理据词典编撰这项惠及后人的工作。王寅先生(2009:36)指出,如果我们能够基于语言象似性从而“编写这样一本词汇认知学习教材”,那么就能够“有效提高与大量识记驾驭英语单词的能力,好像进入到学习英语单词的自由王国一样”。这里所说的“词汇认知学习教材”实际上与理据词典大同小异。
对某一具体词语的理据解释(理据的语言表述)我们称之为理据义。例如“猬缩”一词的理据解释是“恐惧之状犹如刺猬缩成一团”,这就是“猬缩”的理据义。那么理据义和理据性是什么关系呢?我们认为二者的联系与差别表现在这样几方面:
第一,平常所谓的理据可以细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涵义,理据义是狭义的理据而理据性是广义的理据。某一术语兼指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是常见的语言现象。例如“词义”一词,当我们说“要搞清楚这个词的词义”、“我不明白那个词的词义”的时候是狭义的,指某个词的具体意义;而当我们说“词是由词音和词义构成的”、“词义是词的理性意义”的时候是广义的,指语言中所有词的意义。与此同理,狭义的理据(义)指一个个具体的词语的理据意义,而广义的理据(性)指整个语言符号的理据性质。
第二,理据义是具体的实例,理据性是抽象的性质。理据义是创建语言理据学的事实基础,因为只有发现或者掌握了相当数量的词语理据义的时候,我们才能断言语言符号具有理据性质,否则,说语言具有理据性将成为无根据的空谈。这也就不难理解对于某一具体的词语,人们为什么总是要考究它的理据义。从反义关系看,理据性与任意性对立,都指语言符号的性质,而理据义无对立词(没有“任意义”一词)。正是这一点使得我们认为,理据性与任意性虽处于同一讨论范畴,但二者的性质迥然不同。任意性是自明的,即没有任意性就没有语言符号的存在是一个自明的事实。因为任何语言社团里的正常说话人都能依靠直觉而意识到,他们所用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自然的联系,只是普通的语言使用者无法把这种直觉知识理论化而已。也因为这种自明性,索绪尔才断言任意性是无人反对的,而事实上他的著作中有关任意性的正面论证也并不多。自明的任意性以否定的方式指出,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既然无必然联系,就不存在进一步论证的必要性。相反,作为理据性的具体体现的理据义则是非自明的因而是潜隐的和待考的,这决定了它不能停留在“指出”这一步,而是要做出具体的考证。这种差异造成了任意性一方被过度注意而理据性一方却被严重忽略。也正因为如此,编撰一本语言理据词典之类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而编撰一本语言任意性词典之类则是令人无法想象的。
第三,理据义与理据性两个术语的用法也不同。例如可以说几项理据义而不能说几项理据性;可以说考求某词的理据义而不能说考求某词的理据性;可以说理据义的分类而不能说理据性的分类;可以说真假理据义而不能说真假理据性。
理据义的考求应该说是相当艰难的,因为理据义具有易逝性,它只是偶尔在词义或内部形式里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多数时候则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隐没和消失。因此人们为了修复自古以来大量磨损的理据,或者使湮没的理据失而复得,便去烛幽发微,从事相当艰苦的考证工作。鉴此,姚小平(2005:78)提出,“一个词的不可论证,不是因为它没有‘理据’(motivation),而多半是因为这个理据已被时间销蚀殆尽,在今人眼里成为一个谜了”。也因为这种易逝性和历史性,许多词的理据义至今难以探究明白,还有待继续研究。不过,迄今也有许多词的理据义早已探究明白,所以给出词语理据义也并不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任务。随着研究的深入,将会有更多的理据义被考求出来,语言理据学的语料基础将更为雄厚。
2.5 从认知角度解释语言现象的一种新理论(理据论)
语言研究主要有两大范式。其一以语言能力为研究对象,认为语言是一个自足的认知运算系统,其规则与外界环境无涉。其二则关注语言交际的功能性,认为语言是一个进化而来的适应系统,反映了外界环境的特点(Bouissac 2005:22)。两种范式实际上是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的延续,只是不同时期使用的术语不同,而且两者的争论“常出于不同理论背景,为了不同的理论目的,采用不同的表达形式,延绵两千多年”(王寅2008:32)。在当代语言学里,两大范式之间的对立表现为索绪尔的任意论与认知语言学家所坚持的理据论。
索绪尔以假定任意性为首要原则的方式,将任意论看作公理,即“关于人类语言的、无需解释也无法解释的、始源性的事实”(Joseph 2004:68)。它犹如几何图形中的辅助线,能帮助我们理解人类历史的语言奥秘,达到科学研究上的理想状态。任意论所坚持的任意性不仅指语言符号的性质,还指一种理论建构。作为理论建构的任意性是假设的,因此是无需证明的,它打通了语言先验性与可知性之间的隧道,一旦到达理解的彼岸,它本身就无足轻重了。任意性原则与乔姆斯基“拟想的人”的理论假设一样,都是为了满足科学解释的目的。
其实,索绪尔的历时与共时、语言与言语等概念也都属于理论建构的范畴,因为“没有这些原则就没法探讨静态语言学的更专门的问题,也没法解释语言状态的细节”(索绪尔2002:108)。这些理论建构是必需而合情的,因为任意性和物理学中的“能量”、“电荷”等概念一样,虽不能直接观察到,但它们“在解释和预测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是“任何一项科学理论的本体性承诺”(Lakoff & Johnson 1999:109),尽管它们在实践中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可惜人们未充分认识到索绪尔任意性观念的双重价值,即作为语言属性的任意性和作为理论建构的任意性,二者应该分别叫做任意性和任意论。作为语言属性的任意性是客观存在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它和理据性是并行不悖的;作为研究视角的任意论却是可以争辩的,正因为如此才有理据论和它形成对立而存的局面。
理据论认为对语言理据的探求是语言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对科学解释性的满足。许国璋(2001:47)说语言研究者的责任在于解释,即把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解释清楚比消极地承认任意性远为重要。徐通锵(1997:37)认为语言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弄清楚语言编码的理据。陆丙甫等(2005:38)认为语言任意说对追求语言的解释而言是一个十分消极的观点,而理据论则鼓励人们不断探求语言世界背后所隐藏的规律。我们认为理据论可以进一步拓宽文化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路径,从而使自然语言获得更大更多的解释力,而对任意性的过分依赖则成为懒于思索者的遁词和墨守成规者的温床。同时,寻找理据解释也是科学研究的动力,陆丙甫等说得好,“考虑到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发掘尽可能多的理据性,我们还是应该假设所研究的现象都是可以解释的、有理据的,这样才有信心去研究”(2005:38)。
理据论已逐渐显示出它在语言研究中的价值与意义。Margaret Magnus阐述了音义学假设(the Phonosemantic Hypothesis),并通过14个被她称之为phonosemantic experiments的实验详细描述了音位和意义的对应关系。徐通锵的“字”本位论就把理据说作为其立论依据,并把语法重新定义为“理据载体组合为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规则”(2008:115)。认知语言学更是把理据作为解释语言现象的一个理论概念,这与“当代有影响的语言学理论都寻求从内部的大脑和认知结构来解释外显的语言现象”的趋势高度吻合(Leezenberg 2006:4)。Cuyckens等(2003)出版了“Motivation in Language”一书,分别阐述了理据在语法、词汇、社会文化语言学以及应用语言学中的运行原理。Günter Radden 等(2004)撰写了“Studies in Linguistic Motivation”,从认知及功能语言学的角度深入探讨了理据在词汇和语法中的作用,同时把理据分为生态理据、发生理据、体验理据和认知理据。理据论不仅强调语言符号的理据性,虽然这一直都是它的核心内容,它更是一种方法论。正因为它在方法论上的价值,理据论才被广泛用来解释语言的结构、语义、使用、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了句法理据、语义理据、语用理据和文化理据等新理论。当然,面对这些繁杂的语言现象,我们还需要把更多的因素整合起来才能形成语言学中“统一的理论(a unified theory of motivation)”(Radden & Panther 2004:2),即理据论。
理据、动因和象似性是近义词,相互之间存在区别。动因概念源于哲学和心理学,所指范围要大于理据和象似性,而且只有进入语言系统的动因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理据(linguistic motivation)或象似性(linguistic iconicity)。理据和象似性都强调语言符号的可论证性,但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讲,理据的作用范围大于象似性,因为理据重在指出一切类型的语言符号发生和发展的自组织动因,而象似性重在指出语言的句段结构同人类所经验的外部世界或人类的认知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似的关系。一言蔽之,动因的涵义最宽泛,理据次之,象似性为最后。目前来看,“理据”一词最重要的涵义就是理据性(义)和理据论。理据性(义)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不管我们是否赞同它。理据论作为一种新兴理论,还不时受到质疑与批评,但它现在被频繁用于语言学尤其是认知语言学领域。要注意的是,人们曾将任何实际上属于对语言结构的功能的可论证性都冠以“象似的(iconic)”(Newmeyer 1998:114-115),从而导致象似性成为一个涵义庞杂的术语,因此我们不能重蹈覆辙,把任何用于解释语言现象的动因都归结为理据,那样会造成“理据”一词的泛化与滥用,无助于新理论的发展与成熟。
3.结语
迄今语言理据学已成为语言研究中的一个引人关注的重要课题,尤其是近二十年来随着认知语言学兴起以后,人们把理据研究作为一种理论追求,并且以“群体的方式进行了系统的探讨”(石毓智2008:409)。可以说,语言理据学是当代语言学的一个富矿区,其前景十分广阔。学者们围绕理据义、理据性、理据论等基本概念进行着事实的挖掘和理论的阐释,从而拓宽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路径。另一方面,语言理据学毕竟是一门处于“现在进行时阶段”的新学科,其中还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科学术语的严谨性和单一性与词语自身含混性和多义性之间的冲突,使得“理据”这一术语被人们不规范地使用,从而造成了不少误解,也影响了语言理据学的建设。因此对理据一词的多种涵义进行分类和梳理,有助于促使我们的研究更加细致、更加深入,因而更加科学。这不但有利于语言理据学本身的发展,而且能从理据维度上重新审视现当代语言研究,使自然语言获得更加充分的解释力。
附注:
① 浓缩化即吕叔湘(2004)所说的“语言的表达意义,一部分是显示,一部分是暗示,有点儿像打仗,占据一点,控制一片”。例如,“闭幕之后,观众鼓掌,幕又拉开,演员致谢”的语义表达可以浓缩为二字组“谢幕”。徐通锵将其总结为“控制两点,涵盖一片”。详细内容参见《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146)。
② 《中文有理有据三千词》由香港商务印书馆2010年11月出版。
Bouissac, P.2005.Iconicity or iconization? Probing the dynamic interface between language and perception [A].In C.Maederetal.(eds.).Outside-In—Inside-Out:IconicityinLanguageandLiterature[C].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5-37.
Cuyckens, H., T.Berg, R.Dirven & K.U.Panther (eds.).2003.MotivationinLanguage:StudiesinHonorofGunterRadden[C].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Joseph, J.E.2004.The linguistic sign [A].In C.Sanders (ed.).TheCambridgeCompaniontoSaussure[C].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59-75.
Lakoff, G.& M.Johnson.1999.PhilosophyintheFlesh:TheEmbodiedMindanditsChallengetoWesternThought[M].New York: Basic Books.
Leezenberg, M.2006.Gricean and Confucian pragmatic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J].JournalofForeignLanguage(6): 1-20.
Magnus, M.2001.What’s in a Word? Evidence for Phonosemantics [D].University of Trodheim.
Newmeyer, F.J.1998.LanguageFormandLanguageFunction[M].Cambridge/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Radden, G.& K.U.Panther.2004.Introduction: Reflections on motivation [A].In G.Radden & K.U.Panther (eds.).StudiesinLinguisticMotivation[C].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1-46.
方梦之等.2004.译学辞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郭鸿.2008.现代西方符号学纲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陆丙甫、郭中.2005.语言符号理据性面面观[J].外国语(6):32-39.
罗竹风等.1997.汉语大词典(上卷)[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吕叔湘.2004.意内言外[A].吕叔湘著.吕叔湘文集(第5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46-56.
潘文国.2002.字本位与汉语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彭泽润等.2003.语言理论[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
石毓智.2008.语法规律的理据[J].外语教学与研究(6):409-417.
司富珍.2008.语言论题:乔姆斯基生物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和语言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索绪尔.2002.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
王艾录、司富珍.2002.语言理据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寅.2008.语言学新增长点思考之二:语言与哲学的交织对我们的启发[J].中国外语(1):27-32.
王寅.2009.从后现代哲学的人本观看语言象似性——语言学研究新增长点之六:象似性的哲学基础与教学应用[J].外语学刊(6):32-37.
许国璋.2001.论语言和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徐盛桓.2008.语言学研究的因果观和方法论[J].中国外语(5):24-27.
徐通锵.1997.语言论[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徐通锵.2005.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徐通锵.2008.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姚小平.2005.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langue,language,parole[A].李宇明等主编.言语与言语学研究[C].武汉:崇文书局.63-81.
俞允海、潘国英.2007.中外语言学史的对比与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