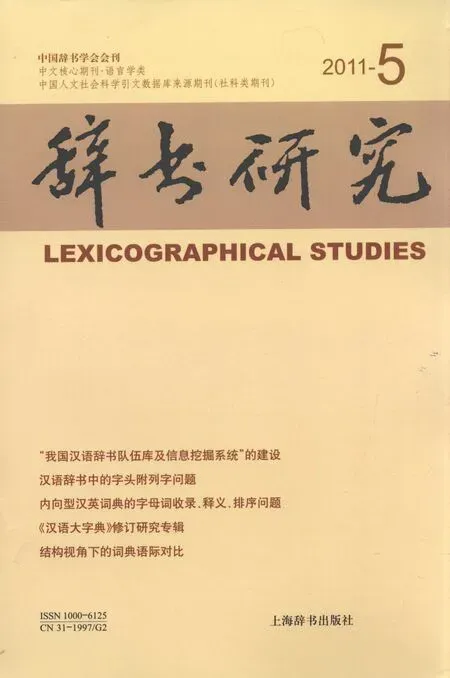汉语辞书中的字头附列字问题
程 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汉语辞书的编纂与西文辞书相比有诸多自身特点,其中字头的设立尤为突出。而字头部分是否收列附列字,哪些字该作为附列字收列,如何较好地沟通附列字与主体字的关系,都是汉语辞书编纂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一、对字头附列字的一般理解
字头附列字是指附列在主体字头后面的跟主体字有异写关系的非主体字,属于字头的可选性组成部分。其特点是,通过在字头后附列这种简明的方式显现非主体字与主体字的关系,释文中大多不再涉及。例如,《新华字典》在主体字头“灯”、“峰”后面分别加括号附列它们的繁体和异体“燈”、“*峯”等。
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通行字不同,所指的正体字也不同,相应地辞书中设立的主体字和附列字也会有所区别。例如,“糠”是现在通用的规范字,“穅”是停止使用的异体字(见于《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的异体字);但过去则相反,“穅”是正体字,“糠”是俗写字,《玉篇》“糠……俗穅字”,《康熙字典》“穅……亦作糠”[1]。也就是说,有些历史上的正体字,后代定为非正体字,继而成为现代汉语辞书中的附列字,例如,《同音字典》:糠(穅);《新华字典》:糠(*穅)。
从现有辞书的附列情况看,字头附列字所涉及的是很广义的异体,包括古今字书中收列的俗体、别体、古体、繁体、简体[2]等,以及传世文献中曾在部分意义上混用的非全等异体。例如,“愽”在《正字通》中被释为“俗博字”,在《中华大字典》中被释为“博”的“讹字”,在“广博”等意义上“博”曾经也写作“愽”,但在“换取”、“博弈”等意义上“博”与“愽”一般不混用,而现代汉语辞书大多在主体字头“博”的后面附列“愽”,通过给“愽”加标义项号说明与“博”的对应关系。又如,“菑”是常被附列于“灾”后的字,它在读zāi音表示“灾害”义时曾与“灾”有异写关系,但在读zī音表示“初耕的田地”、“除草”等义时,与“灾”无关联;此时如果仅在“灾”后附列“菑”,所反映的只是“菑”与“灾”的关系,却不能反映“菑”区别于“灾”的自有读音和意义。而如果因考虑“初耕的田地”、“除草”等义是古汉语用法,不宜在现代汉语辞书中收立的话,那么“菑”作为“灾”的异体也是在文言中使用,似乎同样不宜附列。再如,“挐”是常被附列于“拿”后面的字,《说文解字义证》“挐,通作拏。拘捕有罪曰拏,今俗作拿”,“挐”通过“拏”与“拿”发生联系,但“挐”自身还另有rú的读音和意义(“纷乱”等)。类似的这些字都是作为非全等异体在辞书字头后附列的。
字头附列字是正体以外的字,正体字只能有一个,而附列字可以有多个。例如,跟正体的“窗”对应的就有“窻、窓、、牎、牕”等多个异体,均属字头附列字的可选对象;“亩”是见于《简化字总表》的简化字即正体字,与之对应的繁体字“畝”以及五个异体“、畂、、畆、畮”,也均属字头附列字的可选对象。
字头附列字中的异体字范围并非仅限于《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以下简称《一异表》)以内。例如,《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中附列的就有一些《一异表》以外的曾经较为通行的异体字。例如,在主体字头“为”的后面除去附列繁体的“爲”,还附列有 “為”,在“伪”的后面除去附列繁体的“僞”,还附列有“偽”,“為”、“偽”等字虽都不是《一异表》中的异体字,但十分常见。
另外,字头附列字与主体字的区分只能是相对的,由于汉字在使用中的复杂性,使得有些专用字同时具有作为字头主体字和附列字的双重身份。例如,“叚”读xiá时是姓氏,可作为主体字头收立,而读jiǎ时又可作为主体字头“假”的异体附列字收选。
综上表明,现有汉语辞书涉及的字头附列字较为宽泛灵活;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和标准规定着哪些字是正体字,决定着哪些字该在现代汉语辞书中作为主体字;附列字的范围在主体字确定之后才便于明确。
二、字头附列字的显现方式
在主体字头后面附列相应的异写字,是目前现代汉语辞书较为通行的沟通简繁正异关系的主流显现方式。通过附列显现非主体字与主体字关系的做法,最远可追溯到东汉的《说文解字》。该书在主体字的解释之后简要说明相应的重文(即异体字)字形[3],而不是在字头后面紧接着附列,如“獘,顿仆也,从犬敝声……獘或从死”。南北朝的《玉篇》释字后用“俗作”、“又作”、“亦作”等多种表述方式说明与字头相应的异体,如“準……俗作准”,“疆……又作畺。壃,同上”;或是对有异写关系的字分别出字头,通过“又作”或“亦作”互见,如“栖……又作棲”,“棲……亦作栖”;或是异体字也用较大字号紧随主体字解释之后显现,注“同上”,如“遞……递,同上”,“邶……鄁,同上”;或是只在非主体字之后说明与主体字的关系,如“决……俗決字”,“减……俗減字”,主体字的后面不涉及。《康熙字典》继承了前代已有的表现方式;《中华大字典》中在非主体字的后面说明与主体字关系的情况较为普遍,如:“為,同爲”,“麦,麥俗字”,主体字的后面大多不涉及非主体字。这些辞书在沟通非主体字与主体字的关系时主要采用的是释文注解式。
从《国语辞典》初版(1937)开始,主体字头后面附列异体字的字头形式基本定型。该书“所采单字,以通行习见之一体为主,均加黑体方括弧,以资识别。其一字之异体重文,则加圆括弧,附于通行体之后,如【鐵】(铁、、銕)等是”。正文中的字头附列字,在检字表中逐一编排,能查到其所在页码。1953年问世的《新华字典》初版采用了主体字头后面加圆括号附列异体的附列字显现方式,例如:霸(覇),仙(僊);带有圆括号的正文字头附列字,在检字表中也带有圆括号,并标明正文所在页码,相互照应,方便读者。此种做法延续至今。
字头附列式同释文注解式相比,最大的优点是简明,特别是在显现全等关系的异体与正体的关系时更加突出。尽管附列字处于字头的次要位置,但也属于字头的一部分,对照上一目了然,并能编入检字表,方便查检。对非主体字如果采用释文注解式而又不单独收立字头的话,就不便编入检字表,难以查检。
在字头附列字中区别繁体字和异体字的表现方式,起因于《一异表》和《简化字总表》的公布和实施。随着语言文字规范化意识的增强,人们对辞书贯彻规范标准的要求逐渐提高。近十几年来大陆出版的现代汉语辞书,更加注重依据《一异表》和《简化字总表》收立附列字,并在附列时根据这两个表用不同标志或不同的括号对繁体字和异体字加以区分。例如,有的辞书在附列繁体字时外加圆括号,附列见于《一异表》的异体字时外加六角括号:帮(幫)〔幚、幇〕;从1998年开始《新华字典》对主体大字头后面的附列字,除了用圆括号总体括起,还对见于《一异表》的异体附列字另外加标一个星号,以区别于繁体字:帮(幫、*幚、*幇),对《一异表》以外的异体附列字另外加标两个星号,以区别于表内异体字:粗(*觕、*麤、**麁)。而《现汉》从1973年的试用本到2005年本,其字头附列字中的繁体字和异体字一律放在圆括号内,不另加区别性标志。
在附列字中按照《简化字总表》和《一异表》去严格区别繁体字和异体字以及表内异体字和表外异体字,有时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例如,“閤”字在《简化字总表》中是“合”的繁体,在《一异表》中是“阁“的异体,具有繁体和异体的双重身份;“閒”在《一异表》中只列为“闲”的异体,但事实上它同“间”也有异写关系,此时算表内异体还是表外异体就很难界定。又如,根据《简化字总表》“證”可作为“证”的繁体字附列,“癥”可作为“症zhēng”的繁体字附列,但同时“證”跟“症zhèng”还曾有异写关系而未见于《一异表》,“証”曾与“證”有异写关系未见于《一异表》和《简化字总表》;当“证”立为主体字头时,如果把“証”也收为附列字的话,“証”是标为繁体还是标为表外异体就是个难题。因此笔者以为,是否要在形式上区分繁体字和异体字以及表内异体和表外异体,应根据不同辞书所设定的读者对象的需求而定;而采用不同括号对繁体字和异体字进行区分的方式,除非有分析字形的特殊需要,一般来说不一定适合普通辞书,因为大多数异体字也存在着跟繁体字的关系,不宜用不同的括号隔开,另外从视觉的角度看,字头部分出现多种不同的括号也显得散乱。
三、字头附列字的收列和选择
在主体字头之后收立附列字,其目的在于用这种简明的形式系连与主体字的关系,用较小的空间向读者提供较多的字际关系的信息,方便读者查检,同时也可通过此种形式给读者以用字规范的指导。
根据上述原因分析,以及为了保证发电机高压油顶起系统稳定可靠运行,并结合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相关意见,将1号机组发电机高压油顶起系统的高压油泵出口压力开关整定值进行修改,整定值从10 MPa修改为6 MPa,返回值从8 MPa修改为4 MPa,并在后续机组检修过程中,也将其余机组的该高压油泵出口压力开关整定值进行了同样的修改。
就一般情况而言,专供儿童使用的辞书可以只出正体字,不附列非正体字。因为小学生尤其是小学低年级学生正在识字、学字阶段,认知能力有限,此时不必向他们提供太多的复杂信息;特别是当字头部分还设有笔画、笔顺等信息时,更不适宜再增加字头附列字,否则不仅增大篇幅,还难免影响儿童的正确理解。
如果是设定为特殊用途的,比如,想编一本兼顾小学师生和普通语文工作者的,或是大陆和港台小学生都适用的字典,字头主体字后面附列繁体字和常见异体字(通过检字表均能查到),或许有一定的必要。
以我国大陆中小学生为使用对象的汉外类辞书,附列繁体字和异体字的必要性也不是很大。原因在于:这部分人使用汉外辞书,较多地是要学习外语,非主体汉字不是其关注的重点,而当汉字中的简繁、正异关系不是全等关系时,其间的复杂性难免影响到双语间的义项划分及意义解释,附列后会增加不少处理上的麻烦。当然如果读者对象也含我国港台地区的话,附列繁体字和异体字还是有必要的。
当一部辞书的主体大字头确定为简化字系统,其主体字头是简化字时,可选的附列字是相对应的繁体字和异体字,如:惭(慚、*慙);其主体字头是传承字[4]时,可选的附列字是相对应的异体字,如:睹(*覩)。而当一部古汉语辞书的主体字头确定为繁体字系统,其主体字是繁体字时,有的辞书(张永言1986)把相对应的简化字和异体字附列,如:慚(惭、慙),或是只附列异体字,不附列简化字,而把简化字单立字头,在释文中说明与相应的繁体字的关系。
《汉语大字典》是以繁体字系统为主体字头的大型古今汉语辞书,书中对所有收入的字均单立为字头,繁体字后面附列《简化字总表》里的简化字,不附列《一异表》中的异体字。例如,简化字“备”附列在繁体字“備”的后面:備〔备〕,同时“备”也单出字头:备“備”的简化字。
辞书字头附列字的收立和选择主要应当取决于辞书类型和读者对象,辞书编纂者可以根据辞书类型和读者对象的不同,灵活选择多种方式:供小学生使用的辞书可考虑只出主体字头,不出附列字头;供大陆读者使用的现代汉语辞书最好以简化字为主体字头,有选择地附列相应的繁体字和异体字;供专业人员使用的古汉语辞书和古今汉语辞书,若采用释文注解式,非主体字和主体字分别出列字头,在释文中说明相互关系并彼此照应,似乎更加实用。
以繁体字系统为主体的辞书,当主体字头为传承字时,可选的附列字同简化字系统为主体的辞书或同或异,一般要取决于所立主体字为何者。例如,“兹”见于《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以下简称《通用字表》),“茲”未见于《一异表》,以简化字系统为主体字头的《新华字典》以“兹”作主体字,以“茲”作表外异体附列字:兹(**茲);以繁体字系统为主体字头的《简明古汉语字典》也把“茲”作“兹”的附列字:兹(茲);而《现代汉语词典》繁体字版(2001)(以下简称《现汉繁体版》)中则是以“茲”为主体字头,“兹”附列其后:茲(兹)。
以上情况表明,简与繁的转换,有时会超出《简化字总表》中繁体字的范围,涉及《一异表》中的异体字。这是辞书收立字头附列字时应当注意并考虑的。也就是说,大陆编纂的现代汉语辞书,字头附列字如果确定为只附列繁体字的话,也需要适当选收一些在港台地区通用而在大陆被《一异表》淘汰的异体字。
在《通用字表》等汉字规范标准出台以前,把后来确定的正体字作为附列字的情况在大陆也很常见。例如,《新华字典》1953年版:貓(猫),1957年版改为:猫(貓);1956年出版的《同音字典》:貍(狸);《简明古汉语字典》:稟(禀)、恥(耻)、晉(晋)、災(灾、烖)。由此说明,附列字的收选在正体字十分明确的前提下才便于把握,不同时期收立的附列字往往是随着主体字的改变而发生着变化。例如,《新华字典》1953年版和1954年版:棲(栖)、姪(侄)、從(从),1957年版:栖(棲)、侄(姪)、从(從)。1957年版把字头附列字与主体字换位的原因在于:在1955年12月国家公布的《一异表》中,“栖”和“侄”是选用字,“棲”和“姪”是停止使用的异体字;在1956年1月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从”是简化字,“從”是繁体字。[5]
由此可以认为,附列字系统一般要受主体字系统的制约,具有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又是相对的,辞书编纂者可以根据辞书类型决定其收立范围。以简化字系统为主体字头的辞书,附列字可以包括繁体字以及《一异表》表内和表外的异体字。而由于附列字的涉及面很宽,可收列的异体字数量很大,因此就不能不有选择地去收列。对于现代汉语辞书来说,字头附列字的选收原则首先应当考虑实用性,注重有无查考价值。
依据《简化字总表》和《一异表》在附列字中收立繁体字和异体字,是当今大陆辞书的主流。近年来新出版的现代汉语辞书,基本上是完全依据这两个表收立附列字。而对于使用者来说,这种做法有其优点,也存在不足。优点在于:能够帮助读者通过辞书,较为清楚地了解哪些字是《简化字总表》中的繁体字,哪些是《一异表》中的异体字。不足之处表现在:1.有些见于《一异表》的异体字极为生僻,查考价值甚微,在字头后附列的意义不大。例如,“厯”是清代为避高宗讳而故意把“歷”改写的字,“壄”是“”的错讹字,古今都不常用。这些字在中小型辞书中附列,不具查检性,只能是徒增篇幅。2.有些见于《一异表》的异体字,虽然曾与主体字在某种用法上有过异写关联,但在现代汉语辞书中附列时难以找到相应的义项,附列后无法发挥应有的效用,反而容易引发歧解。例如,“虖”的本义是虎啸,“呼”的本义是吐气,在《一异表》中“虖”作为异体附列于“呼”后,但从传世文献看,“虖”与“呼”主要是在叹词“呜呼”的用法上有过异写情况,而这个用法在单字下难以且无须单立义项,此时“呼”后附列“虖”便成虚设,无法准确标示“虖”与“呼”曾经有过的异写关系。
从另一个角度看,完全依照《简化字总表》和《一异表》收立字头附列字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前面说到的“為”是“爲”字行书楷化的写法,曾极为常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同音字典》把“為”收作“为”的附列字:为(為)。而由于它既不是《简化字总表》里的繁体字,也不是《一异表》里的异体字,这些年来有不少新编的汉语辞书便据此不予附列,也不单出字头,对于以“為”作声旁的“偽、媯、溈”等也同样排斥。这种机械的做法,弱化了辞书的查检功能。“為、偽、媯、溈”等在港台一直通行。台湾的《标准国语字典》收立“為”作主体字,香港的《现汉繁体版》把“為”作为字头主体字,把“为”和“爲”作为“為”的字头附列字:為(为、爲);对“偽”与“伪、僞”、“媯”与“妫、嬀”、“溈”与“沩、潙”也都收入并系联:偽(伪、僞),媯(妫、嬀),溈(沩、潙)。从系联大陆通用字与港台通用字的角度看,在字头附列字中适当收入常见的表外异体字的做法是必要的。
又如,《同音字典》中,“朶、垜、躱、刴”均被作为字头附列字收于主体字头“朵、垛、躲、剁”之后,但《一异表》中只把“朶”和“垜”收作“朵”和“垛”的异体,对“躱”与“躲”、“刴”与“剁”的异写关系未加理睬,在《新华字典》和《现汉》的字头附列字中则全部收入。从表面上看,此种做法使表外字与表内字同收一处,同《一异表》不够合拍,但从本质上看,则是使原本有异写关系的字的收列趋于平衡,增强了系统性。
此外,已经废止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以下简称“二简”)里的个别简化字,似乎也有收列于字头附列字的必要。例如,“荅”是见于《说文解字》的字,同“答”很早就有异写关系,“二简”从1977年12月试行到1986年6月废止,曾有将近10年的时间以正体字身份在社会上试行,在群众中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如果把其中的常用者收列于字头附列字中,既能方便读者查检,也是尊重语言事实和语言历史的表现。
以上所论及的各类非正体字均见于《GB13000.1字符集》,从中有选择地在字头附列字中收立一些,将有助于辞书查检功能的提升。与此同时还应注意在附列字与主体字之间把握一个合理的比例,即:字头附列字的比例不宜太高,同一个字头下收列的附列字不宜过多。
总而言之,字头附列字的收立和选择也是辞书特别是字典编纂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需要辞书编纂者认真对待,精心打理,从实用性出发,根据不同的辞书类型和读者对象,综合考虑字头附列字与主体字的有效配合,使字头附列形式在汉语辞书中发挥更大作用。
附 注
[1]另《说文解字》:“穅,谷皮也,从禾米,庚声。康,穅或省。”高景成《常用字字源字典》:“糠,本作康;小篆又作穅;中古作糠,又作粇。”
[2]简体字是个广义概念,指相对于笔画较多的字而言笔画较少的字;简化字是个特定概念,特指按照《汉字简化方案》简化的字或专指《简化字总表》里的字。
[3]《说文解字》收重文1163个。
[4]指传承下来未经简化的字,如“日、月、人”等。
[5]《新华字典》1957年版“凡例”四:“本字典的字头一律用楷体,以1956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第一表和第二表的简化字为标准正体,原来的繁体字作为异体,用小字号附在正体字头的右旁,以供参考。此外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里的异体字,除别有音义的单字外,也都用小号字附在正体字的右旁。”
1.重编国语辞典编辑委员会.重编国语辞典.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
2.傅永和.辨形正字字典.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
3.高景成 .常用字字源字典.北京:语文出版社,2008.
4.桂馥(清).说文解字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
5.龚恒嬅.标准国语字典.台北:西北国际文化有限公司,2009.
6.顾野王(南朝梁).玉篇.北京:中国书店,1983.
7.国语日报社.新编国语日报辞典.台北:国语日报出版中心,2000.
8.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2.
9.陆费逵等.中华大字典.北京:中华书局,1978.
10.新华辞书社.新华字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
11.许慎(东汉).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
12.张永言等.简明古汉语字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13.张玉书等(清).康熙字典.北京:中华书局,1958.
14.张自烈等(明).正字通.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
15.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国语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16.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同音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993,2005.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繁体字版).香港:商务印书馆,2001.
19.中文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中文大辞典.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