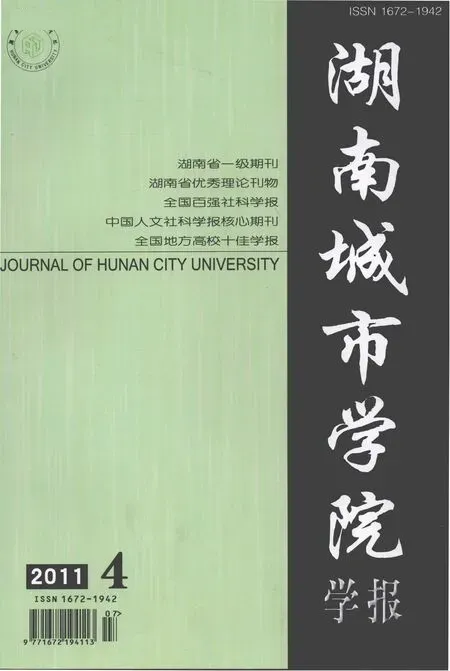古典接受诗学的后现代理论形象
李胜清
作为某种特定的历史阐释话语,中国古典接受诗学生成于古典文学实践的语境中,其所优先的阐释对象显然是中国古典的文学接受活动,换言之,它的问题域主要建构在古典文本的意义阐释中。就此而言,它的逻辑范式与价值身份也基本上呈现出一种传统的前现代基调。但是,基于人类精神谱系衍化的连续性使然,古典接受诗学在其前现代的主导身份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意义元素,它意味着,如果从后现代的问题域与价值逻辑来切入的话,古典接受诗学也具有自己独特的后现代理论形象,并且能够形成自律性的后现代阐释话语。具体而言,微观化的阐释构架、世俗化的阐释内涵与地方性的阐释标准等三个规定共同建构了中国古典接受诗学的后现代理论形象。
一、微观化的阐释构架
与西方的知识生产相比,中国古典知识的生产并不以某种宏大的确定性的理论体系为其学术旨归,不管在理论层面抑或是实践层面,中国古典诗学都呈现出一种微观化与不确定的特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生产理论,特定的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特定的消费方式,以此来观照中国古典诗学的知识生产,则可以看出,在中国古典知识语境中,微观化与不确定性的知识生产原则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它的阐释话语与阐释方式的微观化与不确定性倾向。换言之,作为整体知识形态的一种次级知识形态,中国古典接受诗学所具有的独特规定性就在于其微观化的阐释构架存在以及具体义理阐释的细节性与片段性,应该说,正是这种情况使它具有了某种后现代知识的况味。
在西方的知识语境中,如果说单个个体的接受理论家就能形成一种宏大的接受理论体系,那么在中国古典文论中,则是很多单个的阐释者以各自的相对自律的知识论述共同整合在一起才形成一个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接收理论体系。这就意味着,古典接受诗学的任何一个阐释者及其接受阐释话语都只是片段的、细节的。综其所有的阐释话语才建构成一种关乎文学生产与评价的宏大知识谱系,在其现实性上,它更多地是以一种微观知识生产与微观阐释行为的身份而存在。从价值内容的维度上来看,中国古典接受诗学虽然提出过一些宏大的知识命题,但也不乏丰富的微观接受言说与阐释话语存在,设若传统政统与道统阐释原则的阐释方式曾经构成古典接受诗学本体论问题域之一种维度,那么,微观阐释与细部接受则构成其另一种本体论的意义承诺。作为贯穿古典接受诗学发展的一种核心阐释实践方式,个体性甚至是私人性的体验接受与阐释就鲜明地表征了中国古典接受诗学的微观化价值旨趣。关于诗歌阐释的“言情说”以及“发愤著书”之论,其中的核心命意都在于通过个体微观而独特的情感体验切入文本,力求获得某种只对主体自我具有有效性的审美感受,这种诉求的微观性取向主要就体现在它的纯粹个体性与非公共理性的情感意义上,有论者就指出,“这种情感性的批评话语,说明了批评者在主观追求上并非有意识地从理性逻辑出发,寻求普遍意义上的文本解析,而只是把解析作品当做与古人对话的手段,从中寄托个人的感遇情怀,尽管这种感遇情怀并不排除家国山河的悲愁,但其表现话语却是个人心灵化了的。这种批评没有着力于营构批评的理论体系,而是着力发掘个人内心共鸣缥缈轻灵的感悟”。[1]226事实上,李贽在总结古典接受诗学的特点时,也是立意从个体微观的情感角度来分析古典接受诗学与阐释行为的成因与状态的,“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诸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2]68朱自清先生也认为在中国古典接受诗学中包含着很大的抒发个人怀抱的成分,其实这在另外的意义上就说明古典接受诗学具有一种基于接受者与阐释者立场的微观化特点,韩愈的“不平则鸣”与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之说虽然潜在地指涉着公共历史与普遍价值,但就其直接意义而言,这些说法显然优先表征着主体阐释的私人性问题意识与价值立场。这种阐释行为从深层意蕴上看实际上折射着接受主体从一种道统政统牧师角色向一种民间士人或普通庶人的身份意识边缘化与地位旁落的过程,接受与阐释行为已经从一种庙堂策论与堂皇国家叙事褪减为一种个体微观的价值休闲或自我喟叹,“余事”就是这种微观接受的价值表情,韩愈“多情杯酒伴,余事作诗人”说的就是这种状况,曹植对此深有感慨,“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3]635除却了宏观叙事与国家大义,微观的个体感受与私人之意便成了接受的重要目的。
与价值内容方面的微观化趋势相应的是,古典接受诗学在形式层面也呈现出了很强的微观化结构色彩。在中国古典知识语境中,系统性的接受诗学理论与阐释话语并不多,丰富的接受美学思想和阐释论述常常是以各种微观的知识形态甚至是片段知识单元的身份而为人们所熟知的。就起大端而言,主要有散见于子书中的某些章节和片段阐释文论,针对特定的某个问题抒发接受者的见解;笔记体的诗话和词话,从个体微观感受的独特性论述诗词的幽微意境;文人间来往的书信和各种文集的序跋,往往选取最有感发的一点抒发自己的观后感;此外还有小说和戏曲评点、诗词与其他文体中的各种接受言论等等,从微观化的立场来看,所有这一切阐释形式,“主要目的不再是归纳出一套完整的写作方法供人学习揣摩,也不是按某一标准为作家作品进行高低优劣的评价,而是阐说批评者自己的看法,写自己在阅读作品时的心得体会。”[4]196从宏观上谋求一种普遍性的知识系统与哲学方法论已经不再具有优先意义,以适合自己和对象的微观方式来抒发接受的独特体会成为了这些形式的基本功能。
二、世俗化的阐释内涵
在中国古典诗学的阐释历程中,基于特定的文明形态与价值传统,人们习惯于从精英化的立场或纯粹精神审美的角度来阐释古典文学艺术,从而形成了一种以“雅”为价值取向的主流阐释模式,相应地,注重严肃的教化功能与自我道德人格的修养也构成了这种高雅化的阐释行为的基本价值使命。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种宰制性的高雅趣味的接受阐释模式之外,一种立足世俗生活并以普通日常生活内容为关怀对象的世俗化阐释模式也一直伴随着古典诗学的阐释进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世俗化的阐释不但由潜行状态转变为显在状态,而且在元明清的某些特定时候甚至还成为与那种高雅化的阐释模式并置的一种接受阐释方式。从一种后现代的知识原则与价值态度来看,这种以世俗化价值内容为对象的阐释模式正好轨合于后现代性的世俗化价值取向,因此,从世俗化的内容出发,中国古典接受诗学也能被建构为一种具有后现代气质的诗学阐释话语形态。
虽然中国古代一直处于农耕文明时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居于支配地位,但是在当时的生产关系结构中仍然有着商品经济或明或暗的萌芽,而且就人性的全面性需要而言,虽然纯粹的高端精神与高雅趣味被建构为古代人们的主流需要,但是关乎日常生活的世俗欲求也是人们无法规避的生理或心理需要,换言之,在现实生活中,大众化的娱乐也是人性不可或缺的价值需要。而到了古典时期的晚期,随着市民阶层的崛起,世俗生活逐渐成为了文学艺术的反映的本体论领域之一,这些因素都使得古典接受诗学显示了鲜明的世俗化特点。作为先秦时代的一种音乐形式,“郑声”就是因为其丰富的世俗内容而被人们所接受的,齐宣王曾经向孟子表达自己的接受嗜好,“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月也,直好世俗之乐耳”,魏文侯则从审美效果的角度谈到了世俗之乐接受问题,越王在接受音乐时往往选择那种能极大激发自己感性愉悦的“野音”作为日常的享乐形式。隋唐之际,工商业与城市的出现不但为世俗化的阐释方式提供了大量的题材与文本,而且为世俗化阐释提供了合法性的语境,以俗为美自此成为某种自觉追求,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明确提出,“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他作诗,“必令老妪听之,问曰:‘解否?’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作崦戏,亦须令老妪解得,方入众耳,此即本色之说。”[5]163而到了宋代,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更加促进了世俗化阐释方式的发展,柳永词之所以受到时人的追捧,就是因为其词作中蕴含着丰富的世俗生活内容与深刻的世俗人性因素,并且非常契合于当时人们的接受期待与阐释诉求。元明清一代则更是世俗化创作于阐释蔚为大观的时期,李贽、汤显祖、袁氏兄弟等都从一种反传统礼教的角度张扬了世俗化阐释的革命意义。李贽的“童心说”与袁宏道的“性灵说”都从文学真实性的高度论证了世俗化创作与阐释的合理性,他们认为,俗才是真性情的表现,读者以世俗之心与际会作者的世俗之意才能真正实现文学的愉悦人性的功能,对于现实生活中世俗需要的满足决定了文学接受的世俗化走向,袁宏道归纳出人生五种快活方式实际上也是对于当时阐释标准与接受倾向的有意识引导与建构,“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安,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冩,烛气熏天,珠翠委地,皓魄入帏,花郎流衣,二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无可愧,死可不朽矣。”[6]205-206明清小说的大规模出现与当时社会的世俗化接受期待和阐释诉求处于一种共在的关系,这种创作于接受的互动关系成功地造就了一种世俗化阐释话语的空前繁荣,这就是小说美学阐释。郑板桥说,“写字作画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养生民,而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7]345清代文人则认为,世俗日常生活中蕴含着丰富的美的因素,它就在普通的生活细节中,而不在方外之界,任何一件寻常物件都有其生活情趣在,只要阐释得好就能满足人性的需要,贺贻孙指出,“吾尝谓眼前寻常景、家人琐俗事,说得明白,便是惊人之句。”[7]301审美风尚的世俗化也即现实化、现世化、感性化、感官化。这种倾向的出现从理论上提出了文学阐释提问方式的转型问题,很多接受美学家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将它付诸自己的阐释实践,诸如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等人感兴式的小说评点,虽然未从根本上突破原有的理论范式,但是已经更多地着眼于感性形象及其世俗含义的建构。
就当下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性转换而言,古典接受诗学的世俗化特点正好可以成为它向现代形态生成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增长点,要建构一种具有后现代气息的古典接受诗学模式,就必须开掘其中原本潜藏着的一些后现代意义元素。而世俗化的内容就正好满足了这种需要,因为世俗化的价值内容反映和表达了日常生活与普通人性的平民化需求,它的反权威和消解正统的精神也是契合于后现代民主化、平等化与世俗化的价值基调的。因此,从世俗化的角度来建构古典接受诗学不但能够使原本遮蔽的文本内涵得到全面释放,而且能重构古典接受诗学的提问方式与理论形象。
三、地方性的阐释标准
后现代知识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地方有效性。所谓的“地方性知识”,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而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而且“地方性”也不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说的,它还涉及到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context),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正是基于这样的语境,因此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的情境条件。以此来衡量中国古典接受诗学,我们发现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按照这样一种致思路径形成的一种知识形态,中国古典接受诗学作为一种对古典接受论述的总体性指称,其核心意义并不在于构建一种客观性与实体性的理论体系,在其现实性上,它更多地是对于许多自律性与局部性阐释知识的一种功能性指称,也就是说,在其内部存在着许多独立自洽的阐释言说,这些各自相对独立和局部有效的阐释论述才构成了古典接受诗学的现实形态。它意味着,在中国古典语境中,接受性的知识都是依据接受主体各自的文化体验与价值取向而形成的,这些阐释话语的彼此之间并不以形成可通约的普遍知识形态为目的,它们在阐释的有效性问题上都具有很明晰的意义边界与地方性知识规定。
作为一种地方有效性的知识形态,中国古典接受诗学崇尚一种接受观念与阐释标准的多元论或复调结构。春秋时期,史伯就提出具有地域有效性指导意义的阐释命题“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8]9这种“无听”、“无文”、“无果”与“不讲”除却说明阐释对象的单一性与简单化之外,它也意味着阐释主体接受心态的多元论诉求,从主体这方面来讲,它并非指这些事物不具备阐释的可能性,而是说明倘使只有一种阐释声音或阐释标准,那么这种阐释实际上就是一种无效阐释。因此,在古典诗学语境中,不但不同的接受主体诉求着不同的接受对象与接受期待,即便是对同一个对象,不同的接受主体也会因为彼此的立场差异、价值偏向与审美想象方式的不同而呈现出言人人殊与意义迥异的格局,每一个接受主体都建构着相对于自己有效的地方性阐释话语。古代的百家争鸣曾经鲜明地表征了这一点,老庄、儒家、法家等不同接受共同体对于相同对象的阐释都是基于各自的利益立场与价值想象而进行立论的,由此就形成了古典接受诗学史上诸子百家各有其说的情况。“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说明仁者所期待和注重的意义核心肯定相异于智者的期待视域,每一种阐释者都侧重选择适合自己知识结构与审美经验的客体作为现实的阐释对象,也建构着主要表达自己审美想象和价值取向的阐释话语,就此而言,这些地方有效性的阐释知识都可以被视为是一些自我特设性与限制性的理论言说,它并不谋求形成一种普泛性的知识形态,也不谋求对于其他的接受主体产生相同程度的阐释效力。地方有效性阐释还规定着阐释的具体性与现实性,它意味着针对特定的对象及其形式,接受主体应该阐释出其中独特的规定性,从而形成各具性情的阐释理据。《孔子家语》《黄帝内经素问》《汉书·地理志》《乐志》曾从这个角度就风土与习性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曹丕《典论·论文》的地域气质论、《世说新语·文学篇》《颜氏家训》“风操篇”、“音辞篇”则继承了这种地方性知识的建构传统。明代李东阳在《麓堂诗话》说:“文章固关气运,亦系于习尚。周召二南王豳曹卫诸风,商周鲁三颂,皆北方之诗,汉魏西晋亦然。唐之盛时称作家在选列者,大抵多秦晋之人也。盖周以诗教民,而唐以诗取士,畿甸之地,王化所先,文轨车书所聚,虽欲其不能,不可得也。荆楚之音,圣人不录,实以要荒之故。六朝所制,则出于偏安僭据之域,君子固有讥焉。然则东南之以文著者,亦鲜矣。本朝定都北方,乃为一统之盛,历百又余年之久。然文章多出东南,能诗之士莫吴越若者,而西北顾鲜其人,何哉?”[9]1377由此引申,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分别针对不同的阐释内容和形式形成了一套地方有效性阐释话语的技术方法,关于具体的人物品藻和性情阐释,他认为“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谥;子云沉寂,故志隐面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竞,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倜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10]163而关于审美风格与形式特点,刘勰也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地方性的阐释标准,“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远奥者,馥采曲文,经理玄宗者也;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故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文辞根叶,苑囿其中矣。”[10]156-157从这里可以看出,古典接受诗学的地方有效性阐释内涵着一种阐释类型学原则,它不但规定着适用于特定阐释对象的特定方式方法,而且也揭示了阐释主体关于自我共同体的想象身份建构,就如同罗蒂所说,它牵涉着一个连带性问题,即由阐释主体的相同或相近的信仰、利益关系、观点和立场所产生的接受连带感。
就中国古典接受诗学而言,地方性知识并不意味着某种相对主义,也不意味着一种自说自话,相反,它为知识的流通、运用和交叉开启了广阔的空间。因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各家阐释话语才具有了对话与交流的可能性。知识的地方性同时也意味着开放性。在地方性意义上,知识始终是未完成的,有待于完成的,或者正在完成中的工作,这也是中国古典接受诗学实现其当下意义转型的重要机制与意义生长点。因此,对古典接受诗学来说,开掘、建构其中所蕴含的后现代精神意义绝不是为了与传统实行彻底的断裂,而是在连续性的原则上实现传统接受诗学的现代转型,重构其建设性的后现代阐释形象。
[1] 白寅.心灵化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2] 李贽.杂说[M]//方铭.明清散文选析,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1.
[3] 曹植.与杨祖德书[M]//陈宏天.昭明文选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4.
[4] 刘明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方法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5] 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M].北京:中华书局, 1981.
[6] 袁宏道集笺校: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7] 北京大学哲学美学教研室.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M].北京:中华书局, 1981.
[8] 北京大学哲学美学教研室.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M].北京:中华书局, 1982.
[9] 李东阳.麓堂诗话[M]//历代诗话续编:下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10] 冯春田.文心雕龙释义[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