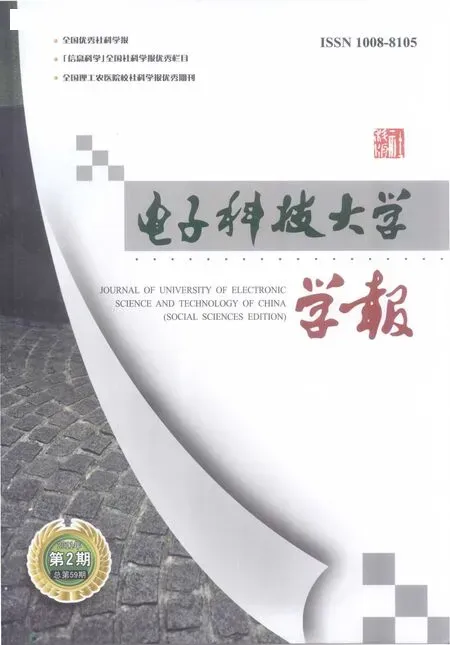网络民意与政府行政决策的法学解构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桂林 541004]
□张劲松 [武汉大学 武汉 430072]
网络民意与政府行政决策的法学解构
□胡启明[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桂林 541004]
□张劲松[武汉大学 武汉 430072]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民意逐渐引起政府决策者的关注和回应。伴随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民意与政府行政决策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如何利用好网络,使其为政府与公民有效沟通构建桥梁成为一项具有前瞻性的课题。网络民意与政府行政决策之间的问题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得以合理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随机的,而是要纳入制度化、法律化。从而,在网络的虚拟空间里,公民和政府的行为及其两者之间的互动,都受到法律的制约。
网络民意;行政决策;法律
一、网络民意与政府行政决策互动的背景及意义
(一)互联网与网络民意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0年7月15日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了4.2亿,突破了4亿大关,较2009年底增加360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1.8%;手机网民规模为2.77亿,半年新增手机网民4334万。网民年龄结构继续向成熟化发展。30岁以上各年龄段网民占比均有所上升,整体从2009年底的38.6%攀升至2010年中的41%[1]。同时,互联网覆盖面开始从以年轻人为主体,发展到逐步覆盖城乡各个年龄段。公众对互联网参与的广泛程度是前所未有。随之而来的是,网民公民意识的增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也愈发明显。也因此,互联网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舆论宣传阵地,一种民意表达的新渠道。本文认为网络民意的含义就是一群特定的人,以网络作为形式,表达出对一些公共事件肯定、否定及相关诉求的意见的总和。
(二)政府行政决策
行政决策是公共行政管理活动的基本环节和组成部分,具体是指行政领导机构和领导者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为履行行政职能而进行的一种抉择对策及做出决定的活动与行为。行政决策在行政管理系统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行政系统的作用与成效如何,关键在行政决策的正确与否”[2]。做出正确的行政决策,需要充分的了解民意,以民意作为决策的依据。而以网络为载体的民意,可以作为政府行政决策的依据之一。
(三)网络民意与政府行政决策的互动
2009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载文,将“微博云南”称为国内第一家政府微博。2009年11月2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对云南省政府开通“微博云南”进行了报道。2010年3月1日,新华社“新华视点”栏目在新浪网正式开通了“新华视点两会微博……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先后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和新华网论坛与网友聊天,对于国家大事和百姓生活都进行了交流,这些举动体现着党政高层正视网络民意、愿意与网络民意互动的一种积极姿态。网络民意在中国民主政治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地位也日益突显。现实生活中的群体或者个体有关民生和群众利益或者事关社会公平公正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在网络上成为公共事件。政府在做出相关处理的过程中,都有网络民意烙下的痕迹。一方面,互联网为每一个公民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进行诉求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另一方面,互联网也让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更好地了解真实的民意,提高了政府的执政能力。从“邓玉娇案”中网络民意与政府互动的整理,以及对近年来网络公共事件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网络民意与政府互动时所起的作用[3]。也正是因为这种网络民意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使得传统的行政行为理论中政府作为行政主体的强制执行性、单方面性等理论受到了冲击。
网络相对于传统的行政行为模式而言,是一个新生的事物,网络民意也因为具有网络这种特征而具有新颖性和强大的影响力,使得政府在决策的过程中,不得不考虑到网络上聚集起来的民意。充分考虑网络民意,是政府落实依法行政原则和执法合理性原则的必然要求。所谓依法行政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的权限、法定程序和法治精神进行管理,越权无效。这是现代行政法治化国家行政活动的一条基本原则。法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而网络民意也体现了一定的国家意志,因此,一定程度上说,依法行政也可表现为依民意行政。所谓执法的合理性原则是指执法主体在执法活动中,特别是在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行政管理时,必须做到适当、合理、公正,即符合法律的基本精神和目的,具有客观、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与社会生活常理相一致。而网络民意在促成政府决策时衡量多方利益,做到合情合理方面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从行政的效率价值而言,互联网的全球性、开放新、即时性和交互性等特征为民众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政府充分地了解民意提供了极大地便利。通过网络这种媒介,以参考网络民意为基础做出的政府行政决策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的低成本和高效率。当然,网络的虚拟性和无边界性的特征,对传统的行政行为模式也提出了挑战。
从人权保障的角度而言,以网络为手段的网民与政府互动的模式,使得更多的民众参与到政府的行政决策之中来,由此能够从行政程序到实体内容角度加强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障,监督政府的行政行为合法、科学且合理,能够“保证行政主体以更高效、更低成本地实现行政目的,实现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同时,通过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协议、协助、指示等方式的互动性行政行为,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共利益,实现社会发展与进步”[4]。
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民主的进程角度而言,民主取决于民众是否能够参与到公众事务中来。网络民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间的意愿,是广大民众突破现实空间的局限参与并监督行政决策的一种重要的表达形式,而这种形式在法律的框架下可形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民主进程的重要力量。政府在处理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时,就要充分尊重和维护公民的权利,在法律的规范下,依照程序行使权力,才能使得民主与法治更好的结合在一起。“社会成员多广多深地以及在什么问题上参与共同有关的事务,这不是已经做了些什么的问题,而是现在正在做什么的问题。民主永远处于尚待改进的状态,而改进的过程是永远也不会完成的”[5]。
二、网络民意影响政府行政决策的法律依据
一般来说,现有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往往只是将相对成熟的社会秩序制度化以维护社会相对稳定,同时,这种秩序逐渐变得相对滞后。“通常,法律的变化要慢于社会的变化。经济结构、社会习俗、传统观念,甚至正义观念的变化一般都不会立即通过法律条文的变化反映出来”[6]。但是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使得传统的法律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民主化浪潮的高涨和民主理论的不断完善,民众的权利保护意识在网络的推动下空前高涨。涉及到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行政行为,有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网络参与到相关行政决策之中来。但是这种互动必须在法律的规范下进行。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对网络民意与政府行政决策的规定并不完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现行的法律中找到法律依据。
首先,网络民意影响政府行政决策的宪法依据。宪法是规范民主施政规则的根本大法,是有关国家权力及其民主运行规则和国家基本制度以及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也是民主制度法律化的基本形式。宪法为每个公民正当行使其权利提供了根本保障。《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有权依照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我国公民有言论自由。另外《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我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以上这些宪法条文都为网民通过网络表达民意提供了宪法上的权利依据。依法治国要求政府的行政行为都必须遵守这些规定。
其次,行政法是网络民意影响政府行政决策的依据。行政法是有关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由调整行政管理活动中国家机关之间、国家机关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民之间发生的行政关系的规范性文件组成。在我的法律体系中,行政法是基于宪法的专门性法律。该法律在政府权力运行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十二条规定,公务员应当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的义务。据此,网络民意可以更好地督促公务员履行接受监督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六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据此,网络民意可以凭借其影响力促使行政机关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公开事件的处理进展,从而实现宪法赋予公民的知情权。
另外,我国还制定了若干单项法律和规章制度。从1994年起,我国政府先后制定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国计算机互联网管理办法》、《计算机国际互联网出入口信道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暂行规定实施办法》、《中国公众多媒体通讯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范网络行为的法规和条例,已经基本形成网络管理的法规体系。但随着网络不断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人们和网络接触的越来越频繁,网络民意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反映社会现实的力量。
然而现有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对网民、政府及其之间互动加以规范,显得力不从心,现有的法律制度远远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不足之处有如下几点:1)从立法的角度而言,网络民意的法律地位没有得到确立。公众通过网络形式参与政府决策的最直接的法律基础还没有在基本法律中得到体现。已经出台的80多部法律法规主要体现了其涵盖面广的特点,由于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框架性的内容多,缺乏可操作性,从而使得现行法律执行起来很困难。2)从执法的角度而言,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还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对于这些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保护流于形式。某些损害公民知情权和参与权的行为,由于缺乏相应的救济制度,使得责任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罚。3)执法、司法过程中缺乏民主监督。作为国家的行政机关,处理着大量的社会事务,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现实利益,因此,政府的行为在依法行政的同时也应当接受来自国家权力机关、国家司法机关的监督,也应该接受来自各政党、社会组织、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当前,很多政府行政决策会依据网络民意的强弱作出相应的反馈,但政府部门对于事件后期信息披露和处理不够透明和公开化;另一方面,网络民意有时候会干扰执法和司法的公正性,导致“情大于法”,所以对于执法和司法过程的民主监督还待加强,以实现依法办事。
三、确认并提高网络民意的地位,确保行政决策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一)从立法的角度而言
为规范网络民意朝着合法有序的方向发展,必须加快网络立法步伐,形成一套完备的、操纵性强的、与时俱进的科学的网络法律法规体系。总的来说,首先,对现有的互联网领域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和修定,修改那些滞后于现实的法律条款,增强法律对现实的指导性,同时,把一些过于笼统的法律条文具体化、程序化,明确规定公民的权利义务,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其次,根据新出现的网络民意与政府决策互动的问题,出台新的法律法规,使法律具有针对性,未能出台法规的则由最高司法机关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最后,应当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公民的网络行为与政府行政决策之间的关系问题,从整体上掌握其内在规律,使立法符合科学性原则。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比如欧盟的公众参与制度里,主体立法过程中的要求广泛公众参与《阿姆斯特丹条约关于辅助性原则与比例原则适用的第7号议定书》第九条增加了进行咨询的要求,该条规定,“在不对提案权构成歧视的前提下,委员会应当:除特别紧急的情况或因保密需要,在立法前尽可能广泛地征求意见,并在适当的情况下公布征求意见的文件”[7]。“在英国,规制和政策的制定中的公众参与称为‘咨询’。自2001年,英国政府制定了《咨询事务准则》,旨在提高政府开展公众咨询的质量和数量。其规定了咨询的六条标准”[8]130-131。在美国,美国的宪法规定了三权分立的体系,同时也规定了联邦体系。“联邦政府的立法性文件主要包括两种类型:国会通过的法律和行政部门通过的规章。重要的法律议案在提交参、众两院讨论前,都要经过有特邀证人参加的对外公开的委员会听证程序。《行政程序法》规定,任何将普遍适用的规章都要在《联邦登记》上公布。该法也规定了一些由于所涉事项的性质而免予进行通知和评论程序的例外”[8]235-238。
(二)从执法的角度而言
狭义的执法专指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行政主体委托的组织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履行职责、实施法律的活动。需要首先强调的就是依法行政,它要求执法的主体、内容和程序都必须合法。其次强调合理性原则,它要求执法主体在执法活动中,必须做到适当、合理、公正,即符合法律的基本精神和目的,与社会生活的常理相一致。网络民意的“呼声”很多时候会助推事件真相的披露,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得以保障,但有时候这种“呼声”会干扰程序正义和司法正义,这就要求执法机构不仅要尊重网络民意,也要在执法过程中规范程序、依法执法。这里强调行政行为司法化,是指“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行政权作用于社会之时,可以或曰应当借鉴或仿照司法权的运作方式,允许、吸收公民参与行政决策过程,与行政机关进行理性的意见交流和沟通,以提高行政行为的民主化、规范化、程式化和法制化”[9]。它的价值就在于改变传统行政的服从模式,开放系统,使得相对人参与到行政决策中来,提高行政行为的正当性,维护了行政权力的权威。
(三)从司法的角度而言
司法,是国家专门机关通过法律适用形式解决社会纠纷的活动,是国家“为当事人双方提供不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方法”[10]122。在法制社会里面,司法是解决社会纠纷、保障公平正义的最后保障。在利益双方纠纷不能解决之时,司法才有介入的必要。也正因为司法如此重要,为在平息纠纷时保证公平,就要使司法保持公正的形象,否则,就算有了结果也不能为双方当事人所接受。因此,民众通过网络在发挥群众监督的功能时,也需要理性地维护司法公正。同时,要保持司法公正中的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协调,要防止司法行政化,也要防止司法完全不受监督。
(四)从守法的角度而言
狭义的法的遵守,又称守法,专指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以法律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依照法律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的活动。遵守法律是广大人民群众实现自己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也只有社会主体都来遵守法律,才能使群众和政府的关系得到良性发展,在法律的框架下解决社会纠纷。网络给公民与政府提供了一个更为通畅的沟通平台,但网路不应该是情感无理宣泄的场所,而是公民意识张扬的一个绿色网络平台。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网络民意的甄别成为政府行政决策的一个重大课题。同时,政府对网络传播活动的管理也应受到限制。在美国,“一般来说,政府如何管理众多媒介传播的信息由特定的信息的内容来决定”[11]。如果影响到思想的自由交流,那么美国政府是无权进行限制网络传播活动的。
(五)法律监督的角度而言
目前关于法律监督的含义,法学界存在两种理解:狭义上的法律监督,是指由特定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对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的监督。广义上的法律监督,是指所有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对各种法律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督。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我国治国的基本方略。而法律监督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是现代法治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保障和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完善我国的监督制度,就需要从以下几点入手:首先,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的监督,应是从宏观上监督,应当是一种一般性的监督形式。其次,制定一部监督法,为人大监督提供法律基础。再次,理顺公、检、法三机关的法律关系,明确三机关的职能。最后,要强化大众传媒的监督功能。“建立合理的媒体监督模式,重要的是要寻求法律所保护的各种权益之间的平衡”[10]291。参考国外成熟的做法,进一步完善专门的发言人制度、记者招待会制度。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EB/OL].[2010-7-15].http://www.cnnic.net.cn/.
[2]李琪,陈奇星.中国公共行政管理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63.
[3]严一云,谢雪.网络民意与政府互动模式研究[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12): 4-6.
[4]程建.互动性行政行为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 11.
[5]科恩.论民主[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8: 39-40.
[6]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M].贺卫方, 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0: 11.
[7]WTKISOURCE.The Treaty of Amsterclam, Protocol NO.7-Protocol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subsicliarity and Proportion[EB/OL].[2008-12-8].http: europa.Eu.int/ comm./civil-socit/apgen_tn.htm/nality
[8]吴浩.国外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制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9]左卫民,万毅.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2003,(4): 139-143.
[10]谢佑平主编.司法公正的建构[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
[11]唐.R.彭伯.大众传媒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22
Law Deconstruction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s and the Governments Administrative Decision
HU Qi-ming
(Guk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Guilin 541004 China)
ZHANG Jin-song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In the age of Internet, Internet public opinions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ers’ attention and response.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public opinions and administrative decision making is more and more close.How to make good use of the network as the bridg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itizens 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has become a forward-looking topics.Internet public opinions and administrative decision making must be resolved by the framework of law instead of random relationship.In the virtual space, the activities of citizens and government and their interactions are restricted by the law.
Internet public opinions;administrative decision;law
G916.1
A
1008-8105(2011)02-0018-05
2010−09−08
广西哲学社会研究资助项目“网络民意与行政决策问题研究——以复杂性理论为视野”阶段性成果(08BZZ002)
胡启明(1979−)男,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干部;张劲松(1968−)男,武汉大学公共管理学博士后.
编辑 戴鲜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