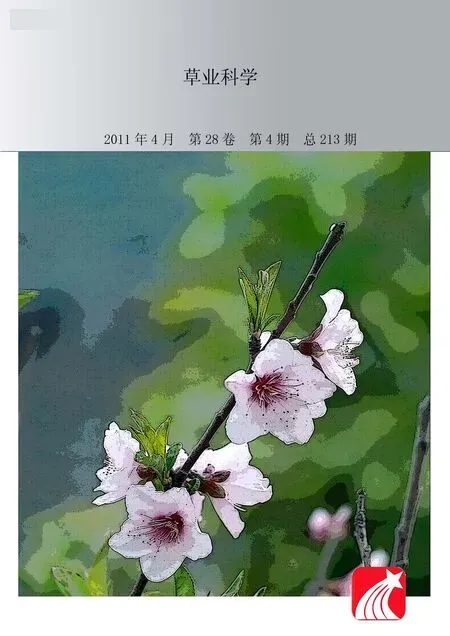草地生态系统健康研究述评
叶 鑫,周华坤,赵新全,温 军,陈 哲,段吉闯
(1.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 西宁 810008; 2.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49)
草地是地球上最重要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之一,也是我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生态系统,具有多种生态和经济功能。草地生态系统储存了陆地生态系统中近1/3的有机碳,维持着约30%的净初级生产力[1],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碳汇功能维持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近年来人类过度的开发活动导致了全球气候反复无常、土壤沙漠化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等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人类开始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也由此促成了生态系统健康学的发展。对草地生态系统进行健康评价能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草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诊断的可能性、病因学早期警示指标、治疗能力及防治措施,提出草地生态系统的管理指南[2]。但如何才算健康,怎样来评价健康却成为了贯穿草地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主线。Pyke等[3]认为,草地健康是草地生态系统中土壤、水分与生物资源的属性。同时还包括草地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于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即草地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目前,很多人对健康一词不能准确定义的原因在于,它把用于个体或小尺度范围的概念应用到了系统的层面。概念模糊的原因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度量标准,不够直观[4]。有学者[5]用全面平衡法计算了环境恶化对人类健康影响的经济价值,它与其他方法的区别在于提出了部分和整体间动态的关系且便于理解。它指出环境恶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降低了劳动力的供给,同时最终增加了对健康服务的需求。Wan等[5]认为对生态系统健康价值评价是将其纳入社会经济体系与市场化的必要条件,其本质就是把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结合起来,以得到人类对生态系统健康的正确认识。基于此,对于草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方法、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并对其评价指标选择、权重确定等难点问题给予建议,指出草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的发展趋势都很有必要。
1 草地生态系统健康研究的发展
1.1生态系统健康 生态系统健康的提法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Leopold提出了“土地健康”概念,他认为健康的土地是指为人类所占领但没有使其功能受到破坏[6]。20世纪70年代,有关生态系统健康的研究才正式开始,但最初的研究都是对其概念进行界定。1992年,Constanza[7]认为如果一个生态系统稳定而且可持续,具有活力,能维持其组织且保持自我运作的能力,对外界压力有一定弹性,那么这个生态系统就是健康的。随后,Karr等[8]认为生态系统健康就是生态完整性,且在受干扰时具有自我修复能力。1996年,国际生态系统健康学会将生态系统健康学定义为研究生态系统管理的、预防性的、诊断性的和预兆的特征,以及生态系统健康与人类健康之间关系的一门科学[9]。1999年,Jorgensen[10]提出生态系统健康共涵盖6个方面:自我平衡、没有病征、多样性、有恢复力、有活力和能够保持系统组分间的平衡。而后联合国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概念框架,将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提供的各种服务作为评估过程中所关注的核心内容, 同时也充分考虑生态系统自身的健康状况[11]。不管健康的概念究竟如何演变,它所涵盖的范畴是越来越广,同时也越来越全面。2006年,国内学者也提出生态系统健康是指系统内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未受到损害,关键生态组分和有机组织被保存完整,且缺乏疾病,对长期或突发的自然或人为扰动能保持着弹性和稳定性,整体功能表现出多样性、复杂性、活力和相应的生产率,其发展终极是生态整合性[12]。
但也有对生态系统健康持反对态度的学者,如Suter[13]认为生态系统不是生物,不会像生物一样生活,也不会拥有生物的健康特性。朱建刚等[14]从整体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角度说明了生态系统健康是客观存在的。也有人认为,因为生态系统健康并不是生态系统本身的内在属性,而是人们赋予给它的,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赋予生态系统健康不同的含义[15]。正因为生态系统不像任何生命个体那样有一个清晰的边界,这些特点使得找到一种参考状态变得非常困难。且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是一个多元的复合体,并没有足够的生态学知识或客观依据来证明某一元素比另一元素更重要,这就给人们关于评价达成共识造成了困难。有提出利用热力学原理来判断生态系统健康程度的方法[16],还有以耗散结构理论为基础设定健康参考态的[17]。Rapport[18]认为不能比较哪一种类型的生态系统比另一种更健康,而只能比较同一类型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
提出生态系统健康概念的本来目的是要为生态系统状态提供一种客观的度量,以及提供一个管理目标[19],Nelson[20]认为它是健康评价也是风险评价的一种形式,它作为服务决策者的工具来比较优先级别风险,以选择最有效率的风险管理形式。1998年,Schaeffer和Novak[21]首次探讨了有关生态系统健康度量的问题,但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Rapport等[22]认为虽然生物的一些特征在它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有很大的波幅,但这仅仅是一种度,这并不否认生态系统健康的范畴很大,但要明确地分解它需要整合社会、自然、健康科学的挑战。如今学者们对于生态系统健康的研究从简单的疾病的尺度,扩展到由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复合系统整体性研究。这种健康不仅反映了系统的自然属性,而且从更大层面上来说它变成了自然、人类、社会所综合考量的指标。
1.2草地生态系统健康研究进展 草地生态系统健康是新兴的生态系统管理学概念的一个分支,是新的环境管理和草地生态系统管理的目标[23]。将健康评价引入到草地生态系统的研究,在我国尚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而该项研究最早起源于美国。1919年,Sampson[24]从土壤有机质及地面凋落物的角度,说明土壤状况是草地基况变化的一个明确标志。1948年,美国学者Dyksterhuis[25]提出草原基况的概念,1949年他们又进一步提出草原地境学说,以减少种、增加种和侵入种反映植物群落的种类组成,以及它们的盖度或地上部分生物量所占比例,反映植物群落的结构变化。同时期,Humphrey和Mehrhoff[26]从草原生产角度给出了对基况的评价。这就是草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雏形。20世纪60年代,在联合国国际生物圈计划的推动下,原来的以较简单的草地组成为评价指标的方法得到了改进和发展,其中还应包括放牧、草地管理、野生动物等。80年代,澳大利亚编制了RANGECON软件对西部天然草地进行基况评价,首次实现了草地基况的程序化操作。最初,南非、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的草地评价都是以植物组成为基准点,以相同模型为基础进行评价比较[2]。90年代,美国全国咨询中心(NRC)及草原管理工作组(SRM)推荐利用阈值与早期预警指标对草原属性进行评价[27]。1994年,Dumanski[28]构建了草原健康评价体系,研究了草地生态系统的监测和调控方法。1997年,美国土地管理局、国家科学委员会、美国农业部形成了一个跨机构的委员会来监管国家草地评价技术的发展,并从事定量指标和协议的发展[29]。国外比较完善且应用于实践的草地健康评价方法是美国2000年发布的草地健康质量评价方法,但仍是以定性研究为主,提供一个初步的评价。2000-2005年,Pellant等[30]先后提出可用17个观测指标对草地的3个属性——土壤稳定性、水文学功能、生物群落完整性进行评价。该评价方法是到目前为止比较完善并且应用于实践的方法。此外,Ludwig等[31]指出生态系统可能会对干扰产生一种滞后响应,这种滞后甚至需要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评价必须加强生态系统质量未来状况的预测与预警。Haas等[32]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评价了18块草地农业在集约型、粗放型、有机型3种不同农业强度下的环境影响情况。Sullivan等[33]利用遥感和模型对草原低地农田的生态状况进行评价,目的在于实现产量和环境保护的平衡,并推荐半改良草地最为适中。由此可见,草地健康评价已不再是仅以其本身属性的好坏来衡量,而是需根据草地功能的不同,综合考虑自然、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的整合。
国内方面,对于草地健康的评价从理论上虽然也强调对综合各方面因素的复合评价,但实际上仍停留在自然属性这个范围之内。但是对方法和评价指标的选择上已取得了很大突破。侯扶江等[34]采用生理阈限双因子法,分析了多年生黑麦草(Leymuschinensis)轮牧草地的健康指标,以实现放牧草地的可持续经营。高安社[2]运用模糊综合评价对不同放牧强度羊草(Loliumperenn)草原进行评价,确定了包括4个植物方面、3个土壤方面共7个健康指标。通过草地生态系统健康的评价,建立兼顾社会经济效益和草地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双赢策略,来管理和开发生命支持系统,既可保持草地生态系统健康又使其免于遭受更严重的损伤。
1.3草地生态系统的退化 我国的草地生产力水平却远远滞后,全国平均每公顷草地仅生产7个畜产品单位,仅相当于澳大利亚的1/10,美国的1/20,荷兰的1/50[35]。统计表明,90%的中国草地正在某种程度上退化,且退化以200 km2/a的速度增加[36]。研究表明,与气候变化相比,土地利用的改变及过度开发对脆弱生态系统造成的威胁更大[37]。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居于种植业、养殖业交错和绿洲荒漠交错区,系统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和脆弱性,长期处于多种生态成分激烈竞争的动态过程中。因此,任何自然或人为的不良外力干扰,都会造成系统的失调和恶性循环[38]。草地退化释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相反健康的草地就必然具有较强的吸收和固碳的能力,起到气体调节和气候调节的作用。Rapport[22]认为随着生态系统在外界压力下变得高度退化,它同时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提供相同水平的服务功能。生态系统将在对需求持续增加的压力下继续退化,除非人们应用保护和恢复措施来实现区域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善。所以近年来人们对高寒草地的健康尤其关注。龙瑞军[39]分析了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的关系;于格等[40]利用RS和GIS技术,以生长季为时间单元,对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动态过程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但是有关高寒草地健康评价的研究非常少,因此对于决策制定者和管理者并没有提供有效地可供参考的依据和措施。吴宁和罗鹏[41]分析了长江上游高寒草地生态建设和管理中生态理论问题,对现行的草地管理体制提出了一些质疑。这对高寒草地进行健康评价的意义非常重大。评价的结果可以完整描述当前时段草地系统的健康水平和整体状况,进行现状分析,横向比较不同地区的健康等级,提供随时间变化的未来趋势,寻求压力和影响,探求受损原因,并定期地为政府决策、科研及公众要求等提供统计总结和决策报告[42]。
2 草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方法和步骤
有些学者认为[43]生态系统健康的评价只是一种在价值上用来衡量的东西,而没有实际的可操作性。但人们对系统健康评价的初衷是一致的,即评价的目的不仅是让人们知道这个系统到底健不健康,更重要的是确定生态系统破坏的阈限,实施有效的生态系统管理,实现系统的服务功能和可持续性。侯扶江和徐磊[44]认为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方法,经历了单因子罗列法、单因子复合法、功能评价法和界面过程法4个阶段。由于草地生态系统评价兼有自然和社会的属性,传统的单因子评价法虽然易于评价,但不能完整反映系统健康状况,多因子综合评价虽更趋于合理,但过于复杂,人为因素大。固此,生态系统健康也成为了多学科交叉的产物。目前,生态系统健康的评价方法很多,其产生的差异主要存在于指标体系选取和模型的建立上。
2.1确定评价的区域 要进行草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首先要确定评价的区域。区域可根据植物的特征、地表环境等条件选择,在此基础上根据人们的研究目的和方法进行划分。应注意的是,被划分为一类的草地应具有植被特征上的相似性和管理特征上的一致性[45]。参考区域的选择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不能是禁牧区,也不能是干扰过频的地区,它应该足够大且管理较好,以便能准确地评价所有的指标。
2.2草地生态系统评价体系 目前常用的生态系统评价体系包括指示物种法、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法等。选择适宜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目前研究较多。联合国环境计划署(UNEP)早在1992年于日内瓦就建立了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的评价指标体系[46],是较早的完整的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
2.2.1指示物种法 指示物种在系统中要求比较敏感,所处的生态位和发挥的作用比较特殊。通过对不同生物组织水平的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可对生态系统健康水平进行评价。目前,指示物种法在湖泊生态系统中应用较多。Sonstegard和Leatherland[47]指出银大马哈鱼(Oncorhynchuskisutch)对北美大湖区的生态系统健康有指示作用。Edwards等[48]采用鳟鱼(Squaliobarbusaurriculus)为指示种来监测湖泊贫营养化。该方法的缺点是:指示物种的筛选标准不明确,有些采用了不合适的类群,指示物种的一些监测参数的选择也会使评价带来偏差。
2.2.2结构功能指标体系法 刘纪远等[11]基于MA概念框架,提出了系统完整的三江源区草地生态系统评估指标体系,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土地覆盖结构和草地退化时空结构)、支持功能(初级生产力、土壤理化性状、野生动物栖息地)、调节功能(以水、碳调节,径流调节,土壤保持)和供给功能(以水供给和草地承载力)的4大类15个一级指标、75个二级指标。南非千年生态系统评价在多尺度上评价了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健康安全、生活安全、文化安全等)的关系[49]。Jorgensen[50]通过结构、功能、系统层面指标(由生态缓冲能力、有效能、结构有效能组成)通过直接测量方法(directly measured methods,DMM)及生态模型方法(ecological model methods,EMM)对湖泊生态系统进行评价。在外部的人为环境压力下,结构指标首先发生变化,其次响应的是功能指标和系统层面指标。周立业等[51]将草地生态系统健康的指标按照其功能分为3类:早期预警指标、适宜程度指标和诊断指标,但要想精确定量化尚缺乏可操作性。目前,对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评价已广泛使用价值尺度来衡量,谢高地等[52]进一步评估了我国各大区域草地生态系统价值空间分布的差异性。
2.2.3综合指标体系 随着研究和探索实践的深入,生态系统健康逐步发展成为包含生态、人类健康和社会经济的综合性概念,并涵盖生态系统服务和环境管理等相关领域[53]。考虑人类活动影响的指标体系可分为生态学指标,物理化学指标和社会、经济指标。针对不同的生态系统,指标体系的层次结构模型分为4层:总目标层、要素层、属性层、指标层[54]。该指标体系法综合了生态系统的多项指标,是从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演替过程,生态服务和产品服务的角度来度量生态系统健康,强调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55]。Foggin等[56]通过对青藏高原游牧民族的健康状况和风险因素的评价,提出了如何对他们的健康状况进行改善,这包括多个角度:教育、环境保护和可持续的资源管理、医疗人员的训练、便利的交通运输等。由于全球不同区域草地类型、规模及环境背景差异较大,统一的草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尚未形成。因此,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草地的特点,建立符合此类草地的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此进行纵向比较,是完善草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的重要途径。
2.3评价指标的筛选与确定 评价指标的选取针对不同的评价对象和研究目的,即使在同一类型生态系统中也可能存在着显著差异。指标筛选是评价过程中的难点,一些指标难以量化且标准值或阈值难以确定。任海等[57]认为评估生态系统健康的标准有活力、恢复力、组织结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维持、管理选择、外部输入减少、对邻近系统的影响及人类健康影响8个方面。Dale和Beyeler[58]的研究认为,生态指标应该满足以下多个标准:易测量,对系统压力敏感,对系统压力的反应可预知,可预测迫近的系统变化,可预测因管理行为而避免的变化,整合性涵盖系统的各个梯度,对自然、人为的干扰下以及随时间变化上的反应可知,低的变化率。综上述,选择指标时应遵循整体性、层次性、典型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可比性的原则。Önal等[59]认为定性定量结合在草地系统健康评价指标的筛选中亦很重要。徐丽君[60]对紫花苜蓿栽培草地的健康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上采用频度统计方法、理论分析法和专家咨询法相结合的方式经两轮的筛选,最终确定评价集合。周艳丽[61]在比较植被和土壤各个指标变化趋势的基础上,使用相关分析筛选出对放牧干扰敏感且变化相对稳定的8个指标,再综合各方面因素确定放牧条件下最适宜的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是凋落物量、群落平均总盖度和土壤的pH值。目前,对草地的评价指标大都集中在对其自然状态的选取上,如稳定性监测指标、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指标、改良土壤监测指标[62]。对社会、经济和人类健康综合指标的考虑还稍显匮乏。
2.4指标权重的确定 权重确定应该多利用数学方法,如利用层次分析法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经归一化处理后,确定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63]。因数学方法严格的逻辑性可对确定的权重进行处理,从而可尽量剔除一些主观成分。于声[64]综合考虑专家经验估计法在实际工作中的普及性和相对客观性,采用层次分析法与专家打分法相结合,是较理想的方式。在对重庆生态系统健康的评价中,高凯等[65]采用基于熵权的客观赋值法对评价指标进行定量化处理,大大消除了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增加了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可信度。一种好的权重应该是指标在决策或评价中相对重要程度的一种主观评价和客观反映的综合度量。但现行的方法大多只考虑了主观评价的一个侧面(如层次分析法等),或者只考虑了客观评价的另一个侧面(如熵值赋权法等)。在对河口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中,首先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系数,然后通过信息熵赋权法对确定的权系数进行修正,实现主观评价和客观反映的综合度量[66]。
2.5获得基础数据和信息 丰富的数据和信息资源可以提升评价的质量和精度。评价指标的数值及信息来自于野外生态调查、室内分析、社会调查及经济核算等方法[67],在对蛟河流域湿地健康评价中利用3S技术在中国湿地信息系统中直接提取2000年1∶5 000空间数据及湿地生态系统属性数据[63],得到评价区域底图的数据获取方式可以被借鉴到草地生态系统的大尺度评价之中。对于某些不易定量确定的指标,一般采用了隶属度评价的方法来进行量化[54]。
2.6草地生态系统评价方法 近年来各种评价生态系统健康的方法大量出现,在城市和湿地生态系统评价之中尤其突出。虽然很多方法并未尝试应用于草地生态系统健康的评价,但是有很大的借鉴价值。由于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本身存在一定的主观因素,因此通过多种方法的尝试和比较分析有助于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得出真实的结果。同时指标体系的建立关键在于评价方法的选择,好的评价方法不仅可以弥补指标选取时的弊端,而且关系到评价指标体系的准确性和合理性[68]。所以,对方法的总结和探索是十分必要的。
2.6.1VOR评价体系模型 用模型进行评价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研究方法。VOR模型是指由美国生态学家Constanza和Rapport提出的为反映生态系统自身特点的指标体系。1999年,VOR综合指数被国际生态系统健康大会接受为生态系统健康诊断指标,在实践中得到了一定的运用[69]。其中活力(V)反映的是系统的能量和活动性,它可用生态系统物质生产和能量固定的总量或效率度量;组织结构(O)反映的是系统结构,可以用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组合特征度量;恢复力(R)指系统应对外部环境胁迫干扰时的恢复能力,可选择抵御病虫害及恢复的能力来度量。其中,恢复力直接测量较困难,一般要求借助于计算机模型的帮助,如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模型(CENTURY)和林窗动态模型(GAP),通过这些模型可以估算出系统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状态的临界值[70]。其评价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GEHI=w1V+w2O+w3R
GEHI代表草地生态系统的健康指数,V、O和R分别代表活力、组织力和恢复力,w1、w2和w3分别代表对应的权重。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决定了其不能用单一的观测指标来准确概括,需要相当数量不同类型的观测和评价指标。
2.6.2COVR指数评价体系模型 基况(Condition)可以表示为生态系统的大气、土地与位点等因子的综合,主要指水热因素与土壤营养库状况的综合。地境是生态系统存在的自然环境依据,提供植被生长的气候条件和营养需求[33]。根据Hutchinson的多维生态位概念,侯扶江等[71]以此建立了植物与气候因子关系的综合评价模型来对草地生态系统健康进行评价,用基况修正VOR能够定量放牧压力和封育对草地健康的作用,避免各单项指标容易造成的误差,包含了VOR指数不能完全反映的草地健康信息。CVOR综合指数可以在相同尺度和起点上比较不同类型草地的健康状况,体现出草地健康主要取决于草地管理水平,具有较大的适用范围。随后,对内蒙古典型草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运用COVR指数,采用相应年份直接有效降水量作为群落的基况指标[72],但由于年份直接有效降水量差别不大,可能突出了基况指标的贡献,使COVR和VOR显著相关。因此,对于草甸草原或其他类型草原,考虑生态系统的群落特征和退化演替中优势种的更替,选取适当的植物种群亦可利用COVR模型进行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王明君[73]应用模糊数学方法与CVOR评价方法对不同放牧强度草地生态系统健康进行评价,虽然两者的健康指数有些差异,但将CK的健康指数都化为1,两种方法得出的评价结果较为一致,较好地反映了真实的健康状况。
2.6.3PSR评价模型 压力-状态-响应(PSR)评价模型是199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启动环境指标评价项目时首次提出的。PSR模型以系统压力、系统状态和系统响应作为生态评价判断准则,其中压力指标反映人类活动给环境造成的负荷;状态指标表征环境质量与生态系统的状况;响应指标表征人类面临环境问题所采取的对策与措施。PSR模型的优势在于综合了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影响、适用范围大、强调因果关系。刘明华和董贵华[74]在RS和GIS支持下建立了秦皇岛地区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压力-状态-响应概念框架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采用典型相关分析分析了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变化的影响。杨一鹏等[75]以遥感数据作为信息源,在GIS技术支持下建立了松嫩平原西部湿地空间数据库,以PSR模型为研究方法,建立了一套湿地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国内对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指标体系大都是以PSR概念模型为基础建立的,包括草地生态系统的评价。Chen等[76]以PSR概念框架为基础,对锡林郭勒牧草进行评价,帮助政府制定合理的政策来实现内蒙古草原的可持续发展。
2.6.4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简称AHP法)是美国运筹学家Satty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多目标决策方法,在各因素之间进行简单的比较和运算,就可以得出不同方案重要性程度的权重[77]。该法被广泛应用于自然和城市生态系统评价之中。周华坤等[78]应用该方法对三江源退化草地的原因和治理措施进行了定量化评价。徐丽君[60]对4种紫花苜蓿(Medicagosativa)栽培草地健康状况进行评价,采用了AHP与模糊综合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并用生态承载力的方法进行验证,得到了与模糊评价相类似的结果。它的特点是利用较少的定量信息使决策的思维过程数学化,从而为多目标、多准则或无结构特性的复杂决策问题提供简便的决策方法。它的缺点是无法有效反映评价结果的空间分布格局。
2.6.5指数评价法 指数评价法以监测点的原始监测数据统计值与评价标准之比作为分指数,然后通过数学综合作为环境质量评定尺度[79],目前最常用的是综合指数法,应用此法,可以体现生态环境评价的综合性、整体性和层次性。它的特点是评价的指标通常有十几个甚至更多,根据不同指标的重要性进行加权处理。通常是指标的完成值除以指标的标准值,乘以各自权数,加总后除以总权数得到。罗海江等[80]构建了区域生态系统生产能力指数评价模型,并对中国1998-2004年间区域生态系统生产能力进行评价,在时空上的差异上给予了很好的解释。该方法在草地生态系统评价中值得借鉴。
2.6.6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简称PCA),可以用较少的变量去解释原来资料中的大部分变异,将许多相关性很高的变量转化成彼此相互独立或不相关的变量。评价中可将众多的生态恢复环境效应的评价指标从新整合,抓住对象的主要方面,剔除众多指标中的重复信息,不仅减少生态健康评价的工作量,提高评价效率,而且可以更加全面地评价生态健康的环境效应[81]。马成德[82]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青海海南州天然草地典型的23个草地型进行综合评价,将海南州天然草地分为3个等级,并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得出了一致的结果。Miller[83]利用PCA分析对Escalante国家纪念区草地健康进行大尺度评价,为明确生态位的管理策略提供了依据。
2.6.7模糊综合评价方法 模糊性是指客观事物中的不确定性,模糊性的根源在于客观事物的差异之间存在着中介过渡[84],模糊综合评价将一些边界不清、不易定量的因素定量化,进行综合评价,是其他的数学分支和模型难以代替的方法。它能将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很好地结合起来,用模糊关系阵对定性定量指标进行模糊量化,再通过模糊权向量与模糊关系阵合成得到模糊评价向量。它在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中的模型为:H=W×R,式中,H为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矩阵;W为生态系统健康评价要素的权矩阵,W=(w1,w2,…,wn);R为各生态系统健康评价要素对各级健康标准的隶属度矩阵[85]。该法在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中运用较多,但它在要素对总体健康程度的权矩阵的赋值上受到了过多人为因素的影响。高桂芹[12]对东平湖区湿地现状和湖区湿地生态功能的评价运用了模糊综合评判模型,计算出湖区湿地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并依此提出了东平湖区湿地健康恢复技术方案。陈铭等[63]对蛟河流域湿地系统健康状况的评价利用GIS空间技术,通过模糊综合运算方法将复杂多层次评价问题转化为定量评价。Ferraro等[86]应用模糊逻辑的环境影响指标评价了南美洲大草原的复合农作物系统,以帮助找出更多可持续的方法来管理农业投入。
2.6.8聚类分析法 聚类分析法是根据离散的数据结果,运用数学方法来计算它们的相似程度或差异性,反映其亲疏程度,具体有欧式距离法和指标聚类树状图[85]。戴瑞[79]进行环境质量评价时应用遥感对所建立的分类模板,在一定的分类决策规则条件下,对图像象元进行聚类判断进行评价。此外,在人为经验划分放牧压力的基础上,周丽艳[61]以植被特征为研究对象,应用聚类法对研究区域做了定量划分,并运用历史资料做了进一步验证。
2.6.9属性综合评价法 属性综合评价系统是在属性集和属性测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对实际问题的定性描述进行度量的一种属性识别理论模型。在比较不同地区同一草地类型健康状况时,可由综合属性测度μi向量对第i个城市生态系统属于哪个质量级别(健康等级)做出判断。这种弱序的分割类只是一种相对的评价,但却能找出影响健康的限制因素[87]。刘丽丽等[88]应用属性层次-识别模型建立了城市生态系统健康属性综合评价体系,得出重庆市南岸区的生态系统属于亚健康类的同时,找出了影响城市发展的诸多限制因素,为合理规划提供了方法和措施。
此外还有典型相关分析法[89]、灰色关联法[65]、投影寻踪法[90]、内容分析法[42]等评价方法。近年来随着大规模高性能计算机的飞速发展,一系列新的计算方法如人工神经网络评价法[91]、集对分析[92]、系统动力学建模法[93]、鱼群算法[94]、粒子群算法[94]等应运而生。它们对解决大规模复杂系统中出现的模糊非线性、高维、多峰值等难解问题非常有利,往往具有通用、稳健、简单、便于并行处理等优点,但它们在生态系统健康领域中的应用还鲜为人知,在国内外现有的生态系统健康方面的书刊中很少有介绍[95]。
随着方法的改进与尝试,许多人希望通过对同一个评价对象运用不同方法所得出的结果进行比较,来进行验证和矫正自己的结论。单贵莲[96]通过对比灰色关联分析、模糊综合评价、VOR指数模型和CVOR指数模型评价结果可知,4种评价方法对内蒙古典型草原的评价结果较为一致。其中,灰色关联分析的计算过程最为简单,评价指标无人为因素限制。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在指标筛选、纳入方式等方面缺少一定的理论依据,但具有信息量大而且全面等优点,并且有利于与定性指标相结合。VOR和CVOR较为复杂,不易掌握,今后对组织力指数和恢复力指数的计算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找出能够指示这些指标的因素,建立准确且可实际操作的评价模式。周晓蔚[94]以长江河口为例,把基于智能算法的多属性评价方法引入到河口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中,建立了基于最大熵的河口生态系统健康模糊评价模型(FAME)、基于集对分析的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模型(SPAM)和基于投影寻踪的河口生态系统健康评价(PPEH)模型,运用FAME模型和SPAM模型分别对长江口生态系统健康现状、变化趋势进行评价分析,并用PPEH模型进行验证分析,为长江口综合整治及其他河口同类生态建设工程提供理论与方法储备。在许多案例中,像人类行为这些“软”的方面生来就不太容易定量,但却并不是不重要。一个完整的适宜的健康评价需要包括两个方面,O’Connell[97]支持开展方法论的工作来将二者最佳地整合成一个连贯的统一的体系。
2.7评价标准的划分 在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中,参考状态可以是同质的一系列生态系统中的平均状态,也可以是同质的一系列生态系统中个别健康生态系统的状态。人们对大多数事实可以有共同的认识,对价值的看法却很难统一。这一难以量化的等级划分迫切需要大量的评价案例和数据做支持。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评价标准可以通过以下方法确定:1)历史资料法;2)称参照对比法;3)借鉴国家标准与相关研究成果;4)公众参与;5)专家评判。但以上方法各有优劣,适用于不同类型的指标对象[96]。卢育红和李富平[98]把建议值作为很健康的标准值,以全国最低值为病态的限定值,在前者基础上向下浮动20%作为较健康和一般健康的标准值,在后者基础上向上浮动20%作为不健康和一般健康的标准值,前后两次确定的一般健康标准值相互调整得到最终值。中国湿地数据库已实现湿地属性数据与空间数据的提取、保存、查询及应用于一体。湿地健康评价模型与湿地数据库实现系统集成,将充分利用湿地数据库数据资源,以获取健康评价所需要的规范化数据文件[99]。对于草地生态系统,也有了数据集成,如锡林河草地资源信息系统以GIS为技术支持平台,建立锡林河草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决策的综合信息管理系统,使草地资源信息数字化、以实现信息的快速查询,且使查询结果图表化并实现同步更新[14]。而更大尺度上的数据库的建设,将是今后工作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如果利用meta分析,对同一课题的多项独立研究的结果进行系统的、定量的综合性分析,可以提供量化的平均效果来回答研究的问题。其优点是通过增大样本含量来增加结论的可信度,解决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
2.8模型时空尺度的扩展及综合评价 与3S技术相比,传统分析方法的主要缺陷是:评价指标难以空间量化、评价单元难以细分、评价结果难以空间显示和制图显示、难以进行动态评价和对比分析,而将评价结果通过ARCGIS软件的属性连接功能导入草地健康评价单元图中,这样每一评价单元都包含了健康评价的结果,通过地图综合和分层设色原理,可生成直观的健康评价图。近些年,遥感凭借实效性强、可实现大面积的同步观测、数据信息量大等特点在监测作物长势、作物估产、土壤水分监测等诸多方面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100]。在草地健康评价中,数据源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利用GIS可将野外数据和遥感数据整合,可同时拥有二者的优点。目前,该技术已成功用于评价包括城市、湿地、稻田和草地等多种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为有关部门采取相应政策措施,以确保生态系统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63]。在草地上,遥感在低高的分辨率上被用来直接提供牧草属性给放牧者,可以被用来管理食物供给和家畜率[101]。一个全面的针对草地应用评价的遥感方法由Hill[102]给出。还有学者[103]利用卫星遥感技术结合草地营养物质产量评价法,估算草地载畜量,将产量载畜量和营养载畜量有机结合。刘纪远等[11]根据遥感影像判读的原理和特点,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天然草地退化、沙化、盐泽化的分级指标(GB-19377-2003)》,制定了三江源草地退化遥感动态信息分类系统。利用已解译生成的草地退化类型数据,通过两期图像对比,判断退化草地是否发生好转,同时也判断健康草地是否发生新的退化。杨婷婷等[104]基于3S技术建立了“植被-风沙活动-土壤”3个层次的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对草地沙化治理工程进行生态效益评价。同时,未来健康评价的重点还应包括对健康风险的预测,Zhang等[105]基于GIS和AHP对草原火灾进行了风险分析和评价。综上所述,将3S技术及评估模型引入到评价体系中去,结合生态系统健康和服务功能,以自然和社会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综合评价将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但遥感也有缺陷,需要和实测数据进行很好的融合和检验,实现有效互补。
3 草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存在问题及发展趋势
3.1存在的问题 草地生态系统的健康评价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还很短暂,因此还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1)到目前为止,对草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仍有许多不确定性,尤其健康的标准还存在争议;2)草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指标体系还不够完善,指标零散,不具有普遍性,很难简单概括为一些易测定的具体指标[85];3)评价多集中在自然系统的领域,将经济、人文社会、人类健康领域都包括进来的评价较少,因此评价的现实意义及服务功能得不到有效体现;4)随着3S技术、数据模型融合技术的发展,依靠传统的实验手法已经很难满足人们对实验资料和准确性的要求,研究有待深入;5)生态系统是一个动态的演替过程,对于究竟是干扰还是演替所产生的影响很难区分[106];6)大多数关于生态系统管理的政策辩论在管理目标上产生分歧,说明生态系统健康未达到目标管理的要求;7)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体系多以亚系统、多组分为重点,以表观为指标,在系统化和综合性方面比较薄弱[51];8)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在经历了兴起阶段的快速发展后,似乎遇到了学科发展的瓶颈阶段,除了在方法上的革新外,没有太大的创新点。健康评价只是特定阶段的一股热潮,一种价值取向,还需要在将来的学科交叉或综合体系中寻求突破。
3.2未来发展趋势 1) 扩展草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时空尺度。由于系统评价尚属新兴科学,起步较晚,依靠短期的数据评价很难得到真实的结果,这就需要人们扩大时空尺度的研究。2)系统评价应以生态学、经济学、人类健康活动为基础,研究它们之间如何影响、如何协调以达到最优化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多学科交叉的复合系统是未来发展的趋势。3)应该要制定出一套有效可行的管理措施,在生态学的框架下,将系统的健康功能经有效管理完全发挥出来,使其成为一项真正实用性的技术。4)草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未来应与其邻近生态系统,周边环境,整个社会联系紧密的一项高度协调的评价技术。5)要进一步健全草原监管机构,强化草地执法队伍的建设。把草地生态系统的管理和建设纳入法制轨道,使草地资源及生态环境得到有效的保护和治理[107]。6)完善数据库系统,将单个的生态监测点纳入数据库管理系统,在此基础上与信息科学交叉建立智能化的监测与优化调控系统[51],并对其进行日常管理维护和信息服务。7)草地健康评价模型与草地数据库实现系统集成,将充分利用草地数据库数据资源,以获取健康评价所需要的规范化数据文件,实现草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横纵向比较,同时实现中国草地数据库功能模块的有效扩展[63]。8)要实现大尺度的统筹与比较需建立草地健康评价相关技术规范,做到有标准可以参考。
[1] 李博.中国北方草地退化及其防治对策[J].中国农业科学,1997,30(6):1-9.
[2] 高安社.羊草草原放牧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D].呼和浩特:内蒙古农业大学生态环境学院,2005.
[3] Pyke D A,Herrick J E,Shaver P,etal.What is the Standard for Rangeland Health Assessments[C].Ireland:Proceedings of the ⅦthInternational Rangelands Congress,2003:764-766.
[4] 陈仲新,张新时.中国生态系统效益的价值[J].科学通报,2000,45(1):17-24.
[5] Wan Y,Yang H W,Masui T.Considerations in Applying the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Health Assessment[J].Biomedica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2005,18:356-361.
[6] Rapport D J.Ecosystems not Optimized: reply[J].Aquatic Ecosystem Health,1993,2(1):57.
[7] Costanza R.Toward an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ecosystem[A].In: Costanza R,Norton B G,Haskell B D,etal.Ecosystem Health: New Goals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C].Washington D C:Island Press,1992:239-256.
[8] Karr J R, Fausch K D, Angermeier P L,etal.Assessing Biological Intergrity in Running Waters: A Method and Its Rationale[M].Champaigre: Illinois Natural History Survey, Illinois, Special Publication 5, 1986.
[9] McMichael A J,Bolinb C R.Globalization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human health: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s[J].Bioscience,1999,49:205-210.
[10] Jorgensen S E.A Systems Approach to the Environmental Analysis of Pollution Minimization[M].New York:Lewis Publishers,1999:20-53.
[11] 刘纪远,邵全琴,樊江文.三江源区草地生态系统综合评估指标体系[J].地理研究,2009,28(2):273-284.
[12] 高桂芹.东平湖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6.
[13] Suter G W.A cririque of ecosystem health concepts and indexes[J].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and Chemistry,1993,12:1533-1539.
[14] 朱建刚,余新晓,甘敬.生态系统健康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探讨[J].生态学杂志,2010,29(1):98-105.
[15] Wicklum D,Davies R W.Ecosystem health and integrity[J].Canadian Journal of Botany,1995,73:997-1000.
[16] Jorgensen S E,Mejer H.Ecological buffer capacity[J].Ecological Modelling,1977(3):39-45.
[17] Kay J J.A non-equilibrium thermodynamic framework for discussing ecosystem integrity[J].Environmental Management,1991,15(4):483-495.
[18] Rapport D.Defining ecosystem health[A].In:Rapport D,Costanza R,Epstein P R,etal.Ecosystem Health[C].Malden, Massachusetts:Blackwell Science Inc.,1998:18-33.
[19] De Leo G A,Levin S.The multifaceted aspects of ecosystem integrity[J].Conservation Ecology,1997,1(1):3.
[20] Nelson D I.Health impact assessment of climate change in Bangladesh[J].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2003,23(3):323-341.
[21] Schaeffer D J,Novak E W.Integrating epidemiology and epizootiology information in ecotoxicology studies:Ⅲ.Ecosystem Health[J].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1998,16(3):232-241.
[22] Rapport D J,Costanza R,McMichael A J.Assessing ecosystem health[J].Tree,1998,13(10):397-402.
[23] 李瑾,安树青,程小莉,等.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研究进展[J].植物生态学报,2001,25(6):641-647.
[24] Sampson A W.Plant Succession in Relation to Range Management[M].Washington: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Bulletin,1919:76.
[25] Dyksterhuis E J.Condition and management of range based on quantitative ecology[J].Journal of Range Management,1949,2:104-115.
[26] Humphrey R R,Mehrhoff L A.Vegetation changes on a southern Arizona grassland range[J].Ecology,1958,39(4):720-726.
[27]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Rangeland Health: New Methods to Classify, Inventory and Monitor rangelands[M].Washington: National Academy Press,1994.
[28] Dumanski J.Assessing the sustainable of Saskatchewan farming system[Z].CLBRR Technical Bulletin,1994.
[29] Pyke D A,Herrick J,Shaver P,etal.Rangeland health attributes and indicators for qualitative assessment[J].Journal of Range Management,2002,55(6):584-597.
[30] Pellant M,Shaver P,Pyke D.Interpreting Indicators of Rangeland Health[M].Colorado: Division of Science Integration Branch of Publishing Services(Version 4),2005.
[31] Ludwig D,Walker B,Holling C S.Sustainability, stability, and resilience[J].Conservation Ecology,1997,1(1):1-27.
[32] Haas G,Wetterich F,Köpke U.Comparing intensive, extensified and organic grassland farming in southern Germany by process life cycle assessment[J].Agriculture,Ecosystems and Environment,2001,83:43-53.
[33] Sullivan C A,Skeffington M S,Gormally M J.The ecological status of grasslands on lowland farmlands in western Ireland and implications for grassland classification and nature value assessment[J].Biological Conservation,2010,143(6):1529-1539.
[34] 侯扶江,李广,常生华.放牧草地健康管理的生理指标[J].应用生态学报,2002,13(8):1049-1053.
[35] 刘兴元,郭正刚,尚占环,等.学科建设是推动草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J].草业科学,2010,27(8):155-160.
[36] State Council.Some Suggestions Regarding Strengthening Grassland Protection and Construction[M].Beijing State Council Circular,2002:19.
[37] Grime J P,Fridley J D,Askew A P,etal.Long-term resistance to simulated climate change in an infertile grassland[J].PNAS,2008,105(29):10028-10032.
[38] 叶笃正.青藏高原气象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
[39] 龙瑞军.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之服务功能[J].科技导报,2007,25(9):26-28.
[40] 于格,鲁春霞,谢高地.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季节动态变化[J].应用生态学报,2007,18(1):47-51.
[41] 吴宁,罗鹏.长江上游高寒草地生态建设和管理中生态理论的若干质疑[J].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2004,10(4):537-542.
[42] 吴阿娜.河流健康评价:理论、方法与实践[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
[43] Kristin S.Ecosystem health:a new paradigm for ecological assessment[J].Trends in Ecology &Evolution,1994,9:456-457.
[44] 侯扶江,徐磊.生态系统健康的研究历史与现状[J].草业学报,2009,18(6):210-215.
[45] 梁燕,韩国栋,赵萌莉,等.草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内容与实施方法[J].生态工程,2004,24(6):107-109.
[46] 马克明,孔红梅,关文彬,等.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方法与方向[J].生态学报,2001,21(12):2106-2116.
[47] Sonstegard R A,Leatherland J F.Great lakes coho salmon as an indicator organism for ecosystem health[J].Marine Environmental Research,1984,14:1-4.
[48] Edwards C J,Ryder R A,Marshall T R.Using lake trout as a surrogate of ecosystem health for oligotrophic waters of the Great Lakes[J].Journal of Great Lakes Research,1990,16(4):591-608.
[49] Van Jaarsveld A S,Biggs R,Scholes R J.Measuring conditions and trends in ecosystem services at multiple scales: the Southern African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SAfMA) experience[J].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2005,360:425-441.
[50] Jorgensen S E.Exergy and ecological buffer capacities as measures of ecosystem health[J].Ecosystem Health,2005,1(3):150-160.
[51] 周立业,郭德,刘秀梅,等.草地健康及其评价体系[J].草原与草坪,2004,107(4):17-20.
[52] 谢高地,张钇锂,鲁春霞,等.中国自然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J].自然资源学报,2001,16(1):47-53.
[53] Gallopin G C.The potential of agroecosystem health as a guiding concept for agricultural research[J].Ecosystem Health,1995,1:129-141.
[54] 毕东苏,郭小品.长三角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J].生态环境,2003:327-330.
[55] 袁兴中,刘红,陆健健.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概念构架与指标选择[J].应用生态学报,2001,12(4):627-629.
[56] Foggin P M,Torrance M E,Dorje D,etal.Assessment of the health status and risk factors of Kham Tibetan pastoralists in the alpine grasslands of the Tibetan plateau[J].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06,63:2512-2532.
[57] 任海,邬建国,彭少麟.生态系统健康的评估[J].热带地理,2000,20(4):310-316.
[58] Dale V H,Beyeler S C.Challenge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ecological indicators[J].Ecological indicators,2001,1:3-10.
[59] Önal H,Algozin K A,Ik M I,etal.Economically efficient watershed management with environmental impac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goal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1998(53):241-253.
[60] 徐丽君.华北农牧交错带紫花苜蓿人工草地健康评价[D].北京:中国农科院,2009.
[61] 周艳丽.放牧条件下贝加尔针茅草原群落特征及健康评价指标的选择[D].呼和浩特:内蒙古农业大学,2006.
[62] 童琪,李洪泉,李才旺.天然草地生态系统功能与建设效果监测评价体系初探[J].四川草原,2003(6):4-6.
[63] 陈铭,张树清,王志强.基于GIS的蛟流河流域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J].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2006,22(3):165-172.
[64] 于声.模糊评价法在区域工业用地适宜性评价中应用[D].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2007.
[65] 高凯,郭跃,姜瑞华.基于熵权灰度关联法的重庆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26(1):72-77.
[66] Peterson M M.A natural approach to watershed planning, restoration and management[J].Wa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9,39(12):247-352.
[67] 单贵莲,徐柱,宁发.草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研究进展与发展趋势[J].中国草地学报,2008,30(2):98-103.
[68] 於方,周昊许,申来.生态恢复的环境效应评价研究进展[J].生态环境学报,2009,18(1):374-379.
[69] Costanza R,Norton B G,Haskell B D.Ecosystem Health: New Goals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M].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1992:239-256.
[70] 张弛,任海,邵华,等.森林管理中涉及的生态因素[J].热带地理,2003,23(2):97-101.
[71] 侯扶江,于应文,傅华,等.阿拉善草地健康评价的CVOR指数[J].草业学报,2004,13(4):117-126.
[72] 王立新,刘钟龄,刘华民.内蒙古典型草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J].生态学报,2008,28(2):544-551.
[73] 王明君.不同放牧强度对羊草草甸草原生态系统健康的影响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农业大学,2008.
[74] 刘明华,董贵华.RS和GIS支持下的秦皇岛地区生态系统健康评价[J].地理研究,2006,25(5):930-938.
[75] 杨一鹏,蒋卫国,何福红.基于PSR模型的松嫩平原西部湿地生态环境评价[J].生态环境,2004,13(4):597-600.
[76] Chen L R,Li Q,Ding Y.The Evaluation of Household Pastur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PSR frame[M].Gyeongj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CCIT),2007:2298-2305.
[77] 杨小波,吴庆书.城市生态学[M].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0.
[78] 周华坤,赵新全,周立.层次分析法在江河源区高寒草地退化研究中的应用[J].资源科学,2005,27(4):63-70.
[79] 戴瑞.规划环评下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价与研究-基于GIS和遥感技术[D].厦门:厦门大学,2009.
[80] 罗海江,方修琦,白海玲,等.基于VEGETATION数据的区域生态系统质量评价之二——生产能力指数评价[J].中国环境监测,2008,24(5):61-64.
[81] 於方,周昊许,申来.生态恢复的环境效应评价研究进展[J].生态环境学报,2009,18(1):374-379.
[82] 马成德.用主成分分析评价青海湖流域各类型天然草地质量[J].中国草食动物,2008,28(3):48-51.
[83] Miller M E.Broad-scale assessment of rangeland health, Grand Staircase-Escalante National Monument, USA[J].Rangeland Ecology & Management,2008,61:249-262.
[84] 夏元旭.辽宁省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D].沈阳:辽宁师范大学,2007.
[85] 尹连庆,解莉.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研究进展[J].环境科学与管理,2007,32(11):163-167.
[86] Ferraro D O,Ghersa C M,Sznaider G A.Evaluation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indicators using fuzzy logic to assess the mixed cropping systems of the Inland Pampa, Argentina[J].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 2003,96:1-18.
[87] 荣四海.基于属性理论的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09,30(3):92-95.
[88] 刘丽丽,刘金萍,李建国,等.基于属性层次-识别模型的重庆市南岸区生态系统健康评价[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0,19(2):214-219.
[89] 刘明华,董贵华.RS和GIS支持下的秦皇岛地区生态系统健康评价[J].地理研究,2006,25(5):931-938.
[90] 陈广洲,汪家权.基于投影寻踪的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J].生态学报,2009,29(9):4918-4923.
[91] 王任华,霍宏涛,游先祥.人工神经网络在遥感图像森林植被分类中的应用[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3,25(4):1-5.
[92] Ganoulis J G.水污染的工程风险分析[M].彭静,廖文根,李锦秀,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93] Linkov I,Varghese A,Jamil S,etal.Multi-criteria decision analysis:a framework for structuring remedial decisions at contaminated sites[A].In:Linkov I,Ramadan A.Comparative Risk Assessment and Environmental Decision Making[M].Netherlands:Kluwer,2004:15-54.
[94] 周晓蔚.河口生态系统健康与水环境风险评价理论方法研究[D].保定:华北电力大学,2008.
[95] 李景波,董增川,王海潮,等.城市供水风险分析与风险管理研究[J].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 36(1):35-39.
[96] 单贵莲.内蒙古锡林郭勒典型草原恢复演替研究与健康评价[D].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2009.
[97] O’Connell E,Hurley F.A review of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quantitative methods used in health impact assessment[J].Public Health,2009,123(4):306-310.
[98] 卢育红,李富平.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及实例分析[J].环境保护,2008,(18):39-41.
[99] 殷力,张树清.中国湿地信息系统的建立[J].东北测绘,2001,24(3):7-10.
[100] 李晶晶,覃志豪,高懋芳.应用遥感、GIS对稻田生态系统健康程度的监测评价研究——以长江下游平原为例[J].生态环境,2008,17(2):777-784.
[101] Roshier D,Lee S,Boreland F.A digital technique for recording of plant population data in permanent plots[J].Rangeland Manage,1997,50(1):106-109.
[102] Hill M J.Grazing agriculture:managed pasture,grassland and rangeland[J].Remote Sensing for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2004(4):449-529.
[103] 金花.基于3S技术支持的草地营养与载畜量评价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农业大学,2009.
[104] 杨婷婷,吴新宏,王秋菊,等.基于3S的草原沙化治理工程生态效益评价与实证研究[J].草业科学,2009,26(9):7-12.
[105] Zhang J Q,Okada N,Tatano H,etal.Damage evaluation of agro-meteorological hazards in the maize-growing region of Songliao plain,China:case study of Lishu county of Jilin province[J].Natural Hazards,2004,31(1):209-232.
[106] 曾晓舵,丁常荣,郑习健.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及其问题[J].生态环境,2004,13(2):287-289.
[107] 才旦.青海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的评价、功能失调原因和治理对策[J].草业科学,2006,23(9):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