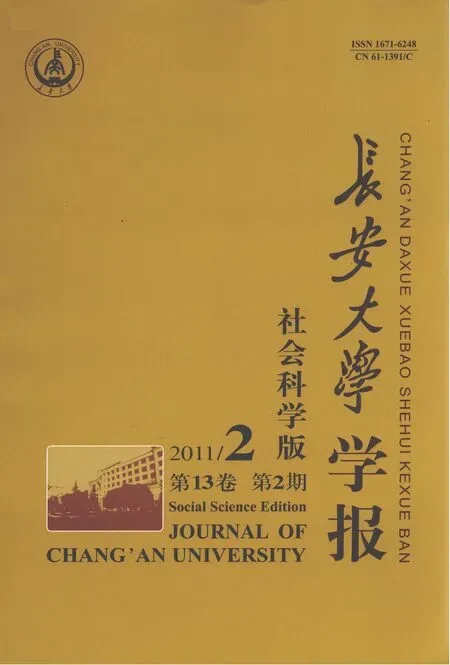从“澄怀”到“味象”
——从宗炳“澄怀味象”看审美条件
胡 牧
(重庆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重庆 400047)
从“澄怀”到“味象”
——从宗炳“澄怀味象”看审美条件
胡 牧
(重庆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重庆 400047)
从宗炳“澄怀味象”的美学意义、“澄怀味象”与审美发生机制、“澄怀”与“味象”的顺向关系、审美的主客关系4个方面探讨审美得以产生的条件。分析认为,美是主客体相互融合、共生的结果,真正的审美就是沉潜于对象中“主客合一”的先“澄怀”后“味象”的一个审美过程。
审美条件;宗炳;澄怀味象;主客合一
审美何以发生是一个关系到美感如何产生的问题。怎样才能产生美?美学界见解蜂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没有定论。叶朗在《现代美学体系》中对审美感兴作了研究,他将审美感兴的过程细化到对审美注意、审美期待、审美知觉、通感、审美想象、审美领悟、审美情感、审美回味和审美心境进行研究,指出审美感兴具有无功利性、直觉性、创造性、超越性和愉悦性的特征。叶朗还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对“澄怀味象”作了专门探讨。审美就是一个探讨有无的问题,审美探讨的核心在于审美如何发生。张法在《美学导论》中对怎样获得美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美基于心理距离”、“美呈现为直觉形象”、“美体现为主客同构”。唐虹在《澄怀味象——宗炳的本体论艺术直觉观》一文中肯定了“澄怀味象”作为艺术直觉思想的积极意义。李健在《“应会感神”:宗炳的感物美学》一文中同样强调了审美主体“直觉”的重要性。郑蓉在《艺术创作主体和审美主体的澄怀味象》一文中着重从审美主体的角度分析了“澄怀味象”这一命题。学者们对宗炳“澄怀味象”命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审美主体的作用上。他们的研究充分说明宗炳思想的价值和意义是重大的,足以形成“阐释的循环”。本文试图发掘“澄怀味象”命题作为审美发生机制的理论内涵,从而阐释这一命题与其他美学命题的“互文性”意义。
一、宗炳“澄怀味象”命题的美学意义
我们知道,儒家美学思想和道家美学思想是中国美学的源头,后世美学的许多观点都肇始于此。宗炳的“澄怀味象”思想也不例外。“澄怀味象”是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美学命题,它揭示的是审美的机制,即主体只有“澄怀味象”,才能在虚静中达到主客合一、天人合一的境界。宗炳在《画山水序》中写道:“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是以轩辕、尧、孔、广成、大隗、许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游焉。又称仁智之乐焉。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在这段话里,宗炳明确区分了主体和客体的不同,提出了类似“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观点。这里的“味”是“象”对“澄怀”的主体生发的一种精神和心灵的愉悦和享受,是一种审美意义上的“味”。宗炳的这一理论,是在继承老子“涤除玄鉴”,庄子“心斋”、“坐忘”命题的基础上对“味”这个美学范畴的重大发展,无疑对钟嵘的“滋味”说产生了启示作用。
其实,宗炳是以佛学家的身份提出“澄怀味象”这个命题的。尽管他是从美的欣赏角度提出“澄怀味象”的观点,但他的观点明确把“味”同美的鉴赏(或艺术鉴赏)联系起来,“这在魏晋南北朝的美学史上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同当时佛学的流行有密切关系”[1],从而在美学史上显示出自身独特的美学意义。
第一,宗炳“澄怀味象”的说法,实质是对老子“涤除玄鉴”思想的继承和深化。“老子哲学和老子美学对于中国古典美学形成自己的体系和特点,影响极大。中国古典美学的一系列独特的理论,都发源于老子哲学和老子美学。”[2]也就是说,老子学说成了后世学说的理论源头和资源。因此,我们考察宗炳的“澄怀味象”,就不能不分析老子哲学及其美学思想。《老子》第十章中有:“涤除玄鉴,能无疵乎?”其中,“涤除”即洗出垢尘,排去人的各种主观欲念、成见和迷信;“鉴”是观照,“玄”是“道”,“玄鉴”就是对于道的观照。后人把老子的命题发展成为“心斋”、“坐忘”,建立了关于虚静的审美理论。宗炳所说“澄怀”的命题源头即老子的“涤除玄鉴”思想,它要求主体要有虚静空明的审美心胸。《宋书·隐逸传》有这么一段记载:(宗炳)以疾还江陵,叹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睹,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这段话表明,“味象”与“观道”是一致的。这显示出宗炳思想与老子思想的一致之处。
第二,宗炳“澄怀味象”的“象”,是与自然山水中的形象给人带来的“味”(审美享受、审美愉悦)分不开的。他一方面说:“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认为自然美给予人的这种精神审美享受是无限的。另一方面,宗炳又指出:“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这里所说的“以神法道”的“圣人”指佛,“贤者”则指佛的信徒和佛学信仰者。佛“以神法道”,化生万物,而“贤者”(佛教徒)则由“澄怀味象”而通于“道”(佛的“神道”)。山水是“圣人”(佛)“以神法道”,化生万物产生的精灵,是佛道的呈现和化身。所以从“圣人”(佛)来说是“以神法道”;从山水来说是“以形媚道”,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山水感“圣人”(佛)之“神”而生,它的“形”(“质有”)即佛“神道”的体现。山水“以形媚道”的“媚”即亲顺、亲和、爱悦之意。因此,山水显示出“道”的感性形态和神妙,即文中所言“质有而趣灵”。从历史上看,宗炳的这种思想显然源于老子美学中“象”、“味”、“道”、“涤除玄鉴”等核心范畴。宗炳所认为的“道”与老子的“道”相通,即自然之道。它从审美观照的角度强调了审美心胸与“道”的内在关系。
第三,宗炳“澄怀味象”的思想,强调了“澄怀”在审美观照中的前提作用,以及“味象”带给人的巨大审美愉悦。宗炳没有忽视对山水之形的描绘,认为山水“质有而趣灵”[3],“灵”与“神”相通,因而无生命的有形山水具有了神性或灵性。宗炳还认为,画者要“应会感神,神超理得”,但由于“神本无端,栖形感类”,所以神还需通过形来显现。可以说,从“形”至“神”的体悟过程也就是“澄怀味象”的过程。“澄怀”即如老子所言:“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第十六章)。
“澄怀”是实现“味象”的必要条件,只有主体“澄怀”、“虚静”,才能达到“万虑消沉”,“胸中宽快,意思悦适”(郭熙《林泉高致·画意》)的审美心胸。主体“精神的‘静虚’实现了心与外物的距离化,是艺术空灵化的基本条件。可见,心境的“空明”充实与艺术的‘空灵’是相辅相成的”[4]。“虚”不是“无”,“虚而万景入”(刘禹锡《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引》),审美带给主体的是感性体验。“味象”就是观“道”,即人通过感觉经验可以达到对“道”的观照,并从中获得身心的愉悦。宗炳的这种思想对后来陆机在《文赋》“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和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乃至刘禹锡、苏轼等人的思想均有启示作用。
除了以上论及的几个方面以外,宗炳“澄怀味象”的美学意义还体现在对孔子“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命题的深化,是“对老子美学的复归”[5],因此更接近于审美的本体,既保持了审美的纯粹性,又充分肯定了山水自然的价值是审美而非实用。
二、“澄怀味象”与审美发生机制
“虚静”是庄子所强调的认识“道”的途径和方法,同时也是能否创造合乎天然的艺术之关键。“虚静”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有两重含义。一方面,它要求人必须“无知无欲”,“绝圣弃智”;另一方面,它要求人必须“澄怀味象”,获得审美的自由性和超越性。为此,庄子指出了达到“虚静”的两种重要方法是“心斋”和“坐忘”。《人间世》云:“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大宗师》又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这就要求人忘掉一切(包括自己)的存在,抛弃一切知识和智慧。因为“道”不是通过人的普通感官和逻辑分析获得的,而只能用虚静的审美心胸“澄怀”体验,直观或顿悟才能获得。这种“虚静”状态直接影响了中国诗性智慧的生成,使创作者十分习惯于通过对审美客体的整体直观把握达到对“道”的颖悟,并通过寓意于物象的“内游”、“内视”、“神遇”、“玄化”、“目想”、“心虑”、“澄怀”、“静观”等观照方式展开审美的全程全域。在庄子学说中,“虚静”成为一种根本的审美态度,一种与天地同一、与万物合一的彻底解放的自由的精神活动。庄子努力维护着审美的纯粹性,也即自由性。这是一个与现实相对而存在的审美自由世界,尽管人在现实世界中不纯粹。人的纯粹性主要是针对更高的本体境界来加以规定的。因此,主体对本体境界的追求成为对自身本质的最高肯定和确证。换言之,“虚静”在审美静观中体现的纯粹性对于人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是人的本质(类本质)体现。这种本质(类本质)体现同“自由”紧密联系在一起。
“澄怀味象”产生于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相互作用中,它是审美主体在审美观照与审美体验中所产生的极其复杂的心理活动和心理过程。这样一来,审美主体对于客体持有一种“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的自然之心,以一种看似无心,实则超越现实的幽独情怀、虚静之心去包容万物,去容纳万境,以博大心胸去挖掘、生成主客体间无尽的“意义”。
审美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即超越性,它是对现实、理性、物质和功利性的超越。这是审美活动本质的一个层面。在审美活动中,人的感觉发展出“全部丰富性”和实现了“自然的人化”,从而体现了本体性自由并成为对人的本质的最高肯定。在这个意义上,“虚静”之心和“澄怀”之心带来的审美自由已完全融入审美活动中,规定着主体的精神气质和审美得以自由实现的内在依据。由此,我们可以说纯粹的审美就是纯粹的审美静观。诚然,美的发生离不开人的感官,这其中尤以视、听两种感知能力最为重要,但这只是审美的一个基础(前提),还是一个较低的层次。中国传统美学从老庄到宗炳讲审美体验,其重心恰恰不在感官所呈现的物象本身,而在于摆脱物象的外在实体向精神自由之境上升。也即,审美活动越能引人暂时忘记现实(物质功利),就越具有纯粹性和超越性;而越具备超越性,体验就会产生更高层次的美感。在康德看来,自由不仅作为本体性存在成为人的审美追求的最终目的,而且也经过审美化而进入审美之域。康德所言的这种自由,首先是一种纯粹和先验的自由,即在审美活动中想象力和知性的纯粹自由。康德在美的分析中通过四个契机具体规定了这一自由活动的非经验、无目的、非功利的特征。这样一来,审美观照和鉴赏活动实现了对人的自身有限性的超越。这一自由是由人的本体性生发出来,并对人的主体性作出了最高肯定。在此意义上,自由完全融入了审美实践活动之中,标识了审美活动的特征,规定了审美活动的本质。因此,精神自由问题是审美体验的关键问题;“象”(作为客体的“象”)的目的不是让人“回到事物本身”,而是向人精神的自由向度回归。所谓“澄怀”,就是使情怀高洁,不以世俗的物欲容心,即《明佛论》所谓的“神圣玄照,而无思营之识”,这就“实现了审美注意的整体持续性、稳定性、集中性、连贯性,审美活动没有中止,审美感受丰富而又整一,趋向质高量巨的境地”[6]。也即“让全部意识之中只有对于风景、树林、山岳或房屋之类的目前事物的恬然观照,使自己‘失落’在这事物里面,忘去他自己的个性和意志,去过‘纯粹自我’的生活”[7],从而实现对“物”的彻底弃绝。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宗炳对“味”的审美功能和前提极端看重,将之视为审美体验的核心范畴。
三、“澄怀味象”:审美是主客体交流中的同构
在现实世界中,审美离不开人的视听。而视听恰恰会让人关注事物本身,从而被外界实在的东西所束缚。因此,人的现实性与美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根本对立的。所以老子才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正是要引导主体在对“音”与“象”的彻底摆脱中实现心灵的高度自由。进而言之,美的产生,“道”的呈现,不仅仅单纯依靠感官,更重要的是依靠整个主体向对象客体的全方位敞开和无限切近,而不是对象世界朝人的全方位敞开。审美产生的关键在于主体性朝向精神向度本身。这就存在着一个“美的规律”的问题。“而‘美的规律’强调的恰是人的内外在自由度,内外在自由度越大,达到的美的层次就越高,获得的美的享受就越多,美感就越强烈。”[8]也就是说,审美主体只有暂时与事物的各种实用功利断绝,才能以超越功利的审美心态来沉潜在对事物美的观照之中。审美依赖审美感觉(直觉),因此我们说审美是一种感性活动,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审美可以缺少理性呢?王国维首先将康德、叔本华等“审美无利害关系”理论引入中国。他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地位》中把无利害关系当作美的根本性质。继王国维之后,蔡元培、鲁迅、郭沫若、朱光潜、宗白华等人都介绍过“审美无利害关系”理论,但丰子恺与众人不同的观点在于,他更倾向于席勒的“美的主观融合说”,并进而解释道:“梅花原是美的,但倘没有能领略这美的心,就不能感到其美。反之,颇有领略美感的心,而所对的不是梅花而是一堆鸟粪,也就不感到美,故美不能仅用主观或仅用客观感得。二者同时共动,美感方始成立。这是最充分圆满的学说,世间赞同的人很多。”[9]丰子恺认为,审美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有两个:一是审美主体要有一颗能领略美感的心;二是审美对象也要具有美感。“澄怀味象”使主体在审美实践中暗合《诗品》中的“人心感物”、“摇荡性情”的美学标准,以及《世说新语》时代“山水之美,天下共谈”的风流态度。谢灵运对山川林泉的眷恋,陶渊明对田园生活的回归与自适,更使人对自然的趋求有了清新任游、物我两忘的逍遥意味,成为钟嵘所言的“神之所畅,孰有先焉”的性情所归。人与自然的这种“合一”正是主体与客体交流中的同构。
四、“澄怀”与“味象”的顺向关系
前文论及,“澄怀”是审美的前提,是主体向内在自我的回归。主体的“澄怀”有利于审美自由自觉地发生,有利于使主体在自由的境界用审美的视角观照客体,有利于形成审美的自由空间。在主体“澄怀”之后,主体还需进一步“味象”,“澄怀”不仅是审美得以发生的前提,而且是审美活动展开的第一步。宗炳的这一思想实际上把审美的重心放在主体上。宗炳认为,主体只有“身所盘桓,目所绸缪”,才能“应目会心”、“以行写形”、“以色貌色”,达到庄子所谓“庖丁解牛”的自由境界。这样一来,“澄怀”与“味象”尽管具有顺向关系,但两者也具有共在关系。按照审美的普遍观点,审美的意义来源于“澄怀”与“味象”的结合,审美意义的生成靠的也仍然是在“澄怀”与“味象”之间建立联系。“澄怀”指涉的是主体的心灵活动,“味象”之“象”指涉的是客体,“澄怀味象”是一个审美过程,是一个有机整体。在真正的审美活动中,在审美心理的作用下,审美主体“澄怀”,开始慢慢与外在世界暂时隔绝,主体充分调动审美感知,进而进入审美感兴阶段,开始对“象”进行审美观照,主体这时所收获的是一份审美的自由和认识。这充分说明“主客合一”、“天人合一”是审美的真正境界,确切地说,是审美的最高境界。
“澄怀”与“味象”的顺向关系昭示了该命题的真理性。王昌龄在《诗格》中谈到“诗有三境说”,可以看作是对宗炳等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精粹的继承和发扬:“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物境一。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情景二。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意境三。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澄怀”与“味象”的顺向关系揭示的是主客合一的关系。审美的自由基于宇宙与生命、艺术的浑然同一。“澄怀”既可指环境,也可指内心,内心一静,就呈“虚”态,“虚”不是“空”也不是“无”,而是“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苏东坡语)的审美境界。作家艺术家自由的创作心境离不开“恬淡”、“虚静”的审美之心去“澄怀”。所谓“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老子》第三十一章)是也,同时也离不开主体“味象”的审美心理过程。
主体的“澄怀”带来的是心境的“空”(“味象”的前提之一)。空明的觉心,包容万千的想象,“空”表征着人的“自由”和“性灵”。“四时自尔行,百物自尔生,粲为日星,翁为云雾,沛为雨露,轰为雷霆,皆自虚空生”(苏辙《论语解》)。司空图在《诗品》里形容艺术的心灵当如“空潭泄春,古镜照神”,形容艺术人格为“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神出古异,淡不可收”。艺术的造诣当“遇之匪深,即之愈稀”,“遇之自天,泠然希音”。“澄怀”实现了心与外物的距离化,是艺术空灵化的基本条件。可见,“澄怀”与“味象”是相辅相成的,它所带来的是“空灵”的境界,如王昌龄“诗的三境”,“空则灵气往来”(周济语)。“灵气”的到来,是美感与艺术品诞生的时刻,也就是“灵”显现的时刻。“灵”是心灵内部方面的“空”。由静入虚,由虚至空,由空至灵。灵的心境让主体从心境的空明无妄中亲近自然和理解自然,可以说,在审美的全过程,人与自然都是亲密无间的,主客合一的。经过“澄怀味象”,审美主体观照之“象”最终变为心中营构之“象”。
五、结 语
“澄怀味象”美学思想的最独特之处,在于它包蕴了审美活动得以发生的主客条件问题以及审美效果问题。这层意义的呈现在中国美学史上无疑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也为我们理解美的生成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艺术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不仅是创作主体虚静之心和“澄怀味象”的产物,也是接受者审美体悟和静观的产物。我们也可以从中获得某些对艺术创造有益的启示,从而使这种“澄怀味象”获得某种方法论意义。我们不但把研究主体作为一般性的个体对客体的反应,而且还把这种考察从个体层面延展到规律性层面,探讨作为多样性与独特性相统一的个体对客体反应的差异性、类似性和多样性等问题。有关审美产生的机制、条件等问题还将继续讨论下去,而这样的讨论无论是对审美的本体问题的揭橥,还是对审美的文本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1]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2] 叶 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3]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
[4] 胡 牧.《静虚村记》:禅境诗意:兼谈创作主体的审美心境[J].名作欣赏,2009,30(2):65-67.
[5] 叶 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 袁鼎生.美海观澜:环桂林生态旅游[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7] 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8] 李启军.文艺活动:与“美的规律”相伴而行[J].社会科学家,2003,18(9):138-142.
[9] 丰子恺.丰子恺文集:第2卷[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
From Cheng huai toWei x iang—esthetic standards of ZONG Bing's Cheng huai andWei xiang
HU Mu
(School ofMedia,Chongqing Nor mal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7,Chian)
The author i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sthetic meanings,creating mechanism for esthetic appreciation,the correlation and subject-object relation of ZONGBing's Cheng huai andWei xiang.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esthetics can be mixed together so thatmore beauty can be produced.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genuine appreciation of beauty often takes place in the process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subject and object,and the realization from Cheng huai toWei xiang.
esthetic standard;ZONGBing;Cheng huai andWei xiang;combination of the subject with object
B83-06
A
1671-6248(2011)02-098-05
2010-11-09
胡 牧(1981-),男,重庆市人,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