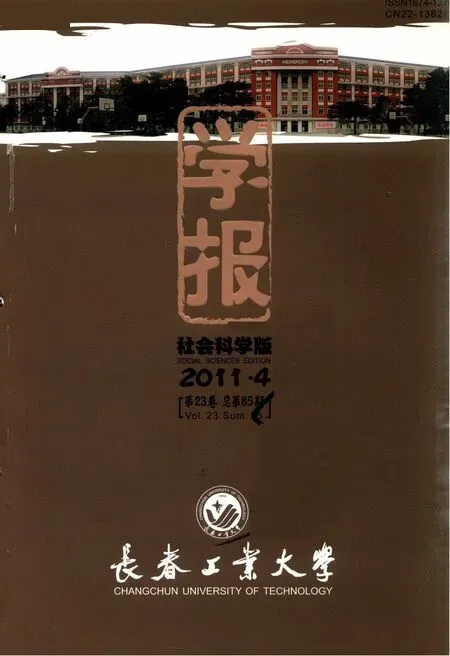从老书店到人民出版事业
——中华书局转型推力分析(1949—1953)
黄礼群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230039)
从老书店到人民出版事业
——中华书局转型推力分析(1949—1953)
黄礼群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230039)
从民国走来的中华书局,在建国初遭遇经济困难,营业空间一方面因为国营出版事业短时间内的迅速膨胀受到挤压,另一方面政府在文化出版事业进行的计划化与专业化改革也束缚了中华书局的手脚。而在内部,中华书局资方的话语权因为外部政策限制和内部工人地位的上升被削弱。有感于此,中华书局急于摘掉“私”这顶帽子,从一家老书店转型到人民出版事业。
中华书局;转型;1949—1953
中华书局1912年创办于上海。经过几十年的辛苦经营,到建国前,中华书局已是民国四大书局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一家文化服务机构,中华书局将如何面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怎样在新环境中完成转型,由一家老书店转型为人民出版事业服务。目前对于中华书局的研究成果较少,在有限的研究成果当中,首先是一些原中华书局工作人员回忆纪念性的文章,主要收录在《回忆中华书局》一书中,这类文章在于其史料价值;另一方面有专门博士论文研究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的关系。本文则主要研究从建国到1953年底最后一次申请公私合营这段时间里,在新环境中是什么推动中华书局急于和“私”划清界限,屡次主动向出版总署申请转型服务于人民出版事业。
一、两大主要收入来源被切断
民元之际,中华书局得益于陆费逵的远见卓识,乘革命共和之东风,依靠新式教科书取得成功,在民国近四十年的经营史上,教科书一直是书局的主要业务,特别是从1930年到1945年这段时间里,在每年的利润中,“中小学教科书占总额的70%以上”。[1]建国初期,国营出版力量还很弱。据当时估计,公营力量只占全部教科书产量的1/5弱,面对全国约28万令纸的教科书需求,公营力量不得不求助于私营力量。1949年7月,中华书局同时参加了新政府组织的华北联合出版社和上海联合出版社,参与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工作。在新成立的这两家中小学教科书出版机构中,虽私营资本分别占了73.6%和79.25%,但是领导权却是掌握在只占股本总额20%左右的公营力量手中。此前中共中央在给武汉市委关于中小学教科书问题的指示中,对于教科书的使用就明确了“全国各地用教科书,除一部分小学教科书本有地区差别外,均应在可能条件下要求一致。华北的教科书编审会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教科书编审机构的基础而成立的。”[2](P129)也就是说建国前,政府就否定了私营出版机构有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的权力,它的出版只能依靠公营力量来进行。以1951年为例,在全国1.4亿余册中小学教科书中,90%是由公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出版。1952年10月教育部、出版总署又同意成立专门的教科书出版委员会,这样原来作为中华书局主要业务——中小学教科书出版发行就彻底掌握在公营力量手中。
除中小学教科书收入丧失外,中华书局印刷所收入的锐减更是雪上加霜。中华书局印刷所在民国时期可以说是私营印刷企业中的佼佼者,除印书外,还承接其他社会业务。开始时候大宗订单来自于印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烟壳,后来则主要承印中央银行的辅币、邮政部的邮票。从1922年到1936年书局变更会计年度,在十几年的发展时间里,印刷所的营业额在书局的总营业额中一直保持在20%到36%之间,此后印钞业务增加,从1945年到1949年5月,中华书局印刷所在上海的总厂的印钞业务繁忙,“除了蒋政府改革币制,换发金圆券时停了一个月左右外,其余时间,都是日夜赶印,连星期天都照样加班。”[3](P197)在书局营业总额中的比重也从原来最高的36%涨到60%左右。这些来自于官方的订单给中华印刷厂带来了稳定的、数额巨大的收入来源,然而建国后,这项特殊的营业来源很快丧失。1950年2月22日,人民银行通知中华书局,原来由中华书局上海印刷所代印的钞券从即日起停止印刷。而当时中华书局的经济情况是“挹注所资,多赖印所”,[4](P231)完全停印意味着收入几近枯竭,影响可想而知。
中华书局1950年净亏2,870,000,000余元;1951年净亏5,766,900,000余元;1952年净亏14,748,800,000余元;1953年净亏6,631,000,000余元①旧币。,不得不靠变卖剩余物料、房产和地基维持周转,书局原办的《新中华》、《中华少年》等杂志也被迫陆续停刊。建国初文化市场萎缩不是解释困难的理由。胡愈之在1952年10月第二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我们的出版事业,在这三年里,有了很大的发展。书刊出版发行的册数,较解放以前大为提高……约为解放前的五倍。”[5](P271)足以说明建国初的文化市场不但没有萎缩反而大大的繁荣了,经济困难出现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建国后国营出版力量在国家政权的保护下迅速发展,大大挤压了中华书局的营业空间,而造成中华书局连年亏损的直接原因则在于:一是教科书出版收入被切断;二是印刷所收入在短期内骤减。
二、发行工作受制于人
民国时期,中华书局在全国主要城市都有自己的分局。在收入上,每年分店营业总额都与总店不相上下,并且略高。建国初中华书局不再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后,遍布全国的分局入不敷出,成为书局一大包袱。
为了减轻经济负担,中华书局联合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向出版总署表示出希望成立一个公私合营的发行组织的愿望,将发行所从书局剥离出来。1950年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后,在出版总署的牵头组织下,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联营书店和三联书店的发行组织合并,成立公私合营性质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以下简称“中图公司”)。原中华书局各地发行机构的业务和人事领导权一并移交。中图公司成为建国后继新华书店之后又一家大的发行机构,负责发行五家公司的出版物。中图公司筹备之时,扮演的就是国营新华书店的助手角色,虽有公股的加入,但毕竟只是一家公私合营性质的企业,和政权的亲密关系远远不如国营新华书店。作为“一个过渡性质的组织”,[6](P94)在建国初追求发行一元化的环境中,中图公司被新华书店合并是迟早的事情。中图公司和新华书店总店通过签订《相互往来合约》以明确各自的业务范围,互通声气、密切配合,原来发行行业中的多极竞争不复存在。
成立之初,中华书局虽收入从发行工作转换为以集中有限资金提高自身出版物的质量和数量,然预期效果却并不让人满意,经济上中图公司对于中华书局业务虽有促进,1951年3月24日中图公司邀集参加单位的座谈会上,中华书局代表就谈到“今年二、三两个月的发货数字,已超过去年全年发行总量的30%至40%”,[7]但与巨额的投入相比仍然是一个负担。除了要支付转入中图公司的原中华员工的部分超额工资外,作为股东之一还得补足中图公司营业上的亏损。中图公司1951年决算时亏损的246,018万元中①,中华书局就须按成立时出资比例交足,同时中图公司增加股本也要求中华书局不断注资。这样,虽然中图公司有助于减少中华书局本身营业亏损,但离盈利的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为了将投入中图公司的资金收回用于编辑出版,中华书局“亟愿把这个发行机构包袱完全卸掉”,[6](P95)多次联合其它几家单位向出版总署表示希望中图公司与新华书店合并,以抽回在中图公司的全部资金。终于,出版总署在1953年2月决定将中图公司并入新华书店,以达到“书籍国内发行工作一元化,提高计划发行效果”的目的,[6](P94)合并后,中华书局出版刊物由新华书店负责发行。如此,在发行上,中华书局就彻底依靠公营力量才可以销售出自己的出版物。
建国前,中共领导的新华书店基本是各自为战。建国后新华书店很快走向统一经营,建立起垂直发行系统。集中统一的新华书店在建国后的发行业上一枝独秀,令其它同业望尘莫及。1950年新华书店所发行的书刊就占到了全国总发行量的73%,截止1951年1月23日,新华书店在当时全国已有“总分店8处,分店47处,支店1031处。”[8](P23)新华书店的集中统一对建国后文化市场的影响不言而喻的。它的网络遍及几乎全部的中小城市、主要工矿区和近一半的县城。依靠新华书店庞大、高效的发行网络,新政权能够全面高效的将自己的政治宣传品和其他文化产品送到广大人民手中,达到教育人民、武装人民的目的。建国初的政治运动,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中央政府就是依靠新华书店将政治宣传品送到全国人民手中,这些书籍的发行数字往往能达到几千万册之巨。除购买政治宣传品本身花费外,一茬接一茬的政治学习也使得广大读者腾不出多余的时间、精力去阅读其它的书籍,间接影响了中华书局营业。不得不承认在政治运动面前,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态度是积极的,然而对于中华书局这样私营出版机构的出版物的发行上,就连新华书店自己也承认在工作上有关门主义倾向,他们总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如中华书局一样的私营出版机构,认为发行他们的出版物是助长资本主义行为,于是就出现了在有的新华书店里,私营出版机构的出版物要么是呆在库房里,要么是呆在货架上最不显眼的位置。
三、资方话语权削弱
书籍和出版业是思想文化战线上最重要的武器和“政治的商品”,[8](P258)因此自然不会放任私营出版机构。建国初学习苏联经验,决定在文化出版行业中实行专业化与计划化改革。专业化方面:1950年9月的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初步商定中华书局以医药卫生及农业书的出版为主要专业方向,而当时中华书局编辑所没有熟悉医疗卫生的人员,农业也只有半个,不切实际的调整方向在中华书局编辑所内造成不小的震荡,“怀疑强调专业,意在排挤旧人,高级编审纷纷有离去之意。”[4](P247)中间几经调整,到1952年7月15日制定《出版总署关于中央一级各出版社的专业分工及其领导关系的规定(草案)》时再次对中华书局的具体任务做了正式详细分工,规定中华书局主要出版以下五个方面的书籍:“一、出版农业经济和农业技术的书刊(包括通俗读物);二、出版农业学校及农学院的课本和参考书;三、出版外国语文及语文教学的书刊(包括中国人学习外国语和外国人学习中国语的课本、辅助读物、字典等);四、出版中苏友好协会委托编印的书刊;五、出版中国文史旧书(与商务印书馆合作)”。[5](P100)至于这样的专业分工是否符合中华书局的实际情况,1958年中华书局调整为出版古籍的专业出版社的事实已足以说明建国初的这种专业分工存在不合理之处。计划化方面:在1952年9月25日颁布施行的《出版总署关于核准营业和登记工作中的主意事项》规定出版机构要将出版书刊种类、出版各该书刊理由、各该书刊内容大要;作者和译者;读者对象和范围;字数和开本;发稿日期和初版日期;用纸数量、品种、规格;准备委托承印的印刷厂;发行册数;定价等11个方面的内容,在每个年度前三个月和每个季度前一个月报请出版行政机构审批。出版机关在得到批准后即编制本单位的用纸计划报出版行政机关掌管用纸计划的部分审批,获得相关数量的用纸。这样在专业化分工与计划化出版的方针的指导下,中华书局只有严格按照政策规定来制定自己的出版计划,才可能得到出版总署的批准。
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使工人阶级这个原先是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上升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在中华书局内部,资方不得不尊重工人的话语权。1949年3月,在工会举行的欢迎舒新城代总经理的茶话会,工会勉励经理为解放上海、保护工厂和文化遗产多做些工作,舒新城向工会明确表态:“经常主动向中共党组织汇报局内情况。”[4](P225)此后从1949年3月15日到1954年5月1日正式公私合营,中华书局举行了数十次的劳资协商会议,为工人参与企业管理提供了平台。1949年6月11日举行的劳资协商会议,在会上劳方要求资方自动检举豪门资本;1950年6月书局调整时建立的五个委员会,工会均派员列席各委员会议;1952年6月4日劳资协商会议决定慰劳留港董事吴叔同在机件、物料内调上的积极态度,去函上,工会不仅取得了与董事会联名的资格,而且位列董事会之前,由此可见工会在书局内部话语权的控制上已不一般。
与中华书局一同走进新时代的领导者们,大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的势微,工人无解雇之忧且以政治力量为坚实后盾的情况下,包括制定出版计划在内的很多事情不再是原先的编辑所、董事会能决定的了。前总经理李叔明滞港不归,最后分裂书局;舒新城1949年初在接任代总经理上勉为其难的态度;以及董事会1949年4月在前几年并无盈利决定“垫发”股东红利和提前清偿同人寿险储蓄等行为,不难反映出中华书局资方对新政权的怀疑与恐慌。而与工人间的马拉松式的劳资协商会议,不仅反映出企业管理者们话语权被逐渐削弱的态势,更是让部分领导者心力交瘁,纷纷请辞。
有感于内外交困,如果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书局四十余年之基业将分崩离析。从1950年初开始,中华书局就屡次向出版总署申请转型成为一家人民出版机构,摘掉“私”这顶帽子。然而直到1954年初申请才得到批准。如果说1950年初的申请还只是因恐惧而“献厂”的话,那么1953底的申请就是感于大局的发展趋势。考察从建国到1953年底最后一次申请公私合营这段时间里是哪些力量迫使中华书局急于转型,发现推力的一极在于政府依靠手中掌握的权力切断了中华书局原来的主要收入来源;另一极则在于自中图公司成立后,中华书局就失去了发行上的主动权。而资方话语权因建国后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管理制度和书局内部工人地位的上升遭到削弱,中华书局的董事们失去对书局前途的决定权则助长了转型的急迫心情。
[1]俞筱尧.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中华书局[J].编辑学刊,1993,(2).
[2]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G].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
[3]李湘波.我和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回忆中华书局[G].北京:中华书局,1987.
[4]钱炳寰.中华书局大事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2.
[5]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2)[G].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6]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3)[G].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
[7]李俊杰.中国图书发行公司纪要[J].出版史料,2004,(1).
[8]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1)[G].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
黄礼群(1987.6—),男,安徽大学历史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