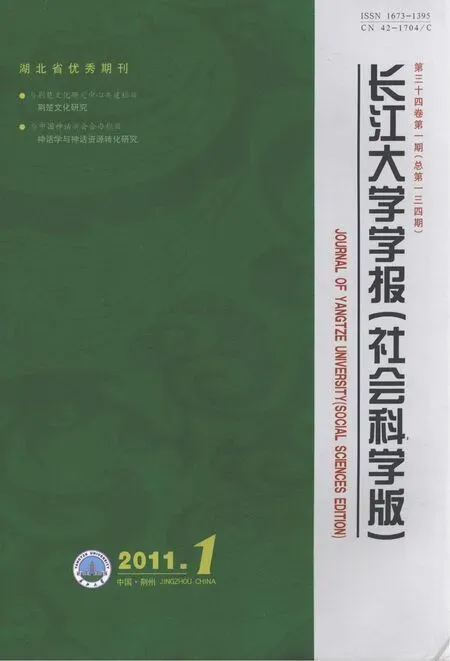古代文学“桃花+女人”题材作品女性形象浅析
何 湘 黄艳林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古代文学“桃花+女人”题材作品女性形象浅析
何 湘 黄艳林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古代文学“桃花+女人”题材作品涉及不同阶层、际遇的众多女性,按生命状态与形象特色,可大致分为壮实农妇、感伤少女、薄命红颜、刚强义女四类。这些形象反映了在男权社会中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寄予了作家们对女性的审美理想与欲望感情,具有文学和社会学的双重价值。
古代文学作品;“桃花+女人”题材;女性形象;衍变;价值
一、“易植子繁”——壮实农妇类
桃花和女人结合的创作题材于中国文学世界的初次出现是古老的《诗经》中的一首《桃夭》。《桃夭》用比兴的手法借桃来塑造一位新嫁娘,一个结实健康、美丽勤劳、繁育力旺盛、生命丰盈的女子。“桃之夭夭”,以少壮的桃树起兴,说明这出嫁的女子是壮实的,将来能承担繁重的家务和农活,能当个称职的农妇。桃树的姿态和女子的体态结合,这位新婚女子给人的总体感觉——健康、青春。“灼灼其华”道出了新婚女子明艳亮丽的容貌,洋溢着喜庆,如桃花般耀眼。“有蕡其实”、“其叶蓁蓁”代表了以后的子孙开枝散叶,绵延不绝。这样生育繁盛的活力女子才适合与之百年,白头到老。
文学作品中女人与桃花意象产生紧密联系,与原始先民对生殖的崇拜意识分不开。花朵是植物的生殖器官,在古人的直观感受与形象思维下,花朵具有无限的繁育后代的能力,所以,植物的繁盛也就与女性的生殖有着相似性。
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周人,在生活中早已熟悉并广泛种植桃花,在《桃夭》中从体态到容貌,从婚后怀孕到子孙满堂,都用桃花来比作女子,一个结实健康、美丽勤劳、繁育力旺盛、生命丰盈的女子,这样的桃花女子能带给周人过上美好生活的信心,并受到众人的无尽祝福和期待。
二、桃花依旧人面无踪——感伤少女类
唐人崔护《题都城南庄》一诗,由今思昔,利用追叙的手法,回忆了一位乍见而又旋离的貌美情深、面若桃花的少女:“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桃花无情人有情,桃花怒放人却无踪。佳人难遇,机缘错过,诗人只能长久感伤与惋惜。
桃花少女亦在后人不同文学体裁的演绎中成为一位经典的人物形象。如在本事中构建情节与人物性格,孟棨的《本事诗·情感》把这首诗衍化成一段凄美浪漫的爱情故事,赋予桃花少女痴情、忠贞等美好品格,她为情而殇的遭遇更让读者感伤;如用诗咏唱,着重突出少女的娇美,有宋代陆游“一篙湖水鸭头绿,千树桃花人面红。茆舍青帘起余意,聊将醉舞答春风”(《春晚村居杂赋绝句》);用词吟咏,更多强调感伤无奈的情绪,有晏殊的“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清平乐》)、柳永的“人面桃花,未知何处。但掩朱扉悄悄,尽日伫立无言,赢得凄凉怀抱”(《满朝欢》)等;[1]或用杂剧演绎,是当年孟棨的《本事诗》中情节的附演,如明后期的孟称舜的《桃花人面》,金怀玉的《桃花记》,曹锡黼的《桃花吟》杂剧,欧阳雨倩的改良戏剧《人面桃花》。
桃花少女在这些传播演绎中由无名变得有名,如叫“叶蓁儿”、“杜宜春”、“桃晓春”等;由无言含情到话语抒情;从只着重表现男方的感伤到着意分析刻画男女双方的感伤;少女委婉含蓄的形象日益直接张扬,单纯的性格品行不断丰富美化。至今未变的,则是这一形象与桃花相映的美丽青春和浓郁的感伤气息。
三、桃艳易凋桃华命短——薄命红颜类
红颜易老、美色易衰,曾是许多与桃花有关诗歌的主题,诗人用代言体的方式抒写了红颜们和自己的恐惧、无奈与悲戚。“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好颜色,行逢落花长叹息”,桃花在唐刘希夷《代悲白头吟》中引发的是“洛阳女儿”红颜易老的忧伤叹息,也是刘希夷自己对生命短促的悼惜,弥漫着不可排解的青春伤感。而曹雪芹借林黛玉之手所写的《葬花吟》、《桃花行》两诗更是这种伤逝情感的具体而隐晦的表达。作者以花拟人,以人拟花,桃花成了林黛玉纯洁优美的化身。漫天凄艳的落花和一个寄人篱下、孤高自许、多愁善感的女子的命运相互交映,字里行间都渗透着忧伤隐痛的哀音,暗示了林黛玉终至命薄如桃花柳絮,接近泪尽夭亡。
如果说以上一类作品还只是自怜叹息、抒发恐惧无奈或者暗示伤感的未来,留有想象空间。另外一类作品便直接表现或者涉及到红颜们的薄命结局,“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如杜牧《题桃花夫人庙》:“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2]这首诗是咏春秋时的息夫人,息夫人美貌无比,面若桃花,在民间传说里是掌管桃花的花神,称桃花夫人。息夫人虽然身存楚宫,心却早随亡夫而去。国破家亡夫死的巨大悲痛和屈辱折磨着她,即便青春还在,容颜未改,她始终不发一言,且如诗中所言“脉脉无言几度春”。她悲不欲生,却因为某些原因“弗能死”,只能采取“无言”的方式消极抵抗。沾露新桃次第开放,鲜妍活跃,无疑是和心灰意冷、无言悲痛的息夫人形成鲜明对比。
四、桃容增其艳——刚强义女类
清朝孔尚任的传奇《桃花扇》中的秦淮名妓李香君,有“东风桃李花”之姿色,虽是弱质女流,却侠义、正直、刚强,有胆识,有理想。侯方域盛赞香君,“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3]香君为着她的爱情理想、政治立场、道义原则,不惜以死反抗恶势力,把面容碰了个稀烂,血溅宫扇,染成灿烂桃花,她的刚强侠义比“辛夷树”更让人敬佩。最难得的是国破家亡后,她不留恋男女之乐,毅然放弃已经不值得爱的恋人和没有意义的恋情,勇于面对理想幻灭后的悲凉与痛楚,红颜薄命,刚强抗争,志气长存。
清朝李汝珍的《镜花缘》塑造的“桃花仙子”燕紫琼“生得面似桃花”,是位武艺超群、行侠仗义的侠女。素来英雄救美,可她年纪轻轻,刹那之间救丈夫于众豪强之中,足见艺高人胆大,绝非芊芊弱质,短识妇人。训易紫菱一席话,侃侃而谈,见识不凡,秉承剑侠之心,遵循公道之义,胜过多少须眉。
在杜牧笔下,桃花与女人的结合跳出了个人爱情、命运哀叹的圈子,而是思考个人命运与政治、国家命运之联系,开启了这一题材新的发展前景,亦赋予桃花女人新颖独特的内涵。清人继承并完善了这种写法,以男女之情的悲欢离合写家国兴亡,演绎了这一题材壮美与凄美并行的意蕴,塑造了悲壮刚强的“桃花红颜”,透视出对历史深刻的思考。在备受蹂躏的黑暗时代里,女性常被妖魔化、淫邪化,只有家庭才是女子实现人生价值的所在,可是这些桃花女人却走出家庭,参与社会活动,努力活出自我,实现人生价值。明清时代追求自由、解放的思想风潮引导了作家的创作方向,他们对女性的关注、同情与尊重也倾注其中。
桃花陪衬佳人,佳人更加流光溢彩、艳丽动人,用桃花喻佳人,不只是突出她们的美,也暗示了佳人的某些命运和前程。人花相映,花人合一,形成桃花女人这一复合文学意象。随着时代变迁,桃花女人形象内涵的侧重点也有所改变,从上古重生殖崇拜、壮实健康到中古充斥强烈的生命意识,表伤感抒情到寄国恨家仇到近古展道义精神、追求自我价值。这些美丽的桃花女人亦反映出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思潮与作者个人的哲理思辨,具有文学和社会学的双重价值。
[1]蒋晓城.旧欢前事杳难寻[J].中国文学研究,2009(2).
[2]冯集梧.樊川诗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孔尚任.桃花扇[M].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合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
I206.2
A
1673-1395(2011)01-0030-02
2010 11 -20
何湘(1979-),女,湖南湘潭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