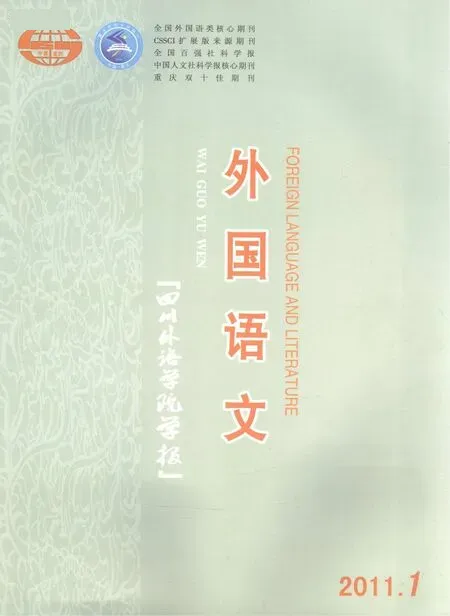关于如何正确说话的理性反思
——公孙龙语言认知哲学思想研究
刘利民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英文系,四川 成都 610064)
关于如何正确说话的理性反思
——公孙龙语言认知哲学思想研究
刘利民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英文系,四川 成都 610064)
先秦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关注的是语言表达思想的问题、概念意义的真理性和确定性问题,其思想是关于语言意义的哲学层面的反思。公孙龙的语言哲学思想具有很强的认知论色彩,其正名的原则以及他以“白马非马”命题进行的例证性阐释对于现代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例如构式义等,具有很重要的思想启迪价值。
公孙龙;理性主义;语言哲学;认知语言学
1.引言
关于先秦名家的思想倾向、其诞生的思想背景、以及名家“诡辩”命题的语言哲学新解,笔者近年来发表了论著予以讨论;这里限于篇幅,不再赘述①详见笔者的论文:论先秦名家“诡辩”的语言哲学意义.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6);纯语言性反思与分析理性思想的端倪.外语学刊,2007(1);惠施“历物十事”的语言哲学新探.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2);语言切分出的意义世界——索绪尔与公孙龙语言认知思想比较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6);以及专著:《在语言中盘旋——先秦名家“诡辩”命题的纯语言思辨理性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但是,先秦名家的思想历史上并没有得到准确的理解,其思想对于我们现代所从事的语言哲学、认知语言学研究具有的启发价值还没有得到发掘。本文打算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对这个方面再作些阐述。
公孙龙的五篇作品存留于世,使我们有了一窥名家思想光辉的机会。公孙龙的这五篇作品,即《名实论》《指物论》《坚白论》《白马论》和《通变论》②通常收入公孙龙名下的《迹府》一文是关于公孙龙事迹的记述,不应该算作他自己的作品;且其中的一些思想与公孙龙在其他几篇文章中表达的倾向格格不入,故这里不讨论。,构成了他的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明确地表明,公孙龙是在先秦名实之辩中提出语言本身的问题的,而且他把自己的讨论完全放置在了语言理性反思的层面之上,着眼的却是人所获得的知识是什么、如何才能保证认知正确性这个根本问题。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自20世纪初的语言论转向(linguistic turn)开始,也就是“用语言学的术语来重塑千百年来的哲学问题(the recasting of the age-old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in linguistic terms);因而语言逐步被视为理解和解决哲学问题的首要手段”,(Baghramian,1999:xxx)这就是说,语言哲学的核心透过语言分析来反思世界、人的认识等根本性问题。而现代西方认知语言学更是强调语言研究与认知的不可分离。从这个角度视之,公孙龙的思想与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气质十分契合:他关于语言的理性思辨是自觉的,他的“白马非马”等命题不仅不是“诡辩”,反而是具有相当深度的对我们当代认知语言学具有思想启发意义的语言哲学命题。
2.语言意义层面的哲学反思
公孙龙的《名实论》讨论的就是名与实。这很自然,因为先秦名实之辩的辩论焦点就是名与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孔子提出要“正名”,因为整个社会秩序、伦理道德的根基就是名与实的相符合。这可以理解,因为如果人人都自说自话,相互之间无法交流,或者无法正确地交流,那么一切岂不乱套?但是孔子的正名方法却是具有先验论倾向的“循名责实”,他要求使实符合名的标准要求,而这个标准则是“先王”所制定。这当然遭到了他人的反对,例如墨家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按实定名”的经验论正名方法。一切都以人的说话是否与实践相符合来判断所说的内容的正确性。此外,孔子要正名,而老子则认为无名可正,因为名只能表达具体的可感之物,而这些物的根本意义却在“道”那儿。“道”是万物赖之以生、依之而变的根本,而“道”却是不可言说的。“道”体现于万物,却不是任何一物。即如此,正名又如何可能呢?
关于名与实关系的百家之争不能不使人提出语言本身的问题。这是因为各家出于自己的立场观点,不可能达到一个普遍接受的结果。于是,为了澄清争论的实质,一个重要问题必须先弄清楚:“名”的本质是什么,“实”的本质又是什么?在“名”与“实”本身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因此,先秦名家率先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且把“名”本身的问题作为自己的核心问题提了出来。这一点在公孙龙的文章中说得十分清楚。
公孙龙在《名实论》中,明确提出,正名是必要的,但是首先应该弄清楚“名”与“实”的关系到底是个什么问题。他提出“夫名实谓也”。对这一句,多数出版物的标点符号都是:“夫名,实谓也”。“名”是主语,“实之谓”是述谓,意思就是“名是对于实的称谓”。本文却同意少数学者(如:杨俊光,1992:194;周昌忠等,2005:265)的看法,即这句话的标点应为:“夫名实,谓也”。杨俊光认为,公孙龙的原意应该是:名实的问题是一个称谓的问题。周昌忠也将此句解释为“所谓名实问题,也就是称呼的问题”,即命名的问题。
不过本文却认为,这句话的含义是“所谓‘名’与‘实’的关系其实是个说话的问题”。公孙龙的关注不仅仅限于称谓,还包括了整个语言交流,即如何才能保证语言概念的真理性,以保证思想交流的正确无误。在说了“名与实的关系是语言表达的问题”之后,公孙龙紧接着强调了思想与语言的准确性。他说:“知此之非也,知此之不在此也,明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周昌忠(2005:265)指出,这句话中的“知”字很重要,因为这体现了公孙龙的认识论意识,说明他认识到命名与认识的过程密切相关。的确如此,因为公孙龙非常明确地认识到,语言是否表达了所言对象的本质意义将决定语言的使用是否正确,而这个问题的把握却在于人的所“知”。这个“知”是对于某个“此”所具有的“此性”的认识。
在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时,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汉语是一种非屈折式语言,其词汇没有任何形态的变化。一个名词或者代词是单数还是复数、是具体名词还是抽象名词,不像西方语言那样一目了然,而是同形的。这也为我们解读公孙龙的文献造成了困难。本文认为,公孙龙所说的“知此之非也,知此之不在此……”这句话中,“此”字应当有不同的抽象层面意义,一个是“此”作为一个名本身,一个是“此”作为该名具有的意义本质,即“此性”(类似于英文的“horse”“Horse”,“one”“oneness”等)。由此重新解释此句子,本文认为其含义应该是:人把握住了概念意义之真,认识到“此”之本质(thisness)并不存在于“此(this)”物之概念意义中,即认识到这个“此”并不真的“是”“此”,那就不应当说“这是此”;只有这样,其语言表达的概念才做到了明晰、正确;认识到“彼”之本质(thatness)并不存在于“彼(that)”物之概念意义中,即认识到那个“彼”并不真的“是”“彼”,则他的思想概念也做到了明晰、确定,而不会说“那是彼”了。这里,关键在于“此性”、“彼性”与“此”、“彼”的语义层次区分。
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其核心是具有古汉语特色的关于“是”的语言分析。公孙龙不是在单纯的关心名与实的联系,而是要通过对于这种联系的语言思维分析,探讨作为认识者的人对于“此之为此”、“彼之为彼”本身的意义的认识和把握。在缺乏“to be”的语言条件下,公孙龙只能力求通过对代名词“此”和“彼”的语义分析,来把握“‘这一个’之为‘这一个’”的所“是”的本质及所“是”之为“真”的规定性。这种以“此”“此性”的探究来思考什么是真的“是”,正是公孙龙语言分析哲学的理性主义精神实质。
那么,公孙龙提出名与实的问题是一个语言表达的问题,这是否证明他认为名是第一性的,而“实是由名产生出来的”(杨俊光,1992:195)呢?笔者认为这一理解完全不正确。《名实论》一文开篇即说:“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这句话明白无误地宣布,公孙龙绝不否认世界事物的客观存在。对于公孙龙而言,物是第一性的,实在的物是存在的本体,也是人的认识的来源和基础,离开了物也就谈不上什么物之为物。
然而,公孙龙深刻地认识到,客观事物的存在是一回事,人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的认识则又是另一回事。人对于事物的真正认识只能通过思想概念的分析操作才能进行,而这离开了语言是不可能的。公孙龙要表明的是,他的理论反思是在语言逻辑层面,而不是在实在逻辑层面上进行的。他反思的焦点不是语词与客观事物有什么样的联系,而是语言意义的本质这样一个涉及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的根本性问题。
杨俊光指出公孙龙认为“实”由“名”产生出来,在这个层面上讲,其理解是准确的。但是,必须清楚的是,公孙龙的“实”不是指客观实在之物,而是指人用语言来切分世界、并由此而范畴化地把握了的关于实在之物的概念性意义。公孙龙说:“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此句中的“实”不是如冯友兰(1962:339-340)所说的那样:“一个物就是那个物,不多不少;这就叫实。”也不是周昌忠(2005:260-261)解释的那样,是物的现实存在。
笔者认为,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用“物”的称谓来指称具有此物本质属性的物而不超过其范围,就是“物”之为“物”的概念意义。只有这样的“实”才可以由恰当的“名”去指称。语言概念之“实”,即是人所把握之“知”。公孙龙想要指出的是,物作为个体是可以变的,但如果我们用“物”来指称物,则这个指称必须符合“物”的本质意义规定性。正由于此,公孙龙反复强调,作为“实”的“此性”就是作为“名”的“此”所必须具有的本质性意义;作为“实”的“彼性”就是作为“名”的“彼”所必须具有的本质性意义;本质性意义是不能变的。否则,知识的正确性就成问题了,语言的使用也就乱套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与现代认知语言学非常契合的观点,即“名”并非指称具体的、个体的物,“名”指称的是物之为物的概念意义。“名”所指称的不是具体的物,而是“物之为物”的概念意义。公孙龙显然已经认识到,人对世界万物的把握是通过语言认知操作来进行的,但人不可能就一物而知一物,对全部物一一加以命名、考察。人对物的认识只能是用语言对世界万物进行切分,或曰范畴化,从而获得对物的意义的概念性把握。
这个观点在公孙龙的《指物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他明确提出了“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的著名命题。这个命题曾经被指责为“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因为“公孙龙认为如果没有‘指’,就不能有物”(冯友兰 1963:333)。而周云之(1994:49)则说,“物莫非指”可以解作“物没有不是由指(名)构成的”,也可以解作“物没有不可以用名去指认的”。前一种解释就是一个唯心主义命题,而后一种则是一个唯物主义命题。
这是严重的误解,因为这类解释与《名实论》的基本立场相矛盾。公孙龙明明宣布“天地与其所产,物也”,怎么会又提出“物是由指构成的”呢?因此,笔者更同意林铭均和曾祥云(2000:180-181)的看法,即公孙龙是在讨论“名”的符号性质和指称功能,并且进一步认为,“‘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的解释应为:客观事物原本无名,“物”之所以为“物”是人用语言词汇对“物”进行指称而成的;语词指称的是概念,而不是具体的实在之物本身,而“指称”并非等于“指认”指认具体事物的名字。佐证这一解释的另一个名家命题就是先秦辩者们提出的“指不至,至不绝”,即“语言的指称并不直接达于具体的物,因为具体的物是无穷尽的(人只能用语言范畴化地认识大千世界的事物)”。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名”并不一定是指认具体物体的名称,其意义是关于物的思想认识,是概念。公孙龙语言哲学思想在此出现了一个升华,他已经不再满足于语言与实在的符合关系的直觉性认识,而是自觉地把思辨上升到了纯粹语言的层面,以及对概念意义的认知本质进行的反思,所以他才明确地把“名”“实”关系问题定义在了“语言交流”的层面之上。这在两千多年前是非常了不起的。
尽管公孙龙在一门心思对语义问题进行思辨,但他着眼的是人的认识,即知识如何为真这样的问题。其理论不一定正确,但就此而言,他的确是世界上第一个货真价实的语言哲学家。我们今天理解公孙龙的著作,不应局限于经验层面,而应从语言的哲学反思的角度进行。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离坚白”,为什么明明知道白马是马,却偏要提出“白马非马”之类的“诡辩”命题。公孙龙实际上是在进行语言哲学的思辨,如下文所议,他的语言哲学具有很强的理性主义认知论色彩,对当代认知语言学具有很高的思想借鉴价值。
3.理性主义的语义认知论倾向
公孙龙的语言哲学思想是从“正名”的问题引发的,因而他当然要求正名。但是他的正名原则却是地地道道的理性主义的。他即反对孔子的先验论正名观,也不仅仅局限于墨家的经验论正名观,①王寅(2006)曾撰文研究过荀子的认知体验观;笔者同意王寅的观点,即荀子并不同意孔子的先验论正名论,而是强调体验性和认知思维的加工(心征)。不过,荀子的著述年代晚于名家最活跃的时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说,荀子的思想兼收并蓄了其他各家的长处。其中,名家的思想无疑对荀子产生了影响,例如语言的约定俗成性等思想应该先由名家提出,而后被荀子吸收。由此,我们也可以窥见先秦名家思想的独特性及其影响力。而是要求从语言哲学的层面对语义的本质规定性进行正名。这就是他提出的“唯乎其彼此”的正名原则。
公孙龙正名原则的具体内容是:“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谓‘彼’而彼不唯乎彼,则‘彼’谓不行。谓‘此’而行不唯乎此,则‘此’谓不行。故‘彼’,‘彼’当乎彼,则唯乎彼,其谓行‘彼’。‘此’,‘此’当乎此,则唯乎此,其谓行此。”按本文上一节的理解,此句说的是:要正确地使用语词来指称事物、交流思想,那么所使用的语词必须具有严格定义的内涵意义;当我们用语词来指称“这一个”和“那一个”的时候,“这一个”和“那一个”就必须具有规定其本质性意义的“这个性”和“那个性”。否则就不能用此语词来指称“这一个”或者“那一个”。
先秦古汉语没有系动词“是”,因而公孙龙无法就“是”的句法意义本质进行语言分析和追问,但是公孙龙反复强调“这一个”只能是具有“这个性”的“这一个”,而“那一个”则只能是具有“那个性”的“那一个”,决不能相互混淆。公孙龙在“此”“此”、“彼”“彼”中的反复盘旋,其中心只有一个:“此”只能是“此之为此”,而“彼”只能是“彼之为彼”。“此性”和“彼性”是对于“此”与“彼”作为“是者”的严格的语义本质规定性。这一规定性是检验和判断真“此”与真“彼”的认知标准。只有达到了这样的标准要求,语言的使用才能得到正确性保证,人们关于世界的知识才具有确定性、真理性。
需再次强调的是,公孙龙的“此”、“彼”并不具体关涉个体的物,而是语词的抽象概念,其理论总是盯住语言,以图分析、澄清人到底通过语言范畴化认知而确切地“知”了些什么。这就是公孙龙在先秦古汉语的条件下,对“是什么”以及这个“是什么”如何为真的问题所进行的思考。他关注的正是规定“是者”之为“是者”的概念,对“是”之为真进行判断和检验,进而保证语言表征的知识之为真理性知识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那么,人以语言认知方式所确定的知识到底又是怎么来的呢?对此问题,公孙龙明确回答说是由理性的分析抽象而获得的。这就是他在《离坚白》中论述的思想,即他所谓之“离”。而且他还明白无误地宣称,“离也者天下,故独而正”;只有通过“离”所获得的概念才是具有真理性的知识,也才是唯一正确的语义确定方法。由公孙龙的论述可见,他所谓的“离”就是“抽象化分析”。
从《离坚白》来看,公孙龙的“离”就是从人对事物的感知中分析、抽象出具有共性的事物特征,并加以概念化的把握。他承认坚白的石头有“坚”和“白”两种特征属性,而且这两种特性只能分别由人的不同感官(视觉和触觉)来感知、体验。但是他并没有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而是进一步提出:当人以不同的感官获得了不同的体验时,他们将以语言的方式对这些体验进行范畴化和概念化。人们用“坚”和“白”两个语词所描述的并不仅仅是具体石头的坚和白,而是一切具有坚硬度和白色调的事物都表现出来的共同的坚与白特征,即所谓“坚”之为“坚”、“白”之为“白”本身。这才是公孙龙说的“神乎,是之谓‘离’焉”的含义。“离”是思想的操作,其成果就是概念。
公孙龙关于感觉体验的“见”与“不见”的讨论关注的问题是体验所导致的范畴化意义的“离”与“藏”。用我们今天的学术术语来说,他所提出的就是,当人感知到事物的一个特性的时候,该特征就出现于人的认知过程,而当人没有感知到某个特性时,该特性仅仅是事物本身的一个属性,但仅仅是一个认知潜势,有待于进入人的认知过程。这些被体验到的事物进而由思维进行加工,从而形成概念。公孙龙着重指出:体验并不等于概念,因为思维加工的对象不是具体物本身,而是人所体验到的内容,即所谓“神不见,而见离”。事物的特性有某些共性的东西,而这些共性给人以共同的体验;在此基础上,人以语词来对这些体验加以范畴化和概念化。这就是语词意义的本质。由此可见,公孙龙已经具有了我们当代才有的认知语言学的思想萌芽,因为他已经开始讨论意义的概念化过程了。
正由于重视概念化过程,公孙龙没有像柏拉图那样将认知抽象的概念实在化。我们在公孙龙的作品中找不到任何关于概念才是实在之类表述。他只是在论证,当人们使用“坚”“白”“石”的时候,这些语词的意义的本质应该是人的认知过程对于人在世界中获得的体验的范畴化概念。因此,冯友兰(1996:155-168)认为,公孙龙着重共相,因而是中国哲学中的柏拉图式理念论,这可能并不准确。或许公孙龙再进一步的话,可能提出某种实在论观点,但至少在现有的文献中,我们对此找不到证据。
谈到语言的范畴化,我们还应该提及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这一著名的“诡辩”。笔者在早些时候发表的论著中已经说过,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命题不是诡辩,而是他对“唯乎其彼此”正名原则的具体阐述。简言之,“白马”这一语词只能指称白马的概念,而不能指称马的概念,因为“白马”的意义中已经具有了“白”的本质规定性。“白”不在“马”的“此性”之中,因而不能谓“此”。随着研究的进展,笔者发现这个命题的深入讨论非常有助于我们推进现代认知语言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
如前所述,公孙龙认为语词的意义必须符合其本质规定性。一个语词(“此”)只能应用于指称具有特定本质(“此性”)的物。但是公孙龙清醒地认识到,他若要坚持自己的语义规定性原则,就必须面对复名(复合词)的问题。例如,复名“白马”由“白”和“马”复合而成。那么,“白马”还是不是“马”呢?如果“白马”是“马”,而“黄、黑马”也是“马”;既然“马”就是“马”,那么我们可能得出荒谬的结论,即“黄、黑马”是“白马”。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语义确定性原则,公孙龙不得不把“白马”本身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概念,而不是由“白”和“马”构成的复合概念。他视“白马”本身与“白”本身和“马”本身为同位的语义概念,以此来维护他的“唯乎其彼此”的原则。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其他文章里已有所论及,此不赘言。
然而,这里本文之所以再次提及这个问题,是因为在这样的论证过程中,公孙龙启发了我们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构式义的问题。在现代认知语言学中,研究者们已经开始了对构式义的关注。例如,当代构式语法明确地以构式为中心,并且提出构式义的独立意义地位,即“构式的意义独立于填入该构式的各词项的意义”(Goldberg,1995;王寅,2007)。这个见解与公孙龙的“白马论”何其相似乃尔!
尽管公孙龙在两千多年前不可能经由认知语言学的路径来对构式义的问题提出有意识的理论,但是他对汉语复名问题的反思无疑提到了这个问题,即“白马”作为一个短语式的构式,其意义已经不等于构成这个短语的各个单字的意义的复合,而是具有了自己的独立的、必须“唯乎其彼此”的意义(短语义,或曰复名义)。
本文无意把公孙龙称为认知语言学家,但认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西方语言学经历了两千多年,由传统语法到结构主义再到普遍语法等等,越来越重形式化分析,直至当代认知语言学才着重以意义为语言学研究的焦点问题。而一旦开始以意义为中心,其研究者就注意到了构式义的独立性。古汉语没有多少结构可供学者们注意分析,因而中国传统的语言分析一开始就聚焦于语义。因而公孙龙很早就注意到并且专门研究了一定意义上的构式义问题。
古今中西不同时代、不同思想倾向的思想家一旦以意义为语言考察的焦点,就都提出了构式义的观点。这很可能不是巧合。这让我们不能不设想,构式义很可能真的是语言意义的一个重要维度。我们承认语词具有意义,否则我们无法把语词与噪音分开;然而由语词构成的更大的语言单位,其意义是不是等于构成该单位的语词意义的总和?这些更大的单位至少包括复合词、短语、分句、整句等几个层面,每一个层面无疑都是一种语法构式。
于是,一个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这些构式的意义是否都是独立于其构成的下位语言单位呢?若是,那么这表征了人类怎样的一种认知机制呢?比方说,我们是以关系框架认知入手,自整体范畴化至个体,还是由个体的范畴化而上升至整体的认知呢?换言之,构式意义的范畴化与语词意义的范畴化是不是同一个过程,抑或是各自相对独立的过程,且都有自己的范畴化方式?哪一种是更为根本的认知方式?至少,我们可以确定,人关于事物特性的范畴化、概念化认知过程与人关于事物间关系的范畴化认知的确可能是性质不相同的。毕竟,前者具有实在的本体性,而后者没有这种本体性,因而完全是人的思维过程所建构的。这些问题,在现代认知语言学里面尚不能找到现成答案;同时,这也是很大的问题,并非本文能够解决。本文只是把问题提出来,希望能够促进我们关于语言与认知问题的深入探讨。
重要的是,本文这些问题是在研究先秦名家的思想,并将他们的观点结合现代语言学的观点进行思考而提出来的。须知,西方现代语言学的思想提出,没有一个不是具有其哲学思辨立场的。中国语言学至今没有自己的学派和独特的方法,或许真的与我们没有对语言是什么,语言交流、语言习得如何可能或者说是怎么回事这样的哲理性反思有关。这反过来又说明了重视并挖掘包括先秦名家在内的中国古代认知语言哲学思想的现实价值。
4.结语
语言反思导致哲学。哲学的问题产生于语言意义问题。西方哲学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而最终来到了语言论。这种发展具有其哲学思想发展的逻辑性。而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注重语言论,并极有可能经由语言论而进一步提出认识论和本体论问题来。这也不是没有其自身的逻辑性的,因为关于语言意义的反思将会导致关于人的认识问题的反思,而认识总要涉及认识对象,因而极有可能提出本体论的问题。以公孙龙为代表的先秦名家对语言意义的追究就是以这个问题为核心的,他们正是在力图透过语言意义的思辨而探讨人关于世界的知识怎么样才能是真的。这本应是中国本体论哲学的雏形。
同时,正是由于中国先秦名家注重语言意义的认知确定性反思,因而他们很早就进行了关于语言范畴化、构式义等问题的思辨。尽管其分析还很粗略、没有系统的科学方法论支撑,但他们对于语言意义的理性思辨性分析是明确地结合了认知的。西方现代语言学历经了结构主义、句法形式主义等阶段之后才诞生了形与义整合的现代认知语言学模式,而先秦名家从一开始就没有严格割裂形与义,而是将两者与认知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似乎可以猜想,假如先秦墨家的经验科学和名家的思辨理性思想倾向作为传统保持下来的话,那么语言科学在中国诞生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很可能中国语言科学一开始就以认知语言形态为其基本取向。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林铭钧,曾祥云.名辩学新探[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
[4]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5]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6]杨俊光.惠施公孙龙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7]周昌忠.先秦名辩学及其科学思想[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8]Baghramian,Maria.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C].Washington D.C.:Counterpoint,1999.
[9]Goldberg,A.E.Constructions: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责任编校:路小明
Rationalistic Speculations on How to Talk Correctly:A Study on Gongsun Long’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ognition
LIU Li-min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Gongsun Long,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pre-Qin Ming Jia,was focusing on the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issue of language expressing thought and of the truth and certainty of conceptual meaning,a typical metaphysical speculation on language meaning.Gongsun Long’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orientation to cognition issues;his principle for the rectification of names and his exemplary discussion of“white-horse not horse”proposition are very valuable for the inspiration of thoughts in modern cognitive linguistic theories,such as construction meaning.
Gongsun Long;rationalism;philosophy of language;cognitive linguistics
H030
A
1674-6414(2011)02-0066-05
2010-10-18
刘利民,男,重庆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西方语言哲学和心理语言学研究。